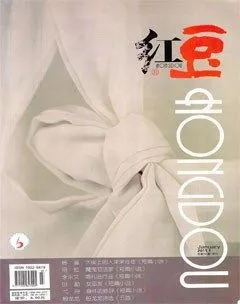女巫友(短篇小说)
2011-01-01叶勐
红豆 2011年1期
叶勐,毕业于燕山大学。业余写作。河北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芙蓉》等期刊。小说《老正是条狗》入选《2005年短篇小说年选》。《亡命之徒》被改编成电影。《塞车》被译成英文。《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这么好》获2008年度河北十佳优秀作品奖。现为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我敢说,你很少,绝对少,甚至不可能见过像巫嵋和金刚这样的震撼婚礼。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当天他俩为什么争吵,这已经是个谜。总之争吵爆发得很突然,而且短暂,大概在仪式开始前半个小时,巫嵋气哼哼地走了。对于这件事,金刚远比在场的任何一个家伙镇定,他拉过伴娘,把另一件婚纱塞给她。
就这样,薄纱遮面的伴娘走上红地毯,给陌生的父母亲鞠躬,代收祝福。不管有没有穿帮,从效果上看都非常好,婚礼圆满结束。整个下午金刚都在跟朋友们喝酒,伴娘在旁边。到了晚上,金刚被朋友们送回家,惯性使然,伴娘也跟去了,也是惯性,大家要闹洞房。没办法,做戏要做全套,伴娘很入戏。就在大家最欢乐的时候,从卧室里面突然冲出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大家落荒而逃,金刚躺在地上,得意地说:怎么样,我的盛大婚礼,我,我一个人的。
巫嵋挑起大拇指说:有胆量,有创意。
所以说,从那天起,我就认识到,不管今后这两个人之间再发生什么,都属于正常。
巫说五点钟到,让我去火车站接她。
她远远地走来了,扎着马尾辫,脑门儿有点可爱。
她穿着高跟拖鞋。
我说:你是巫嵋吗?
她说:你想死是不是?
我说:一个人吗?
她说:绝对一个人。
我们开车去吃海鲜,她吃得直翻白眼。后来她不吃了,捧着肚子靠在凉椅上,天色已晚,海面上升起明月。
可怕的沉默终于开始了,我说:你还能不能再吃?
她艰难地摇摇头,说:绝对不能。
没办法,我只能问一些问题。
巫喜欢被问问题,说是有一种做明星的假象,所以每次面对提问都表现得很耐心,哪怕问题提得再烂,当然,烂也是有限度的,超出的话后果很难预料。
我问巫:来这干吗?
巫说:我出走了。
我说:为什么:
巫说:日常战争。
我说:他知道你来这吗?
巫说:我是出走,拜托。
我说:那,他知道你出走吗?
巫说:知道,我下车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说: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巫说:我有来过你这吗?
我说:没有,才更应该问嘛!
巫说:放心,我走之前删空了他的电话。
我说:你们在搞什么嘛!
巫说:没什么,日常战争。
我说:他知道你来这吗?
巫说:我是出走,拜托。
说到一半她摆摆手先笑了,捂着肚子说不许再逗她。这是我们从前玩的一个游戏,把说过的话机械地重复N遍,直到有一个人妥协为止。
巫走路的样子像个孕妇,在海滩上谨慎地捧着肚子。
巫说:你快想个办法。
我说:毫无办法,要得到总要有代价。
巫说:我居然让螃蟹搞大了肚子。
我说:躺一会儿可能好点。
我也躺在沙滩上,问她:是不是好一点?
巫点点头说:绝对没有。
看着月亮,特别圆。
我说:为什么出走?
她咬咬牙,深呼吸,说:日常战争。
我说:为什么?
巫侧过头看看我,又弹簧似的扭过去,说:因为孩子。
我摸了摸她的肚子:你怀孕了?
巫说:没有,是别人的孩子。
我说:你是说,他和别人有孩子?
巫说:不是,是陌生人的孩子。
我说:他和陌生人有孩子?
巫终于抬起双手,紧握拳头,闷闷地号叫一声,目露凶光。
好吧好吧,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巫很泄气的样子,看看我,又弹簧一样扭过头,说:再坚持一下下嘛。
据巫交代,他们是为了争论一个陌生人的孩子。
巫说:那个孩子的两只眼睛明明离得很远,他偏偏说很近。
我说:那个孩子是谁的?
巫说:陌生人的,说过了。
我说:在哪儿?
巫说:商场。
我说:后来呢?
巫说:战争打响了。
我说:在哪儿?
巫说:商场商场商场商场商场商场!她说到后来开始尖叫,我感觉耳朵就快要被刺穿了。一些游泳的纷纷往这边儿看。
我很局促地说:你干吗?别人还以为我非礼你。
她说:那只能说他们不了解我。
我说:可他们会了解我。
她说:那与我无关。
我本来想问她如果我真被人当流氓抓起来,她会怎么办,但想想打住了,是,很低级,她肯定会——跳着脚在沙滩上喊:就是他,就是他。
我说:因为这个,是不是会很无聊?
巫眼神里流露出几丝冷静的杀气。
我退缩了,我知道,她会用一系列历史故事无情地说教我,结论无非是人类浩劫的原因不过如此,也就是说,理论上讲,他们的事,足以导致一场浩劫。
我看看手机,说: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
巫说:他记得住你的号码吗?
我说:很难说。
巫说:这就是朋友间不常联系的后果。
我说:可是,我有他的电话啊。
巫说:他换号码都没有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可是我还有你们家里的号码。
巫说:我们搬家了你也不知道?
巫对着月亮摇头,语调里充满同情。
我找到金刚的号码,开始拨,巫叹了口气,说:真无情,配合一下嘛!
电话通了,金刚在那边说话:谁?
我说:是我。
金刚说:哦,小贱人把我的电话全删了。她出走了。
我说:她在我这。
金刚说:是吗?
我说:是啊。
金刚说:你让她去死吧。
我说:我们就在海边。
说完我下意识地闪了一下,因为巫很可能扑过来抢电话。
巫没有,她正呼吸着海风,说:我就不去死。
路口没车,巫说不走了,停下来等。我点上根烟,被巫抢过去踩灭了。我说你干吗你?巫有点紧张,说,抽烟多不好。我说:就不是你抽的时候了。巫低着头小声说:我今天有抽吗?我想了想,说:你今天还真是没有抽。
巫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说:你好好的,这是什么德行?
巫就昂首挺胸,理了理头发,立马又像个女干部。
我们的滨海小城,一过十点就没什么人了,出租车开得飞快。
我说:你真没钱?
巫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办?
巫说:凉拌。
我说:行,那就把你卖了吧。
巫说:卖哪合适?
我说:农村吧。
巫说:不,他们会让我喂猪的。
我说:夜总会怎么样?
巫说:我不会跳钢管舞。
我说:那饭店酒楼吧,擦桌子扫地什么的。
巫说:真枯燥,还有没有新鲜点的?
我说:你怎么回事?现在是卖你,你有得选择吗?
巫说:哦。但有个疑问。卖我的钱给谁?
我说:当然是给我。
巫说: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说:好像没什么好处。
巫说:那你干吗要卖我?
我说:当然是对我有好处喽。
巫说:哦,有一点明白了。
我举起手来准备跟她击掌庆贺,她却说:等等,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卖给你?
我说:那钱给谁?
巫说:给我啊?
我说:等等,那就是说,我把你领回家,让你住我那儿,再给你一笔钱?
巫说:差不多吧。
我说:那我岂不是做了和金刚一样的亏本买卖?
在路口,我说:师傅,右拐。
巫却说:左拐,去火车站。
我扛着巫的巨型行李,说:你不是没带东西么?
巫说:拜托,我是出走,没看见电视里出走的吗?都要收拾行李。
我说:那也没必要带那么多吧。真是你拎来的吗?
巫说:当然。
我说:难怪你被螃蟹搞大肚子。
巫有点腼腆,说:其实,也不是啦。箱子下面有轱辘啊。
我愤怒地说:你干吗不早说?
巫说:你没问啊。
我说:这他妈的还用问吗?
巫说:你说粗口。
我说:谁他妈的说粗口了?
巫一把抢过行李,轻盈地拖着,边走边嘀咕着:又没人逼你,自己抢着扛,还赖别人。
事实上,巫带来的东西大都是没用的。一个还不算老的女人,出门带个长江七号很好理解,但是带两个就有点难理解了,何况是带三个,还有投影闹钟,想看到时间就必须选择深夜,另外还有我看不懂的妇女用品。
巫用这些废物瞬间占领了我的房子,然后关切地问我:你睡哪儿?
我尤其受不了她的那种香水味,在客厅里冲她招招手说:巫啊,你来,我们得谈谈了,在这还是我家之前。
巫很认真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我说:巫啊,我们先明确一件事,这里是我家。好吗?
巫点点头说:嗯!
我说:那好,你来我家,住哪儿,好像应该我说了算。
巫说:没问题。
我刚要说话,巫却说:我也明确一件事,我已经卖给你了。OK?
我说:什么时候?
巫说:出租车上啊。
我说:我有答应吗?
巫说:有答应有答应。
我说:不可能。
巫说:好吧,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很快就改写为,我买过她,而且我买她的代价是,给她地方住,外加一笔钱。
我说:我敢肯定,如果倒退些年,你会是个女阴谋家。
巫说:历史没有倒退键,放心,未来也是可以期待的。
深夜,巫睡了,传来轻微的鼾声。
我给金刚拨了电话。
我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
金刚:没事,让她在你那待着吧。
我说:她把我家给占领了。
金刚:能想象。
我说:她还把自己当给我了。
金刚说:没事儿,回头我去赎她。
我说:别扯淡了,你们到底有事儿没事儿?
金刚说:没事儿。
我说:日常战争?
金刚说:是啊。
巫嵋煞有介事地签了卖身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那是一纸空文。
最糟糕的是,她有钱了。
从此屋子里不断地出现陌生的东西,还有陌生的人,我向来都佩服她交朋友的能力,不做传销真是极大的浪费。
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个小城市,还有这么多无所事事的人,他们能盘踞在餐桌前,从白天一直到另一个白天。我并不讨厌他们,也不招他们讨厌,事实上我跟他们混得不错,他们喜欢听我瞎扯。可是时间长了,我也不免烦恼,好不容易调整过来的生物钟,就再次颠倒了。
我跟巫嵋说,我们该谈谈了。
巫嵋说:不用谈,你要是哪天说你烦我了,我立马就走。
我说:我烦你了。
巫嵋说:这不是真心话。
我说:绝对是。
巫嵋说:骗人。
说完,她转身就进屋了。
好吧,不说这个。我对着屋子说,你的钱要是花完了,你可怎么办?
屋子里传来一条坏消息,她说:没关系,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客观地说,巫嵋是个专业人士,但做得并不好,她总是在致力于专业以外的事情。不论什么,不管多喜欢,一旦成了专业,就立刻会厌倦。这大概就是业余爱好者。这么看来,老公算不算?
总之,一个这样的专业人士,出人头地是困难的,但糊口很容易。她给自己找了个轻松的工作,不用奔波,不用电脑,也不用坐班,在这个城市居然还有这种职业,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巫嵋说,第一,你不是女人;第二,你不是业余爱好者;第三……她说了若干条,却没告诉我是什么工作。
过了很久,巫嵋才想起问我女朋友,好像是多日不来的客人,忽然想起了主人家的一只宠物。我说,她出门了。
巫嵋说,很久啊?
我说,是。
巫嵋说,这么说,你很久都没接触女人了?
我说,你不是?
巫嵋说,滚。
然后,巫嵋看着墙上的照片说,蛮有风情的,你要小心了。
我说,没事。
巫嵋说,也是,喜欢的时候会放在心里,不喜欢了就放在嘴上,连说都懒得说了,就放在墙上。
我说,不是,那是张爱玲。
巫嵋说,哦。这就是张爱玲啊。她喜欢张爱玲啊?
我说,不是。
巫嵋说,你喜欢?
我说,也不是。
巫嵋说,那挂她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
她说,无聊。
巫嵋用挣到的第一笔钱给我买了件衬衣,我并不喜欢。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有分歧。这些天来,她一直对我的穿衣品位耿耿于怀。
她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没品位,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都是在和谁交往?老人吗?
她尤其不喜欢我的运动鞋里的一双,简直是恨之入骨,每次我们三者一同出现,她都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她甚至拒绝跟我在街上一块儿走,或者在聚会的时候离我远远的,整晚不跟我说一句话,连看都不看。终于有一天,我不祥的预感应验了,从此,我再没见到过那双鞋。
我有点生气,说:就算你不喜欢,也不能扔了啊,怎么说那也是别人的东西。
巫嵋说:我没扔。只是帮你收起来了。
我就不说话了,我相信她的话,她一定没扔,只是放在了一个地方,让我永远也找不到。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都有这个本事。我忽然想,要是她们想把自己也藏起来,是不是也一样厉害?
这个时候,巫嵋正得意地看着我。她得意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只是把下嘴唇长长地伸出来,不了解的,还以为她是在生气呢。
我含恨穿着巫嵋买的衬衣,她笑靥如花。但这仍不能满足她的征服欲,她走过来帮我整理,还帮我扣上了正数第三个扣子。这样,我不由得端了端肩膀,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她很满意,可能还错以为我弃暗投明了,于是又帮我扣上了袖口的扣子。我实在不能容忍她了,甩开她退到屋子的另一端,并且不礼貌地把衬衫脱了。这个举动让巫嵋彻底崩溃了。
我只解开了两只扣子,袖口的两只,然后像脱T恤一样从里面钻出来。接着,就看见一双喷火的眼睛。
巫嵋跳着脚说:臭猪!
我不理他,去找我的衣服,而它们都在巫嵋的半场,我一下子觉得,它们早晚会像那双鞋子一样消失掉,最后只剩下这件衬衫,朝夕相伴。
我生气了,说:你干吗啊?我又不是金刚。
巫嵋嘴角稍稍上翘,说:你当然不是,他比你优雅多了。
这个词的出现,让我再次紧张。我仿佛看见优雅的金刚,用最优雅的姿势告别了所有女人,站在巫嵋的旁边。而与此同时,巫嵋也泄气地垂下肩膀,斜视着下四十五度屋子的某个地方。
在以后的三天里,巫嵋始终保持着这个角度,冷战开始了。
两个人,每天进出同一个门,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并且坐在一起吃至少两顿饭,而不说一句话,这恐怕只有结婚二十年以上的人才做得到。想想真恐怖,整个房间里只有动作,没有对白,只有偶尔清脆的音效,但想想也真艺术,每一个动作、场景都衔接得那么严丝合缝,几乎是经过排练,又像是有人暗中导演。
我感动了,看得出来,她也是。
我们仍然是最有默契的两个人,从小至今,我说的话,她永远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每次她要捉弄我,也总以穿帮告终。我承认,当初她选择金刚,我崩溃过,这只能说明面对感情,她远比我成熟,而且很多,因为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要是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这真是一个够得不能再够的理由了。
第四天,我的性欲开始膨胀。我需要一个女人。不是巫嵋。
这些天我没有冲动,不是她的原因,也不是金刚,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我想,她也是。这最终泯灭了我们之间的爱情,性欲,导致出一种奇怪的天荒地老,我想是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抛弃我,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她,反之亦然。两男女,紧密无间,无爱无性,妈的,好像有点虚无。
我真的需要一个女人,就现在,但我不知道去找谁。在这个城市里,我没有前女友,而我的女人,正在另一个城市。我也不去找小姐,因为紧张,或者尴尬,或者某种神秘的原因,或者干脆理解成钱吧,这个好。那么,只有巫嵋,见到她我才能平静下来,这对一个女人来讲意味着什么,真难说。
我最终还是搞到一个女人,是送上门的。那是聚会时期的一张面孔,不是很熟悉。
她说:巫嵋在吗?
我说:不在。
她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难说。
她说:我能等她吗?
我说:可以。
然后就进屋了。
片刻,我拉开门对她说:要不要进来等?
战役打得很漂亮,看得出,没有胜者。两个人疲惫地喘息着,很可能导致会再决一次。这个时候,门开了。
我居然有点紧张,我当然知道不是我女朋友。
听见巫嵋的脚步声,迟疑了一下,想必,是看见了女人的鞋。再次迟疑,是在我的房门前。
我开始快速地穿衣服。
我感觉女人在看着我,还轻蔑地笑。
女人出去的时候,和巫嵋打了个招呼。
我来到客厅,巫嵋在看电视。没开灯,屏幕一闪一闪的,她的额头来回变幻着颜色。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我好像做了错事似的,谨慎地坐下来,不说话。
你干吗跟她做!巫嵋说。
冷战终于结束,我松了一口气。但核战一触即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巫嵋跟她有什么关系。
巫嵋背对着我,看不到表情,只看到她的背面,乌黑的半长发,披散在瘦瘦的肩头。上衣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身体,看样子,她好像没戴胸罩。
这句话之后,她又陷入了沉默,屋子里再次安静下来。
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没关系,我想她并不关心答案。换句话说,就是她这句话并不是疑问句,而是感叹。
好像时间停顿了,沉默了好多年。
我忽然又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动起来,想离开。这时候,巫嵋也动了,她说:金刚……
我又坐下来,看着她。
巫嵋继续背对着我,说:金刚和那个伴娘在一起,被我抓住了,他干吗那样?搞别的女人不行么?干吗要搞我的朋友?
而我心中的另一句话却是,她干吗那样?搞别的男人不行吗?干吗要搞朋友的丈夫?
你当时怎么做?我说。
巫嵋说,你猜呢?
会不会是扔给他一只保险套,让他当心不要搞出人命。
我没开玩笑,我觉得她做得出来。也应该这么做。
巫嵋没说话,我看见她肩膀微微抖动。
我猜对了。当时那个样子,她一定很得意。我想。作为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陪她笑上一会儿。
但是很遗憾,没法陪,因为她不是在笑。
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年。我谨慎地走过去,见她眼泪已经默默流淌了一地。
我吃了一惊。
我原以为巫嵋是不会哭的女人,就因为这个,我一度认为她女人得不够彻底。现在她终于彻底了,却又不像女人。或许,巫嵋和女人之间本身就有着某种微妙的差别。
我这个人见不得女人哭,尤其是见不得巫嵋这种人哭,有点不知所措。
我甚至忘了帮她拿点面巾纸什么的,就那么看着。
巫氏哭法,跟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我发现,原来不知所措里,也有点好奇的成分。我潜意识里想让她再哭一会儿,让我好好研究一下。
记不清是谁的小说了,曾经写过一种奇怪的哭,没有表情,呼吸平稳,只是眼泪在不停地流。巫氏更甚,她的眼泪像瀑布一样。
我当时想到了决堤一词。这是积攒了多少年的眼泪啊,不像我女朋友那种自来水女人,随时都可以泄洪排险。
如今,她决堤了,该怎么办?
没有声音,我们默默相对。
我忽然有点害怕了,我知道一个人大量流血是会死的,那流泪呢?会不会有人因为流泪过量而死掉呢?尤其是女人,她们不是水做的吗?
或许,我应该给她补点水吧。想到这我就跑开去拿杯子,倒水的时候,居然还聪明地往里头加了点盐。回去的时候,巫嵋已经不哭了。我把杯子递给她,说:你总算好了。
巫嵋说:还没有。
我说:还没有?
巫嵋说:对,我还在哭,只是没眼泪了。
这句话让我松了口气,原来泪流是不会死人的。
我说:那就别哭了吧。
巫嵋说:不,还没哭够。
我说:算了吧。
巫嵋说:不。
我说:那怎么办?
巫嵋说:换个哭法。
原来,她虽然不哭,却很懂得哭。
巫氏的第二种哭法比较恐怖,就是那种典型的干号。瞬间爆发,吓了我一跳。
如果说刚才担心有人会泪流致死的话,那么现在我担心的是精神崩溃,但不是她是我。我敢说,要是在一分钟之内她不停下来的话,我肯定会从窗口跳下去。为了挽救我自己,必须安慰她。可怎么安慰呢?时间一秒一秒地飞飙,我迟疑地朝她走过去。
一分钟已经过了,巫嵋还在哭,我也没跳,因为我被她紧紧抱住了,哪儿也去不了。
我的耳膜快被震破了,哭声还没停止。我说的一切话都是白费。
其实我也没说什么,只是重复着一句话:算了,算了。
算了什么?别哭了,还是放过我?
我伸出手抚摸着妩媚的长发,仍没有一点作用。她的哭声从窗子冲出去,飘荡在整个小区,整条街道,整个城市的上空,大有继续蔓延,波及千里之外金刚的耳朵里面。
这种哭,基本上是不能截止的了,我认为。所以我踏实了,我想,让她哭吧,一个人总会哭累了,然后,睡倒。
但是,她不累。
我忽然急中生智,说了句:别哭了,对孩子不好。
巫嵋就真的停住了。甩甩头,挣脱我,默默地坐好,整理衣服。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就像从来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看着平静的巫嵋,她恢复得太快了,以至于比刚才还要让人难以接受。我甚至担心,这是她的另外一种哭法,是的话,看起来不算烦人,但势必更加痛苦,因为那一定是用心在哭。
我忽然发现我对哭已经很有研究。或者是女人?
巫嵋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了解女人?
我看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作为一个女人,不,作为巫嵋,不抽烟,只喝少量的红酒。而且在别人抽烟的时候,总是悄悄地躲一下,甚至不用电脑。当然,最重要的是,最近,你经常呕吐。作为巫嵋,不,作为一个女人,在没有醉酒的健康状态下,呕吐,会说明什么?而作为一个男人,就算神经再粗,再没有看过电视剧,也会知道了吧?
说到这,巫嵋转过头,用眼神冲我笑了笑。然后,她动了动身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也稍稍动了动,以便让她靠得再舒服点。
巫嵋说: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崩溃了。甚至连克制一下都没有,就哭了起来。真丢脸。一边哭一边骂自己,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但是忍不住,后来也没有忍住。一直在哭。
也就是说,你从那以后一直在哭?我说。
巫嵋点点头。
包括来这的这些天?我说,直到刚才?
巫嵋说:嗯。
你确定你已经不哭了吗?
嗯。
我动了动身子,发现今天的月亮很亮,上面的山脉都看得很清楚。就想起有人说过,很大比例上的一些人,都在以为地球是在围着月亮旋转,这让我觉得他们真可爱。对面的楼上,有个中年男人,站在窗子前,窗帘拉着一半,没开灯。他依稀有点谢顶,但有旺盛的胡须和胸毛。他站在至少有一百六十平米的房子里面,看我们。
我说:你看,他是不是有点儿像凯文史派西?
巫嵋说:他是谁?
我说:一个可爱的美国人。
我又动了动身子。
巫嵋说:你干吗?
我说:你喝不喝水?
巫嵋说:不喝。
我说:那我想喝。
巫嵋说:不行。
我说:那我去抽根烟。
巫嵋说:不行。
我说:去厕所。
巫嵋说:不行。
巫嵋说:说说她吧。你女朋友。
我说:哦。
“我女朋友是个审计师。”我说。
哇,那你惨了。巫嵋说,听说他们经常不回家。
不,是偶尔在家。我纠正她说。
最长要走多久?
九个月。
连续的吗?
当然不是。
那还好。巫嵋说,她真幸运。
什么意思?我问。
巫嵋说:一个女人漂泊那么久,回家发现自己的丈夫还在,并且没有其他的女人。起码,她比我幸运。
你也经常出门吗?
不,偶尔,所以,更说明她比我幸运。
我说,其实他们很苦的,经常有人一听说是干这行的,就吓跑了,所以很多是大龄女青年。
那,她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那你呢?巫嵋问。
没什么。我说。
什么没什么?她继续问。
没什么。我说。
孩子是谁的?沉默了一会,巫嵋忽然问。这时候,月亮还是那么明亮,那个中年男人不见了。
什么孩子?我莫名其妙。
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的?巫嵋说。她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离开,端坐在沙发正中,没有靠背垫,腰板挺得直直的。
为什么要问?反正不是我的。说完这句话,我有点后悔了,看看她,倒没有什么反应。
我说,对不起。是谁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之前,我和他只有过一次。
他是谁?
你忘了吗?
什么啊?我看着巫嵋,好像有点紧张。
上次你回去,喝多了,在宾馆。巫嵋看着我说。
宾馆?我怎么不记得?我真的紧张了,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咕噜一声。
你当然不记得。巫嵋冷静地说。
真的啊?我呼吸急促。
当然不是,巫嵋忽然笑了,说:傻瓜。
我又咽了口唾沫,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现在,除了怀孕这个事实,我已经不敢相信她说的每一件事了。其实,就连怀孕,也只是我的推测,不是吗?
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你希望是金刚的吗?
话音刚落,巫嵋就站起来,捂着嘴巴朝厕所跑去。她的呕吐声,听起来好像真的是怀孕了,但我想不出,这和醉酒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就没见到巫嵋。直到第二天醒来。
也没有。
她走了,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什么也没写。
我有点慌,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了,是回家了么?还是又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是医院?
我想起金刚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就摸出电话,在此之前,我暗中祈祷,但愿巫嵋不要删除我的电话。
我说:金刚,你在哪儿呢?
金刚说:火车上。
我说:你去哪儿?
金刚说:南方。
我说:去干吗?
金刚说:巫嵋昨晚说,她要和我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