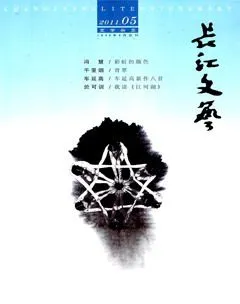蜡烛精神赞
2011-01-01楚奇
长江文艺 2011年5期
王淑耘,1921年生,江苏句容人,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顾问、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1941年,她与夫君骆文结伴同赴延安参加革命,骆文任延安鲁艺戏剧系助教,她在鲁艺文学系学习。后赴冀察热辽解放区,曾任职于《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的副刊。后随军进天津,任职于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南下武汉,任中南新华广播电台科长、中南文化部调研科科长。1956年开始担任中南文联《长江文艺》副主编。主编李季调到北京后,继任为《长江文艺》主编,后当选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编辑工作之余,王老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同时也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
很多人知道王淑耘,是因为她的夫君、著名作家骆文。我曾看过一张照片,是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吴本立为他们补拍的结婚照。这帧珍贵的照片保存完好,虽经过60多年的时光依然清晰鲜明。其实,骆文与王淑耘结为伴侣并不偶然。骆文也是江苏句容人,他们是同乡,又住在县城的同一条街上。当时王淑耘和骆文的妹妹同在句容女中读书,两人是好朋友。不过她虽然常去骆文家,却与骆文交往较少。直到抗战爆发,骆文与同学组织了一个演剧队去重庆,碰巧王淑耘也流亡到了重庆,与姐姐一起在北碚一个小学当教员。一次骆文随演剧队到北碚演出,与王淑耘不期而遇,于是这次相遇在他们的生活中投下了一抹玫瑰色彩,他们相恋了。后来,骆文要去延安,王淑耘也向往陕北,这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便携手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并从此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见到毛主席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几段难以忘怀的时光,王淑耘曾在延安停留四年,这段时间无疑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忆。而最令她难以忘怀的事情,就是她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聆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
王老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42年5月30日下午,鲁艺院方通知,毛主席要来鲁艺与同学们座谈。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既诧异又惊喜,迅速集中到鲁艺礼堂旁的篮球场上等待着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
毛主席终于来了,他身穿一件洗褪色的灰棉衣,站在一张未经油漆的小木桌旁。同学们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坐在用各种绳子、布片扎成的折叠椅上,围坐在下面,聆听他生动精彩的演讲。毛主席首先谈到的是文艺究竟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他说你们这里是小鲁艺,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才是大鲁艺。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你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去熟悉和体验工农兵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他时而站在小木桌前,时而走到同学们中间,一面讲一面用手比画。在谈到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时,他指着篮球场边上的两株大槐树说,我们的作品是不是都要这样的大树?继而又伸出了一个小指,要不要这样的豆芽菜?当然当前我们的工农兵首先需要的是喜闻乐见的普及作品,同时也要求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毛主席这次在鲁艺所讲的,也就是《延座讲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他用深入浅出、风趣幽默的语言,阐明了文艺上许多复杂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一下子使得文艺界一些庞杂和纷乱的思想和论争得到了梳理和澄清。后来,王淑耘说过这样的话:“这次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震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一下子感到延安的文艺空气仿佛越加清新明朗了!”
1977年,王淑耘又专程来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延安。从延安回来后,她写了一篇文章《到桥儿沟去》。文中说:桥儿沟是一个傍山面水的小镇,那里的老乡就是鲁艺各种艺术创作表演的第一批读者、观众和鉴赏、批评家。在桥儿沟近邻的鲁艺,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作为全院集合场所的教堂,虽然屋脊已经出现裂纹,外观却完好。球场旁边的那两棵大槐树还在,站在这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槐树前,不觉想起了当年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教导,他那亲切风趣的话语,那睿智生动的音容仿佛又在眼前显现……
甘为人梯
王淑耘长期从事文学工作,当了几十年编辑,有三十多年是在《长江文艺》度过的。她与骆文携手,共同担负起培养文艺队伍、繁荣文艺创作的使命,为湖北文艺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省内大部分知名作家都是经过他们之手培养起来的。只不过,由于骆文太知名了,王淑耘的许多贡献都掩盖在他的光芒之下。2004年,王老出版了25万字的文集《编辑人》。我读过这本书,才知道她在湖北文学事业的发展中是如何默默耕耘,做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业绩。
提起《长江文艺》,很多文学圈内的朋友都有个共识,就是《长江文艺》是作家的摇篮。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的,因为自创刊起,《长江文艺》就强调必须大力培养新作者,为此,杂志社还广泛开展了“《长江文艺》通讯员”活动。作为编辑部的一员,王淑耘在挖掘新作家、推出新作品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
湖南著名诗人未央就是《长江文艺》第一批发展的通讯员。抗美援朝开始时,他参加了志愿军,在北上的火车上,他给王老和编辑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不仅要在火线上实现保家卫国的崇高愿望,也要拿起文艺武器进行战斗。他回国后,编辑部立即向他发出了约稿信,不久,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诗《祖国,我回来了》《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等。这组闪耀着强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光芒的诗歌让王老大为感动,立即将它们签发了。发表后,这几首诗不胫而走,传遍大街小巷,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祖国,我回来了》还被编进了小学课本。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是作家李凖的处女作,本来是篇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好小说,却因触动了一些现实问题被当地有关部门压制不许发表。当王老和编辑部其他同志看到这篇小说后,一致认为这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佳作,马上决定刊发,并请评论家于黑丁写了推荐文章。小说在《长江文艺》1954年元月号发表后,受到了广大农村读者的广泛欢迎。随后,王老又请李凖来编辑部写作,连续发表了《白杨树》《雨》《孟广泰老头》《冰化雪消》等小说,使他最终成为全国瞩目的青年作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前,王老坚持立足本地区培养文学新人卓有成效,出现了李北桂、李建纲、王维洲、刘不朽、孙樵生、管用和等一批文学生力军。她还把帮助工农作者创作作为编辑部一项中心任务,经常派出编辑人员同工农作者一起生活,具体进行指导,扶持了黄声孝、王英、魏子良、习久兰等一批作者。
有胆有识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王淑耘欣喜若狂,她仿佛看到一轮红日冲破漫天阴霾,放射出万道光芒。
整整休刊十年的《长江文艺》又要和读者见面了,王淑耘又回到了她热爱的工作岗位。此时,王老已经是主编了,她延续了《长江文艺》重视文学新人新作的优秀传统,通过开笔会、办讲习班、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发现人才、发现作品。这段时间内,《长江文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映泉的《白云深处》、楚良的《蚂蚁与珊瑚》、叶明山的《倒掉了的石牌坊》等,一批文坛新秀通过《长江文艺》开始活跃在文坛之上,如熊召政、董宏猷等。如今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家方方,那时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的处女作《大蓬车上》就是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王老在培养文学新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新编辑,如李传锋、刘益善、朱莎莉等,他们以后都成为了编辑部的中坚力量。
1980年1月,《长江文艺》发表了青年诗人熊召政的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在诗中,熊召政怀着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大胆地揭露了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山区县英山县,因为极左路线和“苏区学大寨”给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这首诗最先是编辑刘益善发现的,欣秋读过之后立即送到了主编的案头。骆文和王淑耘看了诗,认为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省内出现的第一首揭露极左路线严重危害的好诗,马上同意刊发。诗歌发表后,虽然遭到了来自上面的一些批判和斥责,但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荣获全国优秀新诗奖。
十年浩劫期间,湖北出现过一个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他就是湖北剧场的跑片员李郑生。李郑生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怀着探索真理的勇气,对林彪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批判,并因此受到迫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80年初,冤案平反不久,王淑耘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题材,便提议组织作家采写和创作。不久,报告文学《线》在作家祖慰、节流的笔下诞生了,编辑部冲破重重阻力将其发表,后来,这篇作品获得了1979-1980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编辑工作不仅需要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强烈的责任心,有时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王老冒着巨大的风险编发《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和《线》,显示了作为一个编辑家的胸怀和胆识。她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献出了全部力量和满腔真情。
延安女战士的聚会
离开编辑岗位后,王淑耘除了坚持自己的文学事业,也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武汉有个“延安女战士联谊会”,这是由来自延安的张建之、李泊、张林苏、莎莱发起组织的,王淑耘也是这个联谊会中的一员。
1996年3月29日,联谊会在东湖翠柳村举行了第一次聚会,把武汉地区近五十位延安女战士聚集在一起。虽然岁月让这些老大姐们脸上刻下了皱纹、青丝染上了霜花,但她们情绪高涨,神采飞扬,仿佛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
王淑耘也参加了聚会,并在会后写了一篇题为《延安女战士聚会》的文章,记录了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发表在《湖北日报》上。她在文章中说:“聚会那天,细雨霏霏,气温似乎有些清冷,而花木毕竟已经葱郁,丛树拥翠的东湖翠柳村春意盎然。滨湖的一间会议室里传来阵阵歌声。热烈而庄严的《东方红》,这是80岁的红军老战士赵明珍在歌唱;旷达悠远的《信天游》是73岁的音乐家莎莱的漫歌;还有76岁的李曦大姐的保留节目轻柔低沉的《蝶恋花》。很难想象出从她们年迈的胸腔里发出如此动人的乐音。可你仔细品味,就会感受到她们心灵深处对往事的追忆:50年前,那西北高原肤施古城(即延安)有着令人难以忘却的劳动者的足迹,人们学习的课堂,人们对革命的缱绻情怀。”
会上,延安女战士们回忆了自己过去的峥嵘岁月,王淑耘还非常激动地讲述了她几十年的编辑生活和培育文学新人的种种感人经历。当她讲到愿为文学新人的涌现当垫脚石、铺路砖而无怨无悔时,姐妹们都鼓起掌来。
当年,青年作家汪洋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红烛》,主人公的原型是著名哲学家李达,小说塑造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辉形象。王淑耘非常赞赏这篇作品,在《长江文艺》发表时,她曾亲笔写过一篇推荐文章《蜡炬性格,真正的人》。蜡炬性格,就是照亮别人燃烧自己,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何尝不也是王老自己的写照?作为一名文学编辑,王淑耘老人高尚的情操令人钦佩和感动,她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