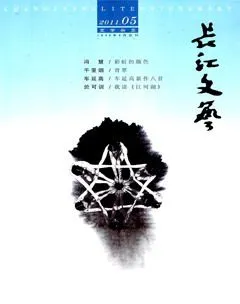历史深处的美学沉思
2011-01-01江岳
长江文艺 2011年5期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江河湖》选择的是有难度的写作。在时间的长度上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在空间的广度上延伸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思想的深度上更是进行了只身挺进险境的美学沉思。这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书。
他探索了一些什么呢?
五年的辛勤耕耘即将收工时,刘继明在《江河湖》的结尾处不无深意地写道:“随着‘巫山神女’号在峡江上一路劈波斩浪,溯江而上,自己正跟随父亲的灵魂一点一点地朝着某个永恒的源头接近。……然而,我找到了美吗?”这里的“我”是双关语,既是作为叙述视角的沈如月,又指作家本人。纵览全书,可知作者的用意是:穿越波谲云诡的历史表相,回溯江河湖的源头,揭示它本来的真相;超越既定的美丑分明的审美模式,寻找新的美学真谛。
在如何叙述我们的历史的问题上,各种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思潮纠缠不清,形成了迷宫式的死结。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个体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高扬,加速了社会进步的进程,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经过一些年的累积,人性的贪婪和堕落也在滋长,极端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负面危害不容忽视。对此,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从一种片面走向另一种片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恶劣惯性,已形成了一个神圣化和妖魔化交织的怪圈。刘继明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很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却偏偏拒绝和反对对改革进行任何‘反思’,就像毛时代不允许人对革命的神圣性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样。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出于扼制对人类文明的新一轮毁损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刘继明通过一系列论说和创作,表达了对被妖魔化了的某些历史和传统思想资源重新检测和评估的愿望,以期激活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是他从“文化关怀”、“底层写作”到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脉。
《江河湖》写到了“文革”时期,但没有像流行的那样对文革作“文革式”的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理性的对历史的勘探精神和宽容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对甄垠年和沈福天这二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以前的许多小说中,像甄垠年这样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神化了,但在《江河湖》中没有美化甄垠年。另外,沈福天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代小说中大多是以漫画化甚至妖魔化的“反面人物”出现的,《江河湖》却没有对其进行丑化。这是通过不对人物经历的“反右”、“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兴修水利等历史事实进行简单肯定或否定来实现的。还原了人物的真相,自然也就修复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刘继明借沈如月之口表示,不愿意把他们写成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也就是拒绝了美丑截然分明的传统审美模式。显然,刘继明在这里悄然引入了一个新的美学范畴——“不美”。
“不美”不等于丑,这是相对于传统美学中的美与丑而言,也可以说成是“不丑”。刘继明笔下风云变幻的当代中国几十年,浓缩了西方四百年的起承转合,简单地对其中的人与事贴美与丑的标签,是要冒人到车走、刻舟求剑的风险的。刘继明找到“不美”这一切入历史领城的新的审美视角,就非常有利于他实现还原历史复杂真相的写作目的。他试图从非此即彼的传统历史观和审美观的夹缝中,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由众多中间人物、中性事件、中立情感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刘继明的小说文本提供着这样的审美信息。
一般而言,激情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原素,但在《江河湖》中,恰恰是对激情的理性的抑制,代之的是对人对物不冷不热的平静,还常常从“心底涌起一股爱恨交织、复杂难辨的感情”。这与作者对“不美”的偏爱有关。三峡大坝建成后,作者写道:“大坝像一条巨龙,模卧在长江上面,将西陵峡拦腰截为两半,显得那么雄伟、壮观、恢宏……”好不客易眼看要来一段激情的宣泄了,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