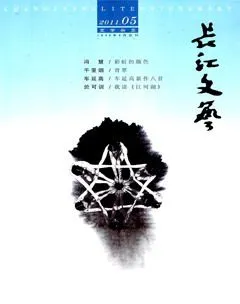我读《江河湖》
2011-01-01於可训
长江文艺 2011年5期
湖北得地利,有开发三峡之便。四川虽也有这样的便利,但像“长总”、“长办”、“长委”这些与开发三峡有关的一些新老中枢机构,都设在武汉,自然就执了天下的牛耳。这虽不是诸侯会盟,但天下治水英雄,从此云集黄鹄矶头,却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用文学书写这段历史,湖北作家也因此责无旁贷,当仁不让。
我所见到湖北作家与三峡工程有关,或以三峡工程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共有三部,一部是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一部是池莉、小涢合作的《江河水》,一部就是刘继明的新作《江河湖》。这三部长篇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但都不约而同地牵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历史:《乌泥湖年谱》多少带有一点悲剧性,我曾在评论中称之为“无事的悲剧”,意谓这些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远离了治水的本业,近乎“无事”,结果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自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江河水》虽在结尾处微露曙色,但主体仍是一代知识分子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和艰难竭蹶的命运悲剧。
刘继明有幸,得见三峡工程的最后完成,所以他的《江河湖》,就不再给人以悲剧的印象,而是多少带有一点正剧的色彩。但是这正剧又不是简单的光明结局,也不是廉价的正面歌颂,而是一种历史的精神或历史的本质的自然显露。我们常常爱说悲剧的历史或喜剧的历史,那是特指某一个时段的历史现象,究其实,整体的历史在本质上,或其内在精神,却是正剧的。这不但是因为,自从人类相信历史是进化的、进步的,就一直相信历史最终会有一个理想的结局,或是在朝着一个理想的结局走去。而且同时也因为,在人类走向这个理想的结局,或对这个结局的理想中,总是在努力克服那些极端的悲剧性的或喜剧性的因素,以便把追求这种理想的激情和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之达成一个理想的结果。这也许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把悲剧的掌握方式和喜剧的掌握方式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也就是西人所谓严肃的正剧方式。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刘继明都在努力展示历史的这种严肃的正剧性。就作品的中心情节而言,三峡工程的上上下下、曲曲折折,既带喜剧性,又带悲剧性。说它带喜剧性,是因为所有对三峡工程充满激情与理想的人们,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都遭遇过社会动荡、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起落等不可预知的变数,他们美好的动机虽频频受挫,但他们却九死未悔、一意孤行,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还要勉力为之,结局自然就带有一点喜剧性。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可预知的变数,所以他们的激情和理想,虽然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但这种要求,却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结果实际上却“不可能实现”,从而造成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悲剧性。
这种悲、喜剧交加的特征,在作品的主要人物沈福天和甄垠年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按照某种归类法,沈福天和甄垠年分别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上派”的代表,他们的共同之wMx5DkQAORttheUcuIgBedzZN08J1iM82aHvla1P/Qg=处是,无论社会变化、个人遭际如何,始终心系三峡工程,在他们身上,既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又体现了一代知识人的激情和理想。但当他们将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付诸行动的时候,历史却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担当了悲剧和喜剧演员的双重角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甄垠年自认是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反对三门峡工程(包括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却不意被划为右派分子,远离了科学研究,当他安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做一个普通的水文工的时候,却又起用他为三峡工程出谋献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当年的“反上”主张占了上风,恰恰相反,他“反上”的三峡工程正在密锣紧鼓的筹划、建设之中。与甄垠年相反,沈福天的“主上”意见虽然一直占着上风,但仍不免于被诡谲多变的政治所捉弄,他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幸免于难,但无论文革中的被重用,还是文革后的被清查,乃至与甄垠年当年一样的靠边站,都不是因为他的“主上”意见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是为某种领袖意志或某个时期的政治潮流所左右。等到他最后复出主事,真正把毕生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却又天不假年,只能在九泉之下笑看三峡功成。
如果把作品的这两个主要人物分离开来,无论以哪一个为主,都可以另成一部长篇小说。刘继明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围绕三峡工程的上上下、曲曲折折,搬演一出出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的人生悲喜剧,正是企图把黑格尔所说的,“悲剧的掌握方式”和“喜剧的掌握方式”,“调解”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严肃的正剧方式。甄垠年的“反上”,不是简单的“反对”,而是希望用更加科学求实的态度,对待三峡工程,以保后世无虞。沈福天的“主上”,也不是好大喜功,而是基于现实需求和科学实践。二者在现实中虽然尖锐对立,但作者在艺术上却在努力进行“调解”,这种“调解”,不但是借助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亲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他们所特有的人格和精神。这种人格精神,既包含有中国传统士人的积极用世,又兼有近代知识分子的科学求真。正因为有这样共同的人格精神,所以他们之间尽管有无尽的恩怨,不解的纠葛,但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共同的心念上,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正是这种互补关系,让他们在迥然不同的命运遭际和人生道路上,能将上述悲喜剧因素熔铸化合成一种历史的合力,最终实现各自的,也是共同的心系三峡、造福人民的人生理想,同时也让历史走完了这个曲折而又艰难的辩证行程,再次显示了它的严肃的正剧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继明的这部长篇新作,不但抒写了三峡工程建设者、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或心路历程,同时也重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睽违已久的历史的辩证法则和史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