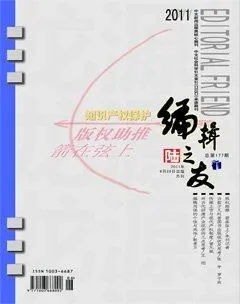读盖伊.塔奇曼《做新闻》
2011-01-01李玮
编辑之友 2011年6期
从现有的教科书和我们主观的教学思维来谈新闻经典,可以说是已经有太多的“经典”:斯诺《西行漫记》是新闻经典,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是新闻经典,史沫特莱《震撼世界的十天》是新闻经典,邹韬奋《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是新闻经典……但是当我们试图站在“建学”的高度去思考相关新闻经典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问题远非那么简单。笔者认为,现在所认可的许多新闻经典多是以教学之“教”为目的,而且对于其能否列入经典大名并未能获得一致认可。本文试图从阅读笔者认可的新闻经典——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的角度,结合目前学界以建学之“建”的高度来思考新闻经典,从而认识新闻经典的属性和特征、形成过程、渠道,以及目前所认可的新闻经典指标有些什么局限与不足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新闻经典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边界拓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以教学之“学”的立场:阅读我心中的“新闻经典”
法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的著作《做新闻》,这本被评价为“一部关于新闻媒介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可靠的实证支持”,“对新闻的社会建构问题进行了富有远见、入木三分的理论分析…能够把实地考察跟哲学思考以及理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堪称典范”的著作,被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列入“20世纪大众传播学名著”。虽然它被称为是“知识社会学”的代表,大众传播学的名著,但在我看来,它与新闻业、新闻学密切相关,是我心中首选的“新闻经典”。
《做新闻》前半部分,盖伊·塔奇曼用民族志的方法,阐述了新闻是现实社会的建构这一深刻的命题。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建构依靠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机构共同完成,新闻机构不仅传播着人们想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信息,并且通过提供议题、控制议题权重、提供语境等来规范着这些信息的意义。可以说,“正是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
新闻的框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空间的网络化,这主要通过对外的地理边界化(以地域为界、以城市为中心,根据不同地区情况确定编辑部的部分划分和人力调配),对内的组织专门化(在那些能够提供新闻而且信息集中的组织设立采访区和记者站),部门分工化(一般按照财经、体育、文化和教育等来进行分工)来实现,不仅如此,编辑还需要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组织和不同部门采集的新闻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产生新闻价值的协商。第二,时间的类型化。所谓类型化,“就是指依照对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处于中心地位的相关特征进行分类”。为了控制工作流程,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件需要进行类型化处理,而新闻工作者界定新闻类别的宗旨,是从他们列举的典型事件以及做出的具体分类来看,就是减少事件的变异性,保证每天计划的连续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第三,在信源选择上,新闻从业者倾向于选择制度内的信息源,而不是普通人所提供的信息,而对不同信息源的选用,不仅建构了不同新闻事实,更展现了不同的新闻信息强度,它同样使得新闻生产呈现框架化和程式化特征。第四,在新闻的表达叙述上,新闻报道同样可以根据镜头不同的时间速度快慢、空间距离远近以及不同拍摄角度等来表现不同意义。
《做新闻》后半部分则深入剖析了新闻建构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机制和动因。首先,塔奇曼质疑了言论自由、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对于人们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总之,要区分报刊的言论自由和电子媒体的言论自由,从经验上看是无效的,因此在理论上也是成问题的。进而言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两种媒体中,专业主义实践限制了激进思想向新闻消费者的传播,因而也限制了每一个人把媒体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来利用的自由,结果最终限制了人们的知情权”。因而塔奇曼的结论是,新闻是意识形态的新闻:“新闻限制了接近权,而且能转变不同的意见。新闻使现状合理化,因而新闻避开了历史分析,而是采取具体的逻辑分析,强调的是事件的偶然性而不是结构的必然性。”其次,塔奇曼阐明了新闻报道如何通过“自反性”(指叙述被嵌入自身所刻画、记录和构成的现实之中)和“索引性”(指社会行动者在运用叙事时,比如使用术语、话语、故事,可能赋予这些叙事各种与其所产生的语境无关的意义),如何通过对新闻事件相关要素的凸显及另一部分相关要素的删除,进而将自然事件转化为公共事件,再进而转化为社会知识,以及认识问题的方法。
《做新闻》对新闻所追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等原则进行了严厉抨击,对新闻所追求的最高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言论自由等进行了质疑,用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了其大胆、深刻而又犀利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以往对新闻的专业学习是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做新闻》则是对以往全部建构的全部摧毁。
二、以建学之“建”的高度:思考“新闻经典”的相关问题
何为经典?经典具有客观存在性还是具有主观建构性?如果经典具有主观建构性,那么其被建构的意义何在?经典的内涵属性、建构路径有哪些?新闻经典的概念提出及建构意义是什么?新闻经典应该具备些什么属性?在新闻理论、历史和业务各领域,相对哪个领域更容易建构出经典?新闻经典是指的单一的著作文本,还是包含新闻行为以外的其他文本?当下已建构出的新闻经典有什么局限性?在新的建构过程中如何实现对其局限性的突围?等种种问题是需要我们站在建学之“建”的高度来思考和认识。
对“经典”进行词源学考察可知,“经”之本义是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后引申出准则、纲纪、自然及历史规律等意;“典”之本义则是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因而经典常常被用以指那些具有权威性、典范性、指导性和重大影响力的伟大著作。出于为人提供典范价值和指导作用的目的,无论是文学经典、史学经典,还是别的学科经典的形成大都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关于经典的内涵属性,有“经典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内在特征”,“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至少包括六大要素: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作为文化符号的经典,具有穿透时空的恒常性,跨学科的影响力等外在特征,具有权威性、原创性、表达的开放性和阐释的多元空间等内在特征”,等等论述。但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大师的肯定、教育机构的传授以及读者的阅读与判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而外,政治权力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也对经典的形成起着推进作用。
从中国新闻经典建构的历程来看,随着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系统研究,新闻经典概念开始被提出,随着诸多新闻作品选、新闻获奖作品选的出版,新闻经典逐步升温并得到频繁使用。但由于对“新闻”的多重理解,以及对“经典”的泛化使用,使得对新闻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充满了争议。一方面,新闻既可以指新闻作品、新闻实践,又可以指新闻体裁、新闻学科;另一方面,对经典的判断和认同见仁见智、人各不同。因而,在新闻学科化建设进程中,对新闻经典的建构也存在极大不同。
关于中国新闻经典,四川大学教授蔡尚伟、博士生刘锐有专门论文对其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目前新闻学著作成为能与其他学科比肩的‘新闻经典’的可能性较小。究其原因,在于新闻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还不成熟,还不完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备受‘新闻无学论’的质疑。”(由于广播电视出现的时间较晚与新闻经典需要经过时空的筛选过滤不符合未被其列入中国新闻经典)。并且该研究认为新闻经典的特征必不可少的应该是“新闻性”这一专属于新闻学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新闻经典评价指标体系,包含新闻性(新闻体裁、发表载体是新闻媒体、著作出版时间距离新闻事件发生的、作者身份是新闻人)、即时影响力(复印次数、读者人数)、历史影响力(版本数、研究数量、引用数、著作中出现的数量)、跨学科影响力(被其他学科引用数、其他学科著作中出现的数量、其他学科研究数量)以及内在经典性(被人称为经典、入选为经典图书的数量)共五个维度以及各维度下共计在内的15个指标。
三、以《做新闻》为例:浅论“新闻经典”的边界拓展问题
蔡教授与刘锐关于新闻经典的相关研究既结合了文本的个案分析,又进行了对样本的数据统计,可谓全面、透彻。但是对其所列选的新闻经典,笔者尚存疑问需要探讨。
第一,其研究样本全是新闻作品,以及“新闻性(新闻体裁、发表载体是新闻媒体、著作出版时间距离新闻事件发生的、作者身份是新闻人)”被视作为新闻经典的首要的评判指标。我的疑问是,新闻作品经典能够构成新闻经典的总体吗,新闻经典之“新闻”到底应该被狭义为“新闻采制、报道”,还是应该被广义为“与新闻采制和报道相关(包括新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内)的”?那些出自非新闻人手中的、发表载体非新闻媒体的、不以新闻事件为内容却以新闻行为为对象的非新闻体裁理论研究著述,是否都可因一个“新闻无学论”而放弃考察其经典性?
第二,其研究样本全是具有所谓的引导作用和典范价值的文本。我的疑问是,这个引导和示范的对象是谁?那些可能以新闻为形式或为手段带有批判性质的作品,以及那些以新闻为研究对象和考察内容带有质疑的著作,是否因引导和示范的对象不统一而落选于“新闻经典”之外?
在笔者看来,新闻作品经典不能构成新闻经典总体,原因在于:(1)新闻经典之“新闻”不应局限为新闻采制报道行为,更不能局限为新闻人实施新闻行为的直接结果新闻作品,作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学科,新闻经典之“新闻”应在更宽泛的范围内来考察,即与新闻相关的理论、历史、教育、研究等都应包含在内。(2)由于新闻作品之易碎性与新闻经典之恒久性的背离、新闻作品写作之程式化与新闻经典之原创性相背离、新闻作品之封闭性与新闻经典之开放性相背离等使得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变小。同时,因受特定时空背景限制和特定政治环境影响,某一阶段的新闻作品其经典长久性和恒久性不可靠。(3)相对新闻作品而言,新闻理论、历史著述是对新闻业、新闻学或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阐述,其内容一般更能超越现时层面,实现纵横两方面的突破。(4)在如今学科大融合背景下,“新闻性”标准只适合于新闻作品经典而不适用于所有新闻经典,因为很多时候其他学科其他行业内人士反倒能以“旁观者清”的立场对新闻、新闻业及新闻学认识得更为深刻,阐述得更为透彻。拿《做新闻》来说,它是一本与新闻密切相关的书,虽然问世已有五十年历史,但其思想观点之异常深刻发人深省,对媒介化生存状态下的每一位都如重锤敲打,其即时影响力之巨大、历史影响力之深远,是一般新闻作品所不可比拟的。另外,被众多权威机构和权威人物所认同和肯定,凸显了其权威性;以解释社会学方法研究新闻业,引入诸多社会学观点,具有论述方面的开放性;其理论观点问世五十年而不衰,可见其恒常性。综上,笔者认为,《做新闻》不仅可被作为新闻经典来加以考察,还可以作为新闻经典的一个类别来加以建构。
除此而外,《西行漫记》、《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国的西北角》、《人生采访》、《萍踪寄语》、《远生通讯》等这些已被建构出的新闻作品经典,虽然具备指导作用和典范价值,但从辩证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权衡一本著作是不是经典,必须将之与是否接近真理、是否获取共识紧密地联系。如《做新闻》,一方面虽斥责着新闻公正性、客观性与真实性,冲击着新闻言论自由、新闻专业主义,但它句句击中新闻人心中之痛,确实,由于人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新闻业所追求的客观、公正、真实都只是无限逼近的目标,它在斥责新闻客观公正真实的同时为新闻业、新闻学的奋发向上、获取认同指明了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它在斥责新闻建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间接肯定了新闻潜藏的巨大能量、新闻业所存在重要作用,可以树立新闻业和新闻学的信心。如果我们积极的眼光、医治的态度去看,会发现其建设性意义在于,它不仅能为新闻业的发展起到警醒作用,也能为新闻受众辩证接受信息起到积极作用。“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笔者认为,在对新闻经典的选取、评判、考察、建构过程中,无论其立场态度如何,应以一个学科该有的宽容、豁达去接受那些能获取高度认同的书籍。
参考文献:
[1][2][3][4]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做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2.67.169.
[5]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6][8][9][10]刘锐.跨学科框架下的“新闻经典”研究[R].四川大学博士论文:54.
[7]刘象愚.经典的解构与重建[J].中国比较文学,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