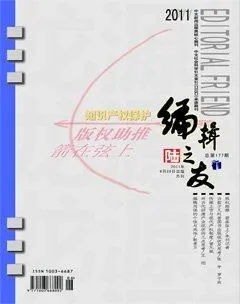关于编辑职业比喻的若干断想
2011-01-01李振荣
编辑之友 2011年6期
围绕着一种职业,衍生出不同的比喻与看法,个中之奥妙幽隐,颇值得我们探寻与深究一番。
一、做嫁衣者
不知从何时起,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这句“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诗,就被视为对编辑职业的一种本质性的写照而流传至今,且有绵延下去之势。这一说法之所以广为流行,一方面它确实道出了编辑这一职业的某些核心特征,如其依附性与被动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地折射出从事此项职业者的某种苦涩与悲凉的心态。试想,要嫁女儿的人是作者,要娶的人是读者,而编辑只是为女儿缝制嫁衣的工匠而已,无名又无分,地位何其低微也哉!
曾几何时,提倡编辑要甘为“做嫁衣者”,要一心一意做扶植作者的“绿叶”的思想蔚成风气。持此论者不少都是文化界与出版界的重量级人物,话经他们之口而出,更显出一种一言九鼎、不容置喙的意味来。比如曾执掌过中国文化界的周扬说:“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服务精神。”被誉为“美国编辑元老”的珀金斯更是将编辑比喻为:“一个蹲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子,建议他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而自己却不引起他人的任何注意。”正所谓众口铄金,似乎编辑这“做嫁衣者”的角色是注定难逃了。
对以上说法,也不乏持异议者。当代女作家张抗抗就说:“我但愿永远也不要当编辑。”细味此语,对于发表过大量作品、与编辑交往甚多的张抗抗来说,倒不是她鄙薄编辑这一行当,可能是因为她太多地目睹编辑工作之琐碎辛苦而又籍籍无名,才会望而却步的吧。如果说张抗抗还只是个圈外人,那我们再看看大编辑家龙世辉是怎么说的:“编辑的社会地位难道低人一等吗?……编辑没有社会地位,对他们又只是使用,使用,这种情况不能再延续下去了。”透过这充满悲凉意味的反诘话语,我们不难看出龙世辉不光是在为自己发“不平之鸣”,而是在为编辑这一群体抱不平了。
关于“做嫁衣者”的种种说法,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编辑这一职业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问题。以前自不必说,即使现在,认为“编辑无学”,抑或编辑工作就是“剪刀加糨糊”的也是不乏其人。今日观之,这种“做嫁衣者”的说法已颇不合时宜,理由有三:1、传统的观点,就是一味强调编辑要具备无私奉献精神,过多地赋予这种职业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结果只能是使其成为“不能承受之重”。2、以前过多地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忽视其商业属性,编辑作为文化产业发现者、塑造者、选择者、整合者的角色基本被剥离或遮蔽,仅余加工者一种而已。最终的结果,就是使编辑成为文化领域的“边缘人”“失语者”。3、编辑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理应成为人才荟萃之地。但我们不得不说,“做嫁衣者”的定位令许多优秀人才对这一职业敬而远之。目前,编辑队伍难以吸纳到高端人才的景况,虽说不能全部归咎于此,但至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杂家
杂家,是编辑圈内的一个老话题了。只要略翻一下20世纪的出版类杂志,此类文章可谓俯拾皆是。方其时也,做专家还是杂家,颇有点类似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样,成为编辑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了。
称编辑为杂家,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与含义。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杂家列为“九流”之一,言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最早将编辑与杂家联系在一起的是罗竹风,若干年后,叶圣陶又写有《要做杂家》为其张目。细绎其语意,罗、叶二公所说的杂家,同儒墨、名法、百家等概念已无多大关系,而是对编辑一种特定的与专家相对应的称谓。鉴于二人在文化界与出版界的影响,此论一出,附和者颇多,影响亦甚为深远,杂家几乎成了编辑的另—个代名词。
罗与叶的说法属于典型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含有为编辑寻求主体归属的一番苦心在,但终究未能跳出班固九流、十家所划定的畛域。将编辑定位为杂家,其主体性固然有所依归,但怎么看都给人一种“万金油”“小摊贩”之感,实难登大雅之堂。从历史上看,杂家在“九流”中本来就属于被轻视的一类。《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见,杂家的缺点在于“漫羡”“无所归心”。即便现在,什么东西一同“杂”沾边,总给人不入流的感觉。如此看来,无论在以前还是当下的语境中,杂家的地位究竟是不怎么高的。
我倒以为,编辑的主体归属,实不必纠结于杂家一途。王建辉曾经有一个提法:通家。此说极有见地。因为说到底,杂家只能说明编辑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而难以看出他在见识、气象、格局等更高层次方面的东西。以杂家一词来概括编辑的全部内涵,总显得有些勉为其难。通家则不然。通者,贯通、融通、会通也;通家,就是要有通才,具通识,见通解,不拘于一识一解,不囿于一科一目。纵观中国百年出版史,张元济、王云五、陈原等可当得起此称号。张元济抱“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之宏愿加盟商务印书馆,编印教材,译介西学,整理古籍,商务印书馆由此而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发展为近代出版史上的标杆企业。据载,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张元济为唯一全票当选者。要知道,当时能人选者可都是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张元济既非专门学问家,也无专门著述行世,若非达通家、通人之境,何以能受此尊崇?由是观之,今日之编辑,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当应跳出传统杂家的窠臼,向着通家的方向努力。
三、教练员
一个编辑就是一个教练员,是吕叔湘在《谈谈编辑工作》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细加思忖,曾做过编辑的吕先生此处可谓颇有深意,它当包含两层意思:1、讲编辑“手”与“眼”的关系;2、讲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先说第一层。将编辑比作教练员,那么当教练员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对体育稍具知识的人都知道,做一名教练,手眼俱高,那是上上之选;若退而求其次,则至少要眼高。环顾当今体坛,有两位教练与此情况颇为契合:一位是中国男乒的主教练刘国梁,另一位是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主教练穆里尼奥。做编辑,如能成为刘国梁,那是最好;如果不行,那至少也得成为穆里尼奥。换言之,如果你不能做到手眼俱高,那你至少也得眼高。否则,你就不适合从事编辑这行。
编辑圈里,手眼俱高的人物不在少数,最具代表性的就属中华书局的周振甫了,他与钱锺书先生的编创合作早已成为一时佳话。你想,能编辑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眼力肯定没的说;而周先生的手力也甚是了得:编辑之余,勤于著述,在《文心雕龙》研究、古籍今译、诗词释读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凡建树,是编辑中手眼俱佳的代表人物。如果说,手眼俱高尚属可遇而不可求之境,那眼高则是编辑的必备之技了。多少经典之作若没有编辑的“慧眼”,可能早就湮没红尘、了无痕迹了。秦兆阳之于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江晓天之于姚雪垠的《李自成》,龙世辉之于曲波的《林海雪原》,都是编辑慧眼识珠的经典例证。
再说第二层。编辑是教练员,那作者自然就是运动员了。但编辑要成为作者的教练员,那可谈何容易!对于许多“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新人来说,正是缘于“教练员”——编辑大家——的点拨与提携,他们才走上文坛并广为人知的。作家蒋子龙曾写过一篇《编辑何以为“大”》的文章,其中谈到当年大编辑家秦兆阳如何帮他改稿。
秦兆阳、江晓天、龙世辉这些编辑大家,是文学新人的教练员,更是编辑圈内的标杆人物、编辑们追慕与奋进的目标。严羽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通过对他们的学习,我们才能悟到怎样做一名真正的编辑,何为做编辑的真谛;而编辑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也正是在追寻这些前贤足迹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确立和高扬的。
参考文献:
[1][3]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23,404.
[2][4]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10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405,430,409.
[5][6](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2.
[7]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9.
[8]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