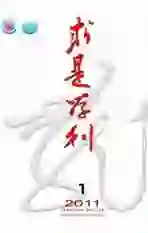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2011-01-01孙蓉蓉
求是学刊 2011年1期
摘要:《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诗纬》;《诗经》;“四始”“五际”;诗句解说
作者简介:孙蓉蓉,女,上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谶纬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BZW002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1-0111-08收稿日期:2010-10-05
《诗纬》是与《诗经》相配的纬书,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纬》有《推度灾》、《氾历枢》和《含神雾》三种①。与其他纬书一样,《诗纬》的内容多样、庞杂。《诗纬》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与《诗经》是毫不相干的,如关于“圣人感生”、“君权神授”等,还有关于灾异祸患的记载。这些内容与“经”无关,而与谶结合了起来。《诗纬》中所论的“诗者”,是指《诗经》及诗的创作,涉及诗的性质、功用等问题。最能体现《诗纬》解说《诗经》特点的,是结合《大明》、《四牡》等诗篇而提出的“四始”、“五际”说。《诗纬》对《诗经》篇义的阐释、对原句的解说和引用等,都体现了纬学的性质和特点。由于《诗纬》以阴阳律历附会《诗经》,因而历来被视为迷信诡异、荒诞不经而否定之。而在《诗经》学史的研究中,很少有对《诗纬》作专门的论述②,也有论及《诗纬》的,是将它归之于《齐诗》而论之③。其实,《诗纬》也是汉代研究《诗经》除毛、鲁、韩、齐四家之外的一家之言,VWhIf5TNBvZ3CEfTzNEtFo9NsDLL+CO/WKzEbubiZZ0=其对《诗经》的阐释亦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诗纬》对《诗经》的阐释上,从对诗的性质、功用的认识,到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的解说,说明纬学诗论的内容,及其对我国汉魏六朝时期文论发展的影响。
一、“天地之心”——对诗的性质、功用的认识
《诗纬》中对“诗者”的论述,提出“天地之心”、“诗者持也”、“《诗》无达诂”等,涉及诗的性质、功用及解诗方法,是《诗纬》中核心的诗论观点。这些观点与传统儒家的诗论有所不同,而表现出纬学的特点。
首先,《诗纬》提出“天地之心”说,这是关于诗的性质的问题。《含神雾》: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府。[1](P464)
诗在天地之间是核心和中心,诗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清陈乔枞《诗纬集证》案:“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情性者人所禀天地阴阳之气也。天地之气分为阴阳、列为五行,人禀阴阳而生,内怀五性六情,仁义礼智信谓五性,喜怒哀乐好恶谓六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情各正,万化之原也。……诗正性情而厚人伦,美教化而移风俗,推四始之义,明五际之要,此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顺阴阳之理,慎德行之用,著善恶之归,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故纬言此以明之。”[2](卷3,《含神雾》)因诗的“天地之心”,诗才能够成为君德、百福、万物的始祖和本源,这样诗成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诗的“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即把诗的文字刻在玉石上,珍藏于书库的金柜中。“诗者”为“天地之心”,说明诗是“天地之心”的表现。这样,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神灵启示的性质。它表现在人事社会上,又是“君德之祖”、“百福之宗”,是人间君主自身道德修养、百姓福祉的源泉。《诗纬》对“诗”的认识,就是通过“诗”的作用,将天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人禀天地阴阳之气而怀有情性,表现人情性的“诗”亦是阴阳结合的产物。如《氾历枢》:
丑者,好也。阳施气,阴受道,阳好阴,阴好阳,刚柔相好。品物厚,制礼作乐,道文明也。[1](P483)
巳者,已也。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出,成文章。[1](P483)
乐者,非谓金石之声、管弦之鸣,谓阴阳和顺也。[1](P482)
这里“文明”、“文章”和“乐者”的本源都肇始于阴阳,天地万物由于阴阳而成文采,圣人的制作礼乐,就是效法于阴阳,以道文明、以成文章和音乐。因此,诗乐是“阴阳和顺”的产物。由“天地之心”到“阴阳和顺”,这是纬学对“诗”的一个根本的认识。
《诗纬》对“诗”的这一认识,与先秦、两汉正统儒家诗论有所不同。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注重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到《毛诗大序》提出“美教化,移风俗”,突出了诗的政治教化的功能。正统的儒家诗论还只是就诗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来认识的,强调了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作用。相比较,《诗纬》的“天地之心”说,将诗与作为自然宇宙的天地联系起来,从诗在天地之间所处的地位上,认识到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种认识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识诗歌的端倪。《诗纬》提出的“天地之心”说,对于开启后来文论对文学本源问题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如王充《论衡·书解篇》认为,天地鸟兽山川等万物皆有文采,而天地之中的人同样也有人文。王充的《论衡》虽是针对谶纬的虚假荒诞而作,但他也吸取了纬学的“人文法天象”之说。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真正从哲学本体的意义上探讨了文的起源问题。刘勰从“天之象”、“地之形”、“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上,推论出天地之中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P1),提出了“文原于道”的观点。《诗纬》的“天地之心”说,以阴阳、五行、天地、日月等具有神性的自然物作为“文明”、“文章”、诗乐的起始之源,这种理论客观上为古代文学艺术创作淡化政治色彩、摆脱诗教束缚,而独立成为一种审美活动而创造了条件。
其次,《诗纬》的“诗者持也”说,提出了诗的功用问题。《含神雾》:
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
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1](P464)
《诗纬》训“诗”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而且“持”可以作为“诗”的假借义。《说文通训定声》释:“诗, 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假借)为邿公羊襄十三年取诗,鲁附庸国也。又为侍或持。”[4](P642)《诗纬》的作者将“诗”与“持”两者联系起来,以此表达他们对“诗”的认识和看法。《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以手承下”是“持”之意,而“抱负”则由“以手承下”的“持”进一步引申为“扶持”。至于所“持”的内容,即“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自持其心”、“扶持邦家”,明确地说明了诗所“持”的是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诗就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诗纬》将“诗”训释为“持”,是把“持”物的本义引申为“持”心。这样“诗者持也”,可释为诗能端正、培养、陶冶和感化人的情性。并且,由“敦厚之教”的道德教化到“讽刺之道”的社会作用,由“自持其心”的个体到“扶持邦家”的家国,“诗者持也”说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功效和作用。
《含神雾》中对“诗者持也”的解释,其基本思想还是来自于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等是《诗纬》提出“诗者持也”的思想资料。然而,“诗者持也”说却也是汉代不同于毛诗等其他四家说诗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诗论观点。孔颖达《诗谱序正义》:“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由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性,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5](P262)这一段话总结概括了汉代不同的诗论说,其中“诗者持也”说成为诗的“三训”之一。显然,“诗者持也”不同于传统的“诗言志”说,但两者并不矛盾对立,而是补充和发展。“诗言志”说是就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的,强调的是诗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诗者持也”说,则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将两者结合起来,抒发诗人志向、理想的诗歌能够具有扶持、端正人的情感、性情的作用,这就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性质和作用。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歌的认识,如《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3](P48)刘勰引用“诗者持也”,并说明诗的“持”,意思是扶持、把握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诗者持也”说作为纬学的一种诗论观点,也影响了文论家对诗歌的认识。
最后,《诗纬》以为“《诗》无达诂”,提出解读《诗经》的方法。《氾历枢》:“诗无达诂,易无达言,春秋无达辞。”[1](P482)“《诗》无达诂”等语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诗》无达诂” 意为对《诗经》无法作出通达、确切的训诂,即难以作出准确、确定的解释。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是对历来解读《诗经》断章取义的一种概括。如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赋《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6](P2000)对《诗经》各取所需而“断章”,又因人而异而“取义”,这在当时是蔚然成风,因而典籍中多有记载。至汉代,人们仍然以此法解读《诗经》,如《韩诗外传》即为典型一例。因此,清卢文弨曰:“夫《诗》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读《诗》者有因诗人之情,而忽触乎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诗人之情,而远者忽近焉,离者忽合焉。《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试观公卿所赠答,经传所援引,各有取义,而不必尽符乎本旨。”[7](卷3,《校本韩诗外传序》)《韩诗外传》的解《诗》方法,就是对“《诗》无达诂”说的准确注解。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指出了当时人们解读《诗经》的主观性、随意性和自由性,读者可以完全不顾原作的本意,而从自己所要表达的需要,随心所欲加以断章取义。然而,实际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董仲舒在提出“《诗》无达诂”之后,又有“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之语①。把前后两者联系起来,或许更能理解“《诗》无达诂”的真正含义。“从变”意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诗经》作品作出灵活自由的理解和解释;“从义”则是强调读者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臆测又必须揭示其微言大义,即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可以说,“从变从义”决定了人们对《诗经》的解读,是有指向性和规范性的,而绝非是随心所欲。《氾历枢》对 “《诗》无达诂”的引用,不仅说明《诗纬》同董仲舒理论的沿袭、承继的关系,而且从纬学的思想体系来看,它对《诗经》的解读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与董仲舒是相一致的。
虽然“《诗》无达诂”是董仲舒提出的一种解经的方法,但它却涉及文学理解和阐释活动的现象和规律,即人们的文学鉴赏和审美活动存在着差异性、多义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由于读者个人的审美心理、审美标准和审美情感不同,因而对同一个审美对象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诗》无达诂”说虽就《诗经》解读的断章取义而言的,但它却深刻地指出了文学鉴赏、阐释活动中读者对作品内容、主题及意义的参与和创作。因此,我国古代对诗的阐释,由“《诗》无达诂”发展到“诗无达诂”。如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8](卷2,《题柳柳州集后》)王夫之《姜斋诗话》:“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9](P3)这些论述都说明了文学鉴赏、阐释活动中读者主体的作用和意义。《氾历枢》的“《诗》无达诂”说,虽沿用董仲舒之语,但它最终成为我国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阐释理论和阐释方法。与经学、纬学的“《诗》无达诂”力求“微言大义”有所不同,后世的“诗无达诂”,则主张“自得”和“意味自出”。如王若虚《滹南诗话》:“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10](P523)又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11](P1)“诗无达诂”的“自得”和“意味自出”,充分强调了读者对诗作的理解和认识。
《诗纬》尽管内容庞杂、论述零散,但是从“天地之心”、“诗者持也”,到“《诗》无达诂”,涉及诗的性质、功用和阐释方法等诸多问题。虽然这些理论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它们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诗论,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四始”“五际”——对《大明》、《四牡》、《嘉鱼》、《鸿雁》的释义
《大明》、《四牡》、《嘉鱼》和《鸿雁》是《诗经》《大雅》和《小雅》中的四篇诗作。这四首诗在《诗纬》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即“四始”说的提出。而《诗经》中的《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及《十月之交》,又同“五际”说相配。“四始”、“五际”是《诗纬》中最能体现其解说《诗经》特点的重要理论。
第一,关于“四始”说。“四始”说是汉代《诗经》研究中的一个术语,鲁、韩、齐、毛四家都有“四始”说。如将“四始”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提出,且有具体而明确论述的,最早见于《毛诗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5](P272)
《毛诗》的“四始”说指出了《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的诗作都具有讽谕美刺的功效,因而它们能作用于王道之兴衰。《诗纬》也有“四始”说,如《含神雾》、《推度灾》:“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1](P464)“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1](P469)
与《毛诗大序》的“四始”说截然不同,《氾历枢》对“四始”释为:“《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1](P480-481)对于《诗纬》的“四始”说,清陈乔枞《诗纬集证》案曰:“四始者,五行本始之气也。亥地西北,坎水居之;寅地东北,震木居之;巳地东南,离火居之;申地西南,兑金居之。少阳见于寅,故寅为木始;少阴见于申,故申为金始;离太阳也,太阳之气见于巳,故为火始;坎太阴也,太阴之气见于亥,故为水始。”[2]这一段话具体说明了“四始”与“五行”的关系。《诗纬》以“阴阳五行”说来阐释《诗经》,其实质是要从阴阳际会、五行运行的自然法则中推论出人事发展的规律。结合《诗纬》等其他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诗纬》的“四始”选择《诗经》的《大明》、《四牡》、《嘉鱼》和《鸿雁》四诗为例,意在说明周朝的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
《大明》表现殷商“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的衰落,而周朝则“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的初兴情景,这是新旧两个朝代更替迭陈之际,即为“亥”。“亥”为“四始”之始,“亥者太也,既灭既尽,将复,又有始者也”[1](P476)。《诗纬》对“亥”的解释,说明了“亥”为万物之始,故“《大明》在亥”。《四牡》是一首君王慰劳使臣之诗。郑玄笺:“文王为西伯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来于其职,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歌乐之。”[5](P406)文王体恤臣民,上下交泰,以求昌达。《四牡》配为“寅”,“寅者,移也,亦云引也。物牙稍吐,引而申也,移出于地也”[1](P474)。故《推度灾》曰:“《四牡》,草木萌生,发春近气,役动下民。”[1](P477) 春季万物勃发,周朝乘势发展。《嘉鱼》描写“乐与贤也,太平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5](P419)。周朝进入太平盛世,故配之以“巳”,“巳者,已也。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出,成文章”[1](P483)。盛极而衰,周朝繁盛的背后又隐含衰弱的危机,故君主宴贤者,共商国是。《嘉鱼》为“火始”,“立火于《嘉鱼》,万物成文”[1](P477)。宋均注:“立火立夏,火用事成文。时物鲜洁,有文饬也。”[1](P477)《鸿雁》写万民劳役之苦,《毛诗序》曰:“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5](P431)周室开始衰落,配之以“申”,“申者,伸也。伸犹引也,长也,衰老引长”[1](P474-475)。故《推度灾》曰:“金立于《鸿雁》,阴气杀,草木改。”[1](P477)《诗纬》的“四始”说,以干支的亥、寅、巳、申,同五行的水、木、火、金相配,以此来解释《大明》等四诗。而《诗纬》的“四始”之所以以“阴阳五行”来解说《诗经》诗篇,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意蕴。因为,“阴阳五行”说在构建其循环往复的自然宇宙系统论的同时,又将历史人事紧密结合起来。其立论宗旨是以论天地而论人事得失宜忌,力图从自然的阴阳交际、五行终始、四季更替和八节相通的法则中,引申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阴阳五行”说提倡顺天守时,强调人事必须符合天道。“阴阳五行”说的这一性质也同样体现在《诗纬》的“四始”说上。如陈乔枞《诗纬集证》:“纬说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托之。盖欲王者法五行而正百官,正百官而理万事,万事理而天下治矣。政教之所从出,莫不本乎五行,乃通于治道也。”[2] 这一评述深刻地指出了《诗纬》“四始”说的性质,即探究王道治乱安危的问题。
第二,关于“五际”说。《诗纬》的“五际”说与“四始”说是相关联的,它们在《诗纬》中往往相提并论,如“下序四始,罗列五际”[1](P464);“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1](P469)。《氾历枢》释“五际”为:
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P481)
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1](P480)
《诗纬》提出的“五际”源自于翼奉的“五际”说。综合对“五际”的相关解释,所谓“五际”,是指阴阳终始往复的五个关节点,即卯、酉、午、戌、亥,这五个关节点正是“变改之政”的时机,即“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1](P480),是一个朝代兴盛衰亡、转折更替的时候。《诗纬》将“五际”配以《诗经》的诗篇,加以具体说明。《氾历枢》:“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1](P480)此说只有卯、酉、午、亥,所配诗是《天保》、《祈父》、《采芑》和《大明》四篇。因此,有研究者将翼奉提到的《十月之交》配以戌位,由此构成五际①。
根据天干地支阴阳的推演,“五际”中“卯”时,旭日初升,夜终昼始,为阴阳交际之时;“午”时,日中而昃,阳初谢而阴始兴之时;“酉”时,太阳落山,阴大盛而阳已微也;“亥”时,由极阴转为生阳,亥终子始。而从《诗经》所配的诗篇来看,配“卯”的《天保》,描写了周公继承文武事业,又有上天的保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5](P412),奠定了王朝盛世的基础。配“午”的《采芑》,以南征荆蛮,赞宣王中兴之功,“如雷如霆,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5](P426)。配“酉”的《祈父》,“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5](P433),兵士怒于久役,指责周宣王用人不当,周王朝由盛而衰。配“亥”的《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5](P508),殷周革命,周朝受命而王。配“戌”的《十月之交》,刺幽王昏庸,小人当道,“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5](P446)。国运尚存,但灭亡将至。同“四始”说一样,从“五际”所配的诗篇来看,从《天保》到《十月之交》,它也是周王朝的一个兴盛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总之,所谓的“四始”、“五际”都是《诗纬》以阴阳际会、五行运行的规律,配以《诗经》的诗篇,来探究、说明时政人事的发展变化。因此,《诗纬》的“四始”、“五际”说对《大明》等诗的释义,完全是作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对《诗经》原作的曲解和附会。
三、“《关雎》知原”——对具体诗篇的解说
《诗纬》中还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对《诗经》篇义的阐释,对原句的解说和引用,以及对国风音律风格形成的说明。这些内容同样体现了纬学的特点,有的有助于对原作的理解,而更多的则是作者的借题发挥。
《诗纬》对《诗经》的解说,对具体诗篇篇义的阐释,主要有《关雎》、《灵台》和《十月之交》等。关于《关雎》,《诗纬》论及的有两条:
《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
《关雎》恶露,乘精随阳而施,必下就九渊,以复至之月,鸣求雄雌。[1](P471)
所谓“知原”,指《关雎》知“有别”的特性。即《毛传》“鸟挚而有别”,“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5](P273)。郑玄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5](P273)因此,宋均注:“嫔,妇也。八妇正于内,则可以化四方矣。”[1](P471)《诗纬》对《关雎》篇义的阐释,同《毛诗序》是相一致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5](P269)《诗纬》与《毛诗序》都将《关雎》诗同社会伦理联系起来,强调了其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所谓“恶露”,是指《关雎》的雎鸠鸟能在隐蔽处求偶。《韩诗》:“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12](P4-5)《韩诗》由雎鸠鸟隐蔽处求偶,又进一步引申为“刺时”,之后《关雎》又有“刺时”说。因此,关于《关雎》诗的篇义,历来有“颂美”和“刺时”两种说法。两说虽不同,然实质相同,都体现了汉代《诗经》学的特点。
关于《灵台》,《诗纬》中共有三条:
作邑于丰,起灵台。[1](P464)
灵台参天意。[1](P479)
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1](P479)
《大雅·灵台》是一首歌颂周文王政治清明,人民乐为其用的诗作。《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13](P3) 孟子以“民本”思想说明了《灵台》诗“与民偕乐”的主旨。《毛诗序》对《灵台》的“序”也基于这一观点,如“《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5](P524)。而《诗纬》对《灵台》的解释,说明周文王建造灵台的地点“作邑于丰”,在“丰”这个地方设置都邑后,建造了灵台。此外,《诗纬》更强调了“灵台”的作用在于“参天意”、“候天意”。“灵台”是天子观察天文,了解天意,与神沟通而受其旨意的一个地方。《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释“灵台”:“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度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诗》云‘经始灵台’。”[14](卷4,《辟雍》)并且,《诗纬》对《灵台》的解释,还突出了“灵台”目的在于“经营灵台,天下附也”,建造灵台是受命天子使天下附从、归顺、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秦汉时期帝王统治者特别重视封禅、郊祀等礼仪活动。到郑玄对《灵台》的笺注,就吸取了《诗纬》的观点,曰:“民者冥也,其见仁道迟,故于是乃附也。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5](P524)《诗经》的《灵台》,由周文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建造有神灵之德的灵台,到《诗纬》指出灵台的“参天意”、“天下附”,说明灵台后来成为天子望气之台,这样的解释具有了纬学浓厚的“天人合一”的神学色彩。
关于《十月之交》,《诗纬》的论述多达五条: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此应刑政之大暴,故震电惊人,使天下不安。[1](P460)
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崒崩,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1](P469)
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1](P469)
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见徵。辛者正秋之王气,卯者正春之臣位。
日为君,辰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为臣,秉权而为政。故辛之言新,阴气盛而阳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1](P469)
十月震电,山崩水溢,陵谷变迁,民生日促。后二年,幽王为犬戎所逐。[1](P487)
《毛诗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5](P445)《小雅·十月之交》是一首刺幽王宠信褒姒,皇父乱政,日月告凶,人民苦难的诗作。原诗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两句,以电闪雷鸣、地动山摇来比喻当政的黑暗和腐败。而《含神雾》则直接点出“此应刑政之大暴”,以“刑政大暴”对应“震电惊人”,这就是“天下不安”的表现,《含神雾》的作者作了发挥和明示。对《十月之交》的“百川沸腾”,郑玄笺:“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贵小人也。山顶崔嵬者崩,君道坏也。”[5](P446)孔颖达疏引《推度灾》:“《推度灾》曰:‘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崒崩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即。’是也。”[5](P446)郑玄笺说明“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都有其象征意义,而孔颖达又认为《推度灾》的解释是符合原意的。确实,当时人们将“百川沸腾”理解为是小人专权、君道败坏的象征。如《汉书·李寻传》:“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书》云‘水曰润下’,阴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惟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15](卷75,《李寻传》)显然,“百川沸腾”的自然现象成了小人专权的预兆与明征。以阴阳五行、灾异祸害解说《诗经》是今文诗学的基本方法,而谶纬学家又进而将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视为是神灵的启示,是对人世的谴告,《十月之交》诗篇正起着这样的一种作用。《十月之交》原本就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萌芽,到《诗纬》阐释时则突出和强化了这一点,以阴阳五行、天象自然同君臣人事、历史进展联系起来。
《诗纬》对《诗经》原句的解释。《诗纬》中有对《诗经》诗作原句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有助于对原作的理解,未脱离原诗作的实际,是有意义的。如《推度灾》:
复之日,鹊始巢。
鹊以复至之月,始作室家,鸤鸠因成事,天性如此也。[1](P470)
《召南·鹊巢》诗原句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5](P283)。《推度灾》释“复之日”、“复至之月”,即冬至。《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16](P97) 而鸤鸠即布谷鸟或称八哥,俗谓鸤鸠天性笨拙,不善作巢。《诗纬》对《鹊巢》作了名物常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显然要比《毛诗》的说明要客观符合实际。《毛诗序》:“《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之,德如鸤鸠,乃可配焉。”[5](P283)郑玄笺:“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5](P283)同把《关雎》视为“后妃之德”一样,也把《鹊巢》看做“夫人之德”。《诗纬》并没有对《鹊巢》作如此的引申和发挥,这有助对原作的理解。
然而,《诗纬》对《诗经》诗句的解释,更多的是脱离原作,借题发挥,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如《氾历枢》:“箕为天口,主出气。尾为逃臣,贤者叛,十二诸侯列为廷。”[1](P480) 《小雅·巷伯》原作有“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5](P456)的诗句,原意是张开那张嘴,越张越大,如同像身小舌大的南箕星。那个好诽谤的人,是谁给他出谋划策。诗中的“成是南箕”,是一种比喻的手法。郑玄笺:“箕星哆然,踵狭而舌广,今谗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犹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5](P456)孔颖达疏:“言谗人集成己罪,又言罪犹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宽大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5](P456)郑玄和孔颖达的笺疏都说明是用了比喻的说法,这是符合原诗的原意的。然而,《诗纬》的解释则完全脱离了原作,把“成是南箕”的“南箕”,释为“箕为天口,主出气”。 箕即箕宿,星名,共有四星,二星为踵,二星为舌。踵窄而舌宽,夏秋季之间见于南方,故称南箕。古人观星象而附会人事,认为箕星主口舌,如《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曰口舌。”[17](卷27,《天官书》)《索隐》:“《诗》云‘维南有箕,载翕其舌’。又《诗纬》云‘箕为天口,主出气’。其箕有舌,像谗言。《诗》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谓有敖客行谒请之也。”[17](卷27,《天官书》)将天上的星象同人间的政治联系起来,因此《氾历枢》对《巷伯》的解释完全脱离原作,而是借题发挥,以宣扬纬学的“天人感应”的理论。
《诗纬》对《诗经》原句的引用。如《氾历枢》:“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1](P479)所引诗句出自《大雅·棫朴》,原诗句并未涉及祭天,只是描写威仪赫赫的文王,群臣捧璋朝贺。而《氾历枢》所引则将其与“受命”、“祭天”联系起来,其说同于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董仲舒认为,君王作为天之子每年要在郊外祭祀上天,上天是各种神灵的主宰,是君王最尊重的神灵。因此,《郊祭》曰:“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每将兴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檝之。周王于迈,六师即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王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处央乎?”[18](P405)在这里董仲舒将《诗经》中相关的诗句联系起来,以此说明“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由此看来,《氾历枢》的观点和所引诗句,都是出自董仲舒的理论学说。
《诗纬》对《诗经》国风音律的评述。如《含神雾》:
齐地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污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之宫角。陈地处季春之位,土地平夷,无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宫徵。
曹地处季夏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徵,其声清以急。
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而扬。
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此唐尧之所起。
魏地处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邶、鄘、王、郑,此五国者,千里之城,处州之中,名曰地轴。
郑,代己之地也,位在中宫,而治四方,参连相错,八风气通。[1](P460-461)
《诗纬》认为十五国风中的各地,所处方位不同,所配音律不同,因而诗乐风格就有差异。《含神雾》中这些对各国地理状况、民情风俗的说法是有所依据的,《汉书·地理志》就论述到各国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以及风俗习惯等。然而,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不同,《含神雾》中对齐地、曹地、秦地等国风诗的解说,主要突出其月位、音位、律位和分野等。如齐地处孟春之位,干支为寅,音位为角,律位为太簇,方位为东,分野为尾、箕;曹地处季夏之位,干支为未,音位为徵,律位为林钟,方位为南,分野为鬼、井,等等。《诗纬》对国风的解说,体现了纬学的特点,即以星占学理论,把天体星辰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相对应。如分野星占术,把天上某一部分星象的变化来占测与它相对应地区人世的吉凶祸福。这就是所谓“天垂象,示吉凶”,它也是天与人交感的一种表现。此外,古代天体星宿的运行还与音律有关。因此,《诗纬》解释国风,有月位、音位、律位,还有星宿的分野等,所处各位不同,于是就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
综上所述,《诗纬》对《诗经》的阐释,由一般理论的提出到具体诗句的解说,都体现了纬学的特点。《诗纬》的荒诞诡异、神学迷信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其神秘的面纱下,还有其合理的因素。作为汉代《诗经》学研究中一个学术流派,《诗纬》对《诗经》的阐释同样丰富和扩展了《诗经》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因此,对于《诗纬》,亦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赞曰”所说,“芟夷谲诡,糅其雕蔚”[3](P29),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诗纬》对《诗经》的研究仍然有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