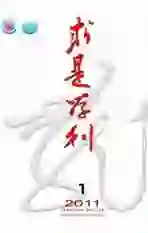城市的精神①
2011-01-01贝淡
求是学刊 2011年1期
摘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城市风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蕴。这是因为,全球化正在使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迅速同一化和均质化,在国家层面,对抗这种同一化和均质化是相当困难的,而在城市层面,城市风尚的培养或恢复可以有效地保护文化多样性。
关键词:城市风尚;全球化;文化多样性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社群主义研究;阿夫纳·德-沙利特(Avner de-Shalit),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民主与人权教授,从事政治学研究。
译者简介:付洪泉,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求是学刊》副编审,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1-0018-07收稿日期:2010-09-21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考最初起源于在不同城市以及它们表达的价值种类之间的比较。古代雅典代表的是民主以及对人民(不包括奴隶和妇女)之庸常判断的信任,而斯巴达代表的则是拥有为城邦荣誉而战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公民-战士(以及相对来说强悍的妇女)的寡头政治的模式。不同的政治思想家从这些相互竞争的模式中选取立场并获得灵感以阐述他们自身的政治规则之理论。柏拉图或许赞许地倾向于斯巴达的模式,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或许可以证明,他对民主的规则持有更为平和的观点并且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优点。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城市——耶路撒冷——则对此世政治成功的关注表示怀疑。生命的终极目的在于投身于道德生活——这种道德生活被定义为崇拜神,而三个伟大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会声称耶路撒冷代表了宗教的价值。
大致在雅典城邦国家达到鼎盛的同时代,被称做“China”的国家分裂为若干敌对邦国,为了政治霸权而相互竞争。七个最重要的政权的国都是有城墙的城市,这些城市使中国此前的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都拥有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口。这些城市为了对民人进行登记、征税和征兵的目的以官僚化的形式组织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形成了一种军事和政治风尚。例如,周朝国都洛阳就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带着不同的强国安民的理念在不同的国家间游历,而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正是从战国时代之城市理念的激荡中产生的。所有理论家都分享的理想是一个没有领土疆界的大一统的世界(这与早期希腊思想家主张小邦之优点相反),但他们在如何达到这一理想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形态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孔子和孟子这样的思想家试图说服统治者依照德性来统治,而以法家为名的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们宣扬通过严刑酷法来统治。法家在秦始皇治下取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是接下来的汉代却逐步地采用了儒家的原则。接下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略微夸张一点儿说,可以被描述为法家和儒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现代世界,城市代表不同政治价值这一思想是否讲得通呢?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古代中国有城墙的城市相比,今天的城市是规模巨大的、多变的、多元的,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价值,是否显得古怪。但是仅仅考虑一下耶路撒冷和北京,还有比这两个城市之间差别更大的城市吗?这两个城市都以围绕一个核心建造的同心圆的方式构成,但是一个核心代表的是精神价值而另一个代表的则是政治权力(更不用说,北京在人口上是耶路撒冷的六倍)。显然,一些城市确实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并且赋予它们以优先性。我们可以将这些价值称为城市的“风尚”(ethos)或者“精神”(spirit)。风尚的定义是人民或者社区具有的独特精神以及情感的流行基调(《牛津英语词典》),在此我们把这个定义应用于城市。确切地说,我们把城市的风尚定义为居住于某城市的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价值和观点①。
城市以各种方式反映了并且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和观点。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政治纪念碑经常标志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以及向死者致敬的不同方式。都市的蔓延式的扩展和交通的广度反映了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不同程度的僭越,反映了不同的人口控制情况,以及国家计划对自由市场的僭越。妇女是否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说明了一些事情,同时也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邻里关系的恶化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并影响着人们如何思考社会正义。社区和街区的构成既可以削弱也可以提高民主和公共参与。贫民区负面地反映了种族关系的状况。剧院、体育馆、咖啡馆和餐馆区与生活方式、享乐主义以及反对大众文化的社会精英等问题相关。为步行而建的城市相对于为汽车而建的城市鼓励并提高了关于可持续性的不同价值。写有不止一种语言的街道标志,表露了对多元文化和少数派权利的不同看法。医院的有无说明了对身体的关注程度。普通市民相互打交道的方式以及他们与外来者打交道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出租车司机谈话的主题甚至(尤其?)说明了一个城市的占主导地位的风尚。不论我们听到的是“全球化”还是“均质化”(homogenization),在这些方面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都是巨大的。
现在,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城市规划、楼房和建筑对城市风尚和其居民反思生活的方式的塑造是有限的,但是确实存在像“耶路撒冷综合征”(Jerusalem syndrome)这种明显的案例,旅游观光者们看到城市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时,被深深打动以至于他们相信他们变成了耶稣自身。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建筑经常有矮化个体的效果,从而使国家更容易让人民相信他们应该屈从于国家及其“伟大领袖”。也许,更积极地说,引起敬畏感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会强化对更崇高的存在者的信仰(拿破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座教堂让无神论者感觉很不自在。”)。泰姬陵(Taj Mahal)很容易感染人的情绪,它也许是世界上对爱的力量的最美的证明。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在毕尔巴鄂建造的恢弘壮观的纪念馆几乎一手将这个西班牙城市从一个衰落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旅游胜地。尽管独特建筑塑造价值观念的作用并非总是有效的——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建在科伦坡(Columbo)市郊的议会岛结合了僧伽罗(Sinhalese)、佛教和西方特征,并试图传达出理想的文化多元和包容的斯里兰卡之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风尚的更广泛的语境中,人们是能被他们的城市环境塑造的。
城市负载的风尚也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评价。思考一下我们经常是怎样比较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经常说“我喜欢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等等”,或者“我讨厌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等等”,城市几乎就是具有鲜明性格的人。一般说来,对一个城市的可欲求性(desirability)的评价不只是一个美学判断;而且也是对该城市居民之道德生活方式的判断。对城市的判断往往比对国家的判断更强烈,国家是更抽象的、想象的存在物。例如,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说“我喜欢(加拿大、中国、丹麦,等等)”以及“我讨厌(法国、韩国、埃塞俄比亚,等等)”,这是很奇怪的,在此类情况下我们预期的是情感上有细微差别的判断。但是,对城市的判断似乎不是这样一概而论的,也不会是道德上成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此种判断的原因总是值得的,而通过反观我们也许会非常同意这些判断。城市也更容易引起外来人的热爱和认同。一个外国人更倾向于说“我喜欢阿姆斯特丹”而不是“我喜欢荷兰”,而对本地人来说,这种认同比对其国家的认同更易于接受。
然而,几乎没有人对这种基于城市的判断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在政治理论中,人们争论的是,究竟是世界还是单个国家应该成为标准的理论创建之场所。但是,为什么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不可以在政治进程中努力培养并提升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在政治实践中,城市往往是集体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的场所,但是当代的思想家们没能以如下方式创建理论,也即:就城市自尊(urban pride)的优缺点提供有根据的判断之方式。事实上,想用一个词描绘城市自尊的理念是很难的,这种理念也就是一个城市的居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努力提升其特定的认同感。爱国主义如今指的是民族自豪感,但是作为(耶路撒冷、北京、蒙特利尔,等等)社区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又当如何呢?我们用“市民主义”(civicism)这个词来命名城市自尊的情感①。
一、世界主义的社群主义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在阿夫纳(Avner)那里,这种观念来自于他论述环境理论的著作。他开始质疑环境就是“荒野”的假设——城市当然也是环境的部分,因此他成为着手研究城市的环境理论家之一。既然他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让环境和你讲话、启发你来从事环境理论,他便写了一篇关于纽约的论文,把它处理成和闲逛者“谈话”的环境,通过纪念碑、楼房、城市坐标图以及和居民们出乎意料的交谈来展示自身。基本的观念是在确定探究的问题和理论之前,积累尽可能多的信息。在贝淡宁这里,他与阿夫纳谈论城市时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然他从比较文明(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降到比较国家(美国和中国),为什么不进一步降到比较城市呢?在由于他们试图“简化” 多变的分析单元而使这种比较变得成问题的程度上,也许通过进一步的“下降”他们的问题会少一些,如果分析的单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体、“真实”的话。此外,贝淡宁在若干不同的城市里长期生活过,他对这些城市所表达和代表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差异有着深刻印象。为什么不按照阿夫纳的模式基于鲜活的经验和情感来进行理论创建呢?
作为政治理论,我们试图描述并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但我们也试图思考对规范问题——如什么是政治生活的合法形式——的意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用我们的著作抵抗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单元将失去抵制全球化之政治、经济意志的担忧。也许国家正在日益一致化,但可以说,城市或许能够幸免。国家往往不得不遵守国际条约和规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欧盟(EU)或者仅仅是自由市场的支配,它们倾向于减少这些国家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主义(globalism)具有将文化趋同,将文化多样性转变成单一的消费文化的效果,其后果是同一感以及文化理念和选择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减弱。那些认为国家应该在好的生活之各种观念之间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由于没有为国家培养、支持受到全球化威胁的特殊生活形式留下空间,因而无意间加重了文化的平面化。
但是,很多人确实想要体验独特性,以保持和培育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和风俗,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是其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共有的生活方式将大为恶化。因此,我们想建议,城市成为一种人们可以通过它来抵制全球化及其对文化的敉平作用之机制。许多城市进行了思想、时间和财力上的投资,通过设计和建筑政策,通过人们使用城市、与之互动的方式,来保护它们独特的风尚。当然,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么做了,有些城市轻易地屈服于全球化的要求。但是,城市能够并且应该提升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理念并没有引起争论,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自由主义的中立性辩护者们也倾向于允许城市层面的独特性的公开表达。并且,以下这一点绝非偶然:具有一种风尚的城市往往具有国际声誉,并且容易吸引那些被这种风尚引来的参观者和定居者。
简言之,一种风尚增加了使人的社会生活变得有价值、有趣味的多样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审美愉悦——不同种类的城市创造了一幅更加美丽的人类图画。另一方面,它是支持多样性的一种道德论据——不同种类的城市增加了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能形式。有些时候,城市可以完成在国家层面难以达到的道德上可欲求的目标。在印度,新德里已经改装了所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以紧缩天然气的消耗。在美国,旧金山正在修改建筑法要求新建筑必须装有电瓶车充电的线路,而这个政策在全国推广是不可想象的。城市还可以实现其他目标。中国的城市重庆正在试验财产权的替代形式以提升经济发展的相对利他主义模式。加之,如果城市之间具有某种相似的风尚,例如致力于保护传统建筑的城市之间共有的理念和专家意见,那么它们可以以自上临下(或者自下迎上)的姿态与国家领导者对话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同时,创造性的思想家们提出依托城市的理念以处理问题,例如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议的“宪章-城市”(charter-cities),将城市规模的行政管区交由若干国家的同盟治理——它可以帮助这些城市摆脱贫困陷阱(poverty traps)。国家不能,但城市却往往能够对抗“绝对律令”(imperative)以在全球化时代保持竞争力。
当然,全球化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它通常是资本、人力和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对外来人和“他者”的开放态度的同义词。谁会反对信息的自由流动,与相距遥远的人们越来越熟稔,全球团结的感觉,以及全球化能够提供给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们以各种经济机会呢?因此,我们聚焦于那些其风尚不反对开放和全球团结的城市。如果某城市的风尚建立于仇外情绪、种族主义或者仇恨之上的话,我们对其不感兴趣。柏林在其不容忍的时期信奉世界上最可恶的政权,因此我们不打算涉及此种风尚。但是,一旦城市(以及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迈过了最小化人权的门槛——人的基本的物质必需品(食物、水、住所)有所保障,不受折磨、杀害、奴役或者系统地歧视,那么对其流行风尚的尊敬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初步的依据。
以下这个谚语最好地表达了尊重一个城市之风尚的情况:“入乡随俗”(when in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