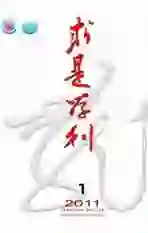建议学术期刊加强对现实世界的研究
2011-01-01朱寰
求是学刊 2011年1期
《求是学刊》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06年7月进入教育部第二批8家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并获得政府奖励;《求是学刊》执行主编李小娟同志于2008年2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殊荣。对学刊学人所取得的优异成就,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向学刊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把学刊办得更好,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作出更大的贡献。
《求是学刊》办刊宗旨和理念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循,毋庸赘言。不过新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最初10年,中国已开始崛起,特别是2007—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世界金融海啸,在全世界凸显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分量。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尽管也受到某些影响,但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以9.1个百分点继续快速、稳定增长。从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世人刮目相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和政府面临着世界许多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期刊,能在中外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消除过去形成的偏见和误解,使世界人民友好相处,和谐共存,则实为幸事。因此,我建议《求是学刊》适应中国当前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在既定方针的范围内尽可能强化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应该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世界社会历史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今后要走向何方?这是当代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我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事实根据。
第一,我国人民渴望了解世界,了解“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利弊。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化”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到底什么是“全球化”,许多人都说不太清楚。有位青年朋友问我:世界“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它是从哪里来的?“化”到那里去?它对中国是利是弊?许多人对这些问题都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因而颇有求知的渴望。但在今天看来,“全球化”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而且也是个现实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关键在于社会分工的加强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分工越细,越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带动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史观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历史,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使世界上各大洲、各地区、各海岛、各国家居住的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类,彻底消除了以往各自社会发展的孤立、分散和闭塞的状态,通过经常性的密切经济联系,把它们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才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
自15—16世纪“海路大通”以后,世界各部分逐渐连接起来。旧大陆的人们新到达的中南非洲、南北美洲、澳洲以及为数众多的各大洋的岛屿,都与亚欧北非“旧大陆”连成一个整体。这是世界“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只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西欧大陆的法、荷等国工业革命也紧紧跟上,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空前强大的生产力,通过生产和贸易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化”。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又过去了二百多年,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核能时代和信息时代等,现今世界“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当年,自不待言。2008年的金融海啸,世界上的大小国家谁都不能幸免,这就是从反面证明今天的“全球化”。
至于这种“全球化”对我国是利是弊?我认为既有利,也有弊,总的说来,利大于弊。首先,“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为世界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力大为提高,社会财富普遍增加。这自然是社会发展显著进步的一种表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三十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两位数快速稳定地增长。这当然是我国13亿人民艰苦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但也是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分不开的。其次,现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化”。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欧盟)操控世界市场,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极力在世界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所谓新自由主义,一个原则是“大市场小政府”,一切通过市场,市场主宰一切,实现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府不得干涉;另一个原则是经济私有化,产权明晰到国际垄断资本家的名下。这样一来,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垄断资本家获得了绝对的自由权利,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政府监督。结果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造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来,2008年华尔街又制造了世界上的金融海啸。这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最后,我国虽然加入了WTO,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和平相处,但是中国按照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走自己发展道路,既保持国家稳定,又根据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虽然我国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影响不大。
另外,我们还不能忘记,我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将来要走向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现代化的大生产才能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页)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资本的文明面”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各种因素的创造。同时他还指出,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将会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垄断社会发展利益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工业文明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巧妙地利用国内国际“资本的文明面”,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协调发展社会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以便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各种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可见,不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尽快地发展自己,关起门来搞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二,外国人在潜心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仅仅改革开放30年就在世界上和平崛起,这与邓小平当年的预见不差分毫。中国的崛起震动了全世界,吸引了世界上各种人的目光。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研究“中国之路”的四本书。该媒体称,很多人想知道世界如何适应复兴的中国。这篇文章的作者戴维·皮林说,如果世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对中国崛起着迷,那么在经济混乱如暴风骤雨般袭击整个西方世界后,对中国的迷恋只会更加强烈。其中第一本书是《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事》,作者是美国学者杰弗里·瓦萨斯特罗姆。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中国问题,但中国还不是他研究的中心课题。他说,中国已强力将自己推到了我们的意识中。如果我们想了解世界,那就努力了解中国吧。皮林报道说,这四本书的共同目的是,如实描述中国,避免对中国的陈词滥调。第二本书是理查德·鲍瑞嘉著《中国观察者》,这是一名美国学者对中国半个世纪的观察。鲍瑞嘉描写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他早期研究中国并不能进入中国,只好根据翻译书籍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坦言“有时发现自己对毛泽东革命的研究毫无意义”,“而如今的中国观察者却拥有大量‘精密研究武器’”,比如经常出入中国进行实地研究以及通过电子科技与数千中国当地媒体和记者联系。第三本书是《社会火山的神话》,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他研究中国的结果发现,中国人对于个人财富积累的容忍度几乎和美国人一样。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奋斗和教育。这与冷战时代结束后的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新富阶层崛起抱有更多的负面看法。第四本书是《中国战略:驾驭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作者是美国咨询公司博斯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谢祖墀。主题是成功的跨国公司必须把中国视为全球经营战略整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一个令人垂涎的市场。最后,作为消息报道的戴维·皮林说,很明显,中国已把20世纪60年代那个封闭、偏执的中国社会远远地抛在后面,而现在中国事实上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人们去认识(《环球时报》2010年7月5日)。
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6月15日在刊载海因茨·迪特里希的文章中正确指出,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看来西方人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有了新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参考消息》2010年6月17日)。
第三,对“全球化”现实世界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
研究“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研究世界的现状和历史。任何事物的现状转瞬即逝,今天的现状,明天就成为历史。而世界历史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解放前中国大学里的历史学课程,只有地区史、国别史,根本没有世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逐步建立起世界历史学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过程,我深深体会到,建立一门新学科之不易。1948年8月,我入东北解放区东北大学(今天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学习,当时校址在吉林市。学校根据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从1948年秋季实现正规化。学校成立了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各院下设若干系。我选的是历史系。我们系从1948年8月先后开设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课程,由杨公骥教授和郭守田教授讲授。1949年7月校址迁到长春后,我开始跟郭守田教授学习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古史。这是新中国大学里最早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世界历史学科,除在有关大学里普遍开设世界历史课外,国家又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项是1955—1957年邀请前苏联三位世界历史学专家来中国讲学。我国为世界古代史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亚洲史专家科切托夫在东北师范大学办两个讲习班,全国有关大学选派青年教师来学习。另一位世界近代史专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第二项举措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建设世界历史学专门研究机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宣传部决定总结十年来教学和研究工作经验和成果,重新编写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高校教材,其中包括《世界通史》在内。这就是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第一部世界通史高校教材。我国的世界历史学只不过有60多年的学术积累,与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国历史学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不揣冒昧,建议《求是学刊》尽可能强化对现实世界社会历史的研究,以促进我国世界史专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