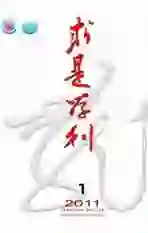我看《求是学刊》
2011-01-01张锡勤
求是学刊 2011年1期
近日,《求是学刊》要为庆祝发刊200期出个专号,执行主编李小娟编审邀我写点感言。我痛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而且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说:“那我就写一篇《我与〈求是学刊〉》吧。”待动笔后觉察到,如果专写此题是会使我的感言受到限制的,因为对于《求是学刊》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于是改为今题。
我第一次向《求是学刊》投稿并被采用是在1980年。我与她的文字缘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在《求是学刊》共发表了18篇论文,数量不可谓不多,称得上是老作者了。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两年,《求是学刊》一年中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可见她对我的厚爱。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渐为学界所知,是几家刊物为我提供了平台,给予我机会,而《求是学刊》便是其中的一家。比如,我第一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便发表于《求是学刊》1983年的第5期。我想,一个人在成长的关键期,是需要他人、他力的关爱、认可、提携、伸以援手的。就学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则需要必要的学术平台。《求是学刊》正是我这三十年不断有所进步的学术平台之一。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学术生命的复苏(甚至是起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亦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国内的学术刊物比今天要少得多。所以,这一可贵的学术平台对我们的成长发展,意义堪称重大。每当我翻拾旧作,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对《求是学刊》是时时心怀感激的。黑龙江大学文科的诸多教师,大概与我会有同感。我想,黑龙江大学文科一批教师的成长,也是靠了这一学术平台。就此而言,《求是学刊》对黑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
如实说,《求是学刊》刚刚问世的时候,她在国内学术园地中不算十分出色(这很自然)。但到今天,她已是国内高校学报中的名刊,“文化哲学研究”系列专栏则是名栏。所以能有这样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她始终自觉坚持求是、求真、求新的办刊宗旨。无疑,求是、求真是学术的真精神,学术研究就是为了求是、求真。为此,则必须不断求新。只有不断求新,才能跳出窠臼,以新的视界、视角,新的方法、路径,得出更接近于是、真的新认识、新结论。显然,求是、求真是通过不断求新得以实现的。《求是学刊》刊名中的“求是”准确抓住了学术的真精神,给自己规定了正确的奋斗目标。作为《求是学刊》的一名老作者、老读者,我以为,在这三十多年中,她一直秉承这一宗旨,而且越来越显自觉。为此,多年来《求是学刊》团结、拢聚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不断发现、联系学界的新生力量。依据学术发展的态势,敏锐捕捉热点话题,不断调整、更新栏目,适时开辟引人注目的新栏目,个性越来越鲜明。在形式上也日趋新颖,诸如访谈、笔谈和特约主持人对一组专题文章的点评,等等,都对读者具有吸引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求是学刊》求是、求真、求新的宗旨是通过力戒平庸、不甘平庸的求精精神落实的。《求是学刊》在走出童年时代,步入稳健发展的阶段后,几任主编和编辑部成员都是力戒平庸、不甘平庸的。首先,她精于策划。回顾这十多年来她陆续开辟的新栏目,大都站在学术前沿,主动参与当前的学术争论,使读者能时时从中见到新见,便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读者所以愿读《求是学刊》,原因就在于能从中看到一些新东西。其次,多年来《求是学刊》审稿、用稿是严格的。一些稿件采用与否都经过一再斟酌,征求同行专家意见(我本人曾多次参与这类工作),往往是不顾人情的。因此,总体而言,《求是学刊》所发表的文章质量是比较不错的。再有,《求是学刊》的编辑工作十分细心,每期清样都经反复校对,因此刊物里的错字、硬伤相比而言也是少的。
《求是学刊》从一所省属大学的学报成为国内知名学术期刊,一路走来实属不易。我清楚记得,由于早先黑龙江大学办公室条件较差,《求是学刊》编辑部办公室相当简陋,且不得不一再搬迁。在20世纪80—90年代,编辑部曾一度在校内一幢家属宿舍的一户单元房内办公,其艰难可想而知。此情此景老一点的作者都会记得。应该说,《求是学刊》能发展到今天,靠的是几任主编、几批编辑部成员的敬业精神和不甘平庸的向上之心。
《求是学刊》已过而立之年,即将步入“四十不惑”的境界。作为一名与她结文字缘三十年的老作者、老读者,我衷心希望《求是学刊》进一步发扬求是、求真、求新的精神,更清醒地给自己正确定位,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在求是、求真、求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