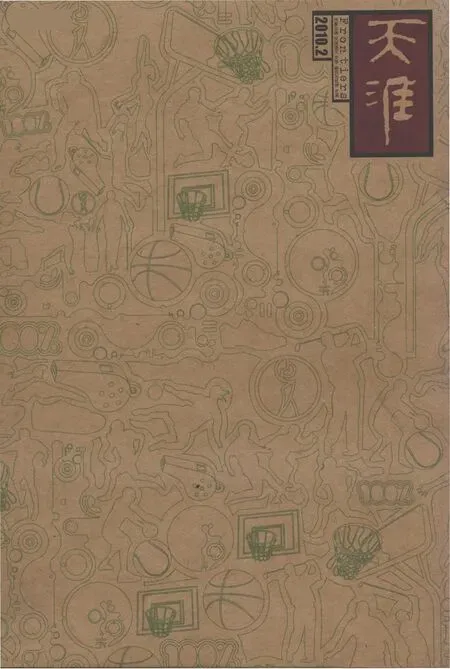洋气
2010-12-27韩琛
韩琛
洋气
韩琛
城里人造反完了又忙着下乡。
大庄跑来三个知青,两女一男。两个女的,一个叫祝云芬,一个叫李素琴。那个男的叫陈宝华。只一个男的,大庄人认为他不错。两个女的却费人的脑筋,不过也不算是什么难事。祝云芬长得白,可不如李素琴俊俏;李素琴俊俏,又不如祝云芬长得白。于是管白的叫白祝云芬,管俏的叫俏李素琴,再也混不了了。日子长了,跟三个知青闹熟,大庄人问他们:“城里多好,还吃供应粮,你们下乡做什么?”
李素琴说:“毛主席说了,农村有广阔的天地,我们下乡大有可为。”
就是下地干活呗,还能干什么?
陈宝华说:“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只有祝云芬不说话。大庄人问祝云芬:“你呢,祝云芬?”
祝云芬脸红了:“我不知道。”
大庄人哈哈笑,陈宝华和李素琴也跟着笑。祝云芬脸更红了,祝云芬的白脸一红起来,是让人很心疼的。
三个知青刚来那会儿,看什么都新鲜。看见鸡新鲜,看见猪新鲜,等到看见公驴、公马夹了硕大的卵子摇来晃去,就新鲜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干不几日农活,三个人再也新鲜不起来,只忙着招呼手脚的泡了。见天早上,支书要在知青点门前喊几遍,三个人才朦胧了眼出来,连脸都赶不及洗。大庄人说:“要抻筋拔骨!筋抻开,骨头拔开,浑身利索了,就大有可为了。”
知青点有三间房,东西两间有炕,中间是灶房,灶房里有两座锅台。祝云芬和李素琴住东间,陈宝华住西间,饭是三人轮着做,一桌吃。大庄人背地里笑:孤男寡女,住得个好住!
话传到支书耳里,支书说:“人家是啥?知识青年!不是你们,除了吃饭操×,还知道嘛?要不,怎么人家是知识青年,你不是?”
先说说陈宝华。陈宝华长得瘦小,扒了衣服,肋条骨子像搓板。支书跟陈宝华说:“你怎么长的,把粮食都吃进粪坑了?”陈宝华真瘦,大庄人一见他就笑,笑他的瘦和小。昨晚上刮大风了,大庄人碰见陈宝华就问:“咦,你咋回来了?你不是让风刮跑了吗?”说完,笑得前仰后合,陈宝华也一起笑。一边笑,一边拍人家肩膀。瘦嘛,小嘛,陈宝华就心安理得干活少,比两个女知青还慢还少。大庄人不埋怨,指着陈宝华笑弯腰:“你看看陈宝华,瘦得连活都干不动了——”
三个知青来大庄不到一年,就分出高下。李素琴数第一。李素琴真有个扎根的样子,来两天,穿的戴的,就跟大庄的姑娘、媳妇分不出了。还有那张脸,本来就黑,风吹日晒的,黑的跟大庄人差不多了。成分还好,三代工人,根红苗正,工人农民一家亲,李素琴来大庄就是回家。大庄的老头老太,哪个不把李素琴当了自己闺女?陈宝华数第二,陈宝华干活不行,陈宝华吊鬼耍滑,可陈宝华有意思,让大庄人得了快活,大庄人想笑了,就去看陈宝华,看着,看着,就笑个不停。这样的趣人,不排第一,也不能排最后,那就排中间吧。只三个知青,李素琴和陈宝华排了第一、第二,不消说,第三就是祝云芬了。真要说起来,祝云芬干活不比别人差,可大庄人对祝云芬有看法:祝云芬都来大庄两年了,怎么看,还是不像大庄人。人家李素琴和陈宝华就像,像得不行,就是祝云芬不像!
祝云芬到现在见了牛,见了羊,还躲,还掩鼻子,大庄就这么大味儿?还有,祝云芬那张白脸怎么晒也不黑,不但不黑,还更白了。也不是晒不黑,你祝云芬夏天头上也捂纱巾,晒得黑才怪!还有衣裳。夏天,哎呀,穿一件白的确良,透明明薄,槐花花白,沁心心凉。全公社除了革委会主任,就是祝云芬穿的确良了,你祝云芬是主任吗?人家李素琴就没这么娇贵,人家也是城里人,人家就穿布衬衣,还洗黄了,比土还黄。冬天,祝云芬更不得了。都穿棉袄,祝云芬穿出来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祝云芬的棉袄不是直通通罩在身上,而是紧紧梆梆贴在身上。哎呀,小蛮腰,小胯骨,小胸脯子,都显出来了。咦,不就是个棉袄吗,你祝云芬要穿出个花来啊?再说说纱巾,大庄哪个女人没个纱巾?纱巾要大红大绿才喜气啊,别人都是红的绿的,你祝云芬的纱巾为什么要月白的?还有,你祝云芬的棉袄为什么是蓝底白花的?你祝云芬的裤子为什么是蓝的卡的?你祝云芬为什么雨天下地要穿雨靴?更让大庄人可怪的是,祝云芬明明长得一般,为什么就那么耐琢磨?祝云芬鼻子是塌的,祝云芬的眼皮是单的,祝云芬的嘴巴太大,祝云芬的额头太高,祝云芬的脸皮太薄。可是祝云芬白啊,一白遮百丑,祝云芬的塌鼻子、单眼皮、大嘴巴、高额头、薄脸皮一白生,就说不出地耐看了。李素琴倒俊俏,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可就是不如祝云芬耐看,真是没办法。大庄人想来想去,觉得只一个字眼能用在祝云芬身上——洋气!
大庄人一想起祝云芬来,那是有一肚子话要讲的。娇气、穿戴的事不要说,你祝云芬都是插队大庄的知青了,你为什么动不动还想家?大庄养不下你这么只花里胡哨的母鸟吗?你想家,你掉眼泪也罢了,你就不能说让土迷了眼?祝云芬就不。大庄人看见祝云芬掉眼泪了,就问她:“祝云芬,是不是让沙迷了眼了?”
祝云芬掉着眼泪说:“不是,我想家了。”
娇什么娇?你祝云芬的成分不就是个小业主吗?看看人家李素琴,大嫂大婶的荤话也能讲了,叮叮当当来两句,跟谁也不落下风。你祝云芬听了还脸红,你脸红什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就算祝云芬排了第三,大庄人也没冷眼看她的意思,就是有点别着劲,心上是很复杂的,一句两句话说不明白。不过,有个人倒没这么含糊,分外地看重祝云芬,以为祝云芬是画上才有的人。这个人是杨炕生。
杨炕生兄弟三个,行二,老大叫地生,小的叫院生。地生十八娶亲,娃都大了,院生还上学,操心不着。杨炕生呢,眼看年纪过了二十,爹娘着急了,张罗着给他说亲。陆陆续续看过几个,都不中意。
他爹问他娘:“你说不就是找个媳妇嘛,他想要个天仙?”
他娘说:“我咋知道?”
不着急也难怪,杨炕生长得漂亮啊,漂亮得公社里都有名。公社排《红灯记》,找了几个李玉和,都不中意。有人说:“去找杨炕生吧,那是个杨六郎!”叫来一看,——长得好!上了妆,在台子上站一站,下面都说:“是个真李玉和。”
长得好也不算什么,难得的是杨炕生脾性还好,不吵不闹,不低眼看人,不讨人嫌,对谁都热心,很对姑娘们心思。大庄的姑娘晚上做梦,头一个梦见的就是杨炕生。
第二个?第二个就不知道是谁了。
大庄姑娘找对象是比着杨炕生找的,媒婆上门了,问姑娘:“要找个什么样的?俊的?壮的?家境殷实的?”姑娘想想说:“杨炕生那样的吧。”媒婆扑通跳下炕:“这个我找不了,杨六郎不就一个嘛。”姑娘说:“比杨炕生稍差一点也行。”
这一点是算不出有多少的,于是姑娘变成媳妇。做了人家媳妇的姑娘夜里梦见的还是杨炕生吗?没人说梦见过,也没人说没梦见过。
不找对象不是眼眶高,瞧不上别人,杨炕生可从来没这样的心思。要怪只怪祝云芬。祝云芬这个知青真是个别,模样脾性跟谁都不一样,满公社也找不出第二个。脸面面跟羊奶子一样白,别人说白是欠晒,杨炕生可不这么想,人家祝云芬不也是天天下地,风吹日头晒的?那是天生白,长个疖子好了,连个疤点也不留。杨炕生想起那张白脸就奇怪:“一个人怎么可以长的这么白呢?”杨炕生还喜欢祝云芬的洋气,那个小袄穿的!那个纱巾围的!除了祝云芬,满公社还有谁弄得出?祝云芬想家的时候也让人爱,让人光想搂她在怀里,让她痛痛快快哭个够!就算这样,杨炕生也没打算找人说合。一来觉得祝云芬到底是个知青,城里人,乡下这一套是不兴的;二来觉得不知道祝云芬的意思,一下子说崩,不好回头了。
打定主意,杨炕生就时时瞅着祝云芬。祝云芬下地了,祝云芬收工了,祝云芬换新袜子了,祝云芬的发卡换了一个了,祝云芬的手腕上套了一个皮筋了……杨炕生眼角藏了祝云芬一切动静。等些日子,大庄要办青年突击队,促进农业生产。队长定了杨炕生。杨炕生跟支书说:“三个知青我也要了。”
“指望那三个货?拖你后腿,还突击个屁!”
“我这是帮助后进。”
现在好了,杨炕生可以大模大样和祝云芬并肩生产了。刨粪,祝云芬碰上硬骨头,啃不下来了,杨炕生就走过去,一本正经地说:“刨不开?让让,我来两下。”一下,两下,开了。杨炕生跟祝云芬说:“要使巧劲。”杨炕生不像只跟祝云芬说,旁眼看上去,像是跟所有人说的。割麦,一人六垄,杨炕生跟祝云芬并肩割,替她多割两垄,还让副队长替李素琴割两垄。这样就平了,谁能说什么?推土,杨炕生和祝云芬一组,祝云芬只管扶住车把就成了,杨炕生拖了车和她一起跑,哪里要出什么力气?
进了突击队,祝云芬就是躺进安乐乡。李素琴和陈宝华就不成,天天累得牙根都咬松了。祝云芬奇怪,自己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祝云芬没怎么想就知道了,自己是沾了杨炕生的光,杨炕生时时顾着自己,面上看不出来,省得力气自己还能不知道?祝云芬一琢磨,就琢磨出杨炕生的心思,他是在打自己的主意。祝云芬是个城里姑娘,开窍早,人又乖巧耐看,上中学的时候,就有男生爱凑前照应。杨炕生这点心思,祝云芬拿眼一照,透心亮。想到这,祝云芬觉得杨炕生有点异想天开了,自己怎么能看上他?想归想,杨炕生给的好处,祝云芬还是乐得享受,自己又没提什么,他乐意帮忙,这个谁也管不了。
姑娘媳妇们在一起的时候,少不了要提杨炕生,说他怎么漂亮,怎么壮实,怎么可人心。祝云芬只听,不说。漂亮小伙子,祝云芬不知道看过多少,哪能像李素琴似的少见多怪。祝云芬也做梦的,祝云芬的梦里可从来不会有杨炕生。祝云芬梦里的男人都斯斯文文,白白净净。坐着的时候,手叠着扣在身前;站着的时候,手背在身后;最好还要戴副眼镜。不过,杨炕生到底还是照顾了祝云芬,祝云芬惬意的时候,也留心多看了杨炕生两眼,看仔细了,才知道原来真是个杨六郎。只是戏上的杨六郎是个白脸,杨炕生实在有点黑,是个黑脸的杨六郎。模样比不上城里人洋派,不过在这里,也是个出众的。祝云芬还看出来,杨炕生在穿衣做派上也用心。他常爱穿件红绒衣,这是很时髦的,县城里也不多见,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的。绒衣上还有几个白字:为人民服务。挺扎眼。穿上这件绒衣,杨炕生在庄稼地里干活的时候,就像一团火,滚来滚去。听说杨炕生还打得一手好篮球,公社主力,投篮准,跑得快。祝云芬没有见过。不过看他干活的灵巧劲,想来错不了。杨炕生扮的李玉和,祝云芬是真的看过,模样还好,只是有点呆,大概李玉和本来就是呆的。祝云芬有时候也想,自己要是个乡下姑娘,跟了杨炕生倒是真不错。可惜自己不是。
祝云芬得了杨炕生的照顾,生活变得滋润起来。李素琴看见祝云芬下了工,脸不红,心不跳,就问她:“祝云芬,你怎么这么轻省,跟没干活一样。”
祝云芬笑着说:“筋抻开了,所以就轻省。”
杨炕生有事没事地爱跟祝云芬说说话,人前的时候,说工作,人后的时候,杨炕生瞅了空子就问别的:
“祝云芬,你累不累?”
“祝云芬,晚上公社放电影,你看不看?”
“祝云芬,你们的烟囱该打了吧,要不要我找几个人?”
“祝云芬,你挑水的时候少挑点,半桶就行,别闪着自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祝云芬,我昨天听见你唱歌了,你唱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是不是你?是?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祝云芬,你怎么不去赶集?集上有卖布的,不是红的,不是绿的,是素的。你不去?你怎么不去?你去吧?”
……
杨炕生说,祝云芬就听。听了,要么点头,要么摇头。祝云芬很少说话,祝云芬觉得自己一开口,杨炕生不知道要想到哪里去,想远了,就回不来了。
日子不咸不淡,抬抬手,没了。杨炕生和祝云芬的事也不咸不淡的,拾起又放下。杨炕生看不出着急,祝云芬也乐得滋润,别的事,她懒得想。知青点的日子也是一天天随便打发掉,每天上工、下工、吃饭、睡觉,来的时候这样,过几年还是这样,于是也不会想明天,明天也不外乎这样。祝云芬和李素琴常半宿、半宿地聊天,解了寂寞,打发了时日。然而又有什么可聊的?愿意说的,都说了几遍,不愿意说的,再亲热也说不出来。那些挠痒痒的话说烂了,连痒痒也没有了,聊天也就省了。陈宝华平常时候也是不见声息,吃了饭就回自己屋,参禅还是打坐,别人就不知道了。知青点里一日日静下去,倒像没有住人一样。
春天,桃花烂漫的时节,夜里会有野猫在屋顶上蹿叫,踩得屋瓦不停响;秋日,草色枯黄的时候,银白的月亮就停在树枝后面,照得蟋蟀冷清地叫。实在冷清不过,就回家探亲。家里自然是好,却也是坐着、睡着。父母殷勤,却仿佛招待远客,生不出太多亲近。街上人来人往,乡音辄起辄落,身在其中,依然是冷清,才想起,原来自己早不是这个城里的人。不等假期到,就匆匆赶回大庄,东西也不曾捎多少。
太冷清了,就生炉子取暖。不知怎么的,李素琴跟陈宝华说到一块去了,两个人凑到一起就吱吱地说,说完了还吱吱地笑,让人听不到说什么、笑什么。剩了祝云芬一个人就愈发冷清。下大雨了,祝云芬坐到窗前,看到豆大的雨点从天上掉下来,啪啪啦啦砸在地上、瓦上。远处的屋顶、树头一层烟。雨水流下房檐,变成一道珠帘子。珠帘子落到檐下的水缸里,水缸一会儿就满了。水溢出来,在泥地上冲出一道道沟。看着看着,祝云芬迷迷糊糊睡了,梦里还是下雨。
李素琴和陈宝华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天天笑得合不拢嘴。三个人再在一个锅里吃饭就别扭了,李素琴和陈宝华亲亲热热地互相夹菜,祝云芬看见难受,捧碗回了屋。三人就分了灶,祝云芬的口粮自己存着,自己开伙。分灶就是分家,祝云芬和李素琴就算还睡在一铺炕上,也没什么话好讲了,便讲两句,也客客气气,透着远。李素琴的快乐是不消说的,脸上写着呢。祝云芬想,李素琴长得也不错,怎么会看上陈宝华呢?陈宝华算个男人?
有时候,祝云芬半夜醒了,李素琴却不在炕上,莫名其妙的声音从天上传过来,一阵雷一阵闪的,雷电交加的紧处,大雨如注。祝云芬觉得自己也被淋湿了,一夜便不能睡好,就是睡着了,也被稀奇古怪的梦缠着。
过些时日,李素琴索性搬到陈宝华屋里。夜里的雨下得更频,雷和闪划满天空。祝云芬常常要醒,静心听一听,好像也没有下雨,心里糊涂起来,难道真是自己做梦?
就这样,一天天下去,李素琴胖了,陈宝华胖了,祝云芬瘦了。
日子过久了,祝云芬渐渐对杨炕生放了松。杨炕生嘘寒问暖的时候,祝云芬也会答应几句。不过几句,祝云芬就看出了杨炕生的快乐。祝云芬心里感慨,觉得杨炕生也不容易,来来回回眷顾自己几年,好处是没有一点的,也不见他有什么怨气,倒像没事一样。这样想了,祝云芬就多给了杨炕生几个正脸,几次笑。一时让杨炕生说话也颠三倒四了。祝云芬又笑他痴。祝云芬有时想想自己,觉得自己也是过分,就是不打算跟杨炕生好,人家这样对自己,也不该一点不领情,可是又不知道该怎样领这个情。
杨炕生得了祝云芬几次笑脸,觉得是个好兆头,想把关系再拉近一点,就问祝云芬借书,祝云芬真的还有几本书。书借了要还,还了还要再借。
杨炕生隔三岔五来一次,李素琴开始有点不自在。后来常了,看见杨炕生的心思只在祝云芬那里,就躲在陈宝华屋里不出来。杨炕生坐下就难走,说些话,有一搭无一搭的。或者什么也不说,只坐着。杨炕生人前的时候是很会说话的,单独跟祝云芬在一起,好像又没什么话要讲了。杨炕生有心把话挑开,不过看祝云芬还是半生不熟的模样,觉得还是捂一捂吧。
这一捂,又是半年过去,有限的几本书不知道借了几多来回。半年里,祝云芬夜夜要听电闪雷鸣,听完了,夜夜半梦半醒。天气也坏,阴晴不定。有太阳还好,最怕是下雨天,人的心思也像雨脚,乱成一团麻。不过还好,下雨天杨炕生也会来,听着雨,说些闲话,光阴便打发得快一些。杨炕生走了,祝云芬更耐不得屋里冷清。有时候,杨炕生被什么绊了脚,来得晚了,祝云芬就在灯下掀一本书,哗啦哗啦响个不停。
秋收到了,杨炕生不在大庄,到公社排戏去了,一去二十天,这可苦了祝云芬。这两年有杨炕生帮忙,自己没出过几分力气,身子骨锈住了,没了杨炕生,祝云芬就没了荫凉,一下子就晒到毒日头底下。大庄人说:“收个秋哪,掉层皮哪。”祝云芬二十天下来,何止是皮,连肉也掉了不知道多少。自打杨炕生常来知青点,李素琴也就知道了祝云芬的惬意是怎么来的,紧赶着笑祝云芬:“祝云芬,筋又紧了?”祝云芬听了不答话,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祝云芬只在被窝里掉眼泪,掉着掉着,就埋怨杨炕生惯坏自己。想一阵,怨一阵,狠狠叹口气,累得睡去了。
半夜里依然是醒,雷和闪闹得更凶,要撕破天。雷闪停了,又有无数梦上来,好像每个梦里都是杨六郎、李玉和、杨炕生。醒了,心跳得慌,又是一阵泪,觉得这把是跳不出杨炕生的手心了,要不这梦里梦外的,怎么全是他?
二十天说长就长,说短也短,眨眨眼就到,杨炕生从公社回来了。祝云芬看见杨炕生,心里一阵欢喜一阵委屈,可脸绷着,没个动静。杨炕生好像也没有把祝云芬放在心上,也没一句热乎的话,只忙着和别人说笑。祝云芬看他笑得没心肺,一时没了欢喜,只剩下委屈。
下了工,晚饭不做也不吃,祝云芬爬上炕坐着去了。太阳西沉,屋里渐渐昏下去。祝云芬围着被子,静静坐着,什么不做,什么也不想。余晖渐逝,太阳没到地下,屋里登时昏黑,祝云芬静静不动,好像打算消失在黑暗里。外间,李素琴和陈宝华忙着洗碗筷,锅碗叮叮当当,人声嘻嘻哈哈。隔世一样响在远方。
太阳落下许久,杨炕生过来了。杨炕生被屋里的漆黑吓一跳,停一停,借了月光,看见了祝云芬的两只眼闪在黑暗里。点上灯,杨炕生看清了祝云芬。脸清清静静,几日不见,显瘦,可是更白了。杨炕生坐上炕,问祝云芬:“你挺好?”祝云芬不答话,脸上的委屈却再也挡不住,要哭了。杨炕生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顿时冷清下去,虽然有两个人,却好像没人一般。
静一会儿,祝云芬的眼泪流出来了。流出来,她也不擦,任它们流。杨炕生赶紧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谁委屈你了?你跟我说。”祝云芬就是哭,不答话。哭一阵,祝云芬挪了挪身子,凑过来,靠在杨炕生肩头,泪水就流到杨炕生身上了。杨炕生明白祝云芬的心思,就伸手揽祝云芬的腰,祝云芬的身子整个滑下去,陷进他怀里。
祝云芬的身子真软啊,杨炕生偷偷笑。过一阵子,祝云芬不哭了,杨炕生对祝云芬说:“我这一次到公社排戏,一个老头子总哼哼歌子,我也听熟一个,说给你听好不好?”“不要!”祝云芬说。杨炕生凑在她耳边,压着嗓子唱起来:
想你想你真想你
找个画匠来画你
把你画到眼珠上
看到哪里都有你
祝云芬听了,知道杨炕生是说他的心意,心里一时松得厉害,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噗,一声,灯灭了。
祝云芬眼里闪一下,满是雷和电。
……
杨炕生和祝云芬的婚事轰动大庄。别人结婚的喜糖都是硬块块,杨炕生和祝云芬撒的是奶糖,软软甜。大庄好几个人让这糖粘掉牙,可谁也不说奶糖不好,吃了这样稀奇的东西,掉个牙算什么?别人驮媳妇,用车,用驴,用轿子,杨炕生用自行车。杨炕生借了自行车,从知青点里驮上祝云芬,绕大庄转了三圈才回家。大庄人看得傻眼,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明白之后,啧啧称赞,到底是祝云芬,嫁个人也这么洋气!祝云芬在炕上会洋气到什么样子?大庄人猜也猜不透,这个东西,人家是不让看的。
……
夜半,杨炕生搂着祝云芬,问她:“万一能回城了,你走不走?”
“都落户了,还回什么城?”
“我说万一。”
祝云芬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
杨炕生也不要她答,就说:“你铁了心要走,我就豁了你,挑出你的肝生吃,在我肚子里,你哪里也去不了。”
“要不要蘸酱油?”祝云芬笑。
“蘸!”
“杨炕生,你疯了?”
……
祝云芬嫁过来不到半年,杨家添丁,女孩,七斤二两。
大庄人说:“洋—气!五个月就生出个七斤二两,怎么生的?”
韩琛,学者,现居青岛。曾在本刊发表电影评论《时代的“盲井”与草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