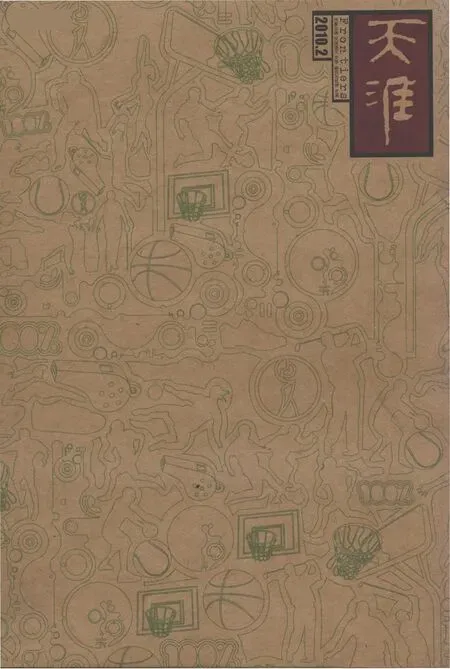巴尔虎草原
2010-12-27萨娜
萨娜
黑马咴咴走进白拉森丘陵的时候,乌奇勒正在缓缓的半山腰乱转悠。
乌奇勒逢遇到一桩难以启齿的,却无法回避的大事。头顶的太阳还像昔日一样温暖地照彻草原,茂盛的绿草还像他熟悉的那样,一个劲儿地舔着他的双腿和肚子。可是他心里长了一块石头,石头上长了一片湿腻肮脏的绿苔。他走累了,两条腿有点哆嗦,像刚睁开眼睛的小狗想趴下,他想坐一会儿,脑袋又像春季的大风,刮得他继续乱走。他终于站下了,低下头看着微微罗圈的双腿自言自语:兄弟,你骑着骏马,像风一样驰骋在茫茫的巴尔虎草原上,你游过九九八十一弯的莫尔格勒河,追逐失散的马群,你走进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显示了男人的力量,现在你老了,想像拔出泥土的树根那样等待死亡吗?
他坐下了,他不得不坐下。从昨天傍晚看见了那一幕,他就想坐下来,让自己脑袋里的狂风变成冬季的雪花,慢一点飘下来吧。
昨天傍晚,乌奇勒赶着羊群往回走。他看见了老婆德玛妮。她不是一个人,她的身后跟着他的朋友,唱起歌儿来连月亮都羞涩的尼木。他是男人,是德玛妮的男人,不用问便知道,刚才他们两个人在草地上干了什么。
朋友,应该是冬日的火盆,秋天的太阳。尼木是什么,春天的毒蛇,夏日的暴风雨。尼木是朋友吗?乌奇勒真想掏出腰间的匕首,刺进尼木的胸膛,然后告诉每一位草原的男人,按照古老的规矩,他杀了那个欺骗自己的恶棍,就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他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杀掉尼木,反而让他跑了。是的,尼木跑了,在他眼皮底下,像圆溜溜的兔子一样跑掉了。他望着骑马奔驰的尼木,望着红艳艳的晚霞一点点地吞噬掉那家伙。美丽的晚霞和长歌一样飘泊的炊烟,弄得他热泪盈眶。该死的家伙,找了这么一个良辰佳时把事办了。他在心里愤怒地骂道。
现在怎么办?杀掉尼木,像任何一个蒙古男人那样,用枪用匕首解决这样的丑事,而不是像多嘴的麻雀那样骂人。
乌奇勒一遍遍地问自己。乌奇勒,巴尔虎草原上有名的硬汉,让许多女人暗自迷恋的男人,这会儿变成了石头和傻瓜,让天空中的雄鹰吐口水,地上的母鸡昂起了脑袋。他可够丢人啦。
黑马咴咴看见了乌奇勒,长长地嘶叫一声,快速地跑到他面前。乌奇勒以为自己正在做梦,惊诧地站起来,朝它猛扑过去。十年前,他的儿子小利布道就是骑着马儿跑进草原深处,再也没有回来。那匹马和眼前的马长得一模一样,莫非是它回来啦。黑马咴咴躲闪一下,又站稳了,用湿漉漉的黑眼睛望着他。他仅仅看了它一眼就失望极了,它不是儿子骑的那匹马,它更年轻,比十年以前的黑马咴咴还年轻,看起来只有三岁。可是,它的眼神和那匹跑丢了的马一样,不错,它俩的眼睛深处都藏着叫人无法形容的神韵,只要你与这样的眼神相碰撞,心里肯定陡然一跳,肯定以为它想告诉你早该知道的东西。至于那是什么,长生天会比你更清楚。
乌奇勒看见了马屁股上的一道伤口,是用刀砍的。那个天杀的真狠啊,大概想卸下来一条马腿直接烤肉吃吧,或许还想在马身上盖一家饭店呐。他心疼地用手抓下几条白胖的蛆虫,接着从怀里掏出牛皮制的酒囊嚷嚷:我的孩子,挺着点吧,大地会给你力量的。他把酒洒在伤口上,马疼得肌肉抽搐着,但是它的身体纹丝不动。啧,好样儿的,是个男子汉,他温柔地抚摸着马的脖子说,你找到了我算对了,伤口若是化了脓,你的命就没了。
他领着这匹不知打哪儿来的黑马往回走。马信赖地跟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乌奇勒边走边想,也许他身后跟着一个精灵,黑马咴咴的精灵,只要愿意,它马上会从他的身边消失。像他的大儿子利布道那样,再也不回来了。该怎么解释那件让他伤心多年的事情,他的儿子利布道,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像鸟儿一样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打那桩事情发生后,老婆德玛妮便有点不对劲儿了。如若她惊天动地哭几场就好了,但是她不哭,每天盼着儿子出现在毡包前面的草场上。利布道,该起来啦。利布道,该换衣服啦。利布道,该睡觉啦……她冷不丁地叮嘱着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孩子,好像孩子化成阴魂,笑嘻嘻地跟她耍赖呐。
乌奇勒去甘珠尔寺庙,请求长生天再赐给他一个太阳一样明亮的儿子。这个家庭,往昔充满着多少令人羡慕的快乐,现在便充满着多少令人担忧的伤痛。他太需要有个儿子了,那样的话,德玛妮便忙碌不已,丢失利布道的痛苦也会慢慢淡下去。
格桑喇嘛从佛祖那儿为他求到一包香土,让乌奇勒在八天内舔光。喇嘛把手放在他的头顶后果断地说,你的儿子还在人世,只不过用另外一种方式返回来。喇嘛告诉他,相信长生天,相信人间有奇迹,相信善良和智慧会让他得到心灵的安宁。喇嘛说,比鹰飞得更高的是无欲无求的灵魂,比草原更宽阔的是包容万物的精神。
乌奇勒嗅了嗅香土,一股清甜的滋味飘进了鼻子。他舍不得一个人舔,便和德玛妮一起在八天里舔完香土。让我们忘掉利布道吧,他抓住老婆的肩膀难过地说,咱们已经找遍了整个巴尔虎草原,现在,咱们重新获得儿子吧。
那天晚上,他们选择了一片草地做了爱。德玛妮不想在毡包里亲近自己的丈夫,她希望长生天亲眼看见他们在一起,用最热烈的方式讨回孩子。而乌奇勒也感到毡包里已经装不下他跳荡的激情和河流一样奔腾的欲望。德玛妮,我的亲亲,他像新婚之夜一样,深情地叫着她的名字,德玛妮,再给我十个儿子,再给我十个太阳和雄鹰。他搂住了她,听凭她一口咬住他的胸膛,在那里留下深深的痕印。
可是德玛妮生不了孩子。她悲伤地对男人说,你找别的女人吧,我的悲伤和绝望像河水一样,日夜在身体里流淌,我再也生不出像太阳一样新鲜的生命了。
乌奇勒再也忍受不了两人夜守孤灯的寂寞。他们老了,是心灵的衰老。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谁也不瞅谁。还有什么好瞅的,彼此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乌奇勒熟悉老婆脸上每一道新添的皱纹,德玛妮熟悉丈夫头顶上每一根新长的白发。而夜里,他俩谁也不碰谁,德玛妮变成了干涸的河床,乌奇勒则变成了游荡的野风。
乌奇勒再也信不着格桑喇嘛那番故弄玄虚的话,再也信不着他的生命里会出现奇迹。在他看来,蒙古人的祖先已经把数十代后人的奇迹占用尽了。是的,蒙古人一直生活在森林里,按照命运的旨意,他们就呆在那里好了。然而,他们创造了奇迹,用七十张牛皮做了鼓风箱。用炼铁的方法熔化悬崖绝壁后,走向了广袤的大地。那些英雄,一旦踏上了平原,又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蒙古帝国。
奇迹在哪里,在长生天赐予人们的梦境里吗?乌奇勒对朋友尼木抱怨地说,在人们比百灵鸟还聒噪的嘴巴里吗?我凭什么相信我的生命里会出现奇迹?
尼木劝慰他,蜜蜂会找到花朵,子弹会找到猎物。巴尔虎草原上的女人比鲜花还美丽,比云朵还温柔,去找心爱的女人吧,去找一个比德玛妮的胸怀还诱人的怀抱吧。
他没找别的女人。他瞧不起那种把性事当做乐子的男人,也瞧不起随便撩起裙子的娘们。男人和女人碰一下容易,不就是听砰砰的肉响吗,他对尼木说,我还不如找片木板,随便拍大腿呐。
心心相印比什么都重要。他说。
黑马咴咴打着突噜猛然加快了脚步。它似乎很熟悉草地上隐约可见的道路,径直朝乌奇勒家的方向跑去。乌奇勒一眼看见白色的毡包就走不动了。怎么办,回家以后逼问德玛妮,为什么那天傍晚看见尼木提着裤子跟在她身后,为什么她不在家呆着,却窜到草地里啦,这一切她说得清楚吗?
德玛妮怎么回答他,难道还像昨晚那样,连一点羞愧感都没有,做饭、吃饭,然后把枕头扔给他,说睡觉吧,倒头睡得像真睡了一样。
他恨死了尼木。这家伙最近不对劲儿,有空就往他家溜,而且来的时间也不对劲儿,每次乌奇勒赶着羊回家,总是能发现这家伙言不由衷,说自己想念仁慈的大哥啦,聚到一块儿喝酒才能感到有亲人的温暖啦。这家伙来了就赖着不走,一会儿唱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非闹腾得德玛妮连礼节也顾不上,趴在饭桌一角睡过去。有一次这家伙喝多了,搂着他居然说起女人只生一个孩子身材苗条一类的混帐话。当然他拿鞭子敲了酒鬼的脑袋,让他看清楚坐在谁家的毡包里。事后乌奇勒说了尼木的坏话。德玛妮却喟然长叹道:宽容点吧,我的丈夫,我们已经没有了孩子,难道还把唯一乐意陪伴我们的朋友也赶走吗?
那个时候赶走这家伙就好了,乌奇勒悔恨不已地想,省得现在想拿鞭子抽老婆一顿。要知道,自打结婚后,他连一根指头都没戳她一下,更别提因为孩子丢失后她疯癫那阵子了。
黑马咴咴站在那儿等着他。乌奇勒欣慰地想,这匹马拿他当自己的主人呐。他想起与儿子一起丢失的那匹黑马咴咴,也是这样动不动便扬起头等待着他。茫茫的草原,生命吸引生命,马从来都是通人性的,黑马咴咴用不着他吩咐,仅仅看他一个眼神,或者他拽一下马缰绳,它就知道干什么。
让乌奇勒不开心的是,德玛妮没像往常那样站在门前等着他。是呀,一大早他就跑出去了,连马都不骑,任凭羊群关在栅栏里咩咩地叫唤。饿着点吧,这些没头脑的家伙,家里出了大事了他顾不上它们的肚皮。他跑出去了,而且跑得很远。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她该清楚。啧嘿,犯不上责备她,缺心眼儿的娘们,出了那桩事她还腆着脸站在门前等候自己的丈夫,那她可令乌奇勒刮目相看。
他进了毡包,重重地咳嗽一声。老婆正在火塘前熬奶茶。她一下一下扬着木勺子,让勺子里的奶茶重新浇在沸腾的奶茶上。草地的女人们都是这么熬茶来着,可是乌奇勒像是头一次看到,直瞪瞪地盯着她。与往常一样,她的表情很安静,好像昨天傍晚的事是他瞎编的。有一瞬间,他真怀疑自己脑袋出了毛病。可是外面羊圈里羊群此起彼伏的叫声,一下子惹恼了他。
他从毡包木架壁上取下鞭子,一脚踏出门外叫道,你出来一下。她看着沸腾的奶茶迟疑了一下,默默地走出毡包,站在他面前。他直直地望着她,她躲开他的目光,低垂下头。他的心快炸了,她躲着他,她从来没躲过他的目光,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他们以往的肝胆相照、相濡以沫都哪儿去啦,难道他们就这么互相躲避着熬度下半生吗?
你昨天和尼木呆在一起,干什么啦?!乌奇勒紧紧握着鞭子,大声喊起来。反正他不怕别人听见,这片草地只有他们一家人,只有一座毡包。德玛妮用手捂住胸口,责备地摇摇头,你从来没对我这么喊过,她说,尼木是你的朋友,你应该问问他。
脑袋里肯定被人塞进东西了,乌奇勒愤怒地想,那个东西快爆炸了。他仰起头望着天空。那轮太阳多么美丽,像刚刚嫁给他的德玛妮那样美丽。他手里的鞭子咬他一口,提醒他该动手了。他要干什么,那么碧蓝碧蓝的天空,那么纯洁悠长的河流,还有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他要干什么?手中的鞭子又狠狠地咬他一下,他举起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着她,她抱住了头,一声不响地挺着。她的驯服彻底地激怒了他,他宁可看到她哭喊她反抗,却不愿意看到她默认似的等待着下一次的抽打。
黑马咴咴嘶叫起来,它的声音惊惧而凄厉,像一只手抓住乌奇勒的鞭子,让他下不去手。德玛妮垂下手,慢慢转过身,看见了黑马咴咴。她怔了一下,摇摇晃晃走过去。天呐,她小声惊呼道,我的儿子,你回来啦。
乌奇勒再也忍不住,扔掉手里的鞭子,嚎啕大哭。
两个人默默地为黑马咴咴洗了伤口,然后撒上了消炎粉。德玛妮翻箱倒柜,找出还没用完的青霉素片给马灌进去。她一会儿走出去一趟,喂马吃奶酪、肉干和牛奶。乌奇勒生气了,在毡包里喊,让它自己吃草吧,牛奶解药,你这个愚蠢的娘们,它不是小孩啦,犯不上娇惯它。
德玛妮不说话,仍然给黑马咴咴喂牛奶,而且一遍遍地用酒擦伤口,两手挥动驱赶苍蝇和蚊子。乌奇勒吃完饭后把羊群放出圈,骑上马跟随羊群后走了。这一天的时间太漫长了,比死还漫长。他收拾了老婆,心情不仅没好受点,反而更难过了。
呸,对女人下手,你还是个男人吗?他对着草地上自己的影子奚落一句。接着他想起德玛妮的话,她让他问尼木去,因为尼木是他的朋友。他跳起来,不错,他应该问尼木,因为他想起来,德玛妮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手里拿着拾拣牛粪的木铲子!这个娘们,下午就独自一人去草地拾牛粪。她把贴在草皮上的湿牛粪起得离开地面通气,待到晒干后再收集起来。她一定在那个时间里看到了尼木,尼木想调戏她,她就说,忘掉这回事吧,尼木,你是乌奇勒的朋友,你不该欺侮他的老婆。
乌奇勒跳起来,她让他找尼木,就是想让尼木自己有胆量承认事实。可是她又担忧,乌奇勒盛怒之下会把尼木杀掉的。他有理由像干掉一只赖皮狗那样了结尼木的性命。草原上的男人重义气讲信誉,从不做背叛朋友的勾当。他待尼木不薄,尼木手头缺钱,只要说一声,他肯定慷慨解囊,除了老婆,他差不多什么都可以给予那个混蛋。至于尼木四处风流,惹下一桩桩烂事,嘿,他帮助尼木解决了多少争端?
傍晚时分,乌奇勒赶着羊群回家了。离很远他便看到德玛妮站在毡包前朝这边眺望。这个傻娘们,他嘟嚷一句,眼睛湿润了。这个傻娘们,她哪里知道,他离不开她。说实话,不是没有女人投怀送抱。在草原上,他经常逢遇这样的事。骑马放牛放羊的可不都是男人,还有女人。在蓝蓝的天空下,在青纱帐一样的草地里,没事时干点那样的勾当也没什么,但他不行,心里不行。为此,寡妇斯琴哭着离开了他,再也不在他放牧的地方出现了。她惦念他几年了,那可是全苏木最出色的女人,比男人还能干。德玛妮,这个傻娘们不知道,他的心交给她了,他相信有一种爱不会在这个世道里变味。
乌奇勒跳下马,大踏步地走到老婆面前。她递给他一碗奶茶,看他咕咚咚地喝下去又斟满一碗。三碗温暖的奶茶进了肚子,他觉得五脏六腑舒服极了。喂,黑马咴咴的伤口好多了,德玛妮边把羊群赶进圈里边说,它的胃口可不小,喝了挺多的牛奶。
我说过牛奶解药,乌奇勒皱一下眉头说,你怎么还喂它这玩艺儿?可是德玛妮自信地说,我看它用不着吃药,只要吃好了,它自己就有劲儿长肉。她再也不躲避他的目光,很坦然地望着男人,好像压根就忘了那桩烂事。
半夜里她叫了一声。乌奇勒骨碌一下坐起来,点燃油灯。她睁开了眼睛,幽幽地说,我梦见了儿子,他说他快到家了,只要过了莫尔格勒河,他就到家了。她抽泣一下,开始默默地哭了,利布道太逞强了,非要从最深的水流里趟过来,我喊他,他听不见。
乌奇勒伸出手无声地搂住女人。她的身体滚烫滚烫的,她的脸也是滚烫滚烫的。她发烧了,从昨天到今天,她经历和承受得太多了。全聚在心里,所以身体里燃烧起大火。他下了铺位,用凉水打湿了毛巾,捂住她的额头。她又睡过去,嘴里不时说着胡话。但乌奇勒不认为老婆胡思乱想,一定是佛祖借她的嘴道出了利布道失踪的原因。那条像巨蛇一样弯弯曲曲的莫尔格勒河带走了他的儿子。莫尔格勒河,人称天下第一曲水,它打大兴安岭里流淌出来,流淌过整个巴尔虎草原。在它的身边,草长得比树木还高,鲜花开遍了两岸。是它带走了利布道。
现在他想让老婆快点清醒过来。她把他曳在一边,独自和儿子会面呐。沉默寡言的女人,居然有这么多的话要跟儿子讲。可是她平素把嘴闭得比门还严。唉,他看见了德玛妮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他也看见了她翻滚时后背的鞭痕。他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痛苦地说:我这儿疼,你挖了我的心。德玛妮,你不能伤了我,否则,我比死还难过。
黑马咴咴的伤口好得很快,它似乎很留恋德玛妮。只要德玛妮走出毡包,它就跟随她身后。每到下午,德玛妮便牵着它朝草地深处走去。除了她家的几头牛,从别处游荡而来的牛群四处遗留牛粪。德玛妮把牛粪拣回来,堆放在一起,用来做饭和取暖。牛粪燃烧起来的味道很好闻,像青草的味道。每逢这时,黑马咴咴便抽搐着湿漉漉的鼻子,不时打着响亮的喷嚏,好像被遍地花香呛着了。德玛妮便说:我猜不出你从哪里来的,我也猜不出谁是你的主人,他怎么会把你弄丢了?
乌奇勒看出来,老婆担心有人认领黑马咴咴,他边修理马鞍子边说,谁也领不走黑马咴咴,即使倾家荡产,我也要买下它。
德玛妮脸上顿时笑逐颜开。呀嘿,黑马咴咴多么懂事,它的眼神像人一样,有时候我弄不明白,它是一匹马呢,还是一个精灵。乌奇勒心里扑嗵扑嗵地跳荡着,老婆没看错,马的眼神像一个人,他的孩子,利布道。
尼木再也不来了。乌奇勒放牧时看见过尼木。那是阳光照耀的中午,尼木随着羊群走来,他骑着马朝乌奇勒大声喊着,然后挥动手里的草帽向他致意。乌奇勒骑着马掉转过头,用不着问这家伙那天傍晚的事,还是让他滚蛋好了。老婆德玛妮做得对,尼木是他的朋友,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带给他许多快慰,德玛妮不是一惊一乍的女人,她有她的厚道和宽容,她可不想看到男人之间动刀子。草地上因为娘们出人命的惨事还少吗?
可是他不想原谅这家伙。真正的朋友不会背叛良知的,该给这家伙点颜色看看。
尼木沮丧地骑着马走进草原深处。乌奇勒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融汇进深绿色的地平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
那天晚上,乌奇勒被德玛妮推醒。在微弱的光线里,他看见老婆正睁大眼睛倾听着什么。发大水啦,你听听多么好听的声音,她兴奋地说道,明天咱们会看见水汪汪的一片。
他也听见涨水的响声,惊天动地的流水声犹如浓浓的白雾,弥漫在整个草原的上空,他们被大水包围了,在十几天之内,他们只能在高处的草地上放羊和牛,再也看不到从别处游荡而至的牛群、马群和羊群。十几天内,他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呼吸,只能看到彼此的一举一动。
两人一起走出毡包,在银色的月光下,莫尔格勒河像丰腴的孕妇,舒展开自己的身躯,哗啦啦的水流声,像神奇的生命热烈地喧闹、嬉戏、歌唱。德玛妮说对啦,草甸子里白茫茫的一片很美丽。过去他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德玛妮拉住他的手,起先是试探的,之后便紧紧地握住手。这天地之间,只有他们俩相依为命,他在那一瞬间深深感到老婆无声的语言和信赖。
乌奇勒抱起德玛妮进了毡包。他们在大水膨胀的声音里做爱。皎洁如水的月光从天窗泻露进来,洒在德玛妮赤裸的身体上。他用手一遍遍地抚摸她,已经很久了,他没有这样动情。德玛妮真好看,只有他知道她的美丽和诱人。给我儿子吧,他把手放在她的小腹上轻声说,你会有儿子的。她抓住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他摸到了泪水,她正在流泪。大水把利布道接走了,大水也会把他送来。她哽咽地说,刚才我听见他喊啦,妈妈,我回来啦。
他伏下身,吸吮掉她的泪水,什么也没说,用身体覆盖了她。利布道回来了,老婆说得对,他的儿子回来了,就在他的身体里,在她的身体里。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利布道应该早点回来,是他们挡住了孩子的回程。该死的,这么多年了,他都干了些什么?
德玛妮终于打开了心扉,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让乌奇勒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她笑着,她哭了,她轻声地呼唤他的名字,羞涩而甜蜜。他们一直在做爱,在爱,直到大水撤下去,直到一场场凉风把茂盛的绿草染成了金黄色。
德玛妮怀孕了。她开始呕吐起来,反应强烈得跟第一次相同,她脸上长出妊娠斑,乌奇勒打趣地形容那是莫尔格勒河流从她脸上流淌过去的痕印。他甚至担心等到她生产后,脸上的斑消失掉。那可是丑死啦,他摇着脑袋犯愁地解释,我看你就这个时候漂亮。
德玛妮幸福地笑了。她没告诉男人,她还会要孩子的,长生天帮助她打开了生命之门,她当然会要更多的孩子。草原的女人,哪个不希望自己儿女成群呐。
乌奇勒趴在她肚子上倾听胎儿的动静,终于听见若隐若现的胎声。再过一段时间,胎儿就像一条丰沛的河流盈盈而涨,在那个神秘的世界里欢快地奔腾着。他惊奇地看着她身体的变化,感到一切都不可思议。直到那一天,他喜忧参半地说:你怀了一座高山呐,到时候怎么生下孩子?
德玛妮满有把握地说,我会生下来的。
德玛妮真的是自己接下了孩子。那天下午,她照例去草甸子里拾拣牛粪,肚子就疼痛起来。四月的草原还很寒冷,大风扫在直挺挺的枯草尖上,发出尖利的啸声。她感到两腿之间流出了羊水,便意识到自己赶不到家了。她把皮袍铺在尚未泛出绿意的大地上,听见黑马咴咴从老远朝她奔来的马蹄声。它跑得真快呀,像草原的心脏咚咚地跳动着,像一道疾风从远方刮来。德玛妮满意地看到,马长得漂亮了,比神话里的马还威武,瞧它四只长着白色毛发的蹄子踩在枯黄的大地上,犹如四朵洁白的莲花,而它黑色的皮毛泛着光泽,像黑色的火焰在草地上燃烧。她欣慰地长吁一口气,利布道该回来了,他就骑在马上,还是十年前的模样,穿着她精心缝制的蓝色蒙古服,头上系着蓝色丝带。阿妈,蒙古人为什么喜欢蓝颜色?小利布道穿衣服时问她,阿爸的衣服都是蓝颜色的。她边为儿子系上蓝色的长腰带边说,看见天空了吗?蒙古人喜欢像蓝天一样的颜色,它宽广、尊贵、安宁。现在她看得见黑马咴咴背上的英俊少年,仁慈的长生天真的把儿子归还给她了。
德玛妮就在草地上生了孩子,黑马咴咴来回转着圈长声嘶鸣。她用牙咬断脐带,用皮袍紧紧裹住了孩子,翻身上马回家。
乌奇勒在草原的深处放羊。羊群走得很慢,嚼着枯黄的草茎。再熬过一个月,大地就会变了模样。大地重新变得生机勃勃,起初的草长出来是嫩嫩的、柔弱的。一根根小草像一只只嫩绿的小鸡嘀嘀咕咕撒娇。可是等着吧,再过一段时间,嫩芽般的小草便突然疯狂地长起来,空中弥漫着它们生长的声音。只要夜晚坐在草地上阖闭眼睛静静地倾听,你会听到生命旺盛的勃动。而外面来的人总是抱怨草原太寂静了,像掉进海水里那么可怕。外来人没有草地人的耳朵和心灵,他们当然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乌奇勒听见黑马咴咴奔跑的声音,心里怦怦跳荡起来。德玛妮一定生孩子了,黑马咴咴赶来告诉他。他看见在草地上飞驰的马,惊奇地发现,黑马咴咴是一匹真正的普氏野马,草原上早已罕见而今却神奇般地降临到他的面前。难怪草原上没有人来认领它。这匹普氏野马的真正主人该是长生天吧。
乌奇勒没猜错,黑马咴咴赶来告诉他,回去迎接自己的孩子吧。他赶着羊群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家。刚刚走上通往毡包的小坡路时,他便听到婴儿的啼哭。那嘹亮的像太阳一般有力的哭声一下子震撼了他。是男孩子,只有男孩子才能这样惊天动地地宣告,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发疯了一样跑进毡包。德玛妮正用早已准备好的白色的熊油擦拭婴孩的肚脐,以免感染。由于全身光裸,婴孩身上的皮肤泛出紫红色。德玛妮用布紧紧裹住孩子,双手托住后举向乌奇勒,看看吧,这是我们的儿子。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用双手托住。在婴孩皱巴巴的脸上,他看到了利布道的眼睛。孩子停止了哭泣,安静地看着他,好像在辨认着他。他感到泪水涌了上来,庄重地亲了德玛妮额头一下,把襁褓里的婴孩高高托到头顶大声说:长生天,请赐给我儿子雄鹰般的勇敢,太阳般的力量,岩石般的坚强和如你般的智慧,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草原男人吧。
他听见德玛妮轻声说,还叫儿子利布道吧。
在孩子降生的那些日子里,尼木意外地死了,他死在莫尔格勒河碧波荡漾的激流中。他是牧归时顺着水流漂走的。人们在河岸边只看见了他的马在痛苦地徘徊,却没有在河流里找到他的尸体。人们都说尼木去了远方的草原,是仁慈的莫尔格勒河送走了他。
多年来,乌奇勒一家依然游牧在巴尔虎草原,他们再也无法见到每天都那么快乐,喜欢唱歌的尼木了,他们再也无法回忆起往日生活的场景。在巴尔虎这片天堂草原,在莫尔格勒河流的岸边,乌奇勒的儿子也骑着黑马咴咴一天天地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