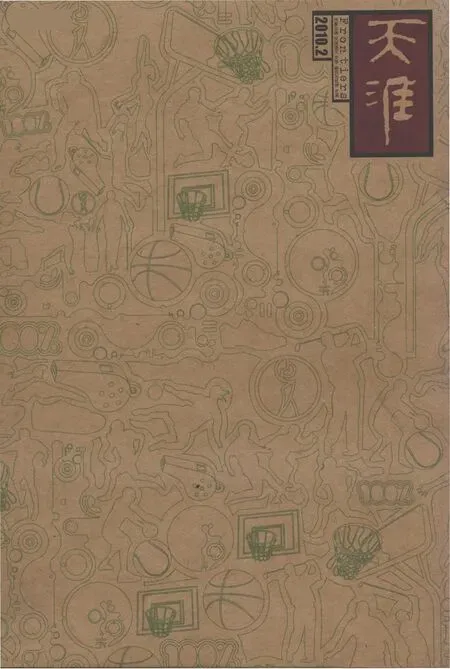走出“冰冷”与“暧昧”
2010-12-27留白
留白
走出“冰冷”与“暧昧”
留白
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题为《冰冷的知识和暧昧的自我》(载《天涯》2006年第6期),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冰冷”和“暧昧”加以揭橥和反省。事隔几年,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是在努力走出这种“冰冷”和“暧昧”的,尽管每一次都那么心力交瘁。
我是个表面温和的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世故圆滑,表现之一就是,喜欢采用多个角度看问题想问题,特别是对亲朋好友,并无所谓严格的“立场”。但这也不过是表面,骨子里,我是个子路般容易冲动的人,认死理,不善迂回,不愿受气,有时候竟会不计后果与利害地发起雷霆之怒,虎啸龙吟,事后想想,这是我的“孩子气”加“书生气”双管齐下所使然,怨不得谁。
半个月前,我打电话给菜场门口卖米的叶师傅,请他送一袋二十斤装的大米过来。和叶师傅认识也很偶然,一次从菜场出来,经过他的“摊位”(其实是路边随意摆放几袋米的一个所在),问他米价如何,没想到他说可以送货上门,从此就和他打上了交道。每次我拨通他的电话,刚说一声“叶老板”,他马上知道是我——大概没有人称他“老板”吧——连忙说:“老师,米又吃完了?我这就送来。”
这一次,送完米、付过账之后,我们又多聊了几句。他说前几天本来想找我帮忙的,因为他的“摊位”被“黑猫”(对“城管”的敬称)盯上了,他们把几袋米装上卡车不说,还要把他抓去,幸亏有几个好心的业主帮他求情,才没有被抓走,本来要罚款两百元,后来大家又帮他说话,被罚去五十元。
我说你怎么会想到找我?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次你帮老太太打抱不平的事,我们都知道。她们说去找那个老师,他会说话。
我笑了,说:那你怎么不打我电话?他说:怕你忙,没敢打搅你。你不知道,那次我都哭了。
我的心一震。这位叶师傅,苏北人,黑脸膛,络腮胡子,年纪约摸五十出头,却过早地谢顶了。他孩子在上海上大学,他就跟过来在这里贩米,算是“陪读”。本来他在菜场有个正式的摊位,可是每年租金两万多,吃不消,只好转让给别人,自己就在菜场旁边小区的铁栅栏门口“打游击”,一晃不少年头了。当这个靠自己的汗水在城市的旮旯中讨生活的汉子说他“哭了”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心里也仿佛要流泪了。我想象着叶师傅的遭遇,感同身受,不知如何安慰他。
叶师傅说的那件事倒是实情,但事后的影响我并不知晓。
那是2007年5月间,我所栖身的大学也成“百年老店”,大张旗鼓地搞起“百年校庆”。一天,我经过所住小区门口,看见一个外来民工模样的老太站在门口哭嚎,之所以说她是哭嚎,盖因声甚凄厉。我这人爱管闲事,忍不住上前问她:“怎么了?”
没想到,这一问不要紧,这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太便如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扯住我的胳膊说:“行行好吧,你一定要救我。”我吓了一跳,茫然四顾,以为中了谁设下的“局”,要不行人来去匆匆,几个门卫怎么站在那里对我似笑非笑呢。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且看“后事如何”吧。
从这老太的哭哭啼啼、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了解了事情的大概:原来老太是安徽来沪的民工,在这一带靠捡废旧物品为生,老伴儿有病在床,三个孩子也不成器,全靠她一人操劳度日。事后想想,这些话也可能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足以引起我的同情了,我催着她说下文。
她说:“俺在路上捡破烂,一不留神,就被门卫把三轮车给抢走了,现在找也找不见,求求你了先生,你帮俺把车子要回来吧,那是三百块钱买的,全家人靠它活命啊。”我回头看看那两三个门卫,他们尴尬地别过头去。门卫虽然穿着所谓“制服”,但他们也属于老百姓,有的并不是那么飞扬跋扈的。我每天走这里出入,觉得他们也还温和可亲。于是我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各位师傅,你们就把她的车子还给她吧,你看她哭得多可怜……”
我还没说完,一个师傅就说了:“车子不在我们这里,你去找警察吧。”
我说:“怎么扯上警察了?”
他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这几天校庆,警察查得紧,这车子在大路上摆着影响市容。”
我说:“她说是你们拿的,到哪里去找警察?”
他们见我不信,便指点我去小区居委会走一趟,管这个小区的“片警”在那当班。
我是个直性子,二话没说,就带着那老太去找居委会。路上听她进一步哭诉,迎面走来的人不住地向我们投来诧异的目光。这目光竟让我有些兴奋。
到了居委会,说明了情况,我请求坐在办公桌后的一个四十出头的警察,归还老太的车子。居委会一位阿姨问:“你和她什么关系?”竟有些质问的口气。
我说:“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就是看她在那哭得可怜,就带她过来了。”
那阿姨不说话了。警察却说:“她的车子被没收了!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说:“为什么啊?”他说:“现在百年校庆,她那辆破车子放那儿是不允许的!”
我一听就火了,说:“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对百年校庆都没你这么起劲——百年校庆算什么啊?百年校庆也不能不让人家吃饭哪?!”
那老太见我发火,吓坏了,说你别和他吵啊,越吵我的车子就越要不回来啦,说着竟然给警察跪下了,拉着他的衣袖作揖叩头,死乞活求。警察嫌恶地别转身,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这种嘴脸最是可憎,不论是谁,只要手里有点小权力,可以给别人设置点“路障”,一律会摆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臭面孔。
我一边拉老太起来,一边对警察说:“我只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是,你就不应该这样。”顿了一顿,又说:“她现在都给你跪下了!你就忍心看着一个老人给你下跪?她也是老百姓啊!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如果是你的亲人你会这样吗?她在这里捡破烂,等于免费打扫卫生,你不付她工资倒也算了,还要抢了她谋生的工具,这算什么为人民服务?再说了,捡破烂也是她的正当权利,宪法没有规定人不能捡破烂,你把车子没收了,等于掐住了她的脖子,她就可以在大学的正门口静坐、抗议,那就不是影响市容的问题了,到时候恐怕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说来惭愧,年轻时我练过演讲和辩论,一通大道理也算得上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最后的结果是,警察让步了(这个警察还不算太差),他打了个电话给大门口的门卫,然后让我们去拿车子。我呢,索性好事做到底,陪着老太一直到她拿到她那被锁在一间废旧仓库里的三轮车。老太对我千恩万谢,还要拿钱给我买烟。我说谢谢,我不抽烟,这事本来就是他们不对,以后再碰到这事,你不要怕,你越是软弱,就越是受欺,别忘了你有你的权利!
老太最后说的话我一直记着,她说:俺哪敢跟他们作对啊,就是敢,俺也不会说啊……
我想,叶师傅之所以想到我,可能跟老太以及大门口那些收购旧电器的民工大嫂的传播有关,而她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会说话”。
这么一个结论让我无语凝噎。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件明摆着的事,决定其性质和走向的难道仅仅是“会说”与否吗?孔子说过很多有道理的话,但有一句话我最反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不知道,这句话被多少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愚民政策”的保护伞和尚方剑。我们的宣传,学校的教育,为什么不告诉民众,你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只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承担服从管理的义务?一个时时处处处于被“管”状态的人,最后不就成了“沉默的羔羊”?可是,恰恰是这些“沉默的羔羊”,经常被剥夺尊严、人格,甚至生存的权利。为什么老太这样的老百姓永远处在“不知情”的状态?为什么他们“不会说”、“不会想”、“不会争”?当受到强权的干预甚至侵犯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只会“求”,甚至磕头作揖地“乞求”和“哀求”?
我所以能“说”,首先是我能“想”,我所以能“想”,是因为我“知情”(明理),尽管也只是部分的“知情”。对那些失去言说能力的人,谁来替他们“说”呢?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吧,在我文债累累、恨不得一天四十八小时的现在?
我坦白,因为就在昨晚,我又一次和警察和城管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从超市买东西出来,就听到一阵广播喇叭的叫嚣,只见一辆警车和两辆卡车停在路口,紧接着传来一阵十分具有威慑力的吆喝和求饶的声音,于是,许多过路的行人赶上去围观。那正好是一些外地小贩晚间摆摊做生意的地方,不用说,这又是一起“猫捉老鼠”的事件。
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去,只见七八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正在拉扯那个卖炒面的妇女的车子,妇女惊惶失措,又是讨饶,又是道歉,求他们放过这一次,下次再不敢了。围观的人有二三十人,没有人说话。我先是想息事宁人,就说,算了吧,人家老老实实做点小生意,警告一下就算了。可是没效果,他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七手八脚地上来搬东西:一桶鸡蛋被搬走了,一锅生面被搬走了,又要来搬锅灶。那妇女哭了起来,护住自己的车子,说,你们别搬了,我有病啊,指望挣点钱看病,下次我不敢了……可那些“黑猫”不依不饶,还是搬东西,拉扯之间,有的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
不知是不是条件反射,总之多年来,我经常会陷入这种“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处境中,这一次,我还是没能学聪明,又扮演了一次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我知道那被城管所管的妇女“不会说”,于是只好“替她说”——“你们态度好一点行不行?”人一着急,嗓门自然就大了:“干嘛要抢人家东西?她又没违法!”
一个城管停下来,冲我说:“谁说没违法,她违章了,当然要处罚!”
“她又不偷不抢,违什么章了!谁定的章?”我嗓门更大,潜意识里,我希望周边的人能够加入我的抗议。
另一个城管看我说话挺硬,十分滑稽地对我做了手势,说:“你证件呢?”这大概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估计对那些小贩很管用。
我马上反问:“你的证件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证件?”
那家伙又指了指自己的帽子制服,意思是我还用出示证件吗?
我火了,语言也就不够斯文,竟指着他说:“你吓唬谁啊?你以为戴大盖帽、穿制服就了不起了?我没证件,你怎么样?有本事你把我抓走?”趁他一愣神,我又加了一句:“量你也不敢!”
这样一来,几个城管围了上来,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对你们的做法看不惯。他们就说,大学的老师怎么了,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多了。这时,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说这么一句傻话:“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是不对的!否则,我就打110了!”
想不到这一说,把他们逗乐了,他们指着一个警察——由于天黑我起初没注意——说,这个就是110的!警察挺挺胸,说:“我在这儿,是我叫他们搬的,怎么说吧?”
我就冲他说:“谁给你们的权利?”
警察说:“政府!有意见你去找政府提!”
我最讨厌这副狐假虎威的嘴脸,我说:“政府怎么啦?政府也有犯错的时候。政府叫你们这么做就更不对,别忘了她也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养活了你们!”
警察说:“听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没领导管似的,你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几个也附和,好像在暗示我要告诉我们领导什么的。
“对!”我说,“你们有人管,我就没人管,怎么着?政府是老百姓养的,你说谁最大,当然是老百姓最大!”这时,我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就借题发挥,说:“你们说,这地上搞这么脏怎么办?我看你们怎么把这儿打扫干净啊!”我这个人火起来说话就不讲章法,怎么过瘾怎么说。他们被我这样的腔调噎得一愣一愣,看热闹的人也都笑了。
这样的争吵相持了大约有十几分钟,我慷慨陈词,寸土不让,要不是妻子把我劝走,城管警察无心恋战,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往前走,心里堵着一股气,不知如何抒发。因为这一次,毕竟孤掌难鸣,我虽然“说”了,可没有真正帮上忙。围观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但除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就是“敢怒不敢言”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总之,没有人为我声援几句,使我的越来越像吵架的陈词成了“街头政治”的演讲。估计在我走后不久,城管的小卡车就会满载而归。那个可怜的卖炒面的妇女,不知将怎样度过这个万家灯火的夜晚……
我想起警察城管说过的一个词——“取缔”。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取缔”意为“明令取消或禁止”。当他们使用一个权力话语的时候,似乎自己也在分享着某种权力,他们为此而自以为是,耀武扬威。殊不知,有多少不合理的制度和章程都是“明令”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却一点都不人道。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有人因为生在农村就要“低人一等”?为什么那些所谓“进城务工人员”要受到如此的歧视、盘剥和欺压?难道他们愿意过这种流寇一般的生活吗?和那些为盗、为娼、为贪、为腐者相比,这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劳动者不是更令人尊敬吗?
说穿了,他们其实就是远道而来的故乡的亲人,他们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看望我们这些被现代生活和繁华城市绑架了的“人质”!
今天早上起来,昨晚的事依然萦绕在脑海,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坐在电脑前,写下这篇文字。我承认,在写的过程中,我曾经流过泪。也许,我的“自我”仍旧是“暧昧”的,我只是在勉力抵抗那种“冰冷”。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我愿意一直抵抗下去,直到彻底走出“冰冷”和“暧昧”。仅此而已。
留白,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会评》、《书与火》、《古诗今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