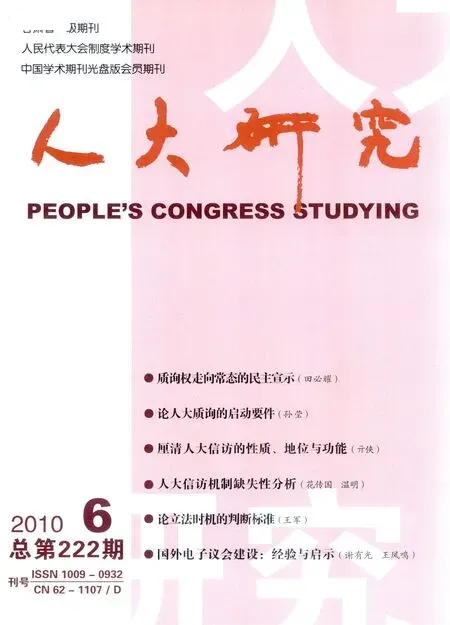立法语言的明确性
2010-12-27张建军
□ 张建军
立法语言是立法者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专门的语言文字,它按照一定的规则表述立法意图,设定行为规范,以形成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在成文法语境中,立法语言是法律条文的物质外壳,是法律信息最直接的外在形式。立法语言在传递法律信息、实现立法意图、体现法律规则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质量的立法需要科学、规范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而法律语言规范与否,直接影响到立法意图能否正确传达和社会公众对立法意图能否正确理解,进而影响到法律法规能否正确实施。立法语言相当考究,几近苛刻,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风格和特质。法律语言应当是运用本民族语言的最高典范,完美的法律不但是法律的杰作,也应该是语言的创作,甚至是语言的典范。“法律的语言绝不可能等同于报纸的语言、书本的语言和交际的语言。它是一种简洁的语言,从不说过多的废话;它是一种刚硬的语言,只发命令而不作证立;它是一种冷静的语言,从不动用情绪。法的所有这些语言特点,就像其他任何风格形式一样有其存在的道理。”[1]
一、明确性是对立法语言最基本的要求
法律语言的根本特点在于其明确性。所谓明确,即明白、确定之意。含糊不清的法律则会给法律的遵守和适用带来极大的不便。法律不明确,必然权威不彰、人人自危;法官各行其是、尺度不一。法律应该明确,可以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法谚云:“法律不明确,等于无法律。”郑玉波先生注解道:“法贵乎明确,使人易知而易守,若不明确之法律,则无法强人知悉而遵守,故等于无法律也。”自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V.Kentucky案首创了“不明确即无效”的理论以来,法律规范是否明确就被作为判断其有效与否的重要标准。后来,该理论也得到大陆法系诸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认可与采纳,成为实行违宪审查制度国家普遍秉持的准则。
人类进入法典时代后,“明确性”是立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这是因为“明确性”承载了安全、自由和效率等法律的基本价值。首先,明确的法律规范使得公民能够根据法律的规定认识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预测自己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从而具有安全感。其次,明确的法律等于在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之间划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避免行政机关和法院以一己之好恶恣意滥权,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再次,明确的法律有利于法律纠纷更快、更公正地解决,能够提高诉讼效率。法的明确性是法律作为行为准则的最起码的要求,是法的指引、评价和预测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正如哈耶克所言,真正的法律“必须是已知而且确实肯定的”,“要是一个自由社会能顺利有效的运作,法律的确定性,其重要意义是如何强调也不大可能会过分的”[2]。
在立法活动中,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在遣词造句方面凸显立法语言准确、简洁和庄重的风貌与格调,以使立法语言能够超越不同文化程度、性别、职业、经历的人们之间的差别界限,而成为一般民众所理解的一种语言文字。
(一)准确
立法是要建立或创设制度,规定社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和职责,即立法的目的是设权定责、定纷止争。如果法律条文含义含糊不清、意指不明,则人们必然会无所适从、进退失据;执法和司法人员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随意地、有差别地执行和适用法律。法谚云:“法律暧昧或不确实,如令遵守,实属苛酷。”因此,立法者需要对词语进行恰当的选择并进行合乎语法规范的表述。
法律语言“不仅要求遣词准确,法律用语之精确度不亚于对桥梁、大厦精确度的要求,它还要求语法的准确,任何语法上的不严谨都会造成法律适用中的歧义和混淆。雄辩的律师可以抓住法律文字的一个词的含义而扭转乾坤,赢得诉讼”[3]。故此,立法语言应当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精雕细刻力求准确无误,力求使读者能作出符合原意的理解。在立法中,准确意味着立法者应当用清楚、恰当、合适的立法语言文字来表述法律的内容。其次,每一个词语所表达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当是确定的,不应使用隐语或双关语。要做到一词一义,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用同一个词语来表达,同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使“法律的用语对每一个人要能唤起同样的观念”[4],在遣词造句时应当以通用词汇来表达,新词只能在已经普遍推广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所使用的词汇具有数个含义,必须在立法本文中指明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以便保证对该法的正确理解。最后,立法用语要符合语法,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和宾语不宜随意省略,也不得打乱语序。否则,有时会产生语法上的弊端,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二)简约
法谚云:“简洁乃法律之友。”法律是民众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标准。简洁易懂的条文便于民众理解和遵守,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查找、引用和适用。此外,立法和会话的最大区别是立法话语是单向的,制定法律时任何立法话语的对象都不在场,不对立法话语形成制约。因此,“法律的风格应该和它们的条例一样简单;它应该使用普通语言,它的形式应该没有认为的复杂性。如果说法典的风格与其他著作的风格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应该具有更大的清晰性、更大的精确性、更大的常见性;因为它写出来就是让所有人都理解,尤其是最低文化水平阶层的人理解”[5]。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它并不是一种逻辑学的艺术,而是像一个家庭父亲的简单平易的推理。”“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直接的话总要比深沉迂远的辞句容易懂些。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完全没有威严可言;君主们被弄得像修辞学家们在讲话。当法律的体裁臃肿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部浮夸的著作看待。”[6]在法律语言的繁、简问题上,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律学家也秉持相同的观点,有过精彩的论述。商鞅强调:“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杜预指出:“刑之本在于简、直。”李世民要求:“国家法令,唯需简约。”司马光认为:“凡立法贵其简要。”
立法要做到简洁通俗,首先需要用词符合语言经济原则,力求言简意赅,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涵,避免冗长、烦琐、累赘和不必要的重复。如果仅从技巧要求上讲,法律规范在语言文字表述方面要力求做到用尽可能少的语言文字,能够表达出尽可能多的内容,而且应当准确无误。当然,不能把简洁凝练错误地理解为简单和笼统。强调法律语言的简洁性,决不能不顾及法律完整性的要求,否则,有可能会损害立法原意,造成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其次,尽管立法需要一些特定的专业词汇,许多词语自身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和日常用语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某些情况下,离开了这些特定的词汇,就难以准确地表达法律的本意。然而,过分专业化的立法会令一般民众望文兴叹、不知所云,也为法律专业人士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玩弄法律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所以,“立法者在立法时要摈弃晦涩难懂、佶屈聱牙、故作深奥的语言和文风,重直接陈述,弃蜿蜒曲折”[7]。立法者不应刻意把法律表述得深奥古僻,通篇全是专业术语。而应该合理、适度地运用专业术语,在不影响准确性的前提下,能不用专业术语的尽量不用。当然,通俗易懂并不意味着立法语言的口语化,而是说应当浅显平直,以便人人理解。
(三)庄重
“法律和法令是一种庄严慎重的东西”[8]。法律的实施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具有极高的强制性,对任何人都一体、无差别地适用。加之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广泛而重要,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各个层次与方面,这就使得法律所规定的制裁手段具有严厉性。法律的严厉性、强制性决定了行文风格的威严。刑法的立法语言要庄重严肃、威严冷峻,少用华丽辞藻而务求朴实无华。
立法语言不同于文学、新闻、广告语言。从语言色彩的角度讲,如果说文学语言是五彩缤纷的,那么,法律文本就是黑白的。立法文本的语言表述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立法是一项理性的活动,而不是对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的感情冲动或美好想象。它冷静地传达立法思想,不显现语言的激情,立法语言不宜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应摒弃带有道义色彩的褒义词和贬义词。例如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其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完全是日常口语,感情色彩浓厚,不够中性和明确。“立法科学要取得进步,必须舍弃这种‘激发情感的名称’,使用中性的表述方式。”[9]
“法律语言不仅是经过斟酌权衡的最准确的语言,也应该是经过筛选净化的最庄重肃穆的能显示法律权威性的语言。”[10]所以,不能以探究的、询问性、商榷性、讨论性、建议性以及其他不确定性的用语来表达法律规范的内容;在表示组织机构、文件、时间时,都应冠以全称,而不应使用简称。此外,立法者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字斟句酌,力求严密周详,无懈可击。语言必须符合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等形式逻辑规律,以体现法律语言的科学性。
二、兼容与互补,明确性并不完全排斥适度的模糊
长期以来,学界对立法语言的研究,过多注重了文意的精确与严谨,而忽略了其模糊界面。结果,“模糊”往往成了被抨击的对象,有时甚至将它和“含混”、“歧义”相混同。但对法律的明确性也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明确并不意味着法律条文中不能有模糊的、弹性的词语存在。梁启超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洞见,他指出:“法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对立法语言而言,明确与模糊不仅在本体上兼容,而且在功能上互补。
(一)模糊性是立法语言与生俱来的属性
首先,立法者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立法者并非全知全能的人,其理性能力以及智识水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他们制定一部部囊括各种社会现象、覆盖全部社会过程、包罗一切社会事实的法律不仅在客观上难以达致,而且会出现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的弊端,极有可能因为立法者的疏漏或因社会的发展,使得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规制。“法有尽而情无穷”,越是具体的法律,也往往越是与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脱节。18、1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司法观念是严格规则主义,立法者凭着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力图制定包含着对法官可能遇到的所有事态都有明确与详细规定的法典,1794年的《普鲁士普遍邦法》有17000多条,1832年的俄国法律汇编达42000多条,但不免百密一疏方枘圆凿,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在立法当中完全排除模糊词语是不可能的。综观当今各国立法,不存在一部完全用精确词汇进行表述的法律,更多的是确切词语为主,适当辅以模糊词语。
其次,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立法采用文字作为载体,而文字作为表达法律的一个不完善的工具,具有永恒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构成法律条文的文字,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可以说,自成文法产生之日起,法律语言便存在模糊问题。因为“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但越趋边缘则越模糊。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议,而其究竟属该语言外延之内或之外,亦难断定……此非立法者的疏忽,而系任何语言所难避免”[11]。“在自然语言中存在模糊性和精确性的差异,处于语义轴两个极端的绝对精确与清晰是有限的,这决定了语义的精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处于语义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是过渡的、分级的,其难以划清界限的模糊现象则是普遍的,这就决定了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12]。法律语言作为自然语言之一种,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这就决定了用语言去精确传达立法的目的、意图、政策是非常困难的,立法语言只能不断地接近客观现象和事实。明确只具有相对意义,即不是本体论意义或科学意义上的绝对客观性,只能是波斯纳所说的交谈意义上的合理性。
再次,法的普遍性本身蕴含了模糊性。“法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13]法律所针对的是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不指向特定的人和行为,否则便失去普遍约束力。这就意味着,立法者立法时通常是以社会现象的典型情况为依据的。卢梭曾指出:“法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它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14]而社会现象不仅千姿百态、复杂多样,而且变动不居,法律规范和具体事物之间不可能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普遍的抽象终究不能穷尽千差万别的具体,立法者为了将纷繁复杂的行为含摄于有限的法律规范之下,必须对具体事物和行为进行“类型化”的概括。况且法律制定之后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活变化靡常,要使法律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较强的适应性,以免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无能为力,就需要适度地使用一些伸缩性的语词,以维护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二)模糊语言的适度使用可消解过度明确所带来的弊害
“法律所应付的是人类关系最为复杂的方面,人们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纠纷并预先加以解决的、包罗万象的、永恒不移的规则,因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含混和有变化的。”[15]如果绝对地、机械地恪守法律的明确性,总是希望立法者能制定一部部明确具体、包罗无遗的法典,那么就可能面临这样一个“法律越来越多,秩序越来越差”的世界。庞德曾指出:“希望有一部包含着对法院或法官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明确、详细的事态都有明确与详细法规的完整法典”,“这种想法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16]
在看到明确性原则在增强法律的理解可能性和预见可能性的同时,应对其负价值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法律规范的绝对明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的明确性意味着绝对的僵化与刻板。极度明确的法律难免卷帙浩繁、繁琐冗长,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发挥其预测和指引民众行为的功能作用;且极度明确的法律刚性太强而欠缺灵活性,必然会使法律的可适用性大大降低,可能会使法官无法将该规则适用于个案的解决,更不利于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西方法谚云:“极端确实,破坏确实。”郑玉波先生对该法谚有精彩的解语,他说:“法律问题与自然科学问题不同,与其注重极端精确,毋宁注重妥当。故有谓‘法之极,不法之极’之说。”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习惯、风俗各异,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立法上难以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事实作出整齐划一的具体安排。作为人们理性的创造物,法律只是、也只能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并不完美的表达,明确性只有在相对意义上方可成立,法律中完全排除模糊词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适度模糊的立法语言则可以有效地消解明确法律规范所产生的弊害,缓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模糊词语的概括性强,可以使立法语言简洁、凝练;使司法人员处理案件时具有“灵活性”,有助于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实现个别正义。
当然,刑法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并非指语言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而是指对明确词汇所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的种类和个体之间“过渡状态”的全面概括。虽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模糊词语可以起到精确词语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旦使用不当,则会影响对行为性质的法律评价,容易引起法律纠纷。所以,立法者对模糊语言的使用不能不秉持一种谨慎、谦抑的态度,即模糊词语的运用,只能是有助于加强刑法语言的明确性,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模糊词语的运用必须是适度的。在刑法规范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关系问题上,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明确性与模糊性相容并互补,该明确就明确,难以明确的就模糊。
[1]【德】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莹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3]周庆生、王杰等:《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序。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7页。
[5]【英】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6~298页。
[7]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8]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9]【英】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页。
[10]潘庆云:《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1]转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12]刘蔚铭:《法律语言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 71页。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1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16]【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