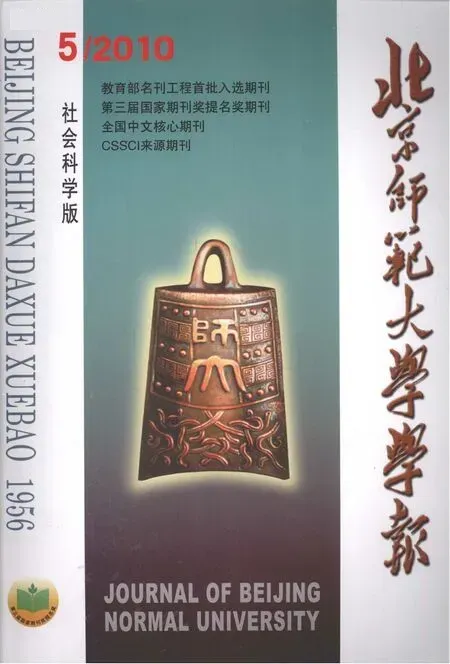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
——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
2010-12-04吴礼权谢元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
吴礼权,谢元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
——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
吴礼权,谢元春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卓然有成,也颇富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将语法与修辞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阐释了汉语中种种不易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全局观,较早地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善于概括归纳相关修辞原则,重视修辞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四是重视在继承与借鉴中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到的修辞理论体系;五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为后人开展汉语修辞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黎锦熙;修辞学;汉语语法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学术界一提起他,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他在汉语语法研究与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的《新著国语文法》和《国语运动史纲》。其实,黎先生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上的成就远非上述两个方面。比如,在汉语修辞学研究方面,黎先生就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珍视。
一、重视语法与修辞的结合
汉语语法与汉语修辞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语法现象最初都是修辞现象,后来慢慢演化、固化为语法现象。因此,黎锦熙先生讲汉语语法重视与修辞的结合,这一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它体现了黎先生学术研究“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明·王夫之《俟解》)的特点。
说到汉语语法与汉语修辞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说到汉语中的很多语法现象从根源上来追究,往往都是修辞现象演进的结果,这一点,对汉语史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认同。比方说,汉语中有丰富的量词存在,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汉语中大量量词的产生,原来是基于修辞的需要。也就是说,量词虽是一种语法现象,但起源却是修辞现象。郭绍虞先生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曾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既然量词“是汉语所独,也就正要在这‘所独’处来发掘汉语的特征,所以必须强调从全面看问题。只从量词谈量词是谈不出什么来的。”①②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26-27页。并明确指出:“从量词的产生也就可看出是为修辞的需要。”为此,郭先生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第一避同字例”,“第二,调剂音节”,“第三,加强形象。”②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26-27页。从郭先生所举例证看,其所提出的三点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汉语中大量量词(特别是“大量的专用的个体量词”)的产生是由于修辞的需要;修辞的需要产生了大量的量词,开始这些量词的出现是一种修辞现象,后来慢慢习用而不察,便自然演化成一种语法现象了。
其实,不仅量词的产生是基于修辞的需要,量词的发展丰富同样也是基于修辞的原因。也就是说,汉语的量词,无论是其产生,还是发展,首先都是一种修辞现象,而不是语法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根据目前学者们对汉语史研究的共识看,汉语的量词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丰富的,而是由于修辞的需要而逐渐丰富起来的。也就是说,量词的产生是修辞的需要,量词的发展丰富也是修辞的需要,汉语量词的使用由偶然到必然、由少到多,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于汉语量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总结说:“在上古汉语里,事物数量的表示,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最常见的,就是数词直接和名词结合,数词放在名词前面,不用单位词。”①②③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2、273、275页。如:“一言以蔽之。”(《论语·为政》)“第二种方式在上古是比较少的,就是把数词放在名词的后面,不用单位词。”②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第三种方式在上古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把数词放在名词的后面,兼带单位词。”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根据王力先生的观点,“天然单位的单位词在先秦已经萌芽了,但真正的发达还在汉代以后。最常见的是‘枚’字。”③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2、273、275页。不过,“枚”作为天然的单位词(即量词),其与名词的搭配则是广泛的,不具有单一性。不像后代说到树要用“棵”,说到石要用“块”、说到书要用“本”、说到旗要用“面”、说到枝条要用“根”等等,搭配具有规律性。这说明其时的“枚”还只是表示语法作用的成份。根据王力先生提供的例证看,汉代以后,与“枚”配合的名词非常广泛,如木器、珠、剑、鱼、珊瑚树、璧、铜铎、盘、竹简、笛、金钗等等。到了后代,天然单位量词发达,特定的名词往往有特定的量词与之配合。这种情况,就是由于修辞需要的结果,因为它可以使表达具有形象、易知的作用。
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旗用“面”、笔用“枝”、树用“株”或“棵”、米用“粒”、水用“滴”等等,其基于修辞需要的动机是明显的。虽然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汉语中有大量的量词存在,似乎不利于学习者,会增加学习者记忆的负担。可是,从表达的角度看,丰富的量词却使汉语的表达力大大增强。而这一点,则正是汉语具有长久生命力与永久活力的原因所在。又如,上古汉语名词前的“有”字,很多汉语史论著或古汉语教材都说是词头。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是修辞现象。其他如偏义复词、比喻词、借代词等等,当初都是属于修辞现象,后来演变成了汉语语法中的词法问题。还有,古代汉语中的发语词,其产生也是基于修辞的需要,一开始是具有篇章结构修辞上的特定功能,后来成了习而不察的词汇问题(已有专文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从略④吴礼权:《关于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的断想》,“第三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10月14-16日。)。
汉语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特点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汉语语法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学者们的共识。郭绍虞先生指出汉语语法有三个特点,那便是“简易性”、“灵活性”、“复杂性”⑤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郭绍虞先生在其所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极力强调汉语语法研究要结合修辞来进行。与郭绍虞先生不谋而合,黎锦熙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他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但却都落实到了自己的文法研究之中。如《新著国语文法》,虽然是讲汉语语法的专著,但书中不仅随处都有结合修辞来阐释的精彩片断,而且还立有讲修辞的专节(第十九章“段落篇章和修辞法举例”),这是其他文法书不常见的做法。如讲名词问题,黎先生在讲到“特有名词”时就有一段结合修辞而阐发的精彩之论:
特有名词,是专属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它的上面,自然不应该加“数词”。但是造语、遣词,有时要简明而有力,往往借用特有名词来象征一种人或一事物;那么,它就变成了普通名词的性质,可以添加数量词了。例如:
纵令有“一百个”“袁盎”,能够离间它们吗?(译自苏轼《晁错论》:“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袁盎”是象征一般的“谗人”,所以上面可加“一百个”数量词,便由特名转为通名了。⑥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这里,黎先生讲特有名词首先将特有名词运用?的“常式”与“变式”作了清楚地区分。“常式”是语法现象,“变式”则是修辞现象。这样,结合语法与修辞,就将特有名词的相关问题都讲清楚了,不仅有利于读者理解,而且让读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远较一般的语法著作要高明得多。然而,黎先生并不满足于这种阐释,而是对上引文字的最后一句“由特名转为通名”作了一个补充说明:
特名转为通名,是一种修辞上的假借法,其例甚多,可是也有把通名用成特名的,那就是一种习惯了;例如从前经义中称“夫子”,是专指孔丘;史论中称“秦皇”,只指始皇,不及二世,皆是。又后来还有一种未改变的习惯,就是以地名代人名,例如称康有为为“康南海”,翁同龢为“翁常熟”等(或只称“南海”“常熟”)。此例起于唐以后;虽然当时共知其人,不致误会,却也有许多不便处,是文法的特名部分中应该改革的。(今按:现在除笔名外,旧习都已革除)。①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这个补充说明,黎先生是从修辞史的角度进行的,这在当时是难得一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一直为学界忽视,直到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才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发表与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黎先生就很重视汉语修辞史问题,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汉语语法现象很多都与汉语修辞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讲汉语文法结合汉语修辞,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一观点,郭绍虞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不厌其烦地予以强调,黎锦熙先生则在20年代的研究中就躬行实践。两位前辈一位以研究语法学为志业,一位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而扬名。虽术业有专攻,但都慧眼独具地看清了汉语的特点,以半个世纪之隔的遥相呼应,向学术界清楚地昭示了汉语语法与汉语修辞研究应该遵循的路径与方向。
二、对修辞学研究具有全局观
20世纪初,在吸收借鉴东洋日本、西洋欧美的学科体系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其间经历了几多曲折,几多坎坷,有蓬勃发展之时,亦有黯然顿寂之时”。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草创与建立时期,时间自1900年迄于1950年”。这一时期“最初二十几年,由于中国学者初次放眼看世界,看到了西洋修辞学和东洋日本修辞学与中国传统修辞学完全不同的新格局,遂在叹服与急切学习的心态下大量引进欧美与日本的修辞学思想与体系。由此便引起了引进借鉴中的负面效果,这就是早期修辞学著作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合汉语修辞实际的机械模仿的倾向。”②③ 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页。“这样,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当西洋派、东洋派修辞学著作的机械模仿弊端越来越明显时,一批崇尚中国传统修辞学的学者一方面抓住新派修辞学的弊端猛烈抨击,一方面则继续发扬、研究中国传统修辞学。由此,便展开了一场与新派修辞学的论争与较量。”“通过新旧两派的论争,一些学者逐渐看清了新旧两派修辞学各自的偏颇与弊端。由此,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了折衷调和古今中外各家修辞学说而自成一家的古今中外派修辞学。”“这一派的早期著作是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之后便有了薛祥绥的《修辞学》、陈介白的《修辞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郑业建的《修辞学提要》、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等著作相继问世,自三十年代以后,古今中外派逐渐占据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汲取古今中外修辞学的精华而又在理论与体系上自成一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的修辞学的基本格局。由此,中国现代修辞学便从草创期过渡到了建立期。”③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页。
了解到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这段历史,对正确认识黎锦熙先生的修辞学贡献,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黎锦熙先生虽然没有写出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但在《修辞学比兴篇》的序中却清楚地勾勒出了汉语修辞研究的完整体系。他预备编写的修辞学讲义共有六大篇,分别是“(一)树鹄”、“(二)明法”、“(三)遣词”、“(四)组句”、“(五)谋篇”、“(六)辨体”④杨庆蕙编选:《黎锦熙语言文字学论著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这一学科体系包括了修辞理论、修辞手法(辞格)、炼字、锻句、篇章结构、语体等六大板块,远比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修辞学著作只谈辞格(修辞手法)而不及其余的作法要科学得多。
即以修辞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修辞学名著都未能做好。如唐钺的《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可谓是20世纪初期学习借鉴西方修辞学的名著。但是,此书只是专谈辞格的著作,并未建构起一个科学全面的汉语修辞学学科体系。全书主要是参考了英国修辞学家纳斯菲尔的《高级英文作文学》(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osition),虽然“不是完全照搬纳氏的修辞学著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汉语的实际,对纳氏的修辞学体系作了‘斟酌损益’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①② 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5、222-224页。,但它毕竟只谈了辞格一个方面,没有建构起汉语修辞学的完整体系。又如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著,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出版),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为学界公认的贡献,但无庸讳言,在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方面并未完成其使命。全书12篇,第一篇是“引言”,谈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第二篇“说语辞的梗概”,谈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等问题。第三篇“修辞的两大分野”,讨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与语辞三境界的关系等问题。第四篇“消极修辞”,主要是提出了消极修辞的四个纲要,并未细论。第五篇至第九篇“积极修辞”,主要谈了38个辞格。第十篇谈“修辞现象的变化与统一”,涉及到修辞史问题。第11篇谈“文体或辞体”,主要谈“简约”与“繁丰”等四组八对辞体。全书内容,如果概括一下,主要包括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修辞格、语体等三大板块(“消极修辞”实际涉及到语法与逻辑问题)。很明显,这三大板块是不能完整概括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体系的,也不能反映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传统。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古今中外派”修辞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郑业建的《修辞学》(中正书局,1944年出版),虽然有了字句修辞方面的内容,但主体仍是讲修辞格,其他方面也都未涉及。因此,就学科体系架构来看,仍然是不完整的。其他各派,如“中土派”、“东洋派”、“西洋派”的修辞学著作,情况亦然,大多偏向谈修辞格,体系上皆呈不完整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两部白话修辞学的代表作,一是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之前在《人民日报》连载),二是张瓌一(即张志公)的《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出版)。前者主要是结合修辞谈语法问题,六个部分分别谈了“语法的基本知识”、“词汇”、“虚字”、“结构”、“表达”、“标点”等问题,由于其写作的性质,其不可能在建构汉语修辞学学科体系上有所建树,这是可以想见的。后者分五个部分,谈到修辞的定义,也谈到了“用词”、“造句”;讨论了修辞格,也说到了篇章结构,以及语体风格。虽然内容深度还很不够,但从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体系架构来看,已呈现渐趋完整的格局。至于真正完整的汉语修辞学体系建立,则是到20世纪末期才真正完成。这一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体系包括“修辞学理论-修辞格-炼字-锻句-篇章结构-语体风格”等六大板块②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5、222-224页。。
回首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再对照黎锦熙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修辞学比兴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感佩黎锦熙先生独到卓越的学术眼光。
三、善于总结归纳相关的修辞原则
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修辞学在吸收东洋(日本)、西洋(欧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中逐渐建立起来。其中,以汉语辞格的研究成果最多,研究得也较为充分。但是,绝大多数谈汉语辞格的著作在谈某一辞格时,率多沿袭“定义——例证——解说”的模式,几十年不变。相比之下,反不如南朝文论家刘勰、宋代修辞学家陈騤等人,它们的著作往往还能抽丝剥茧,提出一些修辞原则。如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论“夸张”,就曾提出过夸张的原则:“夸而有节,饰而不诬”。黎锦熙先生在论“比兴”(亦即“比喻”格)时,虽然罗列材料过多,旁征博引过度,多少带有一些训诂家的“冬烘”习气,但是他却能从诸多丛杂的材料与观点中抽引出新见,并概括成具体原则。这一点,不仅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修辞学著作胜出一筹,就是比起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些修辞学教科书或著作,也让它们显得“稍逊风骚”。如关于“显比”问题,黎先生在旁征博引了很多语料并作了一定的解析之后,提出了五条“显比要则”:
【一】者“异类”:类异情肖,貌离神合,胡越肝胆,妙趣斯出。故同类之物,显比所戒;用之即当,辞亦不藻。……
【二】者“扼要”:类取其殊,情求其肖;肖其要点,所欲比者,而弃其余,不须比者。……
【三】者“真常”:所取之譬,近在眼前,俱所熟习,是谓“常见”;无瑕可摘,斯赖“真实”。……
【四】者“强韧”:所取之譬,结以全力,是谓“加强”;如意指撝,则不失“韧”。……
【五】者立戒:引譬设喻,首戒滥用,滥则生厌,文胜质故;次戒妄用,事不须譬,用譬则妄,成蛇足故。……
规则凡五,守此不失,显比为法,乃呈效绩。效在“明了”,篇首已说。何谓明了?主旨所在,易于把捉,相悦以解,深印心曲,忘则易忆,悬想易得。①杨庆蕙编选:《黎锦熙语言文字学论著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595页。
黎先生这里所提出的“显比”五要则,是从古今汉语修辞实例的分析总结中概括出的,同时又充分融会了中国古代学者的修辞学思想乃至现代西洋修辞学理论。因此,这五条比喻原则就显得相当深刻精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对读者的语言实践特别是修辞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读者洞悉这“显比”五则,自可执简驭繁,有效地将之运用于语言实践之中。
这是就实践方面的实用意义而言。如果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这“显比五则”的提出,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更是值得珍视。如第一条“异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距离”原则或曰“新颖”原则相近,即要求喻体与本体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使比喻显得新颖生动②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这一点,无疑是卓见。第二条“扼要”原则,类于古代刘勰的“切至”原则。今日我们主张比喻要重在找出喻体与本体之间最突出的相似点,扼其要者而喻之,使喻体与本体的牵连搭挂有充分的合理性,其主旨与“扼要”说是一致的。由引可见,“扼要”原则确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第三条“真常”原则,虽然很多讲修辞的书中都讲到比喻要以习见喻陌生这个意思,但未有人将“真”与“常”结合起来,明确概括成一条修辞原则。黎锦熙先生不仅明确概括出一条原则,而且还据此提出了“好比喻”的条件,这便是“好比喻”要“俗”,而且“愈俗愈妙”。为此,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愈俗则愈清楚,愈普遍,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二)愈俗则愈恰切,愈有趣,能使听者心里生极深的印象,久后虽把正式的推论忘却,这印象还是留在心头”。很明显,这个观点也与一般学者不同,但又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提出的哗众取宠之论,而是有其心理学的理据在其中。第四条“强韧”原则,从类比论证的角度立论,倒也不失其成立的合理性。第五条“立戒”原则,即“戒滥”原则,反对滥用、妄用比喻,认为滥用比喻是违反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的修辞观,妄用比喻则是画蛇添足之举。这个道理虽然后来的一些修辞学教材或著作也有人讲到,但明确将之上升为一条修辞原则,则少见其人。况且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这更是不易。
除此“显比五则”外,黎先生还强调了守此“五则”的效绩问题,认为守此五则的效绩就是“明了”二字,并自定义“明了”二字的内涵是:“主旨所在,易于把捉,相悦以解,深印心曲,忘则易忆,悬想易得”。其意是说,比喻的作用是要通过甲乙二事物在某一点上的相似性进行牵连搭挂,从而让接受者经由由此及彼的联想,易于把握表达者所宣达的主旨;并经由比喻表达方式的新颖形象性而加深接受者的印象,愉悦地接受表达者所宣达的思想或情感;同时,经由形象地表达,唤起接受者的记忆,加强接受效果③吴礼权:《修辞心理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这种观点是符合现代修辞心理学的原理的。
四、恪守传统而又吸纳新知
黎锦熙先生在其《修辞学比兴篇》中,引了大量古代例证,同时也引述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与宋人陈骙《文则》论比喻的观点,表现了浓厚的恪守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色彩;但又没有因循守旧,更没有食古不化。相反,在论述相关问题时,他常常借鉴当时欧美修辞学的一些观点,表现了与时俱进、放眼世界的学术眼光与融会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学术功力。如此书开首一段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情想外摅,效因辞起;效率增大,或令专确,远离庸泛,斯有方式,是方式者,名“修辞法”。彼云“语式”(Figures of Speech),重言辞故;此土旧称,当于“笔法”,尚文辞故。
略依远西湼氏(J.C.Nesfield)之论,建诸法首,序为六类,六类所出,咸由“心能”:前三类者,基于理解;第四类者,基于想像;第五,情趣;第六,声色。……
显比在英语为Simile。我国古代相传诗有六义,三曰“比”(见《诗大序》);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诗正义》引);孔颖达云,“诸言‘如’者,皆比辞也”(《诗正义》。所以本篇定曰“比”;比的和所比的,其间显然有所谓比辞,故名“显比”(对“隐喻”而言)。宋陈骙定名“直喻”,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博采经传,约而论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文则》卷上,丙。按:陈氏所举十种,其第三‘类喻’,第六‘博喻’,第八‘详喻’,都可包在这‘直喻’内。)日本人所著的修辞书,都依着“直喻”这个名称。清唐彪又叫它“明喻”(《读书作文谱》卷八)。……①杨庆蕙编选:《黎锦熙语言文字学论著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这是全书开宗明义的第一段文字,作者既比较了中西修辞学在术语上的差异及其原因(西洋重言辞,故称修辞方式为“语式”;中国重文辞,故称修辞方式为“笔法”),又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对修辞格进行了分类。在讨论“显比”(即“明喻”)时,既比较了中西“显比”术语的差异,又追溯了中国“显比”学术术语的源流;既详细介绍了宋人陈骙《文则》对比喻的定名与分类,也交待了日本修辞学术语的来源。这段旁征博引的表述文字,不仅展现了黎先生学贯中西、淹通古今的渊博学识,也充分展现了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与融会古今中外于一炉的治学特点,表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治学胸襟。
又如在论述显比的第一条原则“异类”时,黎先生也是中外比较。至于《新著国语文法》第十九章“段落篇章和修辞法举例”,黎先生中外融通、与时俱进的学术作风表现得更是鲜明。在这一章,黎先生直接从欧美学者那里引进新方法,对汉语语法与修辞进行描写研究。如根据Norman Foerster的Sentences and Thinking的成法而做成的树枝式图解法,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陈望道先生有句名言,说做学问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手向古人要东西,一手向洋人要东西”。黎锦熙先生的做法,可谓是对陈望道先生治学主张的最好注脚。
黎先生恪守传统而又吸纳新知,重古不轻洋,厚古不薄今,善于将古今中外融为一炉的治学特点,不仅是他治学成功的关键,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语言学(包括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一个重要启示,这便是如何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与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有益成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确处理好借鉴国外与继承古代的关系问题。我们都知道,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学科,研究者必须同时具备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及功力,才能有集大成的学术贡献。如陈望道与黎锦熙先生,之所以能在语言学和修辞学上作出重要贡献,那是与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有关,也与他们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学术成果于一炉的学术功力有关,更与他们阔大的学术视野与独立思考的学术理念有关。
五、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
修辞现象是一种语言现象,语言是随时代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修辞现象是语言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因此它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有的修辞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文体的演变甚至交际工具的改变等,慢慢发展出来的。如现代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语言中,就有很多不为以前平面媒介时代的修辞现象;手机短信中特定修辞方式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结果。陈望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强调指出:“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②③④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新版,第244、246、249页。“辞格方面,也常有上落,有的是自然演进,有的是有意改动。”③④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新版,第244、246、249页。“辞格的项目,也不是一定不易。现在已有的或许要消灭了,现在未有的也许要产生出来。”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新版,第244、246、249页。虽然道理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与陈望道先生同时代的许多人,则更不能明白这些。
但是,与众不同的是,黎锦熙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做得很好。他在谈修辞问题时,虽然也喜欢大量使用古汉语中的辞例,但却与当时那些保守派修辞学者不同,他对白话文并不排斥。相反,在他的《修辞学比兴篇》中,他既用古汉语辞例,也用现代汉语辞例。其中,不仅有诸如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近人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梁启超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以及当代作家鲁迅的小说(如《药》、《阿Q正传》)、徐志摩的作品等经典作品的辞例,而且还有日常口语、皮黄剧(如《四郎探母》)、谚语等口语性质的材料。更有甚者,还用到了国外作家的作品,如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如《少年的悲哀》)、美国学者杜威的讲演(《现代教育的趋势》)、《旧约》雅歌、《新约》等。除此,黎先生在书中还特别举了当时人冥昭的一篇文章《春末闲谈》作为分析显比的例证,认为此文“是一首用显比的篇法构成的文章,也可说是一篇新‘经文’。”①② 杨庆蕙编选:《黎锦熙语言文字学论著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6页。举例之后,最末又有一段评论文字云:“此文后路是愤世嫉俗的随感录(作于民国14年4月),但处处顾着这个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Sir L IJin-xi’s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WU Li-quan,XIE Yuan-chun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Sir L IJin-xi’s Chinese rhetoric studies achieved remarkably and w ith characteristics,w hich are rep resented in five aspects:(i)ingenious combin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nd rheto ric study,w hich exp licates effectively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phenomena that are hard to exp lain in either way alone;(ii)a holistic view of the rhetoric study,w hich isone of the earliest complete discip linary theoretic system,w hich hence gains an initiative status in the histo ry of Chinese rhetoric; (iii)app rop riate summarization of relevant rhetoric p rincip les and due attention to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the theo ry per se; (iv)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attemp ts and the references to classical and fo reign view s fo r his unique rheto ric theo ry system;and(v)adv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w hich points out a co rrect direction for later Chinese rheto rical studies.
L IJin-xi;rhetoric;contribution‘蜾蠃用毒针射螟蛉之子’的比喻,所以篇法似松而实紧。若当经义看,其说经的方法却和《郑笺》相近。”②如此高度评价当时人的白话文修辞,实是旷古未有!相比于“五四”时代一些保守派学者所谓“唯有文言可以修辞,白话不能修辞”的偏见,其眼光与识见之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计矣。虽然从黎先生书中所举辞例数量看,现代汉语的用例相较于古汉语辞例少得很多,但黎先生如此高度肯定白话文修辞的价值,可见其有很强的与时俱进的意识,真正懂得修辞现象是发展变化的道理,这与当时反对白话文,否认白话文能够修辞的人比起来,其修辞观不知要高明多少。
H146
A
1002-0209(2010)05-0074-07
2010-06-24
吴礼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当然,黎锦熙先生在汉语修辞学研究方面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对修辞学研究作用的认识,对偏义复词形成原因的探讨入而未深,等等,都是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不可苛求于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