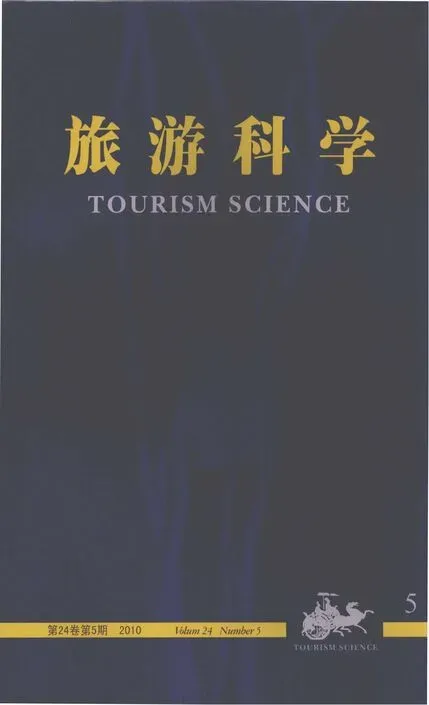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探析
2010-11-27徐本鑫
徐本鑫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5)
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The InternationalUnion forConservation ofNature,IUCN)所界定的概念,自然保护地(p rotected areas)是“一块清晰界定的,以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认可的、旨在实现长期保存自然以及相关生态系统的服务和文化价值(ecosystem services and cu ltural values)的地理空间 (geographical space)”[1]。为加强对自然的保护,中国建立了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但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旅游资源的高度开发,“许多风景区出现商业化、园林化、城镇化现象,……这些‘乱象’的出现”[2],亟需社会各界做出回应。法制建设是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基础,也是自然保护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问题对于完善自然保护地立法,促进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和旅游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现状透视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从无到有;特别是开展自然保护国际合作以来,中国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自然保护地的诸多事务作了制度安排。总体上看,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既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特点,也存在许多不足。
1.1 特点:类型化部门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相结合
中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与其对保护地的分类模式密切相关。中国没有采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地”的概念,而是以保护对象的自然属性为主要依据,设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保护区、自然遗迹、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等保护地类型。
从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模式来看,综合性立法尚未形成,类型化部门立法形形色色。类型化部门立法是指,在将保护地按保护对象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由各主管部门就其管理对象制定单行法规。已有的立法如林业部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文化部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地质矿产部的《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单行立法。
中国至今没有一部自然保护地基本法。国务院于 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下文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具有一定的综合立法的性质,然而《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林业部 1985年发布)还先于《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自然保护区条例》作为《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指导性上位法缺乏立法依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范中的自然保护规定来看,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呈现出类型化部门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相结合的特点。
1.2 反思:现行立法模式的缺陷
中国现行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下的法律法规对引导和规范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立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1.2.1 立法层级低,法制统一性不足
在中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地法规中,《自然保护区条例》属行政法规层级,在层次上不能统领其他自然保护地立法,在效力上也不能有效地协调各自然保护地的部门立法。而《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属于行政规章,其效力层级就更低了。承载着大量风景遗产和文化景观的自然保护地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旅游胜地,而且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文化传承的特殊区域。随着社会对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行政法规的效力等级与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地位已明显不符。检视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地的立法情况,美国的《国家公园基本法》、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特保自然区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日本的《自然环境保全法》等,都是以保护自然为目的的高层级的综合性立法①参见:朱广庆.国外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与管理体制[J].环境保护,2002(4):10-13;王权典.再论自然保护区立法基本问题——兼评《自然保护地法》与《自然保护区域法》之草案稿[J].中州学刊,2007(3): 92-96.。
法制统一性不足首先体现在立法依据不统一上。例如,《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林业部,1985)的制定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1995)则主要是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的。针对同样级别的自然保护地所进行的立法,在指导思想和上位法上并不统一。法制统一性不足还体现在立法内容的冲突上。例如,《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必须“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并提出审批意见,报国务院批准”。但是《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农业部,1997)却规定 ,“国家级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需经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国家级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其设立程序中却没有涉及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由此可见,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之间在部分具体内容上产生了冲突。
1.2.2 立法体系封闭,制度建设滞后于实际需要
如前所述,中国对自然保护地的分类是基于保护对象的自然属性,这与 IUCN基于管理目标对保护地进行的分类不同。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 14529-93),根据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将自然保护区分为三个类别九个类型①三个类别为:自然生态系统类别,野生生物类别,自然遗迹类别。九个类型为: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物类型,野生植物类型,地质遗迹类型和古生物遗迹类型。;与 IUCN“保护地”的定义及分类②依据自然保护地在主要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上的不同,IUCN将自然保护地分为六类,依次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Stric tNature Reserve)/荒野地 (W ilderness A rea)、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自然遗迹或特征(NaturalMonumentor Feature)、栖息地或物种管理地 (Habitat/SpeciesM anagementA rea)、受保护的陆地景观或海洋景观(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以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地 (Pro tec ted A rea w ith Sustainab le U se of Natu ral Resources)。相比,它显然没有把国家公园、风景∕海景保护地等保护地类型纳入立法[3]。不仅如此,目前中国各类型的自然保护地部门规章只有六部③《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林业部,1985)、《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林业部, 1993)、《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1995)、《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地质矿产部,1995)、《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农业部,1997)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化部,2006)。,且类型与国家标准也不完全对应。自然保护地综合性立法的缺失和自然保护地分类模式的缺陷造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封闭。类型化的自然保护地立法在保护对象上未能涵盖自然保护地的所有类型,存在不少立法空白。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是在强大的资源压力和抢救性保护政策导向下发展起来的。现有的自然保护地立法只是将自然资源保护规则和污染控制规则简单组合,是经济优先思想指导下的被简化的特殊区域保护法,其正面临着数量与质量、保护与利用及如何有效管理等各种问题,需在立法体系上加以解决。而且,中国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和一些有关自然保护的国际公约,需要通过完善国内立法来兑现国际义务。还有一些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立法尚属空白,亟需纳入法制轨道。
1.2.3 部门立法弊端多,地方立法缺乏协调性
中国现行的关于自然保护地的六部“管理办法 (规定)”分别由国务院所属的不同部门制定,各部门往往不能从全局考虑,而是较多地考虑本部门、本系统的利益,从各自的角度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关资源。各部规章之间相互协调性差,系统性不强,“不但未形成协同统一的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的规范体系,反而成为扩展部门权力、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4]。如何在立法中达到各个部门利益均衡,实现部门责任与利益并举,实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共赢目的,是自然区保护立法中的关键性问题[5]。
部门立法模式导致中国现行自然保护地法大多属行政法规范。以部门规章形式表现的行政法规范受其自身能效的限制而给地方保护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例如,关于自然保护地的变更和撤销,能找到的法律依据只有《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自然保护区的撤销及其性质、范围、界线的调整或者改变,应当经原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批准。”但是,条款中没有具体规定因何种原因、有何种情形、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为之,将撤销或变更自然保护区的权力交给了地方政府,这样,地方政府以地方经济建设需要为由即可“合法”地裁剪自然保护区了。
自然保护地的地方性立法是中国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大多属于专门立法。单项专门立法的针对性虽强但往往缺乏综合性法所具有的全局意识和统筹优势,法制的内在协调性差。如,200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普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以及舟山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普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与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风景名胜区条例》(简称《条例》)就有诸多不协调的地方。《办法》对在风景区内采石、采沙,在建筑、树木上刻、划、涂、写等行为,对不符合规划要求在风景区内设置大型户外广告以及张贴各类宣传品等违法行为规定的罚款数额与《条例》明显不符[6]。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除加强各保护地内部的制度构建外,还要及时修正已经过时的或不协调的法规规章,以实现法律的协调和统一。
1.2.4 法律概念模糊,保护对象不明确
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采用“自然保护地”的概念,而是广泛采用“自然保护区”这一概念。《自然保护区条例》第 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然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三者之间存在交叉,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又存在重叠,加之主管部门不同,给管理和保护工作增加了难度[7]。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的重要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因此,明确“自然保护地”这一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明确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保护对象及其范围的关键。对同一保护对象在概念阐述或理解上不统一,极可能导致以下两种后果:一是出现对保护对象的多重管辖或无人管辖的局面,致使某些自然资源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有效保护;二是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保护对象的范围与边界,无从适用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地的政策措施,也就难以实现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目标。
2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的选择应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综合考量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后的客观表达。
2.1 “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
自然保护地的和谐秩序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然而,自然保护地开发建设中的种种“乱象”,暴露了政府规制中的工作重心“错位”——过于重视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漠视过度开发对于旅游资源的破坏;还暴露了政府规制中的利益“失衡”——过于照顾企业利益,损伤了原居民、旅游者的利益[2]。因此,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实质是建立健全以界定利益关系、规范逐利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协调机制。明确与自然保护地有关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自然保护地立法应重点考量的因素之一。
在目前情况下应重点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土地管理权与土地所有权混合在一起造成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自然保护区(地)的设立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利益,并同时利用土地管理权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的优势地位,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与民争利[8]。国家通过立法简单地禁止或限制在保护地内进行某些行为是一种对保护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物权的剥夺或限制,因此会导致管理机构对于资源保护的管理权和土地权益人的物权之间的严重矛盾和冲突[9]。要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传统的类型化部门立法模式难以胜任。只有能很好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性立法才能增强与自然保护地有关的各主体遵守和使用自然保护地法的利益驱动,实现自然保护地“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和科学发展。
2.2 “自然资源系统”的一体保护
20世纪的自然保护地法主要是以维护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自然资源利用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及立法原则上,都没有突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土及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而这些精神正是自然保护区 (地)法的“灵魂”所在[10]。自然资源不仅包括生态系统层面的生物多样性,自然与文化相融而成的景观多样性,也包括诸多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各类保护地所承载的各种自然资源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共存于自然界的,其中任何一种资源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资源的变化,任何一种类型保护地的变化也极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类型保护地的变化。这就要求改变以往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内分区而治、各自为政的立法和管理模式。保护地立法模式的选择要着眼于自然资源系统的整体性,注重各类保护地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促进自然保护地整体效益的发挥。
2.3 “社会法治化”的客观要求
实现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是自然保护地法治化的客观要求。自然保护地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在内的动态的系统工程,推进保护地法治化进程离不开上述各环节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从中国自然保护地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无论其表现为哪个方面的问题,追根溯源还是立法的问题,即现有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不科学、不健全,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实际需要。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源上着手解决问题。此外,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不应满足于点状、片状的局部保护,也不应是简单的区域分割和资源保留,而应该主动地去建设、管理、维护、恢复甚至重建绿色空间网络,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自然保护地立法不仅要满足现阶段的需求,而且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立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又具有足够的开放性。
3 中国自然保护地综合性框架立法模式的构建路径
反思中国自然保护地现有立法模式的缺陷,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是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的必经之路。美国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特点主要有:①参见: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3-24页;杨锐《美国国家公园的立法和执法》,载《中国园林》2003年第 4期,第63-66页。以《国家公园基本法》作为其他国家公园立法的立法依据和指导原则;②有与《国家公园基本法》配套的可操作性强的单行法律,如《国家公园及娱乐法案》、《国家公园署组织法》等;③对特定国家公园进行立法,如《黄石国家公园法》,通过此类立法解决特定国家公园内出现的特殊问题,从而使国家公园的立法体系得以完善;④其他自然资源法律对国家公园也有相关规定,如《鱼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①。借鉴他国的经验,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努力。
3.1 加强综合立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地法》
基于中国自然保护与生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提高立法层级,是克服现行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弊端的必然选择。也就是,针对中国自然保护地法制建设的现状,“制定一部能涵盖我国各类型自然保护区(地)建设与管理的综合性立法确有必要”[11]。综合性立法就是基于系统论原理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控制方法。综合性立法将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保护地的特点,对于保护地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活动做出原则性规定,能够很好地协调各保护地相关立法之间的关系。
从立法理念上看,自然保护地综合立法应充分尊重保护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体现科技立法、跨部门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公众参与立法的特点和要求。应按照自然保护优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公众参与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
从立法内容上看,自然保护地综合立法是关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体化设计。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的制约作用,将自然保护地的设立与管理、土地权属与当地居民权利保障、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做出统一的制度设计。
从立法名称上考虑,建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地法”。虽然采用“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可能存在不妥之处,有专指“陆地”之嫌,但至少是创造了一个超越目前的自然保护区的狭窄范围而将所有需要保护的地理空间纳入其中的机会。在“保护地”前加上“自然”一词,一是沿用“自然保护”的用词习惯,二是“自然一词有两个主要的含义:它或者是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的集合所构成的整个系统,或者是指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的样子所是的事物”[12]。自然的系统性和本原性应体现于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之中。而且,IUCN的“保护地”概念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本着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中国目前应该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自然保护地法”。
3.2 完善框架立法,构建合理的保护地分类体系
框架性立法就是将立法置于一个合理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是对各自为政的部门单行立法之固有缺陷的一种克服。自然保护地框架立法能够用一种整体的观念看待环境资源问题,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为价值取向的一体化制度设计,为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地提供一个灵活的法律框架 。同时,保护地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必须按照其不同类型,分别制定不同的法律,不能“—勺烩、一锅粥”。这是有效保护不同类型保护地的可靠的立法保障,否则只能空谈保护[13]。所以,还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地法”的框架内,补充制定或修改完善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办法”,确保各类保护地实现其发展目标。必要时可以通过地方人大或政府制定具体自然保护地的“实施细则”。
选择综合性框架立法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建立起合理的保护地分类体系至关重要。IUCN在 2008年版的《保护地管理类别运用指南》(Guidelines forApp lying Protected A reasM anagem entCategories)中依据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的不同将保护地划分为六类 (具体类别前文已述)。对于管理目标,该指南作了“主要管理目标”和“其他管理目标”的细分。主要管理目标是划分自然保护地类别的基础。一类自然保护地具有一个主要管理目标,只有在主要管理目标实现的情况下才考虑实现其他目标。同时,该指南还认为对主要管理目标的确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某类划分为严格保护类别的区域,其自然恢复不能实现而持续的人工干预方法成为必需的时候,调整这类区域为其他类别则更为合适。这说明管理方法的选择在保护地类别的划分中还具有矫正功能。这样做可以避免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的僵化,为构建合理的保护地分类体系提供了可能。
有学者认为,对自然保护地按照“严格保护”、“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择项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利用”三个等级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分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4]。这一分类方式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目的,即通过立法来协调保护地的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这一分类方式与 IUCN的分类体系也不冲突。IUCN是按照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对保护地进行分类的,而管理目标的差异与保护或开发的力度是具有一致性的。这种按照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或开发力度进行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做法能够革除目前我们依自然要素进行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弊端,既能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目的,又不会与 IUCN依管理目标而进行的功能性分类相冲突,具有合理性,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4 结语
自然保护地具有经济、生态、文化与美学上的多元价值,需要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到法律的多主体和全方位的关注。本文针对自然保护地立法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许综合性框架立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而且这一立法模式的实践也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对中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不能受到冷落,各级政府或立法机关也不应该碍于某种阻力而延迟采取行动。
[1] Dud ley N.(Editor).Guidelines for App lying Pro tected A rea M anagem ent Categories.Gland [Z].Sw itzerland:IUCN,2008:8.
[2] 章尚正,马贤胜.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制衡机制失衡与政府规制优化[J].旅游科学, 2009(5):1-8.
[3] 王权典.再论自然保护区立法基本问题——兼评《自然保护地法》与《自然保护区域法》之草案稿[J].中州学刊,2007(3):92-96.
[4] 王献溥,崔国发.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240.
[5] 张强,薛惠锋,刘雪艳.自然保护区立法中部门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2009 (9):91-95.
[6] 龚正.试论《风景名胜区条例》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兼论普陀山景区的应对[J].旅游科学,2007(2):73-80.
[7] 何吉成,徐雨晴.对铁路选线涉及的景观保护区法规的解读 [J].中国园林,2010(3): 36-39.
[8] 温兴来,包李梅.自然保护地的土地权属法律问题研究[J].知识经济,2010(8):35-36.
[9] 邓禾.中国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0]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16-17.
[11] 肖建华,胡美灵.国内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争议与重构[J].法学杂志,2009(10):67-69.
[12] 吴国盛.追思自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328.
[13] 余久华.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M].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136.
[14] 周珂.环境法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