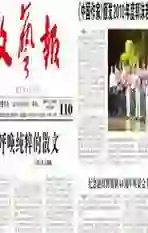重返历史的平庸之旅——评《莎拉的钥匙》
2010-11-25苏宛
苏 宛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凭借自己的法、美双重文化背景,创作了一部当代人游走欧美数国,寻访二战中冬季赛车场大圈押幸存者的小说。女记者“我”拨开60年的历史尘埃,将真相饲喂于人,犹太女孩莎拉仍在人世的旧识和他们的后人中有人喟叹,有人释然,有人重获新生,也有人几近崩溃。
有人在《莎拉的故事》中品味出“两个时代的两种人生”(法国《文化周刊》),更有人说作者让莎拉“重返我们的世界”(《出版人周刊》)。然而,莎拉和“我”都以第一人称视角讲故事,只会让两条叙事线索里的莎拉两相消解,都站不住脚。
“我”与莎拉间隔60年的相遇
后人在虚构小说时,用什么身份,以怎样的姿态进入没有经历过的沉重历史?有些小说如同金庸的武侠,人物虚虚实实,在材料和想象力的帮助下,像史学家一样径直书写过去,比如小说《辛德勒的名单》。还有一些作品曲径通幽,那些后来人、那些历史的入侵者,不论是不是作为第一人称出现,都往往作为旁观的叙事人,在阳光普照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认识个把“有故事”的人,揭开一段可怖历史中的个人黑暗秘史。名作《苏菲的抉择》和《朗读者》都是这样结构的。
碰触20世纪灭绝人性暴行的作者,往往将侦探小说的笔法用作常规武器,“有故事”的人不愿想起的过去是悬疑,为了遗忘而讲的谎言是伪证,叙事人的揭秘是推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后人直接切入这些历史段落的困难。更多的时候,20世纪白晃晃的真实可以将一切平铺直叙的文字烧灼到虚无,作者不得不找一些虚饰稍加遮掩。
《莎拉的钥匙》看起来也是这样一个阳光下的侦探故事,不同的是,作者的叙事在1942年和2002年两个时段交叉推进。犹太小女孩被法国警察秘密逮捕、圈押、送往集中营、逃走、回巴黎寻找她关在壁橱里的弟弟。“我”为了给杂志撰稿,一边四处搜集这一历史事件的材料,一边打理家里的烦心事:意外怀孕,在丈夫的反对下面临堕胎与否的选择。直至“我”发现莎拉原先就住在自己即将搬入的老宅,两条线索会合,“莎拉”的视角消失了,“我”开始一点点揭秘莎拉的战后生活。
“是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小说在两个时空同时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尽管莎拉以第三人称出现。这样,逻辑上有了两个莎拉:一个是“我”——记者嘉蒙德女士在照片上、信笺上、遗书上和人们的回忆口述中渐渐拼接起来的模糊旧影,她只存在于“我”的话语中;另一个是事主用进行时现场播报。既然“我”的话语只能勾勒出剪影,莎拉抛开“我”这一层,自己跳到读者面前倾诉,有多可信?
莎拉已经去世多年,生前她对前半生守口如瓶,“我”不可能得到莎拉的自述。为什么作者敢于无视这两个视角之间的裂痕?因为“我”以为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冬季赛车场的遗址前,“我看到他们被推进汽修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我看到了那张惹人喜爱的心形小脸”。
也许作者自己也曾站在那里,以为自己既可以作为一个资料整理人,又可以借用一个犹太孩子的眼睛。这两种身份选择任何一个,在逝者面前都是谦卑的,但两个都选,则是普世主义的傲慢。
一个乏味的访客
本质上,作者几乎放弃了疑惑和拷问。作为一个历史的访客,“我”以好莱坞大片似的人道主义浪漫情怀应对扑面而来的所有信息。种族灭绝、法国人对同胞的冷漠,仿佛是维基百科的词条或者教科书上的定论,摆在那里而已,不需要再拆开来讨论。仿佛在当代,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恐怖片一样的历史残片,只是一个已经标本化的,仅用于同情和谴责的客体。
人问她:“你为什么要道歉,你是一个美国人,难道为美国没有在1944年解放法国道歉?”嘉蒙德女士答道:“我为我这么多年不知道这件事情而道歉。”为了知道并感到抱歉,就打翻一票人平静的生活,直到将莎拉毫不知情的儿子折腾到妻离子散,这还是强势的普世主义作祟。“我”以为谁都像自己一样想知情,想沉浸在同情中。
莎拉在写给自己的诗里说她“记住了!永不忘记!”可是她向儿子隐瞒了一切,这也许是她对孩子最深沉的爱和保护,这个保护罩居然在几十年后还能被一个鲁莽而自大的访客打得粉碎。无怪乎整篇小说重心失调,嘉蒙德女士的婚姻困境和个性觉醒占据了太多的篇幅。作者的本意是历史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但莎拉除了让“我”珍视生命,就是让“我”参与到一个足够重大的事件中,以至于不再纠缠于家庭的烦扰。法国警察——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在小说中的缺席,也暗示了作者事实上避免了与历史正面遭遇。这终究是一个嘉蒙德女士的故事,而不是莎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