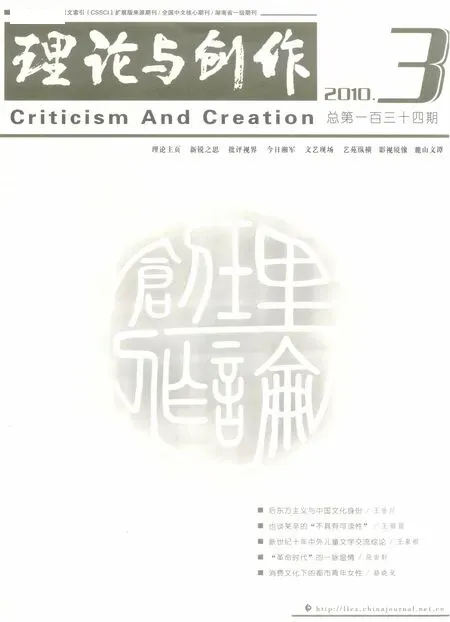论沈从文小说《丈夫》的音乐结构
2010-11-25谭文鑫
■ 谭文鑫
一
沈从文曾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谈到音乐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手中笔知有意识来使用,一面保留乡村风景画的多样色调,一面还能注意音乐中的复合过程,来处理问题时,是民十七写《柏子》,民十八九写《腐烂》,写《丈夫》,写《灯》和《会明》。这些文章当时实为大多数同学举例用。①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沈从文在创作《丈夫》等小说时自觉借鉴了音乐手法。其二,他对音乐的借鉴主要体现在结构层面,即用“音乐中的复合过程”来铺排小说情节②。
众所周知,文学与音乐都是时间艺术,二者的存在方式均体现为一个“过程”。它们的结构便都建立在“过程”之上。然就一般而言,文学与音乐的结构却相去甚远。譬如小说,尤其是叙事型小说,一般采用的是线性结构,即按时间顺序将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交待清楚。即或有时运用倒叙手法打破时间性的叙事链条,造成悬念,但仍可将其视为线性结构的变体。
音乐中的曲式结构则不同。不同之原因正如波兰著名音乐美学家丽莎所言,“各门艺术之间的区别,其根源在于其物质材料”。③众所周知,音乐采用的物质材料是声音。而声音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这使得作曲者,在初次陈述主题(乐思)之后,往往要对它进行重复和再现,就算主题在发展时一般也会保留与原始主题的内在统一。④所以,音乐多采用环状结构。⑤如果说得更为精准点,应是螺旋式环状结构,因为在大部分乐曲,尤其是器乐曲中,主题在重现时常常会有变化。音乐曲式因对主题进行重复和再现,故能不断强化对情感的表现。这正是音乐结构优于文学结构之处,亦是沈从文跨艺术门类移植结构的原因所在。至于《丈夫》具体参照了何种音乐结构,笔者认为应是奏鸣曲式。
在各种音乐曲式中,奏鸣曲式最复杂,同时也最适合表现矛盾冲突。其整体结构具有三部性的特征:第一部分称为“呈示部”,在主调和副调上分别呈示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第二部分是“展开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呈示部材料中矛盾冲突的继续发展和更加剧烈的积极展开;第三部分为“再现部”,再现的各个主题之间对比有了新的发展,乐思在经历了剧烈冲突后形成了新的统一关系,两个主题的调性彼此靠拢附合。因而不会像三部曲式那样原样再现。奏鸣曲式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双主题呈示,及主题矛盾冲突在展开部展开;二是调性在呈示部中对置,于再现部中统一。⑥在大型音乐作品(如奏鸣曲和交响乐)中,第一乐章往往采用奏鸣曲式。
二
《丈夫》是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其结构上的布局安排对应于奏鸣曲式:全篇共六节(每小节均有较为完整的意思,相当于音乐中的乐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节)为引子,主要是背景知识的介绍;第二部分(第2、3节)为呈示部,呈现了小说的主部主题(即丈夫尊严的沉睡)和副部主题(即丈夫尊严的觉醒);第三部分(第4、5节)是发展部,两个主题在此既横向对比,又纵向发展;第四部分(第6节)是再现部,两主题均得以复现。小说因而呈现出典型的环状结构。
让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引子部分。与《柏子》相仿,小说从与主题相去较远的景物写起,就像音乐从远处缓缓响起。接着,便引出河边“烟船妓船”上的妇人,——她们大多来自乡下,因贫穷,离家来到船上卖淫。不过,她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做生意而已,“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⑦就这样,卖淫的乡下妇人渐渐变成了城里人,于是就毁了。
至于她们的丈夫,同样认为此事稀松平常。因为妻子出来做生意可为穷困之家带来不少经济收益。“这种丈夫”(即没有尊严的丈夫)想见妻子时,就像走访远亲一样上城来慢慢找。找到后,会为妻子的城里人打扮吃惊不已。到了晚上,来了客,丈夫就躲到后舱。或许这时,他会觉得孤独而想回家。可晚间路甚险恶,况且船上大娘邀他看夜戏,喝清茶。于是又留下来。睡觉时,“太太”(作者对卖淫妇人的讥讽性称谓)陪着客人,丈夫则在后舱一个人睡。尽管他心中会有些不平,但只要“太太”抽空到后舱送冰糖吃,“丈夫把冰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妻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⑧小说还指出,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女子出乡卖身,男人皆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总有一部分归他。⑨
由此可见,丈夫的尊严感已在生活的重压下完全陷入沉睡中。
为使主部主题的呈现不显突兀(毕竟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罕见),引子部分花了不少笔墨解释丈夫尊严缘何沉睡的社会原因。沈从文一直都强调小说背景环境的介绍,因为人是“环境中的个体”,人物特定的言行只会出现在特定环境中。因而,引子看似游离于小说主体结构之外,其实必不可少,——它为后面主题的呈示及情节的展开筑下了坚实基础。
从第二节始,小说进入到呈示部。首先出场的是水保。他虽只有一只眼睛,“但两只眼睛不能分明的,他一只眼睛却办到了。”⑩因为正直道德,他做了不少妓女的干爹。一天,为配合岸上的案件调查,他准备先问问船上是否留宿行为不正的外乡人。巡查时,他在干女儿七丫头的船上发现一陌生年轻男子。经询问得知是老七汉子,昨晚来的。于是,便进船舱与其交谈。两人聊了大半天。水保因事要走,临走前嘱咐丈夫,要老七今晚别接客,他要来,还想请丈夫喝酒交朋友。此节呈示了小说的主部主题,即丈夫尊严的沉睡,——妻子整晚都在陪客人,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后舱。并且,第二天与水保聊天时完全不因妻子陪客而感到半点羞辱,因为他觉得这只是在“做生意”。
第二节随着水保的离开而结束。接下一节为副部主题的呈示。其开端是个连接部,——丈夫最初猜测老水保一定是妻子的“熟客”和“财神”,因而很高兴,甚至唱起歌来。显然,这是主部主题的延续。但不久之后,故事情节出现突转,——做午饭时,老七她们还没有回来。丈夫因不会烧湿柴而无法做饭。饥饿中,“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正似乎为装满了钱钞便极其骄傲模样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现时,把和平已失去了。一个用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即老水保的脸,引者注),也是极其讨厌的神气,保留在印象上。”⑪他还记起水保临走前的嘱咐,这令其更为愤怒。虽从后面情节来看,他误会了水保,然这一事件促成了丈夫尊严由沉睡到苏醒的巨大转变,——“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身份,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⑬加之因湿柴又导致了“新的愤怒”。这使“年青人感到羞辱,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要走路。”⑬由此可见,小说的副部主题为丈夫尊严的觉醒。
从第四节始,小说进入到发展部。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在其间交织推进。丈夫在街尾遇到了妻子。他开始坚持要回家,因为尊严已觉醒,这是副部主题的发展。但见妻子不允,且明白胡琴是特意为他而买,故未离去。回到船舱后,他便开始调琴,“生疏的音响从指间流出,拉琴人便快乐的微笑了。”由此可见,丈夫觉醒的尊严在妻子温情的“催眠”下,又陷入沉睡之中。这是主部主题的展开。
第五节,故事时间直接跨至晚上:
到了晚上,前舱盖了蓬,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灯罩子有红纸剪成的遮光帽,全舱灯光如办大喜事作红颜色,年青人在热闹中像过年,心上开了花。⑭
此时,男子已完全忘记所受屈辱。这仍是主部主题在延续。
然快乐的琴声与歌声却使他蒙受了更大的凌辱,——两个醉酒的兵士循声来到船边,嚷着要取乐。顿时,船舱里“琴声嘎然而止,沉静了。”这两兵士气势汹汹闯进来继续胡闹,丈夫慌忙拿着胡琴躲到后舱。
接着,沈从文在三个小情境中极细腻地表现了丈夫的言行:首先是大娘问他先前水保说了什么时,回答是这样的:“他说一定要来,一定莫留客,……还说一定要请我喝酒。”⑯句中的省略号并非笔者所加,为原文所有,表明他说话时在此有一较长停顿。可见,丈夫先前感受到的愤怒和屈辱又重新复现。其次是他听大娘说兵士在船上睡了之后,回了句:“睡——?”破折号表示语气的延长,问号意味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的脸色有多么难看。第三是兵士走后,他始终躲在后舱不出来。显而易见,兵士的刺激让丈夫沉睡的尊严再次觉醒。这是副部主题的发展。
半夜时,巡官在水保陪同下来查船。得知新来的男子是老七汉子后,便离开了。但随后又派人告知晚上还要回来“过细考察”(即嫖宿,引者注)老七。乍一看,巡官完全无视着丈夫的存在,可他并非故意要让后者难堪,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地实在是太普遍平常了。大娘清楚“考察”的含义,很开心。而丈夫则完全蒙在鼓里。他“这时节望到老七睡起的样子,上半晚的气已经没有了,他愿意讲和,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话,商量件事情,就傍床沿坐定不动。”⑯对妻子的爱让他不再计较所受侮辱。这是主部主题的继续展开。老七却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心中很痛苦,因而“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小说中顿时没了一丝声音,变得很静,——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静。
之后情节,按一般写作者的处理,会极度渲染巡官带给丈夫的屈辱,进而形成高潮。沈从文没有落入俗套,他把这一段完全跳过,一下写到第二天一早。虽然,我们在文本中见到的只是两小节间一段没有文字的空白,但正是这一空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换言之,沈从文虽在此省略了对副部主题的表现,但因省略而留出的空白就像音乐中的休止符一样,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第六节是再现部。两大主题均得以再现。沈从文一方面通过老七叙说去干爹家吃饭、看戏等事件复现主部主题。另外,也再现了副部主题,——此时,丈夫的尊严已完全觉醒:
男子一大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话不说,……男子摇摇头,把票子(妻子给他的钱,引者注)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⑰
丈夫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遭受的屈辱实在太多,胸膛即使再宽阔也无法容纳,终于爆发。但这是一种弱者的爆发:因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他无法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去索取失去的尊严,而只能哭泣。作者在“哭”前加了一个“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定语,显然是想让叙述笔调变得客观冷静,却令读者心中泛起更大悲哀。
结尾处出现的人物是水保,由他引出“两夫妇一早皆回转乡下去了”的结局。综观全篇,小说以水保始,又以水保终,因而获得了完满的结束感。
三
或许有人会质疑,《丈夫》的情节其实就是表现了主人公尊严的逐渐觉醒,以上论述似乎将其复杂化了。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
假若《丈夫》是表现主人公尊严的逐渐觉醒,那么小说就会采用一种渐进式的写法:开始是其尊严沉睡很深,因受屈辱慢慢苏醒;然后半睡半醒,此时他内心可能会有激烈冲突:是要尊严还是要经济利益;最后,因一个强烈外在刺激而完全醒来。这种处理方式在以往小说创作中较常见。譬如,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就是这般写侯忠全老汉的“醒悟”。
沈从文对《丈夫》的情节安排则完全突破了常规。小说中,沉睡与觉醒作为对立的两极,作者让丈夫的尊严在其间游走,但只在两极而不在中间停留。换言之,沈从文让其尊严要么沉睡,要么觉醒,不存在半睡半醒,即冲突中的状态。这种处理初看异常,却完全合理可行,——社会环境因素令丈夫尊严沉睡很深,就算醒来,一经“催眠”很容易再次睡着;可他所受的屈辱同样很深,且一次次更甚,因而尊严从沉睡中惊醒也完全可能。小说主要表现了丈夫尊严的这两种状态及其相互转换,而未去刻写屈辱和经济利益带给他的激烈内心冲突。
前面提及的那种意识逐渐苏醒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线性模式。《丈夫》在结构上与之截然相异。整篇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三留三去”揭示其尊严的“三睡三醒”——丈夫最初留在船上,同水保交谈时也没有丝毫的屈辱感,表明尊严尚处在沉睡中;随后,他因水保的不尊重而愤怒离开,尊严开始醒来。接着,在妻子温情的“催眠”下,他留下来了,尊严复沉睡;可晚上,醉酒兵士令其再度蒙羞,这时他肯定想走,只是夜间“三十里路上有豺狗,有野猫,有查夜放哨的团丁,全是不好惹的东西,转去实在做不到。”⑱无奈只得留下,实质上是一种“欲去之留”,所以尊严又醒来。后因疼爱妻子,愿意讲和,“就傍床沿坐定不动”,丈夫尊严再次沉睡;第二天一早,男子一起来就决意离开,其尊严因巡官的侮辱而完全惊醒,不复沉睡。这种模式虽也包含逐渐递进的过程,但它更像是音乐环状结构,——尊严的睡与醒这两个对立的主题反复出现,并不断模进强化。与单纯的线性模式相比,这种螺旋式上升的环状结构更能揭示出丈夫尊严沉睡之深与所受屈辱之重,对读者情感上的冲击也能一步步增强,并在最后达到高潮。难怪聂绀弩读完之后,会发出这样的赞誉: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⑲
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亦是沈从文借鉴奏鸣曲式的目的所在。
最后需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丈夫》完全照搬了奏鸣曲式。事实上,这不可能,因为偏差在所避免。譬如,音乐的调性,文学作品就极难移植。举个例子,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勒格尔》虽在英国学者布朗看来采用了奏鸣曲式,——小说中有汉斯与英格两个主题,且结构可分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⑳。但该小说并未将两个主题分别置于主、副调上呈示。《丈夫》同样没有调性表现。由此可见,它对音乐曲式的模仿只是大致。
其实,文学结构也完全没有必要全盘照搬音乐曲式,毕竟二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笔者认为,沈从文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握住了音乐曲式最本质的核心,即螺旋式环状结构,并大胆地用这种结构置换了文学中传统的线性模式,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情感表现力,真正实现了文学与音乐的交融。
注 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②文学与音乐都具时间性,这确保了文学在结构上借鉴音乐的可行性。沈从文亦敏锐地体察到这一点。他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一文中说,“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有些相通地方,即组织。音乐和小说同样是从过程产生效果的。”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此外,他虽一再声称自己对于音乐是个门外汉,但事实上,他精通音乐结构。譬如黄永玉的一段回忆文字:“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哈,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参见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另如,他在1970年写给张兆和的信中,确切指出《红卫星上天》一诗“照组织有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启发”。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③丽莎著,于润洋译:《论音乐的特殊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④著名音乐理论家杨儒怀先生极为强调重复和再现在音乐中的重要性,他说:“音乐发展的最简单的基本手法使重复,但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手法。意义在于:它可以突出被重复的乐思,使人加深感受。短小而又重要的乐思,重复就更加必要……再现与直接重复不同,它是在新的乐思陈述之后再重复。因此再现就使第一次出现的乐思地位突出并成为这段音乐的主导内容,同时起着结构和主题材料的概括统一的作用。”参见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册)1995年版,第97-98页。
⑤以上论述参考了布朗的观点,他认为:“音乐的发展过程是环状的,但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线性的。”不过,他并未对二者结构不同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参见Calvin S.Brown.Music and Literature—A Comparison of the Arts[M].New England:University Pressof New England,1987:165。此外,瞿世镜在《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一书中也谈到了音乐的“环状结构”。但他认为这一结构产生的原因是乐曲开始和结束的音符都是同一调性的主音,笔者认为不妥。音乐的主音的确是整部乐曲的引力中心,且一般出现在结束位置上,但不一定就是开始的第一个音,譬如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的主音是1,但起始音符是3。笔者认为音乐环状结构产生的原因,跟声音这一物质载体转瞬即逝,因而音乐主题需重复和再现有关。当然并非所有曲式都有环状性,譬如,并列曲式便没有再现部分。但它多用于声乐曲中,靠歌词来强化并列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⑥李虻:《音乐作品曲式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⑦⑧⑨⑩⑪⑬⑬⑭⑯⑯⑰⑱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8页、第50页、第50页、第50页、第57页、第57页、第58页、第60页、第62页、第64页、第65页、第49页。
⑲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曹禺也认为“《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参见巴金等:《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出版,第349页。
⑳Calvin S.Brown.M usic and Literature—A Comparison of the Arts[M].New England:University Pressof New England,1987:21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