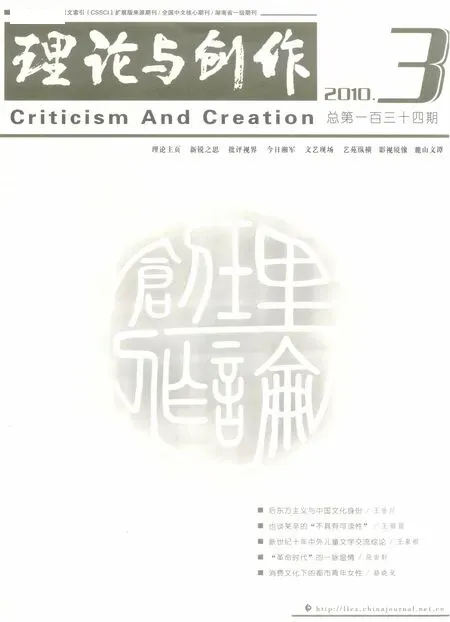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
2010-11-25舒伟
■舒伟
一、说不尽的奇境
2010年3月,由蒂姆·伯顿执导的IMAX 3D电影大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与公众见面,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两部“爱丽丝”小说的关注。作为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爱丽丝”故事不仅在纸质媒介和印刷文化的时代(人类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引领风骚,而且在21世纪的数字化传媒时代(图像、影视、网络及数字化新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仍然具有激进的潜能,原因何在?这无疑是当今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应当大力探究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通过不断的阐释和重新述说而表现出来的对于“爱丽丝”的关注。一方面是批评家和学者们进行的理论阐释和发现,另一方面是作家、艺术家们以模仿、改写、续写、重写等形式进行的文字阐释以及以影像艺术形式出现的影视叙事。在19世纪后期,两部“爱丽丝”小说的发表对许多与刘易斯·卡罗尔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竞相效仿的热潮:吉恩·英格罗(Jean Ingelow)创作了《仙女摩普莎》(M opsa the Fairy,1869)讲述男孩杰克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群仙女,结果他骑在一只信天翁的背上,跟随她们去往魔法仙境,经历了一场奇遇;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不仅自己创作了童话叙事诗《妖精集市》(Goblin Market),而且写了《异口同声》(Speaking Likeness,1874),讲述少女弗洛娜参加一个波澜横生的生日舞会,她夺路而逃,却跑进了一个幻想世界,在那里她发现那些自私孩子的所有令人厌恶的特点都以“异口同声”的方式被人格化了;莫尔斯沃思夫人(M rs M olesworth)的《布谷鸟之钟》(The Cuckoo Clock,1877)讲述孤独的女孩格瑞泽尔达遇到一只会说话的布谷鸟,结果在它的带领下进行了几次历险;G·E·法罗(G.E.Farrow)的《沃利帕布的奇异王国》(W allypub ofW hy,1895)讲述女孩格莉被她的布娃娃带走了,带到一个叫做“为什么”的地方,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奇异而颠倒的。沃利帕布本是那里的国王,但他却被自己的臣民所管辖,还要称呼他们为“陛下”。艾丽斯·科克伦(Alice Corkran)的《雪域之梯》(Down the Snow Stairs,1887)讲述自私的女孩基蒂被一个雪人带到魔法世界,在那里她的不良行为得到矫正。她重返现实世界后决心痛改前非,善待自己家中瘸腿的兄弟;此外还有E·F·本森(E.F.Benson)的《戴维·布莱兹和蓝色之门》以及查尔斯·E·卡瑞尔 (Charles E.Carryl)、艾丽斯·科克伦(Alice Corkran)、爱德华·阿博特·帕里(Adward Abbott Parry)等人的作品。汉弗莱·卡彭特等在《牛津儿童文学指南》中指出,这些仿效之作都没有达到《爱丽丝奇境漫游记》的艺术高度,后者显示的是幻想文学的“无限的可能性”,是难以仿效企及的。在20世纪出现的仿写、改编和续写以及影像表现包括中国作家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中国作家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1933);美国真人实景影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33);迪斯尼动画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51);英、法、美合拍的真人实景与木偶混合版影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51);英国电视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60,1966);美国电视片《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该片将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情节与《奥兹国的魔法师》的情节糅合起来,1960);英国影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72);美国电视片《爱丽丝奇境漫游记》(1985);苏珊·桑塔格的舞台剧剧本《床上的爱丽丝》(1993);麦琪·泰勒的新数码插图版《爱丽丝奇境漫游记》(2008);蒂姆·波顿执导的3D版真人实景与木偶混合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2010)……
人们为什么会对“爱丽丝”故事表现出如此持久的兴趣和关注呢?它能够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什么启示呢?
二、“爱丽丝”走进奇境世界
在成为《爱丽丝奇境漫游记》的作者之前,人们所认识的刘易斯·卡罗尔(Lew isCarroll)名叫查尔斯·路特威奇·道奇森(Charles Lutw idge Dodgson,1832-1898),是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于1832年出生于英国柴郡达尔斯伯里的一个牧师家庭。在小查尔斯11岁那年,全家搬到位于约克郡的克罗夫特居住。查尔斯自幼聪慧,兴趣广泛,而且多才多艺,尤其在文字写作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爱好。从1846年至1850年,查尔斯在约克郡的拉格比公学(Rugby)读书,随后考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读书。在大学念书期间,他以全班数学第一的成绩毕业,并由此获得一份奖学金,成为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助教,并最终留校任教。道奇森从1855年就开始向《喜剧时代》杂志(the Com ic Times)投稿,该杂志后来改名为《列车》(the Train)。1856年,道奇森创作的一首名为《孤寂》(Solitude)的诗作刊登在《列车》杂志上,署名为“刘易斯·卡罗尔”(Lew isCarroll),这是编辑从他本人提供的几个笔名中敲定的,是从他的本名Charles Lutw idge Dodgson演绎而来。关于“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创作缘由及过程是英国文学史上具有浪漫色彩的传说之一。1862年7月4日,一个金色的午后,卡罗尔和他的朋友,牛津大学的研究生罗宾逊·达克沃斯(他后来成为西敏寺大教堂的教士)一同带着基督堂学院院长利德尔膝下的三姐妹泛舟美丽的泰晤士河上,进行了一次惯常的漫游。那一年卡罗尔三十岁,风华正茂;爱丽丝小姐十岁,天真可爱。根据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注释作者马丁·加德纳(M artin Gardner)对此次郊游所做的详细注解,①卡罗尔一行乘坐的小舟从牛津附近的弗里桥出发,抵达一个叫戈德斯通的乡村,行程大约是三英里;然后五人上岸歇息、喝茶。这次泛舟之旅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三个小姑娘不仅像往常一样,要求卡罗尔给她们讲故事,而且在旅游结束后,二小姐爱丽丝突然提出要求,请卡罗尔先生为她把讲述的故事写下来。据卡罗尔当天日记所载,他们晚上8点1刻返回基督堂学院,还一同在卡罗尔的房间里观看了他的缩微放大照片集,然后三姐妹被送回家中——正是在互道晚安时,爱丽丝向卡罗尔提出将讲述的故事写出来的请求。多年后,卡罗尔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以及故事手稿的诞生,他说那是“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呼唤”。在那些令人愉快的郊游中,卡罗尔为利德尔姐妹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它们就像夏天的小昆虫一样,喧闹一场,又悄然消亡。这一个又一个故事陪伴着一个又一个金色的午后,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小听众请求我把故事给她写下来。”卡罗尔回顾道:“多少次我们一同在静静的河水中划船游玩——三个小姑娘和我——我为她们即兴讲述了多少个童话故事……头上是湛蓝的晴空,船下是明镜般的河水,小舟轻轻地荡漾在水中,翻动的划桨上闪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三个小女孩急迫的眼神,渴望那来自童话奇境的故事。”为了让自己热爱的孩子们得到快乐,卡罗尔费尽心机,信口讲述:他把女主人公送进了兔子洞——这就是故事的开端——至于后面将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没有想好;好在卡罗尔深谙童心,才思泉涌,虽即兴发挥,故事却从心到口,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卡罗尔不仅让爱丽丝成为故事的主人公,而且将当时船上的几个人也都编进了故事当中。利德尔姐妹中的大姐洛瑞娜(lorina)变成了小鹦鹉(Lory),小妹伊迪丝变成了小鹰(Fagiet),罗宾逊·达克沃斯(Duckworth)变成了母鸭(Duck),当然他本人则变成了一只渡渡鸟(Dodo)。而在此后两年间,为了让他所热爱的孩子得到快乐,他把故事写了下来,打印成手稿,还配上自己画的插图,取名为《爱丽丝地下游记》,在1864年将它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爱丽丝(后来卡罗尔又从爱丽丝那里借用了这部手稿,使之在1885年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版)。卡罗尔告诉人们,在记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增加了许多新的构思,“它们似乎从头脑中涌现出来,涌进原来的故事当中”。在完成手稿《爱丽丝地下游记》以后,也许是对自己的杰作不无得意之处,他在将手稿本赠送给爱丽丝之前借给几位朋友传阅。在作家乔治·麦克唐纳家中,麦克唐纳太太为孩子们朗读了这部手稿的故事,很受欢迎。所以麦克唐纳力劝卡罗尔将书稿充实一下,送交出版社出版。于是卡罗尔对手稿又进行了扩充(增加了“小猪与胡椒”一章中关于公爵夫人厨房的场景,以及“癫狂的茶会”一章中的疯帽匠的癫狂茶会)、修订和润色。《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终于在1865年正式出版。七年以后,《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出版。从整个创作过程来看,“爱丽丝”故事一方面体现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性,亲密性,互动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文字加工后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部“爱丽丝”小说以丰富的内涵征服了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同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读者。
三、心灵的激情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特定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进步”(工业革命,物质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退缩”(退回内心,怀念童年)齐头并进的时代。在包括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与重返童年的怀旧思潮等多种时代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的诸多英国一流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儿童和童年,乃至于为儿童和童年而写作。②童年的重要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书写童年,反思童年,或者以童年为媒介而进行创作成为一种潮流。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M Polhemus)在论述“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时将梦幻叙事及幻想文学与童年联系起来,阐述了卡罗尔创作的小女孩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儿童主人公的意义,表明儿童成为小说作品之主人公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卡罗尔笔下的小女孩主人公是如何与其他重要的小说大家所创作的儿童和童年相关联的。当然,卡罗尔之所以书写童年是与小女孩爱丽丝息息相关的。如果说贝特丽丝是激发但丁创作激情的女神缪斯,是《神曲》中引导作者进入天堂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指引者,那么人们可以把爱丽丝看做激发卡罗尔创作灵感和激情的贝特丽丝,在特定意义上正是她引导卡罗尔进入了地下奇境和镜中世界,使他以自己的才情去探幽访胜,神游万仞。
现实中的小女孩爱丽丝是激发卡罗尔心灵激情的女神缪斯,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样的解释显得简单化了。卡罗尔对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的热爱在爱丽丝身上得到聚焦,随后通过“爱丽丝”小说的创作得到释放和升华;我们可以借用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艺术的研究成果来审视卡罗尔创作后面的深层因素。简言之,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梦》艺术贯穿了独特的玉、红、情“三纲”文化因素。“玉”乃万汇群品,独具灵性的玉石;“红”乃作为七彩之首的红色,代表鲜花和少女;情乃为“普天下女子”的不幸而痛哭流泪的深邃博大的深情。用周汝昌先生的话说,曹雪芹要牺牲一切而决心传写他所亲见亲闻的、不忍使之泯灭的女中俊彦——秦可卿所说的“脂粉队里的英雄”。正是这样博大深邃的情怀使曹雪芹写出了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作者的心灵激情是一种为众多花季少女的不幸命运而痛哭的悲情。在《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随贾母一行到宁府花园去赏花游玩,一时感到疲惫思睡,于是贾母令人带宝玉去歇息一回。结果宝玉去了贾蓉之妻秦氏(秦可卿)的房里歇息,一觉睡去,进入梦乡,在警幻仙姑的引导下游历了一番太虚幻境。在梦游中他预览了几位女主角(宝钗、黛玉、湘云、妙玉)的结局以及其他女子的最终命运。其间小丫鬟捧上的清香之茶“千红一窟”和甘冽之酒“万艳同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被认为揭示了整部《红楼梦》的主题意旨:“千红一窟”即“千红一哭”的谐音,“万艳同杯”乃“万艳同悲”的谐音。刘鶚(1857-1909)在《老残游记》的“自叙”中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他认为《离骚》是屈原的哭泣,《庄子》是庄生的哭泣,《史记》是司马迁的哭泣,《草堂诗集》是杜甫的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曹雪芹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刘鶚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灵性所滋生的深邃情感。那些千古杰作乃是长歌当哭的艺术结晶。以此而论,卡罗尔之所以写出两部英国最杰出的,难以被超越的童话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创作动机发自内心肺腑的深情,或曰心灵的激情。虽然“爱丽丝”故事以荒诞奇趣而著称,卡罗尔也被称作讲荒诞故事的痴呆的数学家,但人们却解出了其中意,认识到了爱丽丝故事的奥妙和旨趣,认识到了作者精神层面的“洛丽塔”情结。卡罗尔对于儿童,尤其是小女孩怀有特殊的情怀,与她们的交往和友谊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他本人所说,她们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而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反映出作家们将小女孩的美貌和童贞理想化的一种倾向。卡罗尔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对于小女孩的热爱在爱丽丝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这种热爱是对于许许多多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的纯真玉容的珍视,而她们对卡罗尔故事天才的崇拜也使他得到人生最大的宽慰与满足。童年是美好的又是流逝的,对逝水流年的惋惜转化为内心的激情,卡罗尔与小女孩的对话是安徒生式的成人意识与童心的交流,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如何才能留住童年,留住美好回忆呢?回答就是用爱丽丝漫游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故事将所有的遗憾和感伤化为一曲咏叹“夏天”的绝唱。这就是莎士比亚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抒发的情怀,其精湛的诗艺表达了诗人无限的深情,可用以题解卡罗尔心灵的激情:
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吗?/你比夏天还要温柔可爱:/五月的狂风摧折了娇艳的花蕾,/夏天的逗留实在是太短太短:/苍天的骄阳有时酷热难当,/那金色的面容时常云遮雾挡:/世间的美艳终将凋谢零落/或受制于机缘或屈从于时轮运转。/但你永恒的夏天却不会消逝,/你的玉容倩影将永留人间;/死神也难夸口说你在他的阴影中闯荡,/只因为你的生命流淌在我不朽的诗行。/天地间只要有人呼吸,有眼能看,/这诗就流传,就让你永恒。
译诗中的“夏天的逗留实在是太短太短”得之于周煦良先生的译句,这是出现在高尔斯华绥著《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的尾声“残夏夕照”中的莎士比亚诗句。这个尾声描写的是福尔赛家族中正直倔犟的老乔里恩在生命尽头的一个美丽抒情,令人感伤的人生插曲。夏天是英国最美好的季节,正是在这样的季节里,老乔里恩邂逅了前来凭吊亡人的少妇艾琳。老人在生命暮年的爱美之心和惜香怜玉之情使他与艾琳成为忘年之交。面对一个外貌美,心灵也美的年轻异性,真可谓“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而谈宴时而出游,“色授神与”,大慰平生;但也恰恰是这段交往为老乔里恩的生命提前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这个“爱美之心”的插曲是小说中最抒情,最感人的描写。当年30岁的卡罗尔与当年10岁的爱丽丝亦是忘年之交,他把自己融进了爱丽丝故事,把这段友情化作了永恒的夏天。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诗人先将友人比作夏天,转而叙述夏天比不上友人,因为自然界的夏天有诸多不如意之处。物换星移,生命变老本是自然规律,但诗人的情感和文笔却能产生奇迹,因为友人的生命流淌在诗人不朽的诗句之中,化作永恒的夏天。对卡罗尔亦是如此,两部“爱丽丝”小说将流逝的童年和难忘的友情化作永恒的奇境漫游,成为英国儿童文学永恒的夏天。
四、开拓幻想文学的新疆界
罗伯特·波尔赫默斯在《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一文中指出,卡罗尔为艺术,小说和推测性思想拓展了可能性。卡罗尔的开拓性创作不仅体现在儿童文学领域,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成人文学。正如波尔赫默斯所说,通过创造“爱丽丝”文本,卡罗尔成为一个人们可以称为无意识流动的大师。他指明了通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道路。④波尔赫默斯这样论述道:“从卡罗尔的兔子洞和镜中世界跑出来的不仅有乔伊斯、弗洛伊德、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弗吉里亚·吴尔夫、卡夫卡、普鲁斯特、安东尼·阿尔托、纳博科夫、贝克特、伊夫林·沃、拉康、博尔赫斯、巴赫金、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还有20世纪流行文化的许多人物和氛围”。从儿童文学的视野看,“跳进了兔子洞”意味着进入了幻想文学的奇境,由此形成了儿童幻想文学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的一个重要模式(从《纳尼亚传奇》的魔橱到《哈利·波特》的神秘的火车站莫不如此)。同样书写童年,同样将19世纪的儿童作为小说创作中的主角,卡罗尔的贡献是革命性的,无以替代的。他不仅用幻想文学的艺术形式来书写童年,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新疆界,而且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意识和无意识活动,通过爱丽丝的反思和愤慨来颠覆说教文学,颠覆成年人让她遵从的教训和常规。如果把同时代的文学大师狄更斯的书写童年的小说与卡罗尔的“爱丽丝”小说比较一下,人们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卡罗尔的特殊贡献。关于狄更斯,波尔赫默斯指出:“正是查尔斯·狄更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作家,使儿童成为信念、性爱和道德关注的重要主题;作为一个小说家,狄更斯所做的贡献没有什么比他对于儿童的描写更具影响力的。……通过他自身童年受到伤害的经历,狄更斯将儿童的浪漫的形象铭刻在无数人的想象之中,促使人们去感受和认同于遭受伤害和压榨的孩子们,认同于人生早期岁月的心理状况。”如果说狄更斯再现的是真实的童年经历的记忆,那么卡罗尔则以幻想文学的艺术形式超越了这些记忆。波尔赫默斯认为,狄更斯等作家在追溯童年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我是怎样成为现在的我?2.我的童年是什么样的童年?而卡罗尔探寻的是如何才能消解自我,消解成年,如何才能回归童年,甚至重新成为一个小女孩?卡罗尔的回答是,富有想象力地走进小女孩爱丽丝的世界。具体而言,卡罗尔采用梦幻叙事的方式让爱丽丝引领我们走进梦幻般的奇境世界,随着爱丽丝的“意识流”来重返童年。在心理分析学家看来,童年的精神特征体现为自我中心,无法区分自我和他者,万物有灵,等等,所以在爱丽丝的世界里所有动物、植物、扑克牌和象棋子等等都是有生命的,能说会道,活灵活现。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出现的一切物体都像是梦中的境遇,都是漫游者(做梦人)的组成部分。梦幻叙事可以将人类普遍的主观思绪和情感转化为可视的意象。而那些想象出来的,陌生化的奇境、梦境和困境等在人们的脑海中唤起了“似曾相识,依稀能辨,甚至非常熟悉的”感觉,所以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看,它们就代表着人生的境遇、冲突、恐惧、困惑、欲望、挫折、自我宽慰等等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因而具有一种绝妙的心理真实性。一方面,爱丽丝是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女孩,她代表常识和理性的视野;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不乏主见的,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颠覆者,所以她敢于顶撞那个专断暴虐,动不动就下令“砍掉”别人脑袋的王后。通过爱丽丝的视野,卡罗尔戏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逻辑(茶会、宴会、槌球赛,国际象棋赛,等等),以荒诞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儿童权利的捍卫和对成人威权的反抗。“爱丽丝”小说的“颠覆性因素”还表现在以梦幻(噩梦)的境遇或者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错位来颠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理性、道德或者现实秩序的自信,以及对于叙述、时间、或者语言等方面的自信。在语言实验方面,两部“爱丽丝”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作者自撰的词语及语言游戏。例如在《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的第一章,爱丽丝在进入镜中屋后看到的那首反写的怪诗“杰布沃克”(Jabberwocky)必须通过镜子才能阅读。至于书中众多的“提包词”(混成词)更是一大特色。
重返童年而又超越童年,两部“爱丽丝”小说体现了童话小说的双重性,从而使之具有强大的潜能,正如19世纪末麦克唐纳在《奇异的想象力》(The Fantastic Imagination,1893)一文中对童话艺术特征的描述:“一旦从它的自然和物理法则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它潜在的各种意义将超越字面故事的单一性:童话奇境将成为一个隐喻性,多义性的国度,在这个奇妙的国度,‘艺术越真实,它所意味的东西就越多’”。③“爱丽丝”小说是儿童本位的(为儿童创作讲述,创作动机就是为了取悦于特定的听故事的儿童),是作者与童心和童年对话的结果;但它们又是博大深邃的,能满足成人的审美需求和心智需求。
作为英国童话小说的经典之作,两部“爱丽丝”小说不仅具有奇趣,而且富于象征性、哲理性、荒诞性和审美性,是开放性和对话性的文本。这是一个难以说尽的奇境世界,但有一个启示是清楚的,那就是批评家C·N·曼洛夫(C.Manlove)所说的最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特征:
那些为儿童创作的最优秀作品是由那些似乎忘记了自己究竟为谁而写的作者创作出来的,因为话语的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如此完美地融合起来:霍林戴尔称之为“童心童趣”;当刘易斯·卡罗尔在创作爱丽丝故事之前和之后,用一种成人的声音谈论童年的奇事异趣,当他将《西尔维亚与布鲁诺》呈献为对一个早慧婴孩的颂扬之作时,他是笨拙的,窘迫的;而当他驰骋想象,全神贯注于爱丽丝故事时,多少年的岁月流逝都不会使他的光芒暗淡下去。
这无疑是“爱丽丝”小说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注 释
①加德纳在他的注释里引用了卡罗尔当天的日记及二十五年后的回忆;爱丽丝本人的两次讲述;爱丽丝的儿子有关他母亲回忆情形的文章;以及当天同行的罗宾逊·达克沃斯的回忆文章;加德纳还记述了他于1950年在伦敦气象局查询有关1862年7月4日天气记载的详情及相关说明。见Martin Gardner The Annotated Alice: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by Lew is Carroll.The Definitive Edi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2000.pp.7-9.
②有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的怀旧思绪,参见舒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时代语境》,《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4期。
③转引自Mendelson,M ichael.The Fairy TalesofGeorge MacDona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 genre in M cGillis,Roderick editor.For the childlike:George MacDonald's fantasies for children.London: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Metuchen,N.J.:Scarecrow Press,1992,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