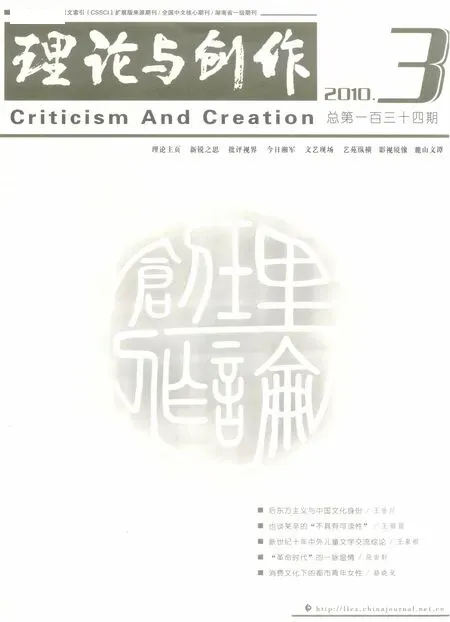话语权威的艰难建构❋: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声音分析
2010-11-25高小弘
■ 高小弘
在现代社会,“声音”这个词已经具备重要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受贬抑的、被强制以沉默为美德的社会群体与个体来讲,“声音”已经成为权力与身份的代称。因此,对于被长久笼罩在性别统治与性别歧视阴影中的女性而言,寻找“失落的声音”并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就意味着女性个人或群体试图通过追求话语权力来摆脱女性客体地位,并通过建构一种与生命体验相连的表达方式来消解男权话语霸权。
然而就批评实践来看,女性主义者强调的“声音”是一种以女性立场、女性体验为中心的观念和见解的表达,它被视作颠覆父权文化秩序的有效策略。因此女性主义者通常并不注重“声音”作为一种形式结构的技巧意义,而是侧重讨论“声音”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所包含的社会寓意。而作为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声音”被更精确地表述为“叙述声音”,它指叙事作品中讲述者的话语,而这既不同于叙事中的隐含作者的叙述意图,也不同于非叙述性人物的独白或对话。叙事学理论家们将叙述声音定位为文本实践中的具体形式,而不认可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寓意的指涉价值。事实上,在以男权利益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希图“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性要想表达自己观念和见解,不仅要适应叙述声音特定的技术要求,而且还要受制于产生叙述声音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化常规,因此文本中的女性叙述声音就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而且还会折射出特定时代女性的性别处境以及社会性别权力关系。针对上述两种倾向,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苏珊·兰瑟主张将政治化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具体的叙述形式技巧研究结合起来,在她看来,可以从巴赫金“社会学诗学”的角度来审视叙述声音,“也就是说,叙事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而叙事声音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得以产生的。”①由此可以得出,“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②因此,处于父权意识形态压制下的女性作家,必须借助浸染着性别权力关系的语言修辞和社会常规,巧妙地采用某些间接的甚至迂回的写作策略和技巧,才能冲破男性主导意识和男权话语的重围,从而有效地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威,呼喊出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真实的声音。
就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而言,尽管多数女性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机构都保持距离,自甘边缘,但是并不意味着她们放弃了话语权威的企求,即获得听众、赢得尊敬与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然而经济转型带来的多元化语境使女性作家在享有空前广阔的文化空间的同时,也使之面临着父权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隐秘合谋的“无物之阵”。更重要的是,女性作家所倚赖的新文学传统,其话语权威始终附属于五四以来沉浮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男性文化精英,这种隐含着性别权力因素的文学传统,在经过历史时间沉淀之后,形成了具有强大规约力量的文化成规,并以一种潜移默化而又无孔不入的影响方式制约着女性写作。因此,以揭示女性成长真相为叙事主旨的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在叙述声音中建构话语权威时,常常面临着一种尴尬的窘境:一方面需要从文化成规中借势来建立女性成长叙事的话语权威,从而争得话语主体的位置来拆解父权社会女性成长神话的虚妄,揭示出女性主体性生成的女性成长内涵,并得到广大读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处于社会权力关系网中的文化成规是一个铭刻着性别等级制度、维护男性主体性位置的规约性力量,因此,对于这种文化成规的全面依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以虚构、歪曲女性真实体验为目的的男性话语系统的认同。这种写作窘境使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叙述声音成为一个充满文本诡计与叙述策略的场域,而每个具体文本叙述声音的处理方式都可看作是对于社会性别文化权力关系的具体回应。根据苏珊·兰瑟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叙述声音的划分,叙述声音的模式有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这几种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都有鲜明表现,“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这样也就表述了一整套互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和危机意识、清规戒律和可能的际遇”。③
一、静默与喧嚣:作者型叙述声音
所谓“作者型叙述声音”,就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也就是说,叙述者处于叙述时间之外,不会被叙述事件加以“人化”,因此这种类型的叙述者比小说人物充当叙述者的叙述模式更具有优越的话语权威。作者型叙述声音一般都不用指明叙述者的性别特征,并且文化常规总是将这种作者型的叙述声音默认为男性的声音,因此女性如果采用这种叙述模式参与到男性的文化权威中,可能会更轻易地获得受述者的认同,但这也无形中强化了父权文化秩序中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权威。而如果这种作者型的叙述声音被明确赋予女性声音的性别特征,那么这种声音又会面临着因受述者抗拒性阅读而丧失话语权威的可能。因此,为了承载更多的、更为有效的公众权威,女性作品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一般不会明确标明女性标记。在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作者型叙述声音可以根据叙述者表述行为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者专注于“超表述”行为,即叙述者不只描述虚构世界,而且还对虚构世界作深层的思考和评价,总结归纳故事的意义,点评叙述过程,寻求与受述者对话;另一类是叙述者专注于表述行为,仅仅叙述虚构人物的言辞和行为,不对事件与人物发表过多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超表述”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在这种声音模式中,叙述者不断就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整体意义发表自己的评论与看法,同时叙述者还概述过于琐细而不值得戏剧化的思想过程和事件,告诉读者无法轻易从文本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作家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达某种价值观念,因此叙述者评论干预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一些价值信念灌输和强加给读者,并获得读者的认同。就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而言,由于女性主体性价值与父权道德价值的悖逆,女性作者通过叙述声音灌输价值观念的现象就层出不穷,特别是针对那些有较多争议性的问题,运用得更是频繁。蒋韵的《隐秘盛开》中,潘红霞那“荒唐”的、“让爱占有一生”的女性成长故事,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个体命运的自主选择,但毕竟是一种不为世俗理解的爱情价值。为了赢得读者的价值认同,叙述者一再以诗意的方式赞叹道:“这样的爱,‘爱情’是不配的,也是它承受不起的。能够承受这爱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和神明——因为那不是爱,那是信仰”,并且一再强调:“爱永远是一个人的事,和被爱者无关。”铁凝的《大浴女》中,对于尹小跳和陈在狂热的婚外恋情,作者不仅通过设置陈在与小跳青梅竹马以及陈在婚姻情非得已的情节,来证明这一恋情的合法性,而且叙述者还充满感情地为其辩护道:
相识二十多年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亲热,他们不断地互相错过,就好像要拿这故意的错过来考验他们这忠贞不渝的情谊。现在他们都有点儿忍不住了……仅有的情谊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这美妙绝伦的破坏。
将叙述者评论的声音从开头响彻到结尾的是王安忆的《流水三十章》。在这个长篇中,张达玲成长历程中凡是溢出传统期待视野的行为表现,如有悖母性神话的母女淡漠、违反成年人想象的幼童心理、抵制“处女无欲论”的情欲骚动和身体欲望等,都由叙述者浓墨重彩地细细剖析和阐释。随着张达玲成长过程中善恶复杂性的增加,叙述者评论的声音便更大量更明晰的响起。然而将这种叙述声音的评论干预发挥到极致的是张洁的《无字》。全文充满坦诚直白而又激愤满怀的评论,特别是吴为成长过程中,那些不为父权文化秩序所容的“仇父”与“仇夫”的心理与行为,都得到叙述者充满极端性政治色彩的有力辩护。这些连篇累牍、慷慨激昂甚至有些浮夸偏激的叙述声音,显现出女性作者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叙述声音建立起一个超越性别等级常规的价值体系,并希望读者根据这一体系来衡量吴为所经历的成长事件,从而认同吴为那偏激极端的个性和极富叛逆的行为。但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正如施洛米丝·雷蒙-凯南所指出的那样:“叙述者如果过于外露,那么他被完全信赖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这是由于他的阐释、评价和归纳并不总是与隐含作者的标准尺度相吻合。”④这种情况对于女性作品中的叙述声音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无字》这部“用生命书写的,通体透明的,惊世骇俗”的女性成长小说,依然会招致有关“节操与原则”、“隐私和尊严”以及“文德和文格”的苛责。⑤
二、真淳的尴尬:个人型叙述声音
按照苏珊·兰瑟的理论,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指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但它并不指代所有的“同故事的”(homodiegetic)或“第一人称的”叙述,而只是指“那些说话人即虚构故事的参与者的叙述”,即热奈特所谓“自身故事的”(autodiegetic)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我”也可以统筹其他人物的声音,在叙述声音结构上保持“优越”的地位,但这地位的取得依赖于“我”是个可信的叙述者这一前提。另外,与作者型的叙事者“拥有发挥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不同”,个人型叙述者“只能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就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而言,个人型叙述声音并不利于树立女性的叙述权威,有时甚至给女性写作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由于个人型叙述声音往往在叙述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再加上内容本身是由人物的成长经历构成,这使许多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模式的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往往被看作女性作家的成长自传而遭受非议,甚至把这类女性写作视为因不具备知识水准、不了解外部世界而不得已的选择,并因此贴上不守礼规、自恋独尊的标签。尽管这样,个人型叙述声音所具有的直接传达生命体验的优势,仍然使其成为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非常重视的叙述策略。
在父权文化秩序中,公开话语属于男性、私人话语属于女性的话语二分法惯例,在悄然地支配和制约着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的使用规则。一位女性作家想要创作一部用个人型叙述声音叙述的女性成长小说,就意味着必须要考虑许多深层的问题。首先,必须在平凡琐细的女性成长体验中,尽可能容纳宏大而深邃的意蕴,以此来抗衡父权文化秩序对于这类女性写作的偏见。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豆芽菜那虽个性飞扬但仍不失为平凡细碎的女性成长故事,在以“禁欲虚伪”和“扼杀个性”为主旋律的文革时代,具有了某种超越性意义。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中,如果没有对“孤独”与“焦虑”等富有人性深度体验的深刻质询,“我”的故事必将成为过于沉闷而单调的女性成长呓语。其次,必须时刻控制作者与充当叙述者的女性成长主人公之间的界限,以此保持公开化的叙事力度和保护个人隐私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这一点上,有些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处理得显然不十分得当,这主要指一些“美女作家”的作品,如卫慧的《上海宝贝》、《艾夏》、《床上的月光》,棉绵的《啦啦啦》、《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等。这些文本,为了商业炒作的需要而过分强调女性自传性的卖点,在强化个人型叙述声音所暗示的“私人话语”的同时,将女性作者本人与充当叙述者的女性主人公有意无意地重合在一起,将虚构叙事与个人隐私或隐或现地联系起来。这种叙述效果在满足男权主义“窥淫癖”的同时,也贬损了小说应有的人文价值。
事实上,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在使用个人型叙述声音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由于个人型叙述声音无法掩饰叙述者的性别,或者说无法像作者型叙述声音那样伪装成男性的声音,而这就意味着在讲述女性自我成长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叙述声音所建构的女性自我形象,逾越了公认的女性气质行为准则,那么她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抗拒性阅读的危险。因此,为了保证叙事的可信度,以及最大程度避免抗拒性阅读心理的抵制,女性写作者必须将女性成长主人公的言行容纳在一种公众能够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之内。就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而言,对个人型叙述声音风险性回避最为典型的文本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
《一个人的战争》初始版本的封面竟是一幅春宫画,而陈染《私人生活》封面的宣传词则是“性感而怪异的人生悲喜剧,危情而玄思的女性成长奇观”。这固然反映了消费社会中带有欲望色彩的男权眼光的性别偏见,但也显露出这两个文本所建构的女性成长主人公形象与公认的女性气质的距离。《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女性成长主人公多米,幼时就能以“自慰”自娱,并且对于同性身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青年时又因抄袭事件被揭发,孤僻与自闭的性格使其受骗失身,而虚幻的爱情又以堕胎而告终;其成长结局最终是逃入一场没有爱情而又年龄悬殊的婚姻中。而《私人生活》中的拗拗不仅以清高孤独自赏,而且总是“特立独行”:虽一再受到T老师的嘲弄与欺辱,却屈从于欲望把自己的初夜给他;她生命中的情欲由异性尹楠和同性禾寡妇共同承载;她以浴缸作为自我成长归宿的怪癖与拒绝流俗的疯狂。按照父权社会的女性道德标准,这两个女性成长主人公确实如“魔鬼般淫荡”,如“女巫般不可理喻”,尤其是个人型叙述声音的使用,更使得文本惊世骇俗。但女作者在坚持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同时,巧妙地使用了改变叙述声音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消极的叙述效果。《一个人的战争》中,在“我”那些颇有争议的行为处往往有意无意地嵌入了作者型叙述声音,如多米受骗失身那段,叙述者一跃成为虚构世界的旁观者,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来理性地审视人物的成长磨难。《私人生活》中,被欲望支配的拗拗在阴阳洞中与T先生初尝禁果的那段,也由第一人称个人型叙述者转换为全知色彩的作者型叙述者。这种叙述声音的转换使得叙述者与人物不再二位一体,而这种临时分身的叙述策略,不仅消除了读者将这种触犯父权律令的行为与女性作者本人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联想,而且也使读者产生了与叙述者相似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在微讽女主人公轻率与孤僻的同时,对其充满怜悯与宽囿。
当然,并非只有叙述声音转换这一种策略可以有效地避免个人型叙述声音导致的叙述风险,还有些作品充分利用了“自居作用”,即通过人物的视觉、心理来感受和想象一切,从而使读者感同身受了所有女主人公所经受的成长体验:苦难与欢欣,挫折与痛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深刻的认同。
三、共济的方舟:集体型叙述声音
所谓的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叙述范畴,这是因为叙述声音的区分性特征在根本上依赖于主导文化的规定,而主导文化极少采用集体型叙述声音,因此集体型叙述声音及其各种可能的形式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苏珊·兰瑟把这种叙述声音定义为“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①在集体型叙述声音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述权威,而这种叙述权威可以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可以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由于主流的文化秩序中,叙事和情节结构都被刻上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等级烙印,集体型叙述声音基本上是边缘或受压制的女性群体所发出的声音,而女性个体要呼喊出集体的叙述声音,却必须以建构具有性别政治意义的女性群体为前提。由于中国从未产生过成熟而独立的妇女运动,这无疑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享有相当多权力的当代中国妇女,在性别群体意识方面却处于匮乏混乱状态,因此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群体基本不存在。但在文学艺术理论领域,由于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语境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大量输入,女性艺术家们则开始形成清醒的性别群体意识,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了集体型的叙述声音,尽管这种叙述声音模式在女性写作中极为罕见,但仍可以将其看作女性个体作者因企慕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女性社群而产生的一种极为隐蔽的策略性虚构形式。按照兰瑟的划分,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存在有三种形式:单言(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共言(复数主语“我们”为叙述者)以及轮言(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就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而言,主要存在着轮言形式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并且集中表现在徐小斌的《羽蛇》与蒋韵的《栎树的囚徒》中。
《羽蛇》是以羽的成长故事为基本的情节线索,同时在跨越百年的历史画卷上,构建了一个由五代女性构成的母系家族历史,而这个“女性世系”的延伸是由多个女性的成长故事构成的。文本以作者型叙述声音为主导叙述模式,同时又让包括羽在内的家族女人以及她的朋友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表达自我的思想意识。这些处于不同时代,同时又个性分明的女性人物,都以自己独特的思想逻辑和风格化的内心语言,不止一次地敞开自己的内心生活:玄溟那端庄正统的内心声音;金乌那浪漫执著而又自由不羁的内心声音;若木那病态忧郁而又充满偏见的内心声音;羽那痛苦不安而又充满神秘直觉的内心声音;亚丹那压抑而又无奈的内心声音;韵儿那因现代意识而显得过分轻盈的内心声音。这些各具风貌的女性声音,构成了一个充满压抑与反抗、爱恨交织的女性世界:既有女友间的温情互助又有彼此的争执抢夺,还有母女之间那以健康、爱心为名的摧残与迫害。然而,文本分散而枝蔓的各种声音无疑会影响到情节的连贯与表述的统一,所以小说又精心设计让单一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来统摄那些思想意识纷纭的个性化声音,以此构建小说形式上的连贯统一。这一精心构建的叙述声音模式,使整篇小说如同一部交响乐,在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指挥下,个性化的声音在不同的声部响起,从而成功地弥合了“众声喧哗”带来的巨大历史跨度与文化断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作为主导模式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虽未特别标明但显然是女性的声音,“她”多次以“我们”这一复数人称邀请受述者参与、判断,从“她”的声音中可以听出遗憾与惋惜、宽容与激赏。正是在这个有明显性别倾向的叙述声音的引领下,那些因为经历和情感各异而构成多元化的女性个体叙述声音,表明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然而这表面的差异之下却是女性生命逻辑的深刻一致: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每个女性都依然故我,都会怀着最初的生命动机,坚忍不拔地走向自我选择的人生之路。她们不迁就外部社会、只听从内心召唤的成长历史,是一种看上去最微不足道,但却最自在、最具韧性的历史。而正是这潜伏于爱恨情仇表象下的深刻一致,使这些跨越历史的、多元化的女性成长故事,最终统一在一幅女性社群全景图中。
《栎树的囚徒》选择的是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另外一种模式:家族中的三个女性轮番讲述,并形成一种扇形节奏的叙述声音。第一章是天菊的声音,第二章是天菊的母亲苏柳的声音,第三章是天菊的舅妈贺莲东的声音,第四章又返回到苏柳的声音,而最后一章与第一章呼应,以天菊的声音作为收梢,每个叙述声音都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女性言说者的感觉、体验笼罩着她所回忆和想象的一切,她们既讲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又讲述他人的故事,轮番担任同故事和异故事叙述者的角色。显然,家族内部女性的血缘亲情成为统筹这一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基本原则,传统的婆媳、姑嫂与妯娌关系,被改写成一种具有“姐妹情谊”色彩的、有精神承继关系的母女与姐妹关系。这些置身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和风雨飘摇的家园里的女性,以一种天然的默契和理解,共同抵御父权秩序的重重压力。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一组分散的叙述声音融入了一个自主自为、平等说话的女性群体中,她们的叙述声音在不断轮换中,没有哪个叙述者能够完整地建构自己或她人的成长故事,而只能在多种叙述声音的集合里,共同拼接完成壮观而又绚烂的家族女性命运成长图景。这些由多元化叙述声音讲述的众多各不相同的女性成长故事,其间却闪现出深刻的相似性,从而使她们能够以理解宽容的眼神隔着岁月的鸿沟深情遥望。作为这一家族女性历史的弥留人与后继者的天菊,象征性地以自己的叙述声音开启和完结整个家族历史故事,她深情地回望着这些由母辈们血泪涂抹的生命风景,并在文本结尾感慨道:
我们家族的女人,她们有多少是用“死亡”这种方式摆脱了生命的困境。她们选择了死来保存生的自尊。她们是些美丽的易折的乔木,构成了我们家族树林的重要景观,而我们,苟活者和幸存者,则是她们脚下丛生的灌木和蒲草。我们永远没有她们那种身披霞彩的千种风情,而她们,则不如我们坚韧。
这一令人感怀的优美意象,隐喻了横亘在女性家族历史长河中两极化的女性成长逻辑:一极是以陈桂花为代表的那种刚烈壮美的“宁死不屈”,另一极是以贺莲东作为典型的那种能够承担最世俗最琐碎苦难的理性柔韧。这两种刚烈与柔韧相济、飞扬与沉稳辉映的生命景观,构成女性群体中理想化的人格典范,而正是这一理想化的人格典范,成为汇聚家族女性群体的精神内核,成为家族女性健全人格与完美生命的真正精髓。
注 释
①②③④[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王蒙:《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读书》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