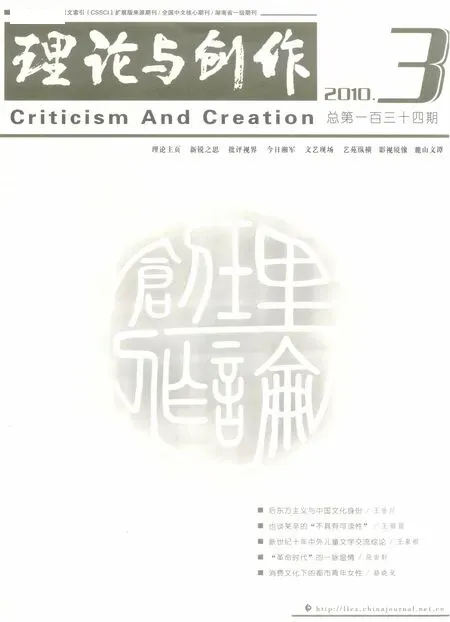话语控制:作家与批评家的权力转换
2010-11-25刘军
■刘军
文学的诞生不仅仅是文本的出现,也包括读者的应运而生。批评家作为读者之中的特殊者,不久便攫取了全体读者的代言人地位。稍稍回忆一下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便不难发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如此的纷纷扰扰。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十九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明显转向读者的阶段。”①虽然这只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但足以说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
一
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具备先天的单一性,一开始它是一个杂合体。也只有在社会分工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文学才可能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但是文学同时又是一个有机体,只指认出它的身份还远远不够,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越来越成为必要。遗憾的是,长久以来这依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我们连文学到底由哪几部分构成也没有弄清楚。文学的本体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艾布拉姆斯在考察了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文本之后,才科学地将文学分为四部分: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②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文学四要素观点。艾布拉姆斯同时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批评明显地以作家为中心,这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在浪漫主义作家看来,作家就是英雄和天才的代名词,是全体公众理应崇拜的对象。
十九世纪,一些实证主义批评家强调重视作家的生平、传记以及社会背景,认为这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对作品的批评,必须着眼于作家。与其说是批评家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毋宁说是作家借助于作品在趾高气昂地颐指气使,批评家只不过是作家手中的一枚卒子,为着作家而东奔西走。批评家对自己的这种出力不讨好当然耿耿于怀:凭什么作家在享有了创作权之后,还要垄断对作品的解释权?批评家的不满意,当然会使他们不安于现状。果不其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为批评家带来诸多契机。
“如果谁想确定本世纪文学理论变化的开端,他大概可以选择1917年吧。因为就在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那篇开拓性的论文《作为手段的艺术》发表了。”③这标志着形式主义批评的诞生。形式主义关心的并不是作家,而是纯粹的作品。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性既然是“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然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内。但是我们又知道,一个完整的文本不仅包括内容,还包括形式,到底是哪一部分在起作用呢?在形式主义看来,是文本的形式,只不过他们对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颇有异议,因此坚决地将它们置换为“材料”和“手法”。换句话说,真正使作品呈现出文学性的便是手法。手法,意味着艺术技巧、结构构思。对作品的研究,便是对手法的研究。
当“手法”成为文学批评的宠儿,作家受到冷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对作家的研究到对作品的研究,这看似很随意的方向转换,实际上暗含了这样的重要信息:作家妄自尊大的时代马上就要过去了,批评家和作家平起平坐将不再是奢望。“新批评”学派的出现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批评,又称“英美新批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英美等国家的文学批评流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理查兹、T·S·艾略特、燕卜逊,美国的兰瑟姆、布鲁克斯、沃伦、维姆萨特等人。他们适时推出文学本体论的论调,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话语制成品,是文学活动的本质和目的,它理应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文学作品诞生的同时,便宣告了作品和作家关系的终结。文本具有自足性,文学研究的方法便是对文本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所谓的细读,如同它的英文原意所表明的:封闭式阅读,即不考虑文本与作家、社会的任何联系,将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对文本作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解释,耐心审慎地解读作品的词语,把握它在语境中的含义,并且着重研究一个文本的内在结构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张力”(tension),④这样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便转向了文学作品的内部,也即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内部研究”。内部研究关注文学自身,把文本看做一个整体,利用透视主义⑤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倚重生平、社会环境、背景等外部因素,皆是轻视作品本身的做法,是不可靠的。
作者的存在对新批评派来讲,与其说是可有可无的,倒不如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毫不客气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意图不仅对文学批评起不了任何帮助,反而是文学批评的障碍。作家的创作意图往往成为混淆批评的渊薮,如果批评家们循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去理解作品,并将其作为评判的标准,那么毫无疑问,将会产生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总之,作家的存在是对文学批评的干扰,因此他们的存留是否有必要,就成为不争的共识。批评家要求作品和作家必须划清界线,只有这样,批评家被作家控制的被动局面才会被改观。
既然作家成了不仅无用反而有害的存在物,那么距离对作者进行“定罪”的时刻也便不远了。所以,当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以毋庸质疑的口吻宣布“作者死了”的时候,我们感到惊讶的同时,又觉得是理所当然:既然作家的意图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阻碍,那么让它消失也便没有什么不妥。巴尔特认为作者只是一个主语,“仅仅是其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⑥作者在语言陈述之外是空的,作者通过写作创造文本只不过是个假象,文本早就存在,它是由多种其他文本构成的,是“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的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其他文本的混合,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事实上,另一位结构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文本的“互文性”理论,更明确地说明了文本间是如何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互文性意味着作家独创性的消失,作家主体地位的倾覆。在《作者的死亡》一文的最后,巴尔特斩钉截铁地总结道:“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现在,我们已开始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⑦
在巴尔特宣布“作者死了”的同时,接受美学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将读者的阅读接受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未经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便不是文学成品;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区分了这样两个概念:文本和作品——前者是指作者创作出来的物品;后者是指经过读者阅读之后的文本。显然,它们的不同在于读者是否参与。在他们看开,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活动是不完整的。读者的到来,有效地转移了批评研究的重心,并使文学批评大有可观。
那么,读者的效用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接受任何一部作品之前,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一个“前理解”图式,或者也可以说有一个“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作品只是唤醒读者的以往的阅读记忆,让它进入一种情感状态,以出现某种阅读期待。在整个过程中,这种期待将会随着作品不断作出调整;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调整视野的过程。这表明,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于被动地位,阅读过程也不是单向输出的过程,而是双向交流的过程。读者十分积极地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并最终完成整个文学活动。读者的积极参与还表现在,一旦达到视野融合,他们便感到索然无味,只有不断地制造期待失望或产生期待受阻,阅读活动才会有效地进行下去。这也可以用罗兰·巴尔特关于“快乐文本”和“极乐文本”的划分来说明。“快乐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是本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极乐的文本是把一种失落感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⑧总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向文本——也即向作者——提出要求,这种“喜新厌旧”的做法最终使文学产生了发展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接受美学认为的文学史便是文学的接受史是无可厚非的。
二
在以上回溯作者的“坠亡”之途时,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家携理论的锐器,是多么的势不可挡:它说服了作品,纠合了读者,一同向作者发起挑战,把作者由荣誉的圣殿拉下来,赶上垂死之路。而作者迟迟不见行动,让我们几乎快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作者已无能为力。
到底是作家惹恼了批评家,还是批评家冒犯了作家?总之作家好像不再沉默了。虽然作家并没有锐器利兵,但是他们对批评家的反击也并非不值得关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
门多萨:评论家总会在你的作品里找到更为复杂的创作意图的。
马尔克斯:要是有什么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门多萨:一谈到评论家,你总是带有尖刻的嘲讽口气,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评论家?
马尔克斯:因为他们总是俨然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看到书中描写的人物加夫列尔带着一套拉伯雷全集前往巴黎这样一个情节,就认为发现了作品的关键。这位评论家声称,有了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中人物穷奢极侈的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原来是受了拉伯雷文学影响所致。其实,我提出拉伯雷的名字,只是扔了一块香蕉皮;后来,不少评论家果然都踩上了。⑨
——在这样的攻击中,作家的沾沾自喜和自以为是更是跃然纸上。新批评家所提防的谬误的意图在很多情况下是作家无意为之,正如马尔克斯的夫子自道:“要是有什么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事实上,作家的“愤怒”除却个人成见外,还有便是他们对批评家解读文本时仿佛无所不能般的随心所欲大光其火。批评家的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文本,一旦忽视了这个前提,批评家所建造的便是空中楼阁。针对这个问题,意大利的作家兼批评家昂贝多·艾柯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解决这场争执。
艾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阐释是否有限度?在他看来,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如何对阐释的限度进行界定呢?艾柯认为,有必要引入这样一个概念:作品意图或叫作本文的意图。“‘作品意图’在本文意义生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意义之源,它并不受制于本文产生之前的‘作者意图’,也不会对读者意图的自由发挥造成障碍。”⑩他接着承认作品意图是“独立表达出来的、与作者意图无关的东西”,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本文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来判断,我们在本文中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本文的接受者根据其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⑪才具有可能性。艾柯关于“作品意图”假设的提出,为批评家否认“意图谬见”找到了措辞,使得他们可以坦然地放开手脚,在扩大的批评空间里对文本进行条分缕析。然而,若批评家们无视作品意图,则会出现过度诠释,它将会“必然导致诠释的失控,无限的衍义只能扰乱文本的解读,使文本陷入虚无”⑬。过度诠释在毁灭文本的同时,也让批评形同虚设。作家当然会据理力争,趁机向批评家发难:批评导致文本之死,难道就不会引起批评之死、批评家之死?⑬
三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尴尬、如此紧张的局面?布尔迪厄在《文化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学(等)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包括说谁被谁允许自称‘作家’等,甚至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更确切地说,文化生产场相反两极的占据者之间的斗争目标都对准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推行,斗争围绕着自主和非自主之间的对立是可以理解的。”⑭结合布尔迪厄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作家”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指称——当批评家撰文批评作家时,他的身份暂时也可以成为作家。在他们对“权威话语权利”、“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过程中,一种权力开始渗透和不断地重新分配。这种权力便是福柯所发现的微观权力。它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不应当将施加于肉体的权力视为一种“所有权”,而是应视为一种“战略”;也就是说,这种权力不应当归之于统治阶级,而应当注意到被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其位置可加以更明显的传达,而且甚至会进一步将之扩大。第二,“微观权力”不像宏观权力那样有明显的来源(国家)和模式(命令或法律),而是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它不固定,随时而变,随地而变。第三,微观权力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因此冲突点也几乎无处不在。⑯
由此可见,这种微观权力和我们业已习惯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宏观的权力是多么的不同。微观权力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在漫长的时间里,它隐藏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不被我们察觉。正是这种权力,一但它与话语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话语的权力、言说的权力被牢牢掌握在强势者的手中,被用于记载历史,控制思想。若以此观点观照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便不难承认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争执,实质上都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书写历史——文学史——的权力,谁就有了被载入历史的资格。
通过以上对西方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中心的不断变化的论述,表明了批评研究的空间正在日复一日、前所未有地增大;在日益扩大的研究空间里,批评家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一种并非严格意义上来说,批评家的地位越来越高,处于一种“上升”状态。而作家日益被挤到边缘地带,走上一条逼仄的“下降”之路。
所有人都在创造历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记载历史,书写历史的权力从来只掌握在强势者的手中。正如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所告诉我们的:历史具有文本性,它只不过是按照书写者的需要所呈现的话语片段。历史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因此他们难免不会产生一种被遗忘和被湮没的焦虑感。而只有被载入历史,作家和批评家被遗忘和被湮没的焦虑感才有可能得到释放和缓解。
在以上对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描述及其实质的揭露中,我们始终偏重于对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争执一面的描述,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承认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除了争执就别无其他。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当然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而这也正如我们所心照不宣的那样,他们相得益彰的时候并不少见。但是这将是另外一个重大话题,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要点,这里暂且从略。不过,如果对这种握手言欢的现象加以深究的话,谁能否认其实质不也是对既有权利的认同和对即得利益的默许?事实上,文学史正是在作家和批评家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
注 释
①③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第1页。
②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及其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④艾伦·退特在《诗的张力》中认为,诗歌的语言包括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前者是指本意,也即指称意义;后者指词语的引申义,也即暗示和联想意。“张力”(tension)便是外延和内涵分别去掉前缀后所产生的一个新词,是“从外延和内涵两极之间能找出的全部意义的统一体”。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84页。
⑤“‘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和其它类型的文学,看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的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相互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参见雷内·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页。
⑥⑦罗兰·巴尔特:《作者的死亡》,见汪正龙等编著:《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第274页。
⑧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转引自狄其骢等著:《文艺学新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页。
⑨加·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谈话录:《番石榴飘香》,见《“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外国名作家论现代小说艺术》(下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713-714页。
⑩⑪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第77页。
⑬南帆:《理论的紧张》,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9页。
⑬关于“批评家之死”、“文学理论之死”的说法,并非噱头;相当程度上这在理论界已引发重视。有论者认为“批评家之死”、“文学理论之死”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指涉:在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一切思想和学科形式”,它无所不包,也就无所能包,因而已经不再是文学理论;在中国由于它“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而趋向于死亡,“一个是做得过多,一个是做得过少”。参见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⑭布尔迪厄:《文学生产场的几个普遍特征》,见汪正龙等编:《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⑯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利的终结:与福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