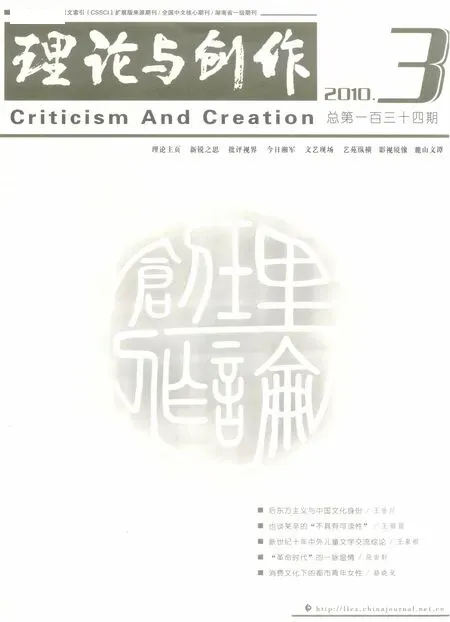巴赫金审美建构论探析
2010-11-25文浩
■文浩
在行为哲学中,巴赫金将现实世界的“主体建构论”引入美学思考中。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和《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他将现实世界的“我”与“他人”的关系演化为审美活动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
一、从审美形式的角度看审美建构论
巴赫金美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审美事件(或者说审美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我们概括他的思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为:在对话关系中作者从外位性出发完成对主人公整体的价值配置,从形式上建构了审美事件。要从形式上建构审美事件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审美事件中存在两个在不同价值层面上独立平等的参与者:作者(意识)和主人公(意识)。
巴赫金认为:“审美事件只能在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①只有一个绝对而统一的参与者时,不可能出现审美事件。在一个绝对单一意识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去限制和丰富自我,就不会有审美化。在巴赫金看来,如果作者意识和主人公意识互相重合趋同,或者互相敌对冲突,审美事件就会瓦解而出现伦理事件(比如抨击谩骂的文章、表彰致谢之辞);如果主人公意识完全消失,成为无声音无生命的认识对象,作者把对象视为客观物,这便出现认识事件(比如论著、讲稿);如果作者和主人公两个意识同时存在,这两个意识中出现一个意识是包容一切的上帝时,两者就不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这时便出现宗教事件(比如祈祷、祭祀、仪式)。因此,只有作者和主人公两个意识处在平等共在的对话关系中,保持相对主体性和独立性,产生纯粹无功利性的价值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审美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肯定“艺术整体的每一具体的价值,都要从两个价值层面上去理解:一个是主人公的层面,这是认识伦理的层面,生活的层面;另一个是完成艺术整体的作者的层面,这是认识伦理的层面,又是形式审美的层面”②。作者(意识)和主人公(意识)各自在价值层面上独立平等的参与“他们的生活,紧张而严肃的关系和斗争所构成的事件,进入艺术整体中凝结成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建构上稳定的、却又能动鲜活的、涵盖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③。在内容和形式关系中,主人公成了生活涵义内容的载体,而作者则是完成这一内容的审美形式的载体,在主人公的内容世界和作者的形式世界里有着各自的边界,这是他们展开审美事件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存在作者的外位性。正如前文所述,存在作者(意识)和主人公(意识)两个平等独立的审美主体,只是审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只有作者外位性的作用,才会最终完成对主人公世界的价值建构,促使审美事件发生。我们细读《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文可以发现:巴赫金的行为哲学承认从价值层面上讲作者和主人公的平等对话关系,但是从形式层面上看,作者却是完成主人公艺术世界的主宰者,作者毕竟是文学作品形式的创造者。巴赫金着力强调了作者的外位性对主人公世界的超视超知和积极建构,彰显了作者的主体性,所以从形式层面上看对话的天平实际上是朝作者这方倾斜的。而在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却着力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主人公在形式结构中的主体性而弱化作者的外位性(超视超知)。正如巴赫金考察复调小说时所说:“在作品的结构中,主人公议论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它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并以特别的方式同作者议论结合起来,同其他主人公同样具有十足价值的声音结合起来。”④可以说,巴赫金在行为哲学和复调理论中关于作者和主人公对话关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对作者的外位性(超视超知)作用也有不同判定。这种区别在长文《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和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彰明较著,中国的《巴赫金全集》编撰者不得不承认:“此文(指《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与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有着深刻的联系。不过可以发现,作者与主人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关系,按照巴赫金的理解,似乎与本文描述的审美活动的普遍条件相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对作者的起完成作用的积极性给以积极的抗拒,作者则放弃自己在审美方面的特权,放弃自己原则上的‘超视’。”⑤简单的说,在行为哲学中巴赫金突出作者在审美形式上的主体性,强化作者外位性(超视超知)作用,在复调理论中他突出主人公在审美形式上的主体性,弱化作者的外位性(超视超知)作用。这种区别是我们正确理解巴赫金行为哲学中审美建构论的基础。那么,巴赫金所谓的作者外位性到底指什么?在审美事件中有何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掌握到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过任何他人的,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所决定的。”⑥自我作为主体看自己总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我的内在观察视角决定了我总是看不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头、脸、后背、后颈),但是,我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外在位置却使我可以看到他人身体的某些部分(头、脸、后背、后颈)。反之,亦然。每个人因为外在于他人而具有一种视觉优势,能够超越他人视角看到他人视角不及的地方。空间上讲是这样,时间上、感觉、涵义整体上讲也是这样。这样我们可以超越他人看到,知晓,感觉到对方视觉知觉不及的东西。这种超视超知的位置不可以替代但可以互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视阈剩余”或称作“视觉余额”。作者作为主人公世界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也具有这种超视超知和“视阈剩余”。
另一方面,在进入审美事件之前的主人公也是一个自我(生活原型,不能完全实体化,只能假设),不是他人,不是作为艺术整体的他人形象。前审美事件中的主人公在现实中也曾经过着认识和伦理的生活,“我总是以尚待实现的,应该而希望有的因素来充实自己,我的自我界定的实际重心只能落于未来之中。”⑦所以,自我一直生活在开放的伦理事件或设定的认识事件里。这个自我从内在视角体验自己,永远是开放的、变化的、未完成的,没有办法得出结论或者盖棺论定,因为自我在现实中一直变化着。这样,作为自我的主人公拥有的开放性、未完成性使主人公无法从自身内部完成自己,定型自己,变成一个生活整体。比如,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创作的原型,但是从审美形式的角度讲每一个原型都是不完整的,也是未完成的,需要作家用艺术手法来“剪辑”定性,创造出一个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总结这两方面,既然主人公无法从内部完成自己,作者又存在“视阈剩余”的外在视角,而审美事件的“建构就是把具体的、唯一性的局部和因素,通过原则上必然的而非偶然的配置与联系,形成为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这样的建构,只有围绕着这个人、这个主人公才能得以实现。”⑧那么,作者围绕主人公世界进行的价值配置就只能存在于主人公之外——外位性。“外位性”是巴赫金美学主体性思考中的核心范畴。关于“外位性”,巴赫金有几段经典论述:
作者的意识是意识之意识,亦即涵盖了主人公意识及其世界的意识。作者意识用来涵盖和完成主人公意识的诸因素,原则上是外位于主人公本身的。……较之每一个主人公,作者总有一定的又是稳固的超视超知的部分,能够最终实现整体性(既是主人公的整体性,又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事件的整体性,即作品的整体性)的那些因素,恰恰就处在超视超知的部分之中。⑨
……作者对主人公所持的一种基本的、审美上富有成效的立场,它的普遍公式就是,作者极力处于主人公一切因素的外位:空间上的、时间上的、价值上的以及涵义上的外位。处于这种外位,就能够把散见于设定的认识世界、散见于开放的伦理行为事件(由主人公自己看是散见的事件)之中的主人公,整个地汇聚起来,集中他和他的生活,并用他本人所无法看到的那些因素加以充实而形成一个整体。⑩
艺术家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有着至高的外位性。但这种针对他人生活事件以及这一生活世界的外位性,当然是对存在事件的一种特殊的但有据的参与形式。发现从外部把握生活的重要立场——这就是艺术家的任务。艺术家和一切艺术也正以此来构建全新的世界观照,来塑造世界形象、世界现实的血肉之躯;而这一点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文化创造所能以企及的。11
由此可见,所谓外位性就是作者对主人公的一种审美立场,作者(审美形式的载体)总是处在主人公(涵义内容的载体)的外位发挥超视超知的优势,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把零散而未完成的主人公生活世界聚合成有血有肉的艺术整体。这样,作者意识从形式上涵盖主人公意识,参与他人生活事件,塑造新的生活形象。
我们以为,外位性概念深刻的体现了作者在审美事件建构中的主体性。
首先,这种“外位性”是能动的。巴赫金指出,在审美移情中,对象“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前提是需要一个处于外位的审美上能动的主体(这里我们抛开人的宗教体验)”12。在巴赫金看来,审美事件的建构可以理解为审美移情的完成。作者作为主体在外位立场上的能动反应,为审美移情对象——完整的内在之人(主人公)的发现提供了可能。具体来说,作者“我”从外位进入他人意识,我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体验他作为内在之人的痛苦、哀伤、欣喜、愤怒,我越深入的体验他人世界,我就越被他人局限,甚至被他人心灵控制着。如果只到这一步,就是消极的移情。关键是第二步,我要从内在之人回归我自己的意识,回归我整体而坚实的外位性立场上,回归主人公意识(他人)和作者意识(我)的边缘上。我栖居在这个特殊的分界线上,自由的“越界”从其内部见他人之所见,又从外部见他人之所未见。这样,我深入体验他人内在意识时把他人看作主体,我回归外位反观他人时又把他人看作客体。相应的,在分界线上对主人公而言,一方面,是我自为的主体性,一方面,是我在他人眼中的客体地位。处于外位的作者和内在的主人公都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交替扮演角色,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最终作者和主人公相遇在边界线上,作者对内在整体之人(主人公)的移情也就成了边缘形象,它既不是主人公世界的独白,也不是作者意识的独白,而是作者外位的能动性和主人公内在世界的对话交集。正如彭克巽在《苏联文艺学学派》里指出的那样,巴赫金强烈的反对将作者“淹没”在主人公的世界里,反对“淹没”作者外位性的能动作用。巴赫金批判费舍尔、李普斯、谷鲁斯的表现美学将审美活动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移情。在审美活动中,体验和沉浸只是个别的审美要素,而不是审美活动的全部。作者可以对主人公进行体验、共感、同情,内摹仿对象的生活,但是主人公内在世界的视角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于作者外位性的超视超知优势,才能从整体上创造出作品来。说到底作品的整体不是被体验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作者外位性立场创造出来。“表现美学以及现代美学的通病在于只分析个别的审美要素,而忽略对作者构筑艺术大厦整体的审美活动的研究。”13
其次,“外位性”是包容的。作者用他稳固的超视超知的视角形成作者意识,它是意识之意识,包容和涵盖了主人公意识及其世界,它也包容了主人公的话语和生活。作者知道每一个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而且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14在宗教事件中上帝意识包容一切,主宰主人公意识,全知全能,但是,在审美事件中作者意识对主人公意识的包容只是形式层面的,即在艺术创作的形式中,我们通过作者意识展现完整可见的主人公。而在艺术价值的层面,作者和主人公仍然是两个原则上互不融合的意识,两个对话的主体。主人公既然是被创作出来的有价值的主体,作者就不能把他视为纯粹的认识对象,也不能把他视为作者意识的传声筒,主人公具有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自足的艺术生命。
再次,“外位性”也是整体的。作为审美完成因素的统一体,“作者对主人公的个别表现所作的反应,是以对主人公整体的统一反应为基础的……这种对主人公整个人的整体反应,正是特殊的审美反应。”15在这种反应中,作者统一的将认识伦理事件中片段零散的主人公生活,凝聚成一个丰富多样的整体。作者将主人公从开放的存在事件中抽取出来,定格为一个形式化的他人形象。
最后,“外位性”是斗争性的。既然作者外位于主人公,那么,作者就要将自己排除在主人公生活之外,作者对主人公世界的建构“是作者以不参与现实认识和伦理行为的旁观者身份,关切地理解并完成主人公的生活事件”16。而实际的审美创造过程中,主人公原型往往就是作者生活事件里的朋友、对手甚至作者本人。作者想坚守自己的外位立场,将现实中感受自己朋友或对手的生活,与创作状态中设想自己感受别人的生活原则性的区别开来,这实际上需要斗争,尤其是主人公具有自传性质时(主人公以作者自己为原型)。
总之,作者在审美事件中从外位性立场出发,把主人公视为他人,视为对话的主体,对他人世界发挥包容、整体、斗争和能动的主体性作用,在对话中建构了一个形式上完成的艺术世界,完成了对主人公整体的价值配置。所以,巴赫金说:“艺术任务在于构筑一个具体的世界:以活的躯体(外在主人公)为价值中心的空间世界,以心灵(内在主人公)为中心的时间世界,以及最后,是涵义世界,三者在具体的相互渗透中构成统一体。”17这是从审美形式的角度看审美建构论。
二、从审美态度的角度看审美建构论
巴赫金以上论述是从审美形式的角度探讨了作者主体性对主人公世界的价值建构,而从审美态度的角度讲,审美事件也是作者对主人公世界整体态度的展开过程。在巴赫金看来,空间形式上的外位性立场背后,其实蕴涵着作者的审美积极性(创造性的珍爱)态度,这也是作者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如前文所述,审美事件可以理解为作者从外位对主人公的移情或者共感,“审美积极性本身则表现在对共感内容的创造性珍爱这一因素里,是这种珍爱创造着外位于共感生活的审美形式。审美创造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统一的意识中内在地加以阐释和理解,审美事件不可能只有一个参与者,他既体验生活又把自己的体验表现在重要的艺术形式里。”18作者对主人公的审美态度可以理解为审美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创造性的珍爱,珍爱紧密联系着审美形式和审美态度。一方面,“珍爱创造着外位于共感生活的审美形式”,另一方面,珍爱又饱含着作者丰富无私的审美态度。巴赫金所谓的“创造性珍爱”融合了康德的“纯粹无功利性的审美判断”和东正教的博爱情怀,强调作者对具有多样性价值的主人公(生活涵义内容的载体)应该抱有一种无功利性的关怀,把它视为一个可爱的主体对象。正如巴赫金所说:“艺术家正是善于超越生活而积极观察的人,不仅是从内部参与生活(实际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生活)并从内部理解生活,而且要从外部珍爱生活……”19从审美态度的角度讲,审美事件也可以理解为饱含创造性珍爱的作者和充满价值多样性的主人公在审美形式里的相遇,审美态度的展开和审美形式的创造紧密联系起来。
从巴赫金行为哲学的角度讲,审美事件是存在即事件的一个特殊因素,“人的主体在巴赫金看来首先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过程。”20审美事件中,审美主体作者发挥外位的审美积极性,拥抱和珍爱具有多样价值的主人公世界,参与存在即事件,同时也就完成了对整体人的完形,获得了鲜活的审美形式。而在抽象的理论认识事件和日常生活的伦理事件中,要从整体上创造一个他人都是不可能的。巴赫金强调:“只有他人在我的体验中才能与外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在审美上令人信服地融入这一世界,并与这一世界相协调。”21和他人的内在联系,成了主人公自我和世界的桥梁。自我没有办法从内部实现自我,自我在内部是消极、幼稚而单纯的,只有另一个处于外位立场上的自我(作者)对我抱有审美积极性,释放创造性的珍爱,才能把具有多样价值性的主人公定格为主人公形象(他人形象)这一审美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说:“心灵(这里的“心灵”就指“内在主人公”,主人公形象的一个方面,论者注)是我的精神(“精神”指作者自我,论者注)赠给他人的礼品。”22这是一种无私的馈赠,一种无私的爱。“这里是要建立一种针对他人的崭新的情感意志立场。我们把这种立场称做爱,但这种爱完全不可能在自己身上体验到。”23这个创造性的爱,正是珍视之爱,它不是我们私人情感意义上的爱,而是带有东正教的博爱普众的情怀,是客观的、无私的、利他主义的情感意志立场,是作者对主人公的馈赠,不求回报的形式馈赠。
所以说,从审美态度角度讲,审美事件中,作者从外位性立场上灌注的审美积极性(创造性的珍爱)和价值多样性的主人公在审美形式中相遇,完成了对审美事件即存在的参与,艺术形象成了作者对主人公的馈赠。这是巴赫金从审美态度的角度展开的审美建构论。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5 16 17 18 19 21 22 23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第99页,第100页,第 5页,第498页,第119页,第225页,第77页,第108-109页,第110页,第288页,第182页,第101页,第111页,第287页,第185-186页,第287-288页,第137页,第230页,第145页。
13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
14注意,在审美事件中作者因为外位优势比主人公知道的多,并不意味着在小说中叙事者知道的一定比主人公多,因为叙事者不等于作者,叙事者对于主人公可以是全知视角,也可以是限知视角。
20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