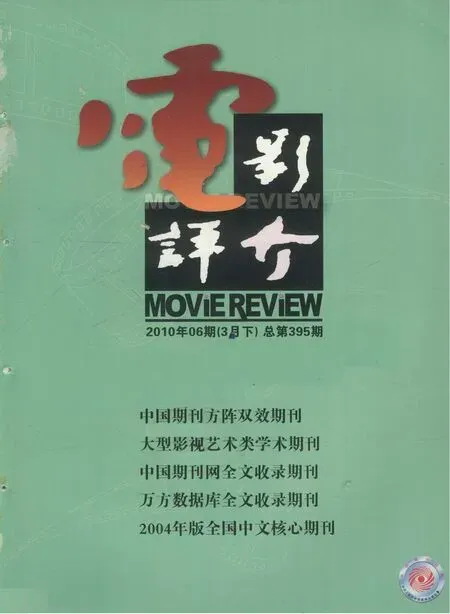浅析纪录片创作中“情景再现”的使用
2010-11-16郑德梅
爆竹声中,红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大大的福字贴到门上,孩子们开心地在巷子里放着烟花,夜市上熙熙攘攘……大型纪录片《故宫》一开始便利用情景再现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403年元月一日这一天,向观众呈现了当时人们庆祝元旦的情景。片中类似于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大都采用了情景再现的创作方法,带人们回到那个时代,走进宫中,了解历史,了解文化。毫无疑问,情景再现这种创作技法的使用,成为《故宫》创作的一个亮点,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提高了收视率。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观众到底是在看一部纪录片还是故事片?近年来,伴随着情景再现的广泛应用,类似的争议日渐频繁。那么,到底孰是孰非?该如何评论这种现象?该如何来看待情景再现呢?
一、关于情景再现
狭义上的情景再现,是指纪录片的一种创作技法,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过声音与画面的设计,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种电视创作技法。它一般是在失去现场纪录机会的题材和场景中使用,是纪实风格的一种异化手段。
情景再现发轫于纪录片创作领域,但它很快就超越了纪录片的范畴。因此,广义的情景再现是一个节目层面的概念,是一种节目的创作形态,它泛指一切运用了情景再现创作观念与技法的纪录类节目。在这些作品中,作为创作技法的情景再现,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与采访、资料引用等众多纪实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因此,广义的情景再现,是指采用包括情景再现在内的众多创作技法共同构成的纪录作品,它不仅包括作品中再现部分的内容,而且包括作品中与真实再现结合使用的采访和资料部分的内容,这类节目作为一个整体也被称为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的出现有其深厚的实践背景和理论渊源。情景再现的应用源头可以追溯到纪录片鼻祖弗拉哈迪的影片——《北方的纳努克》。1920年,弗拉哈迪在制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就使用“摆拍”手段拍摄纳努克人造冰屋、捕猎等场面。弗拉哈迪在后来的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实现了“结果的真实”。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弗拉哈迪这种对真实性的独特而富于启发性的理解对今天的纪录片创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推动了情景再现的发展。在他的不少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情景再现。1935年,伊文思在拍摄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纪录片——《博里纳奇矿区》时运用了情景再现。其中一处是由矿工扮演警察,强行搬走矿工的家具。伊文思认为,“这场戏在我们的完成影片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在博里纳奇拍摄这部影片期间,我们的电影美学经历了重大的修改”。在当时,这种创作技法被伊文思称为“重拾现场”或“复原补拍”。他认为,只要补拍场面不是出于捏造,而真正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那么生活本身将赋予它力量,并使它充满了新的内容和情感。
最初在中国电视荧屏上探索使用情景再现的,是1995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当时,《东方时空》中出现的一些以真人扮演的手法来创作纪录片,是国内较早出现的对这一手法的自觉探索。较早的样片之一是王子军的《南京的血证》,短片中编导利用情景再现的手法重现了当时的一些场景。当老人讲到自己当年在照相馆当学徒时藏起一本反映日本人罪行的照片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照相馆里,一个男青年正在忙碌,这时一个挎着战刀、穿着皮靴的日本人大步走了进来。之后两人对话。男青年在洗照片时看到了照片的内容,极为震惊,偷偷保存了一套,藏在墙砖的缝隙里,直到今天。通过这一情景再现,观众更直接的了解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创作者在使用情景再现这种创作技法上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益与效应,并通过经验总结和专家的理论探讨趋向成熟。此后,真实再现这种创作形态的节目呈现出了批量生产的趋势。北京电视台的《记录》、《新闻故事》等栏目,河北台、济南台等也直接开办了以“真实再现”命名的栏目。这些节目大多现在仍在播出,而且收视率较高,观众反馈比较好。
二、情景再现的表现形式
情景再现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扮演、搬演和资料摘录。
扮演是指利用演员扮演人物。根据情景再现程度的不同,对演员的挑选也有不同层面上的要求。与故事片不同的是,纪录片对演员的演技不做过高要求,最多要求他们的面貌与气质特征与作品接近。相反,对于纪录片来说,演员的道具、服装这些细节性因素往往比演员本身还要重要。一部谨慎的纪录片应该尽量要求这些道具细节极端真实。
搬演是指重现一个有意味的场景或事件。搬演常有演员参加,就融入了扮演的因素,但它与扮演的不同之处在于,扮演重在表现人物,而搬演重在表现一个场景或事件,比之扮演,多了叙事性因素。搬演需要利用或设置与历史事件情景氛围相近似的场景,使之能有效地传达出所要表现的主题。
资料摘录是指利用各种影像资料(主要是故事片段落)作为纪录片的真实再现段落。真实再现的部分不一定都需要创作者自己去制作,有时也会借用一些其他的影视作品达到同样的目的。例如,出于文物保护或其他一些原因,中国故宫的镜头比较难得。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火烧圆明园》和意大利导演贝尔•特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中大量镜头是在故宫实景拍摄的。因此,在反映清代帝王生活以及其他与故宫有关的纪录片中常会借用以上电影的镜头。
三、情景再现的作用
1、情景再现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技法,情景再现的出现打破了此前电视纪录片的诸多束缚,可以通过各种形象化的手段表达人们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还能够尽可能的表现或还原过去发生或存在的、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文化历史,增强了纪录片的可视性。
对于创作者来说,情景再现解决了编导无米下锅的烦恼,尤其是拍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时。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史料,史料是最有说服力的。可无论是文字性的、实物性的,还是影像性的,这种资料都是少之又少,无法撑起一部完整的作品。况且,这些过去发生的历史行为和历史事件,往往就是关键性事件,是节目的核心事件。如果不把这些向观众交代清楚,观众的理解就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形成叙事断点。而情景再现恰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情景再现根据历史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和痕迹,用演员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重现那些过去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缝合叙述历史时遭遇到的断点,使叙述更加完整、流畅。
2、情景再现增强了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
纪录片既是技术本体,又是艺术本体;既有纪实性,又有艺术性。在情景再现的作品中,编导可以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创作才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融入作品,以纪录片真实的内容为基础,辅以形象化的表现手段,使纪录片真正与艺术接壤,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纪录片《失落的文明》为了表现庞贝城在奢侈安逸的生活中突然遭受天灾,搬演了这样的画面:堆满水果的茶几与注满美酒的酒杯忽然翻倒在地……这种画面与庞贝城在毫无准备中突然遭受灭顶之灾极为相似。这种模拟场景的方式,不仅有效的传达了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还增加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3、情景再现提高了纪录片的观赏性
情景再现让镜头跳出史料的故纸堆,创造性的反映历史情景,将呆板的历史解说形象化,让观众能够置身其中,深刻地感受当时的历史情境,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审美感受。大型纪录片《故宫》中就再现了靖难之变这一历史事件。战场上炮火轰鸣,战马嘶鸣,身穿铠甲手持长枪的士兵在进行激烈的交战……这几个镜头就很好地展现了当时的战争场面。影片开头的这两处情景再现明显增加了作品的可视性和故事性,同时给观众以逼真的感受。在接下来的内容里,编导还真实再现了大殿里雍容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几百个朝拜的大臣、碎步行走在宫中的太监……这些真实再现的镜头基本上都是模糊的,我们看不清人物的面貌,人物也没有对白。但是,观众被带进了逼真的历史氛围中,进入了一定的艺术情境,而这种艺术情境又符合人们对历史的神秘、浪漫、繁华的主观想象,自然会产生美的感受。
四、情景再现带来的问题及使用原则
情景再现的应用的确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逐渐成为创作领域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可以说,情景再现一定程度上养成了纪录片“舍本逐末”的风气。众所周知,真实是纪录片的根本,纪录片中最有含金量的东西是历史上真实存在和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对于那些有真实记录镜头的段落,应尽量避免使用情景再现。只有在编导面对历史的缺憾无能为力时,情景再现才能被派上用场,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中央电视台栏目制片人周兵在发现梅兰芳在美国百老汇演出的一段一分钟长的影音资料后,一秒钟都没有剪掉。周兵说,如果有100分钟、200分钟梅兰芳表演的原始资料,或者当时出现活动的胶片资料,他在节目里肯定不使用情景再现。然而,现在一些电视台的编导却把情景再现当成了救命的良药,放弃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完全寄托于情景再现,生生把一个纪录片拍成了故事片。而任何使用情景再现的电视工作者都必须真切地认识到,情景再现是电视工作者面对历史缺憾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切不可把它当成工作的重心,沉溺于其中。
另一方面,情景再现的广泛应用使中国纪录片开始呈现出娱乐化、泡沫化的趋势。吕新雨在《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中写道:“情景再现使用的底线是不能掩盖我们对历史真相把握的信念,否则会使观众丧失掉对纪录片的信任感。情景再现是有边界和底线的,不可以泛滥。否则,会造成我们对纪录片最重要功能的抹杀,这个功能就是为历史提供证据。”因此,纪录片的发展不能在情景再现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偏离了正轨,否则,纪录片就失去了它内在的深度,仅仅成为一道快餐。
情景再现作为纪录片制作的一种新的虚构方式,引起了人们对纪录片真实性的重新思考。然而情景再现作为众多电视手段中的一种,它本身并不会动摇纪录片的真实性。可情景再现如果在实际操作中被不加限制地滥用,却会影响到纪录片的真实性。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制作者如何使用,能否把握好分寸。因此,我们在应用情景再现时,要遵守一定的原则。
1、情景再现的使用要有必要性
说到底,情景再现毕竟是编导面对历史缺憾的一种无奈选择。对于那些有真实记录镜头的段落,应尽量避免使用情景再现。例如,《周恩来外交风云》中有不少新拍的内容,虽然它们画面构图工整,影调色彩鲜艳,摄影机运动平稳,但其魅力远不如那些陈旧的影像资料,原因就在于,历史影像资料所具有的历史现场感是无法复制的,真实再现的处理稍有不当就会露出马脚。这启示我们,真实再现的优势是在于弥补历史镜头的缺失,在于再现而非真实,可有可无的再现应该尽量避免。
2、情景再现的使用要符合真实性原则,符合逻辑
纪录片创作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作,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真实永远是纪录片相较其他艺术作品最具区隔性的属性。因此,情景再现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即使客观事实难于把握,也应当要有事实根据,切忌编导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为了记录片的观赏性而随便臆造。某电台报道一媒体的电视人是这样进行“纪录片”创作的:只差没带化妆师了,其他所有的场面和内容都是真人表演,用当地人演当地的戏,一个受过师范教育的年轻的乡村教师,硬是按照导演的意图把漂亮的小分头用大碗扣住剪成了锅盖头,以突出其意想的乡村效果……。这样拍出来的片子,其实质是用业余演员扮演的一部具有纪实风格的电视剧,而并非纪录片,严重背离了真实性的原则。
同时,情景再现还要符合逻辑,让观众看后感觉真实可信。也就是说情景再现的内容不能违反人们所感知的真实生活中的一般惯例。获美国199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的纪录片《九月的某一天》,讲述的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在奥运村遭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袭击丧生,另有5名枪手和1名警察死亡的惨剧。这个惨剧当年曾经轰动世界。这部纪录片有很多镜头是1999年补拍的,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一些场景,但其中一些镜头却让观众感到迷惑,例如恐怖分子在房间外巡逻的镜头,让观众有些分不清真伪。从内容常识上判断,观众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怀疑:恐怖分子这么明目张胆地守在外面,难道他们就不畏惧狙击手的子弹?这些让观众产生疑惑的情景再现镜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3、情景再现的使用要注意身份标志
身份标志是情景再现不混淆视听不误导观众的前提。在使用情景再现这种创作手法时,需要在编辑中注意资料还是再现的身份标识,对容易造成认识混淆的段落加以显著区别,以防误导观众。一般说来,电视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部分都要用字幕、解说词或是经过一些特技处理的画面来告诉观众这是重现或故事片资料,让观众一眼就能辨别出来。因为情景再现这种创作技法只有具备一定的间离性,才能获得观众对其真实性的认可。任何抹平了观众与真实之间距离的情景再现的处理方式,都是失误的。
情景再现的应用已成为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一直以来,关于纪录片中能否使用情景再现,进而能否运用一定的虚构手段来进行创作,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其实,情景再现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它既受纪录片发展内在规律的影响,又与当下的媒体环境、观众的欣赏需求密切相连,是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相信,只要纪录片创作者对情景再现合理使用,遵循一定的原则,情景再现的独特优势必会给纪录片带来一片新的艺术表现天地。
[1]程宏,苏峰,罗琴,“真相”与“造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石屹,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董长青,申思,高苒,浅议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新闻传播,2007,(4)
[4]孙宝国,电视纪录片形态辨析,北方传媒研究,2006,(4)
[5]王辉,纪录片想法与做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