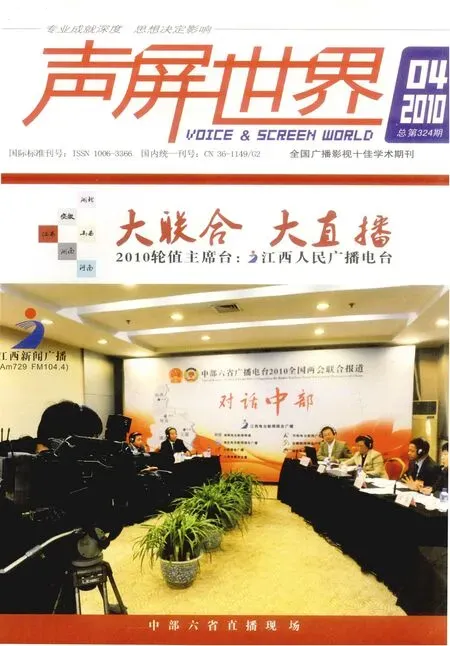魅力永存的谍战剧
2010-11-16常凌翀
□ 常凌翀
魅力永存的谍战剧
□ 常凌翀
近年来,电视荧屏上枪声不断,谍报频传,就算是谈场恋爱,也没准是“美人计”……频频亮相的谍战题材影视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追捧,一度成为收视新宠。从《暗算》到《剑谍》,从《潜伏》到《密战》,从《誓言无声》到《誓言永恒》,《秋喜》《风声》随后紧接登场,各路英豪一路走红,各个剧种你方唱罢我登场,接连创造不俗的收视成绩。谍战剧热播并非偶然,依托宏阔的历史背景,谍战剧以其人文的英雄叙事和精致的人物造型向观众展现了隐蔽战线特殊职业的光彩与魅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幕后“旧闻”“战事”。观众通过影视剧文本反映的重要年代和重大事件来不断解读特殊时期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赤诚情怀,并进而激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集体追忆,极大程度地契合了观众追新求奇的收视心理和英雄情结。
谍战剧缘何如此火爆
事实上,谍战剧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影视剧市场上的热门题材。自194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反特电影 《无形的战线》后,其故事模式相继被模仿沿用。《一双绣花鞋》《冰山上的来客》《保密局的枪声》等都是观众熟悉的经典谍战片。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新世纪《暗战》《潜伏》《特殊使命》《重庆谍战》《誓言永恒》《密战》等一批新创作的影视作品,均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可以说,作为一种类型片,谍战片是中国影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已经远离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但谍战题材仍旧是影视剧市场永不凋谢的花朵。
一方面,谍战剧的出现与受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新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到现今热播的 《誓言永恒》《密战》,谍战剧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另一方面,在古装剧式微、涉案剧逐渐淡出黄金档,亲情剧让观众看得厌烦之时,谍战剧乘机而入,为自己创造了播出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更有其深层次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相比于涉案剧的低俗立意,谍战剧贯穿始终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具主流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带动公众的观赏热潮。另外,目前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为谍战剧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部分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逐渐公开,为谍战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使得谍战片再度兴起并魅力不减。
英雄叙事架构契合受众的审美期待和心理诉求
相较于现实生活剧的平淡叙事和情感偶像剧的缠绵悱恻,谍战剧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复杂多变的人性让人耳目一新。从理论角度讲,谍战剧热播是观众对“革命时代的崇尚,对革命英雄的怀念,是一种革命情结的折射,是一种欣赏情趣的回归”①。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受众更倾向追新求奇,偏好紧张、悬疑的影视剧作品,从而为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平添几分惬意和宣泄方式。
对于谍战、特情类影视剧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性挣扎、紧张刺激的悬念冲突、惊险玄妙的情节推理向来是其标志性特征。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敌我莫辨、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等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要素。一方面,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出发,某种程度上它暗合了当今社会受众在重重的社会压力下,真实自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现实生活的裹挟之中所产生的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人性的弱点、社会的逼仄、情感的纠葛、生活的浮躁都仿若谍战片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现和演绎,给人一种虚实难辨的错觉。另一方面,从观众审美心理的视角来讲,在观剧过程中观赏者都会有一种保守和创新的期待视野,谍战剧中贯穿始终的革命情结和峰回路转,契合了受众内心深处的心理诉求和审美期待②。
谍战剧在情节架构和悬念、对抗、冲突的叙事技巧上,充分运用多向度的发散情节,营造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扑朔迷离的氛围。如《暗算》,全剧分为“听风”“看风”和“捕风”三个部分,三者看似相对独立,但其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部影片通过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谍战活动,不断增加观众的观赏兴趣和审美期待。《潜伏》以“每10分钟一个危机,每5分钟一个意外”的悬念密度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使观众在“突转”的叙事策略下不断被抛向浪尖又被卷入谷底。正是因为有悬念,观众才期待“柳暗花明”的谜底,而危险能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悬疑得释、化险为夷能帮助人们释放焦虑情绪。与观剧的焦虑相伴随,现实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焦虑也得到转移或适度缓解。谍战剧就是在这种突变和悬念的牵引下增强了观众观赏的主动性,保持了观众持久的观赏兴趣和心理期待。这正是经典谍战剧的魅力所在。
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彰显谍战剧的精神内核
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主题,它着力描绘了“潜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平凡的,又是特殊的,他们在坎坷磨砺中慢慢成长为英雄。他们不可能如那些“显在”的英雄一样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谍战剧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品位,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③,镌刻在平民叙事结构上的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使观众感到亲切可触,产生由衷的认同和敬仰。
《特殊使命》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几度把主人公的个人“信仰”推向一种极致。在展现敌我双方高智商的斗争中,用情节表现出了高手与高手的对话,而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志存高远的坚定者,这些正是该片所着力张扬的人文主题。而“信仰”这个主题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尤为发人深思。人行于世,不是单纯地追名逐利,而应追求自己的真理和信仰,这应是谍战剧带给现代观众的启示。当余雪瑶劝巩渭平退党时,他说,“我想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在接受“特殊使命”后,巩渭平改名为巩向光,深含特殊寓意。
余则成的信仰,是在“潜伏”中不断成长、成熟的。余则成起初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信仰,在和左蓝谈起信仰时只是说,“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之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生活”。这时候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生活是平静的。在左蓝和吕宗方的引导下,他逐步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左蓝临去延安前的谈话,使他决定投向共产党,正式踏上自己的信仰锻造之路。在复杂险恶的斗争中,余则成的信仰才逐渐得到提升、净化。最后他高诵《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自然是水到渠成而不显突兀。很显然,余则成的人格就其底色来说,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普通人。余则成并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更能够唤起观众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使创作者更易用故事里的情境来带动故事外的人,实现其意义引导,而这正是信仰的力量,是精神的力量。
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演绎,谍战剧实现了受众对智慧与力量的崇拜,对冒险的渴望,对革命岁月的向往。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潜意识里的英雄情结和心理期待,使观众获得了心理共鸣与认同,从而在“拟态环境”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个人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谍战剧扎堆的现实隐忧及突围之路
明星云集的阵容、快速闪跳的剪辑、生动流畅的音效,使谍战题材呈现出精美的格调和异样的风情。与此同时,浪漫爱情、激烈枪战、重重悬疑、错综矛盾、智力挑战、酷刑展示等复杂刺激的审美元素,令谍战片形式越来越丰富。然而,随着大量“跟风”之作的出现,谍战剧渐渐身陷“模式雷同”的泥淖中,多数作品缺乏独特风格与精巧剧情设计,盲目套用美剧模式,失去了革命历史题材所应具备的传统特色与文化品位。“美女特务+帅哥卧底”的组合,已成为绝大部分谍战剧的通用法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作为类型剧的谍战剧,多以商业价值为第一诉求,多按照传统经验进行模式化生产,在人物和故事层面开掘不深,缺乏突破和创新,基本上都是人物被动服从故事情节,多为满足娱乐和迎合市场而生。
谍战剧要走出当前不正常的同质化竞争,获是长足发展,不应仅盯着收视率和市场需求,要从类型剧的思维方式和制作模式上追求突破和创新,在架构故事时要力避刻意渲染恐怖、暴力、猎奇、惊悚、怪鸷;要致力于“复杂人性的深度开掘,保持观赏性、加强思想性、提升艺术性”④,从信仰、智慧上寻找推进故事的依据和力量,撬动整个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建构;要确立高尚的审美格调、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的主题思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促进此类题材创作的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
①状 态:《谍战剧的火爆与隐患》,《大众电影》,2009(10)。
②胡元:《谍影重重——论当下荧屏谍战片热》,《视听纵横》,2008(5)。
③李 庚:《谍战题材电视剧的文化解读》,《光明日报》,2009-08-17。
④周见新:《可圈、可点、可称道的人性开掘——电视剧<重庆谍战>评析》,《当代电视》,2009(2)。
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