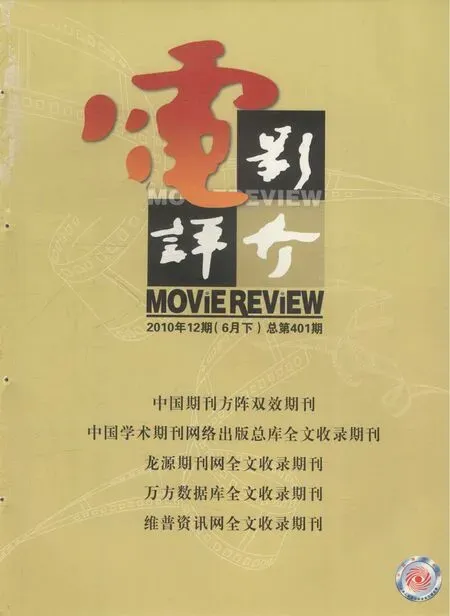许鞍华的影像叙事——谈《半生缘》的改编
2010-11-16黄元英
电影和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联系是这么地紧密,远远超过了电影与其他艺术联系的紧密程度。“把小说的叙事因素,把它那种从现实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中刻画人物性格、透视人物心灵的艺术可能性引进电影,这是电影艺术在对诸种艺术进行综合中所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1]文学向我们揭示了心灵,而电影则为我们展示了形象。
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影视导演的改编开始倾向于现当代的一些作家作品,在香港就出现了对张爱玲作品的成功改编。它们是:1983年香港女导演许鞍华改编的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1988年台湾导演但汉章将《金锁记》改编成的《怨女》,1994年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1997年许鞍华的《半生缘》,1998年侯孝贤的《海上花》。
电影《半生缘》(1997年),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是许鞍华第二次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对于名著改编,虽然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但改编本身就是一种解读,是一次新的创造。电影《半生缘》是许鞍华理解的《半生缘》,而不是张爱玲的。在电影中导演只有知道自己要讲什么,才能真正讲得好。那么要使影片“有戏”,就要对原著进行恰当地修改,敢于依据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审美需要和电影自身的特点对原著有取有舍,创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
一、叙事视角及顺序的改变
“确定从何种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观念方面的。”[2]“叙述人称从表面上看是解决指代的问题,而在实质上是叙述视角的选定。从叙述称代上选定视角,有你、我、他的人称视点;从叙述方位上选定视角,有仰视、俯视和平视;从叙述的层次上选定视角,有表层叙述(行为叙述) 和深层叙述(心理叙述)。”[3]
小说由于和电影同为叙事性作品,都要展现环境、刻画形象、铺叙情节,小说遂成为电影改编的主要来源。世界上著名的影片,绝大多数改编自小说。诚然,同一故事,能用不同模式(如小说、电影、戏剧等)加以叙述,而且“说法”并非相同,但重要的并非是所叙述的故事,而是叙述故事的方法。
在《半生缘》这部小说中,作者张爱玲选择了全知全能的传统小说的叙述视角,她的视点和当时的政治气氛基本无关,她只是想用自己的笔写一些旧事和“凡人”。所以,选择这样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有了俯视的味道, 整个社会或所有人物基本都处在一个被描摹的地位,叙述人俯瞰全局无所不知。《半生缘》不以故事“开端时间”为起点进行顺序叙述,而偏离“现时叙述”采用追溯过去的叙述方式。小说以世钧十四年后的感悟开始回忆,回到十四年前曼桢、叔惠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着力营造出一种悲凄、苍凉之感。叙事学认为,时间的距离感容易使文本与接受者之间产生悲剧效果,该文本即是用遥远的过去调动读者的好奇和联想,淡淡哀愁和忧郁氛围自然营造,不留痕迹。
《半生缘》第一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4]小说开端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叙述,全知视角。此时,叙述者似乎试图将读者带入男主人公的世界,去了解他的心理和故事。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策略。然而,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作家又从作品里慢慢引退出来,变成有节制的叙述,作者通过“显示”的叙事方式将故事与人物和盘托出,而作者自己的声音从作品中消失。
十多年的情缘,张爱玲采用了一系列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对传统言情小说中的从相识——相知——相恋——误会——消除——圆满结局进行了颠覆。张爱玲的小说很少用大喜大悲来收场,她将世俗生活还原,揭示人性的普遍与深刻。“张爱玲在高潮来临时每每笔锋陡转,避开人们预想的常规结局”[5],曼桢与世钧的重逢,只能是“回不去”而徒增伤感,叔惠和翠芝的会面也只剩凄凉情绪的余绕,重逢却无法圆满,这是人生最大的无奈和缺憾。
对于电影《半生缘》,许鞍华将这部小说的内容纳入了100多分钟的电影中,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叙事顺序作了精心考虑。片中,许鞍华采用了男女主人公的视角交叉叙事。先用女主人公曼桢的画外音引出男主人公世钧:“他来城里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一共见过他四次,每一次他都像看不见我,可能是他太专心做事吧,根本就没留意旁边的事情。”观众可以从这句话里听出女主人公内心的不确定,进而设下一个小悬念。在这里旁白起到了强大的叙事功能。接下来四个镜头之后,视角转变,男主人公上了电车,当路过多年前的那条街道时,久远的记忆开始浮现,画外音:“年轻的时候,我做过许多无聊的事,也见过许多过后就忘记的面孔。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一个全景后,镜头摇着进入了小饭馆,一个特写镜头凸现出曼桢,反映出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关注和重视,回答了先前的疑问,也解决了预设的悬念。电影从这两个视角叙述着男女对方的故事,同时向观众表露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两个视角交叉进行,相当于一个全知全能视角。又如,影片进行到十多分钟的时候,导演在俩人感情进展中加入的第二次旁白——世钧:“我发现当你没想过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爱上了她……我想要去看她,却一直找不着借口。”曼桢的旁白是:“我一直担心叔惠会来我家拿钥匙,我想每一个人总会有些事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世钧已然爱上曼桢,而曼桢则开始担心自己不堪提及的家庭是否会影响到这段感情。同样是两个视角交叉进行,帮助观众理解人物的内心,这是一种更贴切原小说的手法——让人物直接用非对话话语来表达内心。张爱玲小说的况味,除却影像,有些是只能还原为文字的。电影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方式,通过剧中人的“眼睛”将他们的心理活动一一交代出来,使接受者处于剧中人物的位置,这就造成了接受者心理自居作用和想象性认同,引领着他们的观看情绪。电影充分把握住了两个主角的心理,使故事具有一种饱满的可信性。影片贴切地进入主人公隐秘的心灵深处,真实地感受他们的思想。
在小说中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回味过去的一段故事,客观叙述和人物主观感受交融。而电影则打破原著的叙事顺序,总体上以曼桢和世钧相识、相爱、分离、重逢为序,时间上先后承继,这样更符合电影艺术的叙事方式和观众的心理习惯。但是许鞍华在故事整体框架内部运用的是倒叙的手法,如影片开始不久用旁白这种能给人一种恍如隔世之感的方式,插入了世钧在电车上对曼桢的回忆;用闪回通过曼桢的母亲、奶奶的对话,交代曼璐与豫瑾的故事,这也为后面曼璐的心理刻画做下铺垫。这样的顺序与倒叙相交织的手法,使观众在体会俩人感情发展的同时又时不时被导演拉回现实中,对这段缘分保持有一种客观、冷静、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态度,能更深层次阐释出张爱玲原小说中苍凉的味道。
二、情节场景的选择
从叙事角度看,小说和电影都是讲述故事的艺术。何谓故事?故事是叙述出来的事件。李幼蒸指出:“人类生活由各类事件组成。事件,即有目的的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及其结果;无数事件在时间和空间内的组合即历史;对历史的部分或全体的描述即历史记叙。记叙的对象可以是真实事件,但也可以是想象事件,后者即为通常所说的‘故事’。”[6]而故事是由情节讲述出来的。但是电影一两个小时的长度决定了电影改编必须对小说的故事情节精挑细选,这即如菲尔德所提示的:“要精心地挑选那些事件,从而使它们能通过最好的视觉能力与戏剧性成分来描绘你的故事,使它们趣味盎然。……原始素材毕竟只是原始素材。它只是个起点,而不是终点。”[7]一般来说长、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尤其是改编长篇小说时,必须对书中的事件及人物关系恰当地进行选择取舍,以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矛盾,从而实现叙事目的,揭示叙事意义。这就需要改编者对小说进行彻底的重组,确定主线。是否需要添加一到两条副线,这要因人物、情节而定。
小说《半生缘》为电影《半生缘》的拍摄提供了丰富而有深度的文化资源及广阔开掘的空间。许鞍华对小说中的事件、人物、叙事顺序进行了精心取舍,挑选出最重要、最吸引人、最具表现力的场景、事件和人物,连缀成完整的故事,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其中也不乏原著的苍凉和细腻,也是导演的个性体验和对生活的领悟。整个影片以曼桢和世钧的爱情、经历为主线,曼璐与豫瑾、叔惠与翠芝的感情纠葛为副线,由一个个细腻的场景、镜头和画面连缀起来,舍弃枝蔓情节。使叙事更具体、集中、紧凑,步步推进,一气呵成。
影片用很长的画面仔细地叙述了世钧、叔惠、曼桢到郊外拍照,曼桢丢失红手套,世钧趁夜深人静时独自到郊外,借手电筒微弱昏黄的光亮,为曼桢找回手套的情节。其实在这要表现的是,世钧在一片漆黑中寻找的岂止是曼桢的红手套,还有他期待已久的爱情和幸福。送还红手套,不仅成为世钧向曼桢表白心迹的契机,也为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郊外灰黄的色调,轮到世钧、曼桢照相时却没了胶片,突然下起的小雪,似乎都暗示某种凄冷、遗憾的结局。世钧、叔惠、曼桢第一次在小饭店用餐,曼桢帮二人洗筷子,世钧因过度紧张,无意间把刚洗净的筷子顺手放在肮脏的桌上,并误饮了涮杯子的茶水,一个活脱脱的腼腆内向、手足无措的沈世钧跃然而出;祝鸿才指着曼璐的相片问:“这是你妹妹什么时候照的”,曼璐一边痛心地说“我真的老得那么厉害吗”,一边冲到穿衣镜前,捧着自己浓妆艳抹的脸庞仔细端详的一幕,把一个容颜即逝、希望和信念随时光的流逝渐渐远去的风尘女子的形象,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世钧和叔惠回南京的前一晚,曼桢来到许家,带来一盒点心并帮世钧收拾行装,两人贴近地细语,有几分柔情,也有几分羞涩,曼桢一声“你忘了把热水瓶盖上了”,有意打破这个局面,贴切地展现他们不温不火、含蓄内敛的感情……影片通过环境、语言、动作、背景、造型,展示这些耐人寻味的情景,细腻刻画出人物性格,完整地交代了情节线索,在琐屑和细微中透射出苍凉感。
电影改编是将一种艺术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艺术创造。它既要忠实原著,又要有导演今天对艺术形象的再认识。那么在电影改编中要善于把握好艺术分寸,处理好对原作的删与增。但不管怎样的增减,都要符合原著的精神。
先说“删”。尽管在改编时删除原作的某些内容,必然会损害原著,但这种删减还是十分必要的。从篇幅上说,一部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影片容量刚好,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一部影片,就势必要删减原作中的一些人物、情节和线索。
许鞍华为使故事情节线索简洁明晰,在电影《半生缘》中略去小说中许多次要情节和事件,简化了很多人物形象。比如本来就暧昧不明的许石恋,电影里只有三场戏:划船、爬山、婚礼,简单地交代清楚,含蓄又精到。小说中,世钧与叔惠回南京探望,沈母、世钧嫂嫂及其他亲戚竭力撮合他与翠芝的婚事。第二天,世钧、叔惠、翠芝同去一鹏家赴约,被支去看电影。翠芝不慎折断鞋跟,无奈中,世钧回石家帮她拿鞋,回来时电影已近终场,他负气扔下许、石二人,独自补看错过的半场电影。许、石单独去玄武湖游玩,由此滋生一段隐隐约约的恋情。而电影将其简化为三人同游玄武湖时,翠芝折断鞋跟,于是世钧回去帮她拿鞋,叔惠和翠芝单独泛舟玄武湖,二人后来通信一事也被省略。有些时候电影为了情节的紧凑,一些次要人物乃至重要人物也要删剪掉。一部电影中的人物不能太多,主要人物一般是二至三个,而小说中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很多个主要人物,并表现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沈父、沈母与沈家姨太太的纠葛,祝鸿才与曼桢结婚后再发国难财,继续花天酒地等情节,电影均淡化处理。许先生、许太太、世钧嫂嫂、阿宝等小说中着墨不多者在电影中都是“蜻蜓点水”,只是作为某种符号存在。而石太太、沈家姨太太、金芳等次要人物,则根本没有出场。
电影中对于曼桢受辱那场戏,拍到她半夜惊醒就戛然而止,与小说里“有人在这房间里”的恐怖气氛相得益彰。许多枝节也大胆地删去了,比如世钧父亲的病,曼桢逃出医院的详细过程,张豫瑾在上海生活的那部分,等等。电影的结局是:世钧与曼桢重逢,百感交集但又无可奈何。镜头一转,又是多年前那个初春的黄昏,世钧打着手电找到了曼桢的红手套,拣起来,轻轻地笑。那样一张年轻的脸,那样一颗年轻的心,世界在他面前还很美好。
再说“增”。将一部时间跨度达十多年的长篇小说搬上银幕,需要取舍的素材太多了,稍有差池,就可能伤筋动骨,破坏整体结构。在这里,编导下了一番苦功,除了删除一些情节事件人物之外,基本保留了原著小说的故事脉络,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如:张豫瑾为了顾曼璐悔婚去做舞女而跟人斗殴;顾曼桢为沈世钧买手套。前一段出现在顾曼璐的回忆中,表明她是为了家庭迫不得已才沦落风尘,在她的内心一直为自己的牺牲而耿耿于怀,为后面对妹妹的报复提供合理的心理基础。后一段则是顾曼桢的投桃报李,沈世钧曾为她深夜去荒郊野外去找寻丢失的手套,由此,两人开始漫长的十八年爱情长跑。此后,这双始终未能送出的手套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见证了两人感情的起起落落。此外,还有细小情节上的增加,比如沈世钧初见顾曼桢显得手足无措,慌乱中端起曼桢洗过筷子的茶杯喝了一口,叔惠笑着指出后,他连说没事,曼桢调皮地说,那你再喝一口。憨直的他居然真的又喝了一口。
除了对原著小说的故事情节做出合理的增减之外,影片还对其中的对话与细节做了修改,以适应电影艺术特有的视听要求。比如在小说中是在出发前,顾曼桢就发现了沈世钧脸上的污点,而在影片中是在拍照时她才看见,特地跑到他的身边替他擦去。电影首先是视觉的艺术,影片正是要顾曼桢通过她显而易见的肢体语言形象地表现出她对世钧的关心。再比如顾曼璐骗他曼桢已结婚,并退还他俩的订婚戒指。在小说中他出门不久就扔到路边的荒草丛中,而影片却是在他走水路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南京途中扔入水中,使得他扔戒指的行为更具有象征意义。
三、环境、人物心理的刻画
电影中细致地刻画人物一般比较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二是环境描写的衬托。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改编者遇到的更大的难题,它既不能晦涩难懂,也不能直白无物,心理活动的展现更多的是要和观众产生内心的共鸣,这就需要用电影镜头语言来解决。在小说中是较容易也倾向于揭示人内心深处的秘密的,电影则不然。对此,悉德•菲尔德说得较为中肯:“一部小说通常涉及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在戏剧性动作的思想景象中发生的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和回忆。在小说中,你可以用一句话、一个段落、一页稿纸、或一个章节,来描写人的内心对白、思想、感情和印象等等。小说时常发生在人物的脑海内”;电影“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体的细节……是一个用画面来讲述的故事,它发生在戏剧结构的来龙去脉之中”[8]。但是电影在它的探索道路上,运用声音等电影语言实现了很好的转化,也摸索出了一些可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途径。如画外音中的内心独白、旁白,再如明暗冷暖色彩的渲染等等。
影片充分运用了电影的各种表现手法来发展故事情节,展现人物心理活动。比如影片开始时先用曼桢的画外音引出世钧:“他来城里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一共见过他四次,每一次他都像看不见我,可能是他太专心做事吧,根本就没留意旁边的事情。”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曼桢内心的不确定。又如沈世钧要回南京,顾曼桢来替他收拾行李,两人对话到一半,突然插入他坐在北上的火车上微笑沉思的画面,然后又回到他俩的谈话,最后再接到他在南京坐人力车上回家的画面。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组织镜头也没有错,但时空打乱以后,临别这一段就变成甜蜜的回忆,这时两人关系尚未明确,她能不避嫌跑到叔惠家来替他收拾行李,足以表明她的态度。再比如沈世钧第一次来顾曼桢家吃饭,饭后送她去补习,他第一次牵着她的手,向她表示爱意,来到补习家门口,他舍不得放手,又拉着她往回走。最后时间到了,无奈两人只得松手,他眼看她走进门去,一个人慢慢地走到路口,远处传来欢乐的音乐,路灯投下红彤彤的光芒。他坐上电车,从那家门口经过,只见里面透出一片奇异的红光。影片在这里运用特殊的声、光、影处理手法将沈世钧初尝爱情滋味、喜不自禁的心理直观地表现了出来。昏黄的灯光,温暖的调子,夜市有点喧闹的人声,加上小提琴优美舒缓的伴奏,俩人之间那种柔情蜜意被细致地表现出来。等到曼桢走进门去,世钧循着一下子凸显出的热闹音乐声来到一片亮处,小提琴的舒缓变成了欢快的节奏,灯光也变作喜悦的红色,镜头拉近,笑容在世钧脸上散开。他内心在激情兴奋与美好的期望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又不失含蓄。这一点是文字无法达到的效果。此外,曼璐与豫瑾重逢,欲与他再叙旧情,她蹲下身去替他捡钱,张却一再申明,想起过去真是幼稚。她不禁愣在那里,两人前后景一蹲一站,在一个镜头中便交代了两人过去的恩怨情仇以及当下各自的复杂心态。还有顾曼桢被姐姐囚禁后,整理家里送来的衣物,翻到她买给世钧的手套,这时一个上升的镜头将她背后窗外正往外走的世钧的背景纳入画面。
电影《半生缘》,作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改编经典原创小说、具有创新意识的电影,无论它是否具有经典性,都已变成具有当代阅读意义的对照性研究文本。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改编过程中,许鞍华导演并未只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拘泥于小说,从叙事顺序的改变到情节的选择调整等等,都是以适合电影的声画表现及观众的接受为目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改动确实损伤了小说的丰富、多义与厚重,存在一些不足,但有很多地方还是优秀的。但我们对改编影片的评价,不能只以是否忠实于原著为标准,而应从电影的角度、从声画语言的影像化表现上,用与普通影片同样的眼光来衡量得失。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修定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2]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3]毛克强, 袁平. 当代小说叙述新探[J ].当代文坛,1997(5),12页 .
[4]张爱玲.半生缘.选自陈子善主编《张爱玲文集》. 第一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页。
[5]章渡. 反高潮――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4)
[6]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51-152页
[7]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44页,第154页
[8]同上,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