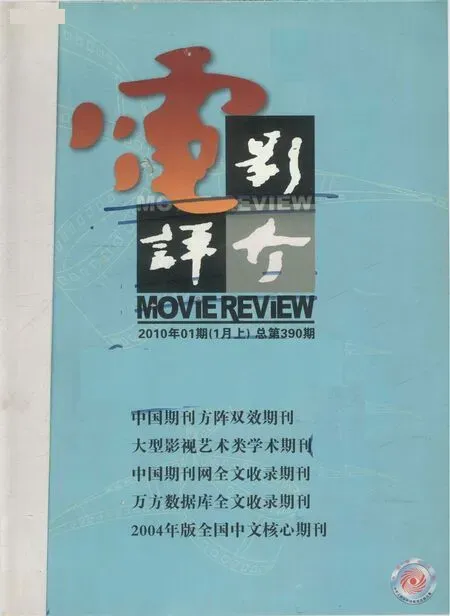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暖》 的影像修辞手段
2010-11-16张文浩
电影导演霍建起从自修美术到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设计,都和美术有关。也许是缘于这份醇深的专业浸染,他后来导演的影片都很重视影像的修辞效果,比如《赢家》、《那山,那人,那狗》、《蓝色爱情》、《九九艳阳天》、《生活秀》等电影作品,观众对片子里的影像设计意图和效果想必是不会忽略的。根据莫言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由李佳、郭小冬和香川照之主演的电影《暖》更是充分显示了影像画面的修辞功能,它极力牵引观众进入视听背景之后的人物及故事体验中。
电影开片的抒情式风景镜像暗示了整部影片的叙事结构,即以“我”的行踪和思绪为线索,划定了一个“回乡——在乡——离乡”的结构框架。这个框架其实很普通,只要在前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明察导演的这一意图。那或明或暗的大树先以远镜头形式出现,慢慢推近;再以移镜头形式向左淡出银幕,继之而来的是连绵峰峦,自上而下盘旋逦迤的山路;淡入一个青年人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茫茫青山与芦苇丛,瞬即视线随着自行车的运动来到了山里面的一个村落,出现无边的金黄稻浪和秋波翻现的乡间小路。在这系列充满动感的构图中,配以第一人称的旁白,从而透露影片的结构倾向:村里十年前的大学生,如今回乡替当年的曹老师谋事并作短暂的居延,必然在影片结尾处也即事情办完之后以再度辞乡而终。可以设想,只要对鲁迅的小说《故乡》稍有一些印象,我们就不难发觉,两者的结构完全相同,只不过文本表现的具体媒介不同罢了。如果把《故乡》的开篇文字置换成电影镜头的话,估计与《暖》类似,只须将群山换你河流、自行车换作乌蓬船而已。也许霍建起是有意采用“回乡——在乡——离乡”的叙事结构,借以唤起观众的参与热情,并将观众导入其特设的召唤结构而最终在影片含蕴方面打破观众的心理期待视野。总之,他的首尾圆融呼应的结构意图,完全可以在开片之初猜测出来。这是一种显山露水的修辞手段。
其次,影像修辞手段着力体现在其替补语言表达的效能上。影片中,戏班里的武生自始至终鲜有台词,他大都以脸谱形式和一些肢体动作出现,成为符号化表征,即成为女主人公暖的生活企求。可以说,他表演技艺时的画面,正是呈现在暖面前的生活幻影,在暖心里激起爱的涟漪和憧憬;然而,这种美丽情愫是建立在脸谱化和戏剧化的非现实基础上,注定要以绝望和创伤告终。武生出现的画面往往采用慢镜头或特写镜头,如武生帮暖化妆的影像部份,基调舒缓,如歌如诉,虽没有片言只语,却足以表现暖内心的细水微澜。而她的陶醉感,恰恰反映出城市文明对于闭塞农村少女的巨大诱惑力。同时,希望越强烈,失望的痛感就越剧烈。影像的无声效果也由此产生。这种修辞效果无声胜有声,较好地替补了语言台词不能达意的缺陷,而激起观众情不自禁的惜惋默叹。当然,这一修辞手段体现在很多方面。又如秋千架骤然断裂之后长时间的特慢镜头,以及村人匆忙抢救暖的摇晃镜头,非常沉郁而简省地交待了人物命运转折的关捩点和前因后果,也非常有冲击力地唤起观众由衷的感喟及思索。再如,林井和,也就是“我”去探访暖的家时,暖在楼上梳妆台前对镜顾盼,反复地为悦己者容,而楼下则是其哑巴丈夫与旧情人“我”的长久对峙,无言的尴尬、疑惧、拒斥等内心活动都相当明晰地经由人物的神情纤毫毕现。这些情景画面,皆无需人物台词从中辅助表义,观众亦全然可以心领神会其中的人物关系及意旨。
如上所举,影片中的秋千架旨关大节,其中的多次特写乃影像修辞的反复凸现手段。一个乡村的普通秋千架成为叙事的关结物,许多悲欢离合的情绪都能在其中摇荡出来,显现在观众眉睫之前。它出现的频率很多,既可作为影片的文本之眼,又可推动故事发展,还可渲染命运氛围,解释人物与境遇关系,预示生活的幻想与失望,诺言与无奈,等等,可谓淋漓尽致。比如哑巴与林井和一块荡秋千的镜头,导演设计成井和站在秋千架上,俯视哑巴;而哑巴则推动秋千,似乎暗含一种城市人对乡村人的居高临下的优势姿态;哑巴的憨憨笑声,又似乎在宽容或默认这种差异悬殊的事实。井和与暖也荡过几次秋千,最意味悠长之处有两个。其一是,井和即“我”特意取出母亲的红纱巾,盖在暖的头上,然后共荡秋千,晃来晃去,表白出小伙子美妙的恋爱心理。但好景不长,红纱巾在大幅度的摇荡中飘落下来,画面缓慢,悠长,轻柔,重叠,复现,渐次飘落于地上。这个荡秋千的情形,寓意自然存于其中,等待几代人和亲身体验式的解读。红纱巾从高高的秋千架上飘落,势必造成观众心理期待落空,原以为是一段美好爱情征兆,不料以后事与愿违。这就涉及第二个画面,即更为扣人心弦的“我”和暖共荡秋千的画面。两人相向站在秋千架上,暖头靠在“我”并不宽阔的肩膀上,使我充溢了幸福感。画面色调由明转暗,由温转凉,依据观看电影的一般经验,也许观众觉得镜头会转入次日早晨。其实不然,这既暗示自然时间的迁移,又折射人物命运的急转直下。那个秋千架依然晃动,来回不止,产生心理延宕的效果。而且,画面拍摄角度选择恰当,从底部向空中拍摄,使得观众心理不由自主正襟危坐,仿佛在担心什么似的。尤其是加上秋千架枯涩刺耳的嘎吱嘎吱的音响效果,这镜头在观众心理上的震摄力获得了张力。果真,该发生的最终发生了。接下来的是散架的秋千依然在无助而沉默地晃动,让观众自己去填补影片的留白。那个四分五裂的秋千,交待了暖瘸腿的原因,昭示了幸福感觉的瞬间烟灭。真是此憾绵绵无绝期,此憾却关秋千架。秋千架的断裂,表征着联系城市与农村的纽带的脆弱性,表征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纠葛与鸿沟,表征了罪孽与忏悔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此外,皮鞋、雨伞、芦苇、草垛等特殊影像都体现了“我”对乡村文明进行回瞥时产生的留恋与悔意及莫可名状的无奈感。这种依赖特写而反复凸现的修辞手段,使影片主旨的辐射收效甚佳。
另外,大量的闪回镜头,将现实与回忆融为一体,产生影像的互文修辞效果。故事的叙述却仍然极为流畅,没有丝毫滞涩感,做到了叙事顺序井井有条又穿插有度。如“我”回到家里埋头洗脸时,镜头闪回到少年时代与暖共荡秋千及一起读书返家的情形,很自然地将故事的原始发生时间引出,原初的恋情也顺延出来,可谓水到渠成。那双皮鞋先穿在小女孩的脚上,后来闪回到与皮鞋有关的故事,现实与过去相互交织,相互推进,相互发凡,展开影片的下一步叙事。完全可以说,这些闪回镜头构成了影片的半壁江山,是各种对立关系中一端。古朴体验与此在的遭遇发生碰撞,寄寓在闪回镜头与现实镜头的穿插印证关系中。从而,影像的这一互文修辞功能通过这些平衡相对的关系群浮现出来了。
很明显,各种影像修辞手段在电影里的运用并非尽善尽美。就拿结尾来说吧,显得太仓促突兀了。它仅仅停留在河边就定格了。依我之见,影片结尾最好与开头有所回应,也即补上“我”推着自行车孤独地走在山路上,而暖一家的背影渐渐淡出画面,以远镜头和拉镜头再度淡入描绘那棵大树、那些芦苇和那绵延的峰峦,最后淡出以至闭幕。惟有如此,首尾结构才能真正做到形式上圆合而意义上开放,像鲁迅的《故乡》样处理得从容有致,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