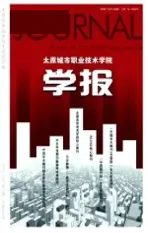荒诞里的重生
——简析《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2010-08-15赵盼盼
赵盼盼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荒诞里的重生
——简析《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赵盼盼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从荒诞幻觉给剧中人物带来的片刻的幸福,到它分崩离析后给剧中人物带来的幻觉破灭,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揭示了人们从荒诞幻觉里重新觉醒的过程。论文从对剧中一系列荒诞形象的分析,揭示了阿尔比对我们的启示,即在现实生活里,人们要敢于正视荒诞的存在,并且用行动远离荒诞,认真生活。
爱德华·阿尔比;《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荒诞;重生
1962年10月13日,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在纽约百老汇的首次演出在美国戏剧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该剧被普利策戏剧奖拒之门外,但是它还是先后获得了“纽约剧评界奖”和1962-1963年度戏剧的“托尼奖”。虽然在此之前,他先后创作过《动物园的故事》、《贝西史密斯之死》以及《美国梦》等一系列作品,但是美国剧评界认为他只是一个“有潜力却未经考验的作家”,直到《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出现,才“改变了这样的怀疑”。正如麦卡锡所说,此剧“一夜间使阿尔比从一个外百老汇的实验剧作家变成了一个美国经典作家”。
阿尔比在Mel Gussow为他写的传记中,曾经透漏他的作品深受“契科夫、皮蓝德娄、贝克特的影响”。诚然,契科夫剧中人物行动的懒散特点、皮蓝德娄处理现实和虚幻的手法以及贝克特的语言风格和幽默特色都对阿尔比的喜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1961年,Esslin在他的《荒诞派戏剧》中把阿尔比的早期作品归入荒诞流派,并指出其作品“抨击了美国的乐观主义根基”,而Way更进一步指出阿尔比正是使用了荒诞派的写作技巧来抨击“美国人生活方式”中存在的病态。
在此基础上,论文从《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剧本本身出发,通过对剧中的一系列虚幻形象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此剧的荒诞主题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并认为阿尔比在处理这一荒诞主题时,更强调的是一种对荒诞存在的承认。即徘徊在虚幻和现实中的人们应该明确地区分两者,用行动来远离虚幻,在现实世界中达到精神世界的顿悟。
在讨论文中出现的荒诞形象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关于荒诞这个词的理解。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中有一段关于荒诞的论述,他指出,由于人们被“剥夺了对失去家乡的记忆”,并且“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使得他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浪者”。这种“人与他的生活的分离”就是所谓的“荒谬感”。同样,Esslin在他的《荒诞派戏剧》一书结尾处指出,荒诞派戏剧并不是表现绝望,它反映的是现代人类对其所生存世界的一种“积极的妥协与让步”。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更为简洁地给出了荒诞的定义,他强调荒诞是“失去目标”。即当人们的宗教信仰等理念被“割断”的时候,他会变得“迷失”,他所有的行动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诞”。阿尔比也曾试着给荒诞派戏剧下了个定义,他指出,荒诞派戏剧是在吸收了一些存在主义和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描写了人们努力使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毫无意义”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的这一过程的徒劳。
基于上述一些对荒诞派戏剧或是荒诞一词本身含义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由于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社会等的发展变化,人们对自己原本的价值观发生了质疑,从而也就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疑惑,当他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引起这些疑惑产生的原因时,只有退回到自己编织的虚幻世界里,荒诞就由此产生。《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中的两对夫妇也毫不例外。
《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讲述的是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一个学院起居室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凌晨两点钟,涉及了一对年长夫妇乔治和玛莎以及一对年轻夫妇尼克和哈妮。围绕着他们看似甜蜜的婚姻生活,阿尔比深入地揭示了他们婚姻生活的荒诞与脆弱,并塑造了乔治这一顿悟者的形象,他引导着玛莎最终抛弃虚幻编织的过去,面对现实。写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此剧是对当时美国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美苏冷战、朝鲜战争以及核武器的研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身存在的安全开始担忧。无论是出现在50年代末“垮掉的一代”还是60年代的“嬉皮士”都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挑战。面对现实,人们开始觉得无所适从,甚至逃避。于是他们选择用“虚假的价值观”代替“真实的价值观”,错误的幻觉随之产生。这种幻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荒诞性这一特点。因为荒诞正是产生于“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阿尔比认为这种荒诞本身具有“破坏力”,所以他想通过逼问人们“谁害怕没有幻想的现实”来终结这种荒诞。在他眼中,只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人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敢于直视自己的内心。同样,文中也有多个具有荒诞性的意象,但作者想要揭示的是荒诞背后人们的内心的成长。
首先,文章的标题就暗示了荒诞幻觉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威胁。在阿尔比的传记中,Gul Gussow曾记载到,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阿尔比在格林尼治村的一个酒吧后面的一面大镜子上看到用肥皂水胡乱地涂写的几个大字:“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这几个字便是他标题的来源。谈到标题的含义,阿尔比在他的一次采访中解释到,它可以理解为:“谁害怕没有虚幻的生活?”所以,标题本身就是对虚幻生活的质疑。在剧中,标题以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形式的反复出现贯穿了全文。第一幕刚开始时,玛莎哼唱了这句歌词,她纯粹是因为觉得“有趣”,而并没有对歌词本身进行思考。而当乔治在第一幕快要结束时再哼唱起这首歌时,他表面上是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掩盖过”玛莎的,但实际上是把它当作挡箭牌。因为玛莎一直在细数着乔治的失败,所以乔治是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自己过去的失败。但是,在剧本快要结束的时候,当乔治已从对现实的荒诞逃避中解脱出来时,他“轻轻地”为玛莎哼唱这首歌时,目的是想把玛莎从虚幻中唤醒。终于玛莎承认说“我害怕”时,乔治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这对夫妇认识到各自对现实的逃避,玛莎和乔治最终挽回了婚姻。阿尔比通过乔治和玛莎各自对婚姻的重新评价,所努力树立的是一种西西弗般的生活理念,即虽然面对荒谬,却要“努力永不停息”。正如加缪所说,“幸福和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所以人们只有和乔治一样,敢于面对现实生活中荒谬的痛苦,才能明白幸福的真谛。
除了标题之外,乔治和玛莎编造出来的“儿子”这一形象可谓是剧中虚幻意象的最好象征。虽然在剧中乔治夫妇和尼克夫妇代表了不同的婚姻观。前者代表的是“传统的”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情观,而后者则代表的是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观。但是,这两对夫妇的共同点之一却是都没有孩子。孩子这个话题是玛莎先提来的,她告诉哈妮她有一个快满二十一岁的儿子。尼克从一开始就告诉乔治他们没有孩子,而后者却精心在编造了一个有关孩子的童话。在知道真相之前,尼克夫妇一直以为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因为玛莎提起了他们的儿子有着“泰迪熊衣服”和“来自澳大利亚的古式摇篮”的幼年,“喉哮病”和“动物饼干”等曾出现在他的童年里,以及后来孩子的不小心摔倒以及孩子学会走路,再到后来孩子的长大和与家里的争吵与“离家出走”。所有这些细节的描写无一不说明了虚构孩子的真实性。所以孩子这一形象在文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孩子在这两个家庭中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他们对未来的迷茫。所以孩子的存在与被判死刑,象征着乔治夫妇摆脱荒诞的过程。乔治一直把孩子当成是他和玛莎对现实恐惧的替代品。当玛莎向外人透露他们的孩子时,无疑是把他们对现实的恐惧向现实社会呈现。所以乔治开始对他“虚构的私人生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困惑。正如他所说的,“真实和虚幻,谁能区分的清楚呢?”,他开始思索虚幻本身存在的意义,后来他亲手杀死了“虚幻里的儿子”,象征着他“回到了现实。”从孩子这一形象的出场到他的消失,正象征了乔治精神世界的恢复健康的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他也引导了玛莎抛弃虚幻。而哈妮在“虚构的孩子”的影响下,竟也有了想有个孩子的愿望,说明尼克夫妇也重拾了对未来的信心。所以,通过孩子这一荒诞的意象,剧中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精神世界的成长。
和“虚构的孩子”相互渗透贯穿全文的便是出现在文中的四个游戏,即“羞辱主人”、“羞辱客人”、“和女主人有染”、“揭开商标”。而这四个游戏本身也充满了荒诞性。在酒精的作用下,这些游戏充满了“暴力和谩骂。”但是通过这一系列看似荒诞的游戏,剧中人物的“不足”被一一暴露。
第一个游戏是“羞辱主人。”在这个游戏里,玛莎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了乔治的历史。在少年时期,他因为失误杀死了自己的父母。结婚后玛莎发现他是一个怯懦的人。玛莎父亲原本打算在他退休之后把学校交给他管理,可是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乔治并没有那方面的才能。这一切充分说明乔治的过去是失败的。但是面对失败,乔治却是一个具有“妥协”性格的人,虽然是历史老师,他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是“否定”而不是“面对”。直到玛莎在游戏里残忍地揭开了他的伤疤,乔治才不得不对他的过去进行思索,而这种思索刚开始也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幻想与再加工,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单纯回忆。也就是说,乔治所逃避到的历史世界也是被虚幻了的。在他的历史世界里存在着他们虚构的孩子,有代替他而存在的造成父母死亡的朋友,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因此也具有荒诞性的特点。乔治一直活在这个荒诞世界里,直到游戏结束,他才挣扎出来,并且充当了“医生”的角色,重新恢复了玛莎的“精神健康”。
而第二个游戏“羞辱客人”反映的则是尼克的性格特点。尼克在剧中是位教生物的大学老师,他年轻、潇洒。在乔治的眼中,他是“未来一代”的象征,并且对乔治代表的较老的一代人有着“直接的威胁”。这正是因为尼克代表的是注重实际、为满足自身利益不折手段的年轻的一代。他出于金钱和哈妮结婚,所以他们的婚姻里并没有幸福。当他和乔治谈起他的事业规划时,他提到了三点策略。其中有一点便是在对自己有用处的人的妻子身上做文章。由此可见,尼克代表的正是传统价值观缺失的一代,虚假的价值观的横行便导致了人们残酷无情的病态思想的产生,而此正是加缪眼中“荒诞性”的所在。
第三个游戏“和女主人有染”是这四个游戏中最荒诞的一个。玛莎把“性”当作是报复乔治的工具,而乔治却用“凌晨四点看书“来表现对玛莎的冷漠。正因为他对玛莎和尼克调情的漠视而激怒了玛莎。玛莎威胁他说她要让乔治“后悔和他结婚”,可是对玛莎肢体和语言上的威胁,乔治却依然无动于衷。一直以来,玛莎都在婚姻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乔治对待她的冷漠的态度正是对她权威性的挑战,这也是乔治勇于面对现实的表现之一。
而第四个游戏“揭开商标”可以看做是这四个游戏的点睛之笔。“商标”在文中象征的正是剧中人物一系列荒诞的幻觉。乔治以人类自身为例,把“揭开商标”这一过程比作从人的“皮肤”深入到“骨髓”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商标被揭掉之后,剧中的人物不得不面对各自的现实。所以乔治才有可能亲手杀死他和玛莎虚构的孩子,并帮助玛莎走出虚幻,而哈妮才会有想要孩子的想法。尽管本文的结尾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剧中的人物远离“虚幻”,“认真生活”,就能幸福。
所以,荒诞的虚幻是人们在面对现实时很容易产生的现象。而剧中的四个游戏恰恰循序渐进地展现了人们对荒诞这一现象本身的探索。从剧中人物沉醉在荒诞带来的片刻的幸福到荒诞幻觉的分崩离析后给剧中人物带来的重生,这个发生在凌晨两点的校园里的故事同样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所要表达的一样,面对困境,人应该享受和它“斗争”的过程。同样,人们在面对当今的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时,也应该如此。
I106
A
1673-0046(2010)7-01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