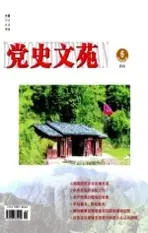简评胡玉堂的爱国情怀和历史地位
2010-08-15艾兵有潘亿生
艾兵有 潘亿生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临沧 677000;云南大学 云南昆明 650091)
在阿佤山有一位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胡玉堂,他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加艳丽”。因而,我们今天传承胡玉堂的爱国精神是对他最好的缅怀。
一、“司岗里”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水有源,树有根”“司岗里来,葫芦里生”的思想强烈地表征着同宗同源的民族情结。佤族《司岗里》史诗的母体说表达了“木依吉神”是人类万能的女始祖,是各族人民的母亲。人类从“司岗”出来时,汉族、拉祜族等都跟着佤族出来,各民族都懂得大家是从一个母体里孕育出来的同根同母的弟兄姐妹。佤族《七兄弟》的民间故事中也诠释了汉族、白族、彝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是同根同源的弟兄姐妹。诚如《民族大团结》歌词中所唱:“不分汉族和傣族,不分拉祜和阿佤;村村寨寨是亲戚,男男女女是兄弟姐妹。”[1]在佤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人与同时被造就的万物在生命的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万物都有灵魂,不管是谁,无论大小、强弱,都一样平等。平等共生一直是佤族人民的生活处事态度,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愿望。
佤族与其他各民族同根同源的思想历经沧桑,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人民的心底,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在抵抗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统一、维护边境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佤族自比作抱团的蜜蜂,尽管外面会烧死烧焦,他们依然紧紧地抱在一起,尽可能让里面的同伴活下来。佤族老人说:“亲兄弟围成圈,就是‘司岗里’;亲兄弟抱成团,就是‘司岗里’;亲兄弟有力量,就是‘司岗里’;亲兄弟得胜利,就是‘司岗里’。 ”[2]在1934年“班洪抗英事件”中,班洪佤族部落王联合17个部落举行盛大而庄重的“镖牛盟誓”,表示联合抗英到底。“要到滚弄江洗到(萨尔温江)”,多么豪迈的爱国誓言啊!正是这种爱国热情,对捍卫祖国的安全和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胡玉堂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并为捍卫祖国的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抵抗侵略,捍卫疆土的佤山雄鹰
1.创建班老佤族守边自卫队。
英国占领缅甸后,侵略的矛头直指云南,以便“为中国西南无限的市场打开一个门”[3],阿佤山首当其冲。敌人对“葫芦王地”银矿垂涎三尺,制造了中缅“南端未定边界”,妄图实现云南边地的合法化。1932年,胡玉堂到缅甸木邦等地探亲访友,沿途亲眼目睹了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心中激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回到家后,他把在缅甸的所见所闻告诉父亲和寨人,建议父亲组织武装以防患英军入侵。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他们创建了一支约30人的民众自卫武装,指挥官就是胡玉堂。
2.顾民族大义的铮铮铁骨英雄。
1930年后,英国为了达到目的采用以武力恐吓和物资收买等手段,买通了班弄上层马美廷、户板头人宋钟福和永邦德校麻哈。这三人伙同与英国总工程师波朗签订“开办炉房银矿办法”。从1931年到1934年“班洪事件”爆发前后,英方多次派洋人到班老、班洪以交友送礼物手段试图收买班洪王、班老王,被严词拒绝后,又去收买胡玉堂,表示愿以2万银元给部落头人,叫胡玉堂把班老归属英国。胡玉堂严词回绝说:“我们是中国人,不受英国人管,只受中国管。”1934年春,英方再次托人给胡玉堂“送礼”,并说:“只要给英国人开矿,愿给3驮金子、3驮银子”。胡玉堂说:“金子、银子再多也不!即使你们把红毛树变成大清树,也无法把班老变成英国人的领地,不能把中国人变成英国人。”[4]在旁的英方武官放话威胁说:“你们的中国政府都怕我们英国的枪,你们班老就不怕?!”胡玉堂轻蔑地说:“你们要打就打!即使男人死完了,我们妇女也能上战场!”不久,英国官兵以荷枪实弹相威胁,他们拍着炮筒说:“我们的大炮可以把臼窝粗的大树打断,把大石头打烂,如果你们不归英国管,我们就打你们。”唇枪舌剑的胡玉堂回答说:“大树可以打断,巨石可以打烂,我们是中国人永远不变!你们要打,我们不怕,局势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中国的土地!”[5]在抗英斗争中,胡玉堂至始至终都参与了。他参加了班老、班洪举行的盛大“剽牛盟誓”和“南依河之战”“龙头山之战”“南滚河之战”,以及配合“义勇军”收复班老之战。1934年3月,胡玉堂被推选为葫芦王地十七王请愿团副代表,到昆明晋谒龙云,报告“班洪事件”情况,请求发兵援助。1934年2月,英国侵略军两千余人向班老、班洪等地进犯。胡玉堂拿出自家深埋多年的银元到孟定、耿马购买枪支弹药,配合班老部落昆刚、保卫国等组织群众在南依河一带抗击英军。南依河抗英失败,班老寨被烧后,胡玉堂掩护老人和妇女被迫转入南滚河丛林中继续坚持抗英。他与民众虽备受疾病和饥饿困扰之苦,依然参与指挥“火烧龙头山”战役,重创英军。后配合“西南义勇军”和各地各族人民打击英军。
3.大义凛然赴“鸿门宴”,去留肝胆两昆仑。
1935年7月,中英第二次会勘边界时,胡玉堂参加中英会勘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会议上,他慷慨陈词,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并展现古印、朝服及祖先与吴尚贤开矿的盟约信物木刻,古印、赐封凭证,证明滚弄江以北属中国领土,力争回归中国。然因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致使滚弄江以北大片领土未能划归中国,激起葫芦王地人民的无比愤慨。1936年2月,胡玉堂率班老部落头人10余人到公明山参加17部落头目剽牛盟誓,联合起草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佧佤十七王敬告全国同胞书》,再次陈述阿佤山隶属中国领土,表达拳拳爱国之心,“宁可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驽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6]“佧佤山地与祖国为一体,不能分割。”[7]诚如《司岗里》所说:“汉族说我不丢开同伴,我要跟随阿佤……”阿佤山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共同维护着祖国的安全。
三、矢志不渝“回归路”,赤胆忠心爱国情
1948年胡玉禄病故,胡玉堂继承班老部落王位,承先辈之志继续反英,拒绝英缅封官的邀请,反对英缅人员入境登记户口。1955年,在中缅两国勘界谈判前,胡玉堂拿出明、清朝廷赐给先祖的朝服、官印、祖传“木刻”等宝物,以铁的事实证明班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把这些宝物送到昆明,要求回归祖国版图。同时,胡玉堂发起与班洪“代王”及各寨头人联合在班老举行盛大的“剽牛盟誓大会”,同饮“咒水”,对天地和祖宗发誓:“上天一起上,下水一起下,见火一起见,死也死在一起!”同饮“咒水”,踏着沉重的脚步,唱着无欢笑的歌声,表示要与中国同一块天地,誓死也要做中国人,承担起对维护国家疆土完整的责任。1955年国庆观礼期间,当周恩来总理关切地询问胡玉堂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向中央表达出“回国”要做“中国人”的强烈愿望。为了友好地解决中缅边界问题,1956年12月,胡玉堂不顾境内外李弥集团的威胁和迫害,果断前往芒市参加中缅联欢。在芒市胡玉堂又一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再次向周总理表达了班老部落回归祖国的愿望和决心。以后,胡玉堂继续为班老的回归积极努力。1960年10月1日,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既考虑到历史上传统的习惯线,也考虑到片马、班老、班洪地区曾掀起过反英入侵的民族情感的精神,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规定:“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南蜿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考虑到缅甸方面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统一把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的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本条约第一条所规定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鼓浪、岗房地区和第二条所规定应该划归中国的班洪、班老辖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由缅甸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8]至此,矢志不渝“回归路”的愿望终于实现。1960年中缅双方签订《中缅边界条约》后,缅甸官员由衷地对前来参加签字的胡玉堂说:“这次算你是中国人! ”[9]
四、历史的结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胡玉堂1955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他。在接见过程中,周总理深情地说:“你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祖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期间,周总理和胡玉堂等佤族头人合影留念。邓小平和乌兰夫副总理还为胡玉堂一行举行了特别宴会。邓小平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周总理回赠了衣服、布匹等礼物。1961年,周恩来总理来到昆明,再次接见了参加中缅勘界的全体同志,并又一次肯定了胡玉堂等佤族上层人士的爱国行为,高度赞扬他的顾全大局,并将自己使用的一只“英雄”铱金笔送给胡玉堂。1967年2月,一生致力于爱国守边的胡玉堂因病去世。
在“班洪抗英事件”50周年时,当年曾声援过佤族抗英斗争的著名爱国人士张凤岐教授和其他一些爱国人士都说:“班洪、班老佤族人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这就是人民和历史再次对胡玉堂这位佤山英雄的高度颂扬。○
[1][2]那金华主编:《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259页。
[3][英]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125页。
[4][5][9]段世琳:《佤族历史文化探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39、361、361 页。
[6]《告祖国同胞书》,见《班洪抗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7月第17页。
[7]《佧佤山部落首领致中英勘滇缅南端边界务委员会主席书》,转见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8]《临沧地区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4 年版第 522、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