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富有,越弱势?
2010-05-30张静
张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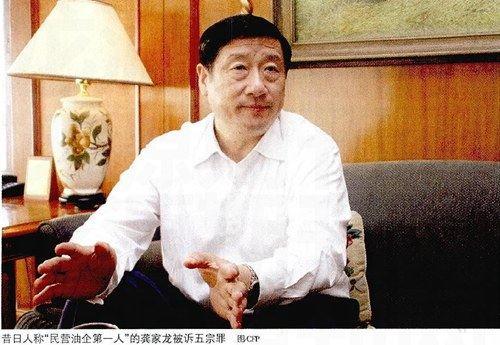
“在他被抓以后国美并没有马上垮掉,说明他们公司相对比较规范,而且黄光裕过去做了准备。”也许在他投靠利益集团、频繁游走于权钱交易边缘之时,内心早如明镜一般?
“除了股权之争,黄光裕事件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他在狱中居然能够发号施令,还可以写信向全国人民道歉,看似是忏悔,更像一种宣言,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做过20余年法官、律师生涯也长达12年的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看来:“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以至于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质疑:他为什么享有这个特权?难道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
曾经烈火烹油,顷刻风流云散
黄光裕的确很幸运。
“在他被抓以后国美并没有马上垮掉,说明他们公司相对比较规范,而且黄光裕过去做了准备,一旦公司遇到重大危机,例如董事长被抓,会紧急启动一个预案,由未涉案的管理层担负起责任。”钱卫清认为。
也许在他投靠利益集团、频繁游走于权钱交易边缘之时,内心早如明镜一般。据说在某年公司的年会上,黄光裕酒喝高了,上台讲了一通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话:“你们今天在这里玩得都很开心,我也算开心。但是你们有谁想过我的负担有多重,压力有多大?你们每时每刻都可以从国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远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而在他被刑拘后,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王海虹透露,其享有一条特殊的“绿色通道”。不仅可以委托权利、会见律师,会见不限时间和次数,甚至还可以在看守所内签署公司文件,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
中国现阶段,企业家已成为高发犯罪人群。致力于预防犯罪研究的王荣利律师曾统计,仅仅在2009年一年之中,便有49名民营企业家涉案,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
他们之中除了曾为“国内首富”的黄光裕夫妇,有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慈善富豪”周小弟、“公路大王”刘根山;有福布斯富豪、曾为“湖南首富”的吴志剑父子;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80后“富姐”吴英;有曾获“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的王奉友,曾获“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的陈相贵,曾获“中国房地产经纪风云人物”的刘益良,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开发商”的向世全,曾获“2003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铁本事件”主角戴国芳,掏空“爱建系”的颜立燕……
但进去之后尚能“垂帘听政”,与传说中的“白眼狼”隔空对掌,黄光裕之前,没有先例。
周正毅曾有“在狱中开董事会”的奇闻。最终谜底揭开,原来是行贿了狱官俞金宝。另一个例外是创维掌门黄宏生。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被裁定串谋盗窃及诈骗上市公司资产等4项罪名成立,被判6年监禁。但正式服刑的黄宏生,却始终享有对创维战略制定和核心管理层调整的把控。几乎每月,创维董事局主席张学斌都会向黄宏生汇报工作,而黄宏生的妻子林卫平则一直代行其在董事局的职责。无论是创维管理层的新老交替,还是引入新人,均由黄宏生拍板决定。但需注意的是,黄宏生是在香港服刑。钱卫清曾担任过“金融大盗”国洪起的法律顾问。“2004年3月23日清晨6点钟,我突然接到国洪起的电话,说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在国宾宾馆。我赶到之后,发现房间外全是公安的便衣。国洪起不肯出来,在里面四处打电话找人救他。公安就强行把门撞开,将他带走了。临上车之前,我问他公司事务如何善后,他想委托给我,需要写一个亲笔授权,但遭到办案人员的断然拒绝:‘哪有这样的事,根本没先例,走走走……”
钱卫清从国宾宾馆一直跟到北京站附近的经侦大队,无论怎么交涉,最终还是一个字都没被允许写。
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的公司有50家以上,有人估测他个人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那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可以委托我参与他公司的事务,把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理清楚。”钱卫清回想起来便感慨。“他一抓进去,群龙无首,所有到期的,没到期的债权人、银行一拥而上,起诉的起诉,查封的查封,拍卖的拍卖。”
至于昔日的“中国民营石油大佬”龚家龙,其遭遇更令钱卫清唏嘘不已。“因为罪名不清,为了不让他跟外界接触,把他名字都给改了,网上查无此人,就像这个人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而且在一年零七个月里转移了好多个地方,让他根本不可能跟律师通电话、见家人、遥控公司。”
“合法伤害”
“按照法律规定,黄光裕行使的其实是他应该行使的权利。”钱卫清表示。尽管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公司法都有相关规定,即使死刑犯在未被执行枪决之前,都在法律上拥有对财产的占有、处分、转让、继承等基本的民事权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企业家一旦落马,这些法律上赋予他的民事权利随即被剥夺,公司迅速陷入危机。
钱卫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权利的维护,在构建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法律危机防范体系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问题就在于执行中缺少制度上的安排。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比如这些权利虽然有,但怎么行使,由哪个部门来审批都不清楚,导致这些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对涉刑企业家民事权利的无视,还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系。过去公安、法院都是专政的工具。都是犯罪嫌疑人了,对阶级敌人、专政对象,还讲什么民事权利?对犯罪嫌疑人同仇敌忾,是阶级觉悟高的表现。”
司法界人士透露,企业家一旦卷入刑事案件,通常也就是企业噩梦的开始,哪怕只是吸毒、交通肇事这类与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行为。
在司法腐败导致冤假错案频发的当下,如何保护涉刑企业家的民事权利这个命题,显得更为紧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在今年上半年召开的“涉刑企业家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障”研讨会上讲述过一个案例:“某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冲突,一方故意使坏,从而达到对董事长采取临时拘留措施的目的,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公司内部控制权非正常变动。等到这位被刑事拘留的董事长被查明并不构成犯罪后,再回到公司,发现董事长的位置已经没有了。”
钱卫清最近就在帮一位知名女企业家维权。“她收购了一家国有企业,发现大量资产都被原来的高管私分,于是就向有关部门报告。没想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居然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那些“问题高管”。一旦追查起来,这些人都要身陷囹圄。犹如芒刺在背的高管们开始反击,举报她金融诈骗,并买通了当时的该市办公厅秘书(后被双规),下令公检法联合调查这位女企业家。查了半天没查出问题,该秘书便发火了:‘为什么查不出来,她十几个亿的资产就没有一点问题?是不是你们得了她的好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得到好处,这些人只好找了一个虚假注册、抽逃注册资金的罪名,将她判了4年,并通知到期的、未到期的债权人都来起诉她。在明知道她家人地址的情况下,故意找一个联系不上的地址通知应诉,最终做出缺席判决,将她的财产卖的卖,分的分。如果她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委托律师,就能提出抗辩,指出有些债权还没到期,怎么能来起诉?现在她坐了4年牢出来,财产都败完了。不要说在里面行使权力,现在行使权力都状告无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红帽子”问题曾经困扰了整整一代企业家,因此而落马者也不在少数。
“龚家龙就是一个典型。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红帽子戴上又摘,摘了又戴。在政府支持之下,给了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又反过来帮政府分忧,安置了大量职工,买了很多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产权不断在变,过程比较复杂。有些官员便错误地认为,这家企业就是国有的。双方对这个问题产生很大的分歧时,地方政府就动用公共权力去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刑事责任。”对“红帽子企业”有过深入研究并曾经提出过立法建议的钱卫清认为,这里面不排除有些公权私用的嫌疑。“比如他的很多资产都是高资低估给卖掉了,为什么要去这样处理?几个亿的财产卖到几千万,几千万的卖到几百万。是不是有些民营企业看中了龚家龙的资产,通过先划归国有,再贱卖的方式得手?再比如江西的企业家涂景新,在“红帽子”摘除过程中,跟海南一家公司发生了纠纷,最后以贪污挪用国有资产的名义,被判处了死缓,后来又改判为无罪。”他认为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机制来维护企业家的权益,一旦公权力被一些少数腐败分子把持,他们就可以行使“合法伤害权”来获得巨大利益。
制度完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是否有企业家,因为涉刑后无法行使正当的民事权利,而拿起过法律武器维权?
钱卫清表示:“有上告,但是没人理你,至于要求国家赔偿就更不可能了。按理说,如果能行使民事权利,企业本来不至于遭受巨大损失,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国家应该赔偿。但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即使完全是冤案,最后判无罪,赔偿也非常低,把无辜者的牢狱之灾按职工一天8小时工作的收益计算,虽然你在里面是坐了24小时牢。这个赔偿标准本身就非常荒唐,并且赔偿还往往不能到位。所以民营企业家的权利根本就得不到有效保障,企业家除了管好自己不违法乱纪,还要防止自己的企业被人惦记,或者得罪人。一旦涉嫌刑事犯罪,必然会在刑事侦查阶段、起诉阶段以及服刑期间,丧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后果很严重。这样会造成民营企业家的离心力,用脚投票,将资产转移到国外。黄光裕案对中国法制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但他也承认,黄光裕案是个特例。“因为涉及到供应商、合作者、银行等等很多第三方利益,十几万职工和社会影响力,也许政府出于维护稳定和职工利益,积极寻找了一种创新的处理办法。而其他企业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要看具体执行部门的领导有没有这个魄力和意识。在侦查阶段,往往是为了侦查、保密的需要,防止各种关系渗透进去,需要限制犯罪嫌疑人跟外界联系。如果我是公安局长、办案人员,抓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允许他行使民事权力对外通话,如果出什么事我不是要承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黄光裕的案件,肯定是得到了更高指示,具体的经办人不可能自作主张。”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把这个事件制度化、规范化,否则会导致不公平。由两高联合出具一个规范性的文件,明确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羁押以后,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可以行使民事权利,怎么行使,权利应该委托给谁,手续应该怎么办理,如何限制,由哪些部门审批。比如黄光裕虽然有绿色通道,但是每次活动都会给录下来。证明当时行使的这个权利,是在限定的范围内。今后对于这类事件的处理就有了一个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