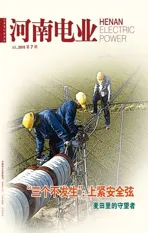行者肖伟才
2010-05-17Article陈妍妍Pictures寇宝刚
文 Article_陈妍妍 图 Pictures_寇宝刚
人物名片 肖伟才,现就职于商丘供电公司。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记者、言论专栏作者,其间发表过200多篇文章。此间,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经常性地选读他的文章。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外著名报刊上发表100余篇文章,受到海内外著名媒体的关注。现兼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网等专栏作家,著有《是什么让我们不能沉默》等著作。

对肖伟才最初的了解是从“徐楼事件”开始的,经过他的报道,罕见的乡村小学被卖、教师举债赎校的事实才广为人知,进而引起高层的重视。后来又在他的努力下,一场跨国援助促成,用于救助和奖励徐楼小学的学生。听说,他还是位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曾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这更激起了我对他的好奇。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第一次见到肖伟才,浓重的乡音,朴实的外表,亲切而低调,与他的交谈如同旧友般随意与轻松。
“我血液中流淌着‘农’的元素”
“我从不在城市人面前掩盖我曾是‘乡下人’的历史,相反,我永远以有这段历史为荣。”这是肖伟才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一段话。肖伟才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爹娘艰辛劳作的情形成为他记忆中的永恒画面。爹娘一辈子省吃俭用,为了省钱供他上学,父亲甚至在夏天里很少穿鞋。
农村的生活与经历使得肖伟才对生养他的那片土地及父老乡亲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中国是农业大国,要想读懂中国,必先读懂中国农民。因此,作为农民的儿子,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思想者,一个为农民命运而进行思考的思想者。“尽管现在我的生活已经远离了农村,但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农’的元素,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种本原的平民意识。”肖伟才说。
他给笔者讲起多年前冬夜里的一次经历。晚饭后,他和妻子散步,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一个70多岁的做爆米花生意的老人,在寒风中等了几个小时的老人,一分钱没有挣到,反被城管人员罚了几十元。“我永远忘不了老人那无助、渴望、等待的眼神。”肖伟才说,“在寒冷的冬夜,有钱人能干这个吗?只因为他是农民。”
强烈的城乡生活反差和一些城市人对农民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心,这也成为他一直以来持续关注中国农村、农业问题,思索农民命运的动力。
他在《中国农民转型路程遥远》、《进城还是守乡》、《中国农村不该选择梦想》等多篇文章中,表达出对“三农”的观点,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担忧以及解决办法。
肖伟才在10年前就认为,有效地组织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他在《谁来组织中国农民》一文中提出“能够成为组织农民中坚力量的,应该是新兴的工商阶层。随着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一部分人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农村新兴的工商业领袖”,今天读到这些话,仍感到他的观点是非常前沿的。
以良心来观察和回报社会
当谈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时,肖伟才说:“一直以来,我都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分子,但每天看着那些自称‘左派’或‘右派’的知识分子通过传媒,打些无聊的嘴仗,不禁为这些人感到悲哀。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坚定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在精英阶层的话语影响力无处不在的今天,他们的话语已经不是属于他们自己,而这点,经常被许多知识分子所忽视。”
他说,自己作为一介平民,无意与这些精英对抗。他之所以推崇鲍德里亚,是因为今天许多精英人士的所作所为,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了。平民,大多数是对自己负责的。这并非是一个武断的判断,因为,平民的思想大多是切合实际的。他认为,唯有个体思想活了,整体思想才活,普天下的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他始终认为,平民的思想,是和谐的支柱。平民知识分子,更应该用良心来观察和回报社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
2002年,他家乡的唯一一所小学被村支书卖掉顶村委会欠建筑商的建校款,几百名小学生面临失学。后来,学校里的12名教师举债赎校,才保住了学校。
在当时还是民办身份的12名教师们为了学校和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还债路。肖伟才为教师们的义举而感动,就采写了《乡村小学,教师的命根,村民的灯塔》的稿件,刊登在2003年6月29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文章发表后,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华侨和当地民众为徐楼学校的教师而感动,许多人为学校捐款。“可惜的是,当地政府谢绝了人家的善意。”肖伟才说,“当地政府认为,这样使他们很没有面子。后来,新加坡一位老教授通过外交部把款捐到了徐楼学校,还清了教师们的债务。他还在徐楼学校设立了奖学金。”
报道发出后,肖伟才心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那个偏僻的乡村里,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有基层官员还认为他揭了村里的丑,扬言要报复他。值得庆幸的是,高层的过问和中央电视台的后续报道,使徐楼学校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他以自己的良心和对家乡的挚爱为家乡实实在在地做了件在当地“轰轰烈烈”的事情。现在,徐楼学校有几百名小学生享受着助学金带来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肖伟才的报道引起关注后,国家当年就专门针对农村学校建校债务问题下发了相关解决的文件,自此,全国乡村小学的此类问题成为历史。
挑战权威,提出自己的见解
肖伟才说,正是因为自己熟悉农村的一切,关注农村的一切,所以在读到那些被称之为农村研究专家的文章时,总是充满着一份谨慎的挑剔与怀疑。
2000年7月,一位经济学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的思考》的文章,尽管他从内心十分敬重这位经济学家,但仔细拜读后,认为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不太符合中国实际。于是,肖伟才勇敢地拿起笔,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的再思考》一文。该文被《联合早报》刊在“天下事”栏目的头条,后被人民网、法新社、亚洲新闻联合网等10多家国内外网站、媒体转载。他写的《中国农村四大问题》在《联合早报》发表后,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国研网以“国研专栏”的形式迅速做了转载,香港凤凰卫视网站接着也做了转载。他撰写的《中国民工潮:危险的信号》在《联合早报》发表后,中国新闻社在每周编发的国外媒体关注中国栏目中,全文引用了这篇文章。
他的文章,对“三农”问题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打动了许多读者的心,但也招来了许多非议。如《中国民工潮:危险的信号》、《令人忧心的中国农民陋习》、《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农民需要理智引导》,每篇文章发表后,都有专家撰文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撰文对他的文章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
在激烈的观点碰撞中,肖伟才经历着一种难得的磨砺,同时,他也为一些专家因缺乏了解中国农民的现状而对中国农业大唱赞歌,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我要感谢那些与我进行观点交锋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对农民充满感情的。但是,他们多处于社会上层,并不很了解处于底层的农民现状。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在于淡化身份符号,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转型,而许多专家的观点是以城市化带动农村等。”肖伟才说,“没有身份的转变,不可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他几次重复这个观点。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忧虑
谈到新生代农民工,肖伟才语调沉重起来。
“那些手提皮包或者是提着笔记本电脑的工作者,比起他们的父辈背着编织袋而四处漂泊的打工族,表面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他们是打工者,但是他们心灵深处的东西本质上没有变。”肖伟才说。
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能在城市里安家,生活的成本和心灵的重负加剧了他们的急躁和不稳定。那些跳楼的富士康员工,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仅要看到这是个体的极端案例,其实,它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经济在转型中遇到的问题。
“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不要小看他们这个群体。”肖伟才说,“他们的焦躁和不安,其实正是中国经济的焦躁和不安。等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了,也就不存在‘农民工’这个称呼了,他们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整个中国经济的进程。”
时光在愉快的谈话中悄悄流逝,肖伟才忧国忧民的思绪也在感染着我,窗外,夕阳渐渐下沉,给远处的天际抹上一缕金色。从现实到理想之间会有多远的距离?不管多远,相信一定会有走完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