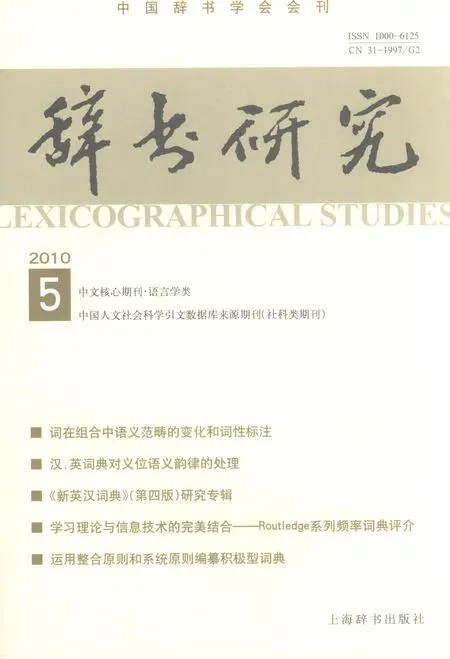科学与民主的实践——忆我国第一部法学词典的诞生
2010-05-13曾庆敏
曾庆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编纂的我国第一部法学词典1977年开始筹备,1978年召开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1979年秋冬统稿,1980年6月出版,全书共87万字。应该说,该词典只是一部中型偏小的工具书,把它提到“科学与民主的实践”的高度来回忆,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处在30年前的时代背景下,组织此项工作,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尊重人才,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需要科学的治学态度,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十年浩劫,人们再也经不起“乱”的滋扰,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法律秩序破坏殆尽,而法学更不被看成是一门科学。曾有司法工作者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求索资料,我们却拿不出像样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的法学科研机构,我们觉得要为社会做些什么。法学所领导科研工作的王珉灿同志认为,与其分散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或专著,不如先写一部将法学各个学科的内容整合起来的专科词典,可以使司法工作者先对各法律学科的概念有一个科学的了解,将各学科有内在联系的概念串起来,就可以对该学科的基本面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说,对丰富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知识而言,这是一种短平快的做法。在这一想法较成熟之后,王珉灿同志即向社科院的领导请示,并得到了社科院的大力支持。
二、组织队伍
得到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之后,本应该很顺利地展开工作。但是,在30年前,国家并没有公布过各种基本的法律,而法学界也没有尝试过承担如此大的项目,大家对此项目的完成缺乏信心,在所内讨论此项目时也反映平平,个别同志甚至说,在没有基本法律的条件下,写这样的书是容易犯错误的。当王珉灿同志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协助他工作时,我同样顾虑重重。经过两次谈话,我终于下决心同意协助他开展工作。于是,王珉灿同志专门设立了一个“词典组”作为编写该词典的职能机构。我开始为此项工作做一些基础工作,如收集各科词目,制订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等。同时,王珉灿同志还在所内物色一些同志参加写作,最终物色到三位同志,均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显然,完成此项目的人力不足,必须开阔思路,面向全国组织队伍。
说到组织队伍,必须打破旧的框框。所谓旧框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片面地强调集体力量,找某一个学校的某学科教研室的负责人来承担一个学科,而这位负责人又将这个学科的词目分给教研室的成员来写。这就是当年的所谓集体主义,否则就是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二是片面注重权力。一般都认为位高权重的就是专家,就是权威,就能胜任或主持某项学术工作。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不打破这两个框框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此项工作。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观念。
我们需要的写作人员,是法学领域中具有特定专业和真才实学的人才,在那个年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老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没有在政治运动中经历过各种坎坷。当我们去邀请这些专家的时候,部分专家表示欢迎此项工作,他们认为此项工作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值得做。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这些专家还没有其他事情缠身。还有部分专家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不敢轻易表态,当我们把问题说清楚,使他们感到我们的真心诚意以后,才勉强同意。但是,在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这些老先生感到我们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下决心来完成此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并且充分贡献出他们的学术才智。
有一位老先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现年已98岁高龄的安徽大学的老教授陈盛清先生。他曾经是解放前的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受到冲击,当时已远离北京赋闲在家。他和王珉灿同志相熟,1978年,王珉灿同志邀请他的时候,他已68岁,年近古稀。他来到北京,住在我的办公室,同我一起工作,没有一点老教授的架子。在整个编写、组织工作中,他始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他的介绍下,我们还吸收了其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参加了我们的编写队伍,如毕生研究罗马法的专家周柟老先生。
在基本队伍形成之际,我们开始物色出版单位。我们同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联系,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上海辞书出版社得知消息,立即同我们联系,希望将来词典完成之后,交由他们出版,并且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
三、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
在筹备工作基本完成、队伍基本确立后,我们于1978年8月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参加者除了承担编写工作的专家外,还有不参加编写工作的某些法学界的领导同志,以及出版社的部分领导和编辑人员。
这些专家就编撰我国第一部法学专科词典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进行商讨:

参会人员合影。前排就坐者从左至右依次是骆静兰、丘日庆、周子亚、潘念之、解铁光、张友渔、芮沐、曾昭琼、陈盛清、巢峰、王珉灿。
第一,对词典筹备组提出的词目作一个原则性的讨论,而不是逐个讨论词目。在讨论中发生分歧是正常的。有的领导同志对法学概念内涵的理解较为狭窄,似乎只有刑法、民法、诉讼法这一类词目才是法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如劳动法之类的词目都应该属于经济类词目,不属于法学词目;而大部分同志从本人研究的学科出发,认为某些词目看起来似乎属于经济类的词目,如“女工”,乍看起来根本不是法学词目,但是女工的权利保护必然是有法律内涵的,在我们的法学词典中一定要有所反映,其他如工资制度、工龄等一系列词目也应收录到词典中,这样才能使法学的概念丰满。讨论的结果是同意多数专家的意见,反映出参加者尊重科学、尊重客观实际、“不唯上”的科学态度,也反映出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民主精神。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但是在30年前,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讨论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参加者一致同意筹备组提出的意见:首先词典是一种工具书,而不是论著,因此它必须以丰富的知识为前提,没有具体的知识就不能成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工具,在研究学问时也起不到辅助作用。其次,强调词目释义的科学性。在阐述概念的内涵时,要坚持该概念本来应有的含义,而不应该有任何发挥、联想、杜撰的因素。第三,坚持概念内涵的客观性,而不能按照我们的政治需要加以政治上的修饰。如此等等。在讨论这些原则的同时,大家也没忘记词典的政治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编写词条需要考虑词目释义的政治性,但是反对穿靴戴帽式的政治性。由于我们在这些原则方面达成了共识,并且反映在其后撰写的词目释义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掀起的所谓“反自由化”运动中,我们所坚持的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有人翻查这部词典看是否有“自由化”倾向,翻了几遍居然没有发现。可想而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左”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清理,还处在心有余悸的状态之中,不能不承认这些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学术领域里尝试着拨乱反正,将撰写这部词典作为科学的实践。
第三,讨论成立编委会的原则。大家一致反对挂名制,认为应该先成立一个常务编辑委员会,参加常务编辑委员会的同志原则上应该是参与撰稿的人,而且没有必要设立主编。有人私下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人,没有人有资格担当主编的角色。”这种看法主要还不是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还没有真正落实政策,而是因为没有一位法学专家能够通盘了解法学各学科的内容。这样既否定了多少年来形成的惯例,只要当权,不论是否参加具体工作,都有资格当主编,而真正出力的人反而将名字排在后面;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当时学术界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设想不仅是大胆的,而且改变了某种陈腐的观念。
这是一次成功的编辑工作会议。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大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增强了凝聚力,为以后的成功写作铺平了道路。
四、团结一致,坚忍不拔
在这次会议之后,各位专家分头编写自己学科的词条。但这时法学所出现了人事变动,王珉灿同志被调出法学所,“词典组”没有了具体的上级领导,而所内也没有领导来同我们交换意见或布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词典组”必须作出选择:是使此项工作不了了之呢,还是继续前进,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和陈盛清先生商议之后,认为必须继续工作,不能因为人事变动而对不起那些正处于热情高涨状态下的专家们,更不能使那些专家们认为法学所是言而无信的组织。我们必须自己挑起这副担子,继续同各位作者以及出版社联系,看样稿、讨论各种疑难问题,以及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使整个工作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
从1978年8月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直至1979年7、8月间,整部书的稿件陆续寄往出版社审读,并决定在1979年10月起集中大部分常务编委、部分编委,以及出版社的部分编辑人员在一起统稿。由于各学科词目是由各位学者分头写就的,要将这些分散的词目编成有内在联系的一部书,确实是一个大工程。应该说,参加者,包括出版社的同志,团结一致,这些专家们不是只在挑毛病,而是解决存在的所有问题。经过3个月的苦战,统稿工作终于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北京的常务编委提出要某位领导同志担任主编,并说出一堆理由,但我们坚持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的意见。我们不想将大家辛辛苦苦做出的成果拱手送给他人。而我们更担心的是,如果某位领导同志因工作忙,请秘书看看,挑挑毛病,那么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集中专家来讨论了,出版此书将会遥遥无期。在专家的心血和领导挂名之间我们更在乎前者。尽管我们因此会得罪某个人,或者某个领导。但是,只要此项成果能顺利出版,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了。
整个统稿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在稿件方面遇到困难时都是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同该词目有关的专家共同研究后即刻作出决定。
统编之后的书稿,出版社是满意的。于是,该书在1980年6月出了第一版。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要求,又请这批专家修订原词典,之后出版了《法学词典》增订版、第三版,使原来的一部中等偏小的词典发展成一部中等偏大的词典。《法学词典》累计印次达8次,累计印数达119.1万册。
五、社会效应
《法学词典》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我们的一批老专家被社会重新认识。当我们还在统稿的时候,安徽大学法律系派员到我们统稿的地点,邀请陈盛清、周柟两位老先生在书稿完成之后去安徽大学任教授。中南政法学院的曾昭琼老先生告诉我:“有朋友原以为我早不在人世,见到法学词典后才知道我仍健在。”之后就邀请他去中山大学讲学,使他的学术生涯获得了新生。当年的一些中年专家在晋升职称时,此书成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最重要的是,这部词典不仅成为司法工作者系统掌握法律知识的基本工具,而且为那些法律科教工作者以及法律院校的学生所倚重。这部词典所起到的普法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实难估量。
在国外,这部词典同样被许多人所重视。我们的一些法律代表团出国的时候,往往将这部词典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一位美国教授为此书写评论文章,赞扬它“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世界标准”。最能说明这部词典在国外的影响的是:该词典的一部编委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曾以法学辞典的编委身份作为专家证人出席美国法院审理的一件涉华案子。
30年后看这部词典,其概念的阐述仍有相当的稳定性,其内容仍有可取性。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主要还是因为一批老专家坚持科学与民主的观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