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严亲述两岸包机内幕及身世
2010-04-23曹可凡蒋孝严
曹可凡 蒋孝严

当两岸首航包机像一只寒冬过后的春燕,带着暖春的信息从天而降时,台商协会理事长蒋孝严的内心无比兴奋与骄傲。因为整个春节包机方案由他带头启动,在两岸包机实现过程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推手。他做客“可凡倾听”,还讲述了曾经是“蒋家门外的孩子”等一些事情。
(以下“曹”为曹可凡——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主持人。“蒋”为蒋孝严,被访问者。)
曹:您好,很高兴能够在台北给您做访问,我知道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致力于推动春节的台商包机,这在当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您,靠着自己的毅力和执著,历经很多的困难,终于把这样一个浩大工程完成,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希望能够做成这样一件事情?
蒋: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在2002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候有一个客观的环境比较困难。2000年之后,我到大陆去,最早是到奉化去祭祖,就是到蒋家的祠堂去行礼,去扫墓,是认祖归宗的第一步。但是在那个旅程当中,碰到了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台商,也就是从台湾到大陆去投资的朋友。然后在我奉化溪口祭祖以后,我还到桂林去扫墓,先母埋葬在桂林,在桂林也有台商。尤其我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的台商都是蛮重要的。在交谈里面,他们就跟我提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每年要回台湾过年的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买不到机票。从上海到香港机票都很难买,因为过年的时候是长假,几亿人口在流动,他们买不到机票。我心里想,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解说词:那么如何尽快让台商实现春节返台与妻小团聚呢?孝严先生最后从一个“包机”的概念里寻得了灵感。因为1994年11月他曾经安排过“包机”,将身患脑溢血的孪生弟弟孝慈从北京平安接送回了台湾。
蒋:十五年前,我弟弟那时候在东吴大学当校长。因为在那之前,他是法学院的院长,在法学方面有很深厚的研究,所以他在这方面到大陆去做了很多的交流。但不幸的是,那年到北京的时候他突然脑溢血。那时候我在美国访问,听到这个噩耗我就从美国连夜赶到北京,把他接回到台湾。接回台湾就是用包机,医疗包机。在这过程当中,我跟台北商量,我说我弟弟是病人,从北京花钱包机,包机从北京到台湾一定要经过香港吗?他说要,因为我们跟大陆没有直航。我说这是一个特殊状况,基于人道考虑,一个病人,你降落一次,再起飞一次,对他的身体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是不是可以不要绕香港,直接从北京过来,或者绕过香港到台北降落。他第二次跟我见面,还是说不行,这个例子不能破,飞机还是要到香港,你就是滑行一下都没关系。所以飞机就到香港滑行,跑道上转了一圈再起飞。
曹:匪夷所思。
蒋:很折腾。我就先回来,然后在机场等孝慈的医疗包机降落在桃园机场。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另外在1992年,由于我工作的关系也办了一个包机,用华航的包机去前苏联,我们送米,送药给他们。那这药怎么送去呢?我跟台北方面说,我要用包机送过去。他说你们交给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就行了吗?我说不行,我们的包机要直接送过去。后来我坚持让中华航空公司把整批的药装好飞过去。那个经验让我知道,我们跟莫斯科没有任何的航权,也没有任何的航约,但是可以用包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所以这两次的经验累积起来,后来碰到台商朋友,提到他们没有办法回来过年。我想可以用包机,因为它是商业行为,而且为单一的目的,单一的目标来做安排,我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时候连战先生是国民党主席,我私下跟他作了详细汇报。他说这很好,这可以的,然后再在常务会里面专案报告,就拍板了。中国国民党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要我到北京去访问。所以在2002年,我就去访问了,见了陈云林先生,还有民航总局的总局长,还有其他几位国家领导,都沟通得挺好。但初步提到这个意见的时候,也没有很快回应,因为大家搞不太清楚,到底可行不可行。但都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我们可以来研究。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然后我又把这边的一些进展再带去北京,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总算差不多接近了。最后我记得到北京的时候,陈云林先生跟我谈,因为飞机是非常敏感的,怎么查验。我就到北京去谈,后来我发觉北京方面比较开放,超出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弹性。我就跟陈云林先生讲了一句话,我说很多很敏感的问题,我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处理对美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模糊,照道理讲是不应当是做事情的态度,但是我跟他说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模糊,为了解决问题而把它模糊化。陈云林先生就跟我讲,这样子吧,原则上我们可以来飞了,但最好是对飞,不要单单是台湾的飞机,我们也要过来,这是商业行为,包机利益分享。我心里想这也是合理的,我回来把这个消息带到台北,这边说绝对不行,大陆的飞机一下过来这怎么行呢?
曹:怕特洛伊木马?
蒋:对,他们说,假如第一个民航机飞过来,我们认为是台商,可以降落,结果不是两百多个台商下飞机,而是两百多个解放军,拿着冲锋枪冲出来怎么办?我说有这个可能吗?他们又说,假如在雷达上面看到一下来了很多飞机,看着是民航机,后面躲着几架米格机,对着我们,我说你太天真了,如果真这样的话,他不需要用米格机,飞弹就可以过来了,还要弄这些东西干什么。最后这边说大陆飞机不能进来,一定要我们先过去。我又跑一趟北京,然后很恳切地谈,我说这样子好了,北京这边就做一次让步,我们先飞一次,飞了以后第二次再对飞,最后他们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很多的让步。也希望两岸的关系能走得比较密切平顺,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总算在2003年春节,第一架台商包机从我们那边飞过去,中华航空飞过去的,第二架是复兴航空飞过去到上海把台商接回来。我本来说我要坐包机去的,因为是我安排的,而这边小气到这个地步,他说不行,你不是台商你不能坐。
解说词:当两岸“三通”的民生大事终于落到实处后,孝严先生的内心深感宽慰。但是当我们问及他曾经隐姓埋名的人生,他的心再一次不能平静。他说因为自己是经国先生的非婚生子,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私生子”,一直被蒋氏家族拒之门外,是一个蒋家门外的孩子。
曹:我特别想知道您跟孝慈先生,你们是孪生兄弟,你们小的时候大概多大知道自己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世?
蒋:坦白说,这件事情我们真正了解透彻的时候,是我跟孝慈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在新竹,新竹离台北开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1949年,我跟我外婆还有舅舅到台湾来。事实上我们从厦门上船,上一个军舰。这艘军舰还带了一部分故宫的宝物,一起运送到台湾。所以我们上船的时候,父亲还来送行。我们太小了,也没有记忆,才六岁多,也不认得谁是谁。但是他跟外婆碰了面。当然他登舰的理由很简单,我要来巡视一下宝物,有没有妥当地收好。我们离开大陆的时候,坐军舰到基隆上来,在旅馆休息了几晚我们就直接到新竹,没有住在台北,所以小的时候就没跟蒋家其他孩子在一起生活,也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我们在新竹很苦。
曹:您曾经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你们当时的状况,说你们的生活跟难民差不多。我很吃惊,为什么那时候的生活状况会那么差呢?

蒋:我们起先也不晓得,因为我到高中的时候才知道我的父亲是经国先生。外婆有天早上把我跟孝慈叫到床前,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人。当时她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当然大吃一惊。那时候我们心里想,如果父亲是经国先生,爷爷就是蒋介石先生,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苦?我们当时这么想,可是我也不敢问。后来到大学,王升先生告诉我们,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他跟我的舅舅之间发生过矛盾,可能我舅舅要找工作,或者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在我们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每年过年或者是端午、中秋,王升都会从台北来看我外婆,他来的时候,我们日子就好过一些,桌子上有鱼了、有肉了。他不来的那一两年,我们日子就很苦,显然是他带了生活费来交给我外婆。后来他跟我舅舅关系不好了,可能叫我舅舅去拿钱,舅舅不去,王升也不来,我们日子就很苦,苦到像难民的日子。舅舅没有钱买东西,家里家具都是竹子做的,没有什么沙发、电器,唯一的电器就是个电灯泡,而且电灯泡连灯罩都没有,就是一个书桌上面放一个电灯泡。哪里有什么吹风机、音响,什么都没有。日子非常苦,一直到我们读高中、大学,日子都非常艰苦。当然到大学以后,我们自己做家教,找点工作维持生活,缴学费都延期交的。
解说词:当身世不再是秘密时,孝严了解到自己美丽大方、气质不凡的母亲章亚若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与在江西赣州任职的经国先生相爱的,之后母亲特别转移到桂林生下了他们,祖父为之取名“孝严、孝慈”。但是就在他和弟弟六个月大时,母亲章亚若在桂林的一家医院猝然去世,且死因不明。
曹:您后来也对母亲的死因做了很多深入的调查,经过调查,您发现您母亲在去世的前后都出现了一些什么特别异常的状况?
蒋:我到桂林医院去过,是在2001年的时候。后来陆续几次去,我都去医院查看原来的病历还在不在,接待的人告诉我统统找不到了。当然也可能年代久远,经过战乱等等,找不到病历。但也可能病历在出事以后就被人家带走了,所以这是一个查不到结果的案子。但是我可以认定,先母她是被害的。
曹:据说您母亲头一天到外面吃了一顿饭回来就有呕吐。
蒋:晚上回来就有呕吐,第二天早上起来,还由一位朋友陪着步行到医院去,就说状况是呕吐,有腹泻,可是还不至于……
曹:不致命的。
蒋:不致命的,因为她可以到医院去,到达医院以后才出这个状况。当然我们在小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就感觉到异常,我舅舅我外婆特别叮咛我们,不能在外面随便打针。我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通知下个礼拜一要种牛痘,我印象很深我舅舅特别陪着我们到学校的医务室种牛痘,他还站在旁边,很紧张,牛痘他也不知道怎么种,还以为是打针。事实上就是臂膀上面划个十字,这疫苗就放在上面。他说不能够随便接受打针,而且对医院有一种恐惧。外婆生病到医院,病得很重,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家了,不敢在医院待,对医院有一种恐惧症。我们绝对不能够随便打血管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都跟先母的死因有关。

曹:据说当年您母亲去了医院以后,有一个“王”姓的医生给您母亲打了一针就出了状况了。
蒋:没错,这时母亲的一个妹妹陪在旁边,后来告诉我外婆,转述的。所以这个“王”姓的医生,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不是姓“王”我们现在都无法查证。先母在医院里面,本来还可以跟她朋友,一起谈天等等,医生过来,给她打了一针,然后她就昏天黑地,一下子不行了,显然这个针是有问题的。
曹:您刚才说到您母亲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被害的。对于为什么会被害,坊间有很多的流传,究竟是谁下了毒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归纳起来好像有几种说法,有种说法说可能是您的祖父,有种说法说是您的父亲,还有种说是军统,也有一种说是您父亲的亲信,您的认定大概是偏向于哪一类?
蒋:我想,跟我祖父跟我父亲是没有关系的。外面有牵强附会的一些说法,我不太能够接受。我所了解的就是周边的人,为了护主,自以为是地采取这样的一个伤天害理的行动。连我父亲事先都不晓得,所以当我父亲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痛苦万分,好几天戴着墨镜。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去追究凶手是谁,我觉得也没有意义了,冤冤相报没有意义。我希望对这个事情有个了结,把这个仇恨化解掉。找出凶手又能怎么样?当然对母亲来讲我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也可以说因为我和孝慈,所以她到桂林去,到了桂林,因为我和孝慈而遇害。我们心里面都有相当的一个负担,所以对母亲来讲,能够完成她的一个心愿,回到蒋家,是我一直在努力,没有舍弃的。
解说词:母亲去世后,孝严,孝慈,几乎像弃婴一样,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闯荡。虽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父亲最起码的关心与呵护。与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相比,他们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把人生当中许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曹:我知道你们兄弟俩成年以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著,可以说完成自己人生的一种蜕变,一种成长。孝慈先生成为一代学者,当上东吴大学的校长,您也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外事部门工作,是不是那个时候心里还有这样的想法,设法想和父亲能够接个头,尤其您是在外事部门工作,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场合,会和父亲遥遥相对?

蒋:有时候命运很捉弄人,父亲在生前,我跟他见过面,我有印象的见过一次面,是在一个酒会上面。我父亲出现,那时候他担任“院长”的工作,远远地我看着他,那种感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跟我目光也有接触,我感觉他好像认出我了。我很想过去叫他一声,可是我不敢,我躲开了,我也不知道我走到他面前,他会怎么样,我想叫他,但是我避开了,这是心理上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我们小的时候在桂林,他去看先母,抱着我们。我们不会有记忆的,才几个月大,先母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六个多月,我们没有记忆。有记忆的就是那一次。后来我在外事部门,一步一步担任更重要的责任,“科长”“副司长”,“司长”、“次长”、“部长”。我的职务事实上是负责对美关系的,很重要的。比方说做到“司长”,有外宾来晋见的时候,通常“司长”去做传译的,或者陪见的。但我担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父亲那边不找我去了,找那个秘书做传译。我心里完全有数,我也可以体谅。但是当我在“司长”要升“次长”时卡住了,因为“次长”常常陪见的几率更大。你去陪见的时候,媒体上两个人同时出现的镜头会很多,所以就有人有顾虑。耽误了一段时间后,因为我表现不错,照样升“次长”,但是不去负责对美的事务了,因为访美太多了。叫我负责我从来没有处理过的,没去过的地方,负责沙特阿拉伯、中东、伊拉克、伊朗,还有欧洲,这些国家是没有访宾的事务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我才有机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跟父亲见面的机会就反而没有了。我跟孝慈事实上从大学开始就再三地要求要跟父亲见见面。当我成了家,有了孩子,我还跟王升将军讲,让我带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去陪陪老人家,让他高兴高兴。提出来几天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说不方便,那我心里面就有数了。天天可以看到他的消息,媒体上可以看到他,而自己的父亲我却没有办法去跟他见面,心里讲不出来的情绪。
曹:其实是一种很残酷的现实。
蒋:对,白天我可以压抑,有时候晚上会做梦,会梦到父亲。我在那本书里面也写了,有天晚上梦到父亲,我就叫“爸爸,爸爸”。我内人睡在旁边被我叫醒了,把我摇醒后她一摸我眼角都是泪水。这个过程是残酷的,所以我说我是蒋家门外的孩子。
曹:那么多的时间,跟父亲近在咫尺不能见面,您和孝慈先生是不是会为坊间可能俗一点的说法、私生子这样的身份而感到自卑过?
蒋:也觉得不公平,外婆叫我们要争气要努力,还好我们选择这条道路,自己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表现。但你说这种自卑的感觉完全没有吗?好像也很难,在念高中时,生活很困苦,这种坊间的传闻有时候是存在的。我们也听到过,有人指指点点过,心里面是有一些压力,可是别人问,我们又不能讲什么。我踏上社会,在外事部门工作,有同志就问,你父亲是不是谁?我不敢讲,我不敢承认,问你是哪里人,我只能说我出生在桂林,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能讲我是浙江人,我是哪里人。
曹:奉化就根本不能讲。
蒋:都不能跟任何人说,一直到我父亲过世以后,在1988年我的身份才反而可以坦然地面对,也因为父亲过世以后,我和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来往反而比较自然。
曹:我听说孝慈先生可能性格跟您有些不一样,据说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也很无奈。我听说他有时候去卡啦OK也会唱一首叫《心事谁人知》,来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是不是他长年的抑郁和不快乐,其实也损害了他的健康,所以他那么年轻、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就发生了脑血管的意外?


蒋:我想这个跟他身体是有关的,他比较内向,很多东西都压抑住。所以他血压就一直很高,血压跟情绪是有关的。血压高他又没有妥善地来调理,医生也没有硬性地强迫他吃药,他的低压曾经飙到一百三四十。
曹:低压就一百三四十?
蒋:低压就一百三四十。后来我们发现,到医院去查他病历的时候,发现血压太高了,那时候事实上就应当要强迫他住院的。但是他自以为身体还好,自己每天还在操场跑个五千公尺。他觉得还好,事实上血压高不能太剧烈运动,这方面他有点疏忽。他的心情不好和整个成长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压抑是有关的。
解说词:就在母亲章亚若遭人暗害后,孝严、孝慈兄弟俩被送到江西万安由外婆抚养,在他们三岁大时,为了避免不测,他们的大舅章浩若以父亲的名义为这对双胞胎报了户口,并把蒋姓改为章姓。谁知这一改,竟然改出了日后需要他们崎岖漫步几十年才能走通的认祖归宗之路。
曹:您跟孝慈先生大概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讨论认祖归宗这一件事?
蒋:在大学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认祖归宗。但是怎么做呢?我们在大学不知道怎么做,父亲面都见不到,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提出来要求和父亲见面,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接触,来往。父亲的面都见不到,爷爷就更见不到了,祖母更见不到了。祖父过世了,祖母在纽约,我到纽约去要见面都见不到。
曹:您去了四趟都没见到?
蒋:对,去了四趟,我的身份都是绝对可以见祖母的,都是高等职务。可都被人家挡住了,有次我跟我内人一起到纽约访问。我就跟祖母的办公室联络,透过我们的办事处的处长联络,说要晋见。好,他们那边有个叫武官的,她带了位武官,宋武官。我还跟他通电话,他说他会请示汇报一下。等了一天,没消息,我特地再多等一天。后来,来电话告诉我们纽约办事处,说祖母最近身体不好,所以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见面。那我当然失望,我内人也很失望,我们知道前前后后还有很多人到纽约去都见过面。事实上老夫人对我们的事情很早就知道了,有次她回到台北,波士顿大学颁给她博士学位,在妇联会,我们有个妇联会的礼堂。我在外事部门工作,我也受到邀请,去出席这个茶会。她看到我好高兴,她一眼就认出我了,她讲上海话,宁波话,“侬好伐?”她说你好吗?你工作做得很好。她都知道我。我还介绍说这是美伦,她也很高兴看到美伦,去纽约就反而见不到。
曹:也未必是老人家本人的意思。
蒋:不,我想绝对不是她老人家的意思。
曹:所以您感受到周围人的压力。
蒋:可能根本连通报都没通报,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纽约。但我跟孝慈说回到蒋家,我们在大学就谈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后来到社会工作,我们也谈,媒体也会来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回到蒋家,那我们只好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叫顺其自然,一直到父亲过世了。
曹:父亲过世以后,您跟他老人家见了最后一面吗?
蒋:见了最后一面,临时的灵堂。孝勇先生在父亲过世后,第三天陪着我跟孝慈到荣民总医院去。半夜十一点半,开车到荣民总医院,就是不愿意让别人晓得我们去了,就避开。然后到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到那边都十二点多了。灵堂后面就是冰柜,他老人家躺在里面。我跟孝慈就很激动,跪在地上,向他老人家磕头,那时候我们兄弟也叫着他,爸爸,是见最后一面。人生就是很悲惨、很凄凉的那一刻,但也总算我们见上了一面,见上了最后一面。当时我就想我应当要一步一步地回到蒋家来。妈妈很早交代这两个孩子要抱回蒋家,而且父亲也交代过,这是孝仪先生在父亲过世后第二天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不要太难过,经国先生有交代,你们要认祖归宗,你们要觉得宽心,只是突然走了,来不及处理你们的事情。那我心里想父亲有这样的决定,母亲有这样的遗愿,那我就一定要一步一步来走。
解说词:当孝严、孝慈把“回蒋家”看做生命中的必须时,他们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双双在美国修完博士,一个当上了大学校长,一个成了外事部门高级人才。在这之后他们再改父姓,从父姓,并不是要从这个家族拿走些什么,而是要为先母尽一份孝道,对儿女担一份责任。
曹:我觉得您跟孝慈先生真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典范,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一个人生。
蒋:因为我认祖归宗的时候,蒋家已经不当道了,他们都过世了。然后纬国将军,我叔叔也过世了,老夫人也过世了,家里面没有人了,后来孝慈也过世了。这个事情,我所承担的就是一份责任。有时候看我孩子都大了,他们将来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不要像我以前吞吞吐吐的,这段痛苦我不能够留给孩子,也不能留给他们的下一代,我不做没有人会做的。我知道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为什么你要改姓蒋呢?为什么要认祖归宗呢?你是要抢蒋家的光环,或者要蒋家的遗产。我心里觉得很可笑,我开始认祖归宗的时候,蒋家没有人在了,蒋家更没有遗产。
曹:无法给你任何庇荫了。
蒋:原来说老夫人的遗产我可以继承。后来我说只要她有遗产,我继承,我全部做公益。我也不会要,何况他们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对父母亲,对子女,身为人父,身为人子,身为人夫,我都该做的一件事情。在2002年,把整个法院程序走完,我的身份证父母栏就把它改过来了,父亲是蒋经国先生,母亲是章亚若女士,改过来。我改姓蒋……
曹:好像又过了两年?
蒋:又过了两年,一直到2005年的3月。为什么呢?我一直等到2004年12月,蒋方良女士过世以后,我再去户证事务所,申请一个新的身份证,父母栏改了以外,我自己要改姓蒋。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也不需要跟他们解释,因为我答应过孝武先生,他说你认祖归宗该做,但是不是等我母亲百年以后。我记得我对他的答应,也是我对方良女士的一个尊敬,这是中国的文化,她毕竟也是我父亲的妻子,我要尊敬她。等她过世以后,台湾的习俗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我在2005年的3月5号重新去拿完整的身份证,才正式地改姓蒋,所以整个的过程总算画上一个句点。
曹:那您现在已经完成了归宗的一些法律程序,也从过去的章孝严改成蒋孝严,从内心来说,您觉得对蒋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有没有怨恨?
蒋:会有一点。孝慈一直到后来都很不平,甚至于他到东吴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都对过去很不平。他跟我讲,我们甚至于讨论要不要归宗,蒋家给了我们什么?蒋家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要慎避,而且问到我们要含含糊糊的,一般的生活都没有被照顾好,那我们为什么回到蒋家呢?就从母姓,我们也有这种气话。可是从来没有什么仇恨,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恨父亲呢?我们倒没有过,我们会体谅他,我觉得我们很早就很懂事了。尤其我在工作的时候,知道政治的一种复杂性,我会去体谅父亲的一个处境。当王升先生跟我讲,不好安排见面,见面的地方不容易安排,我可以体会,因为那时候,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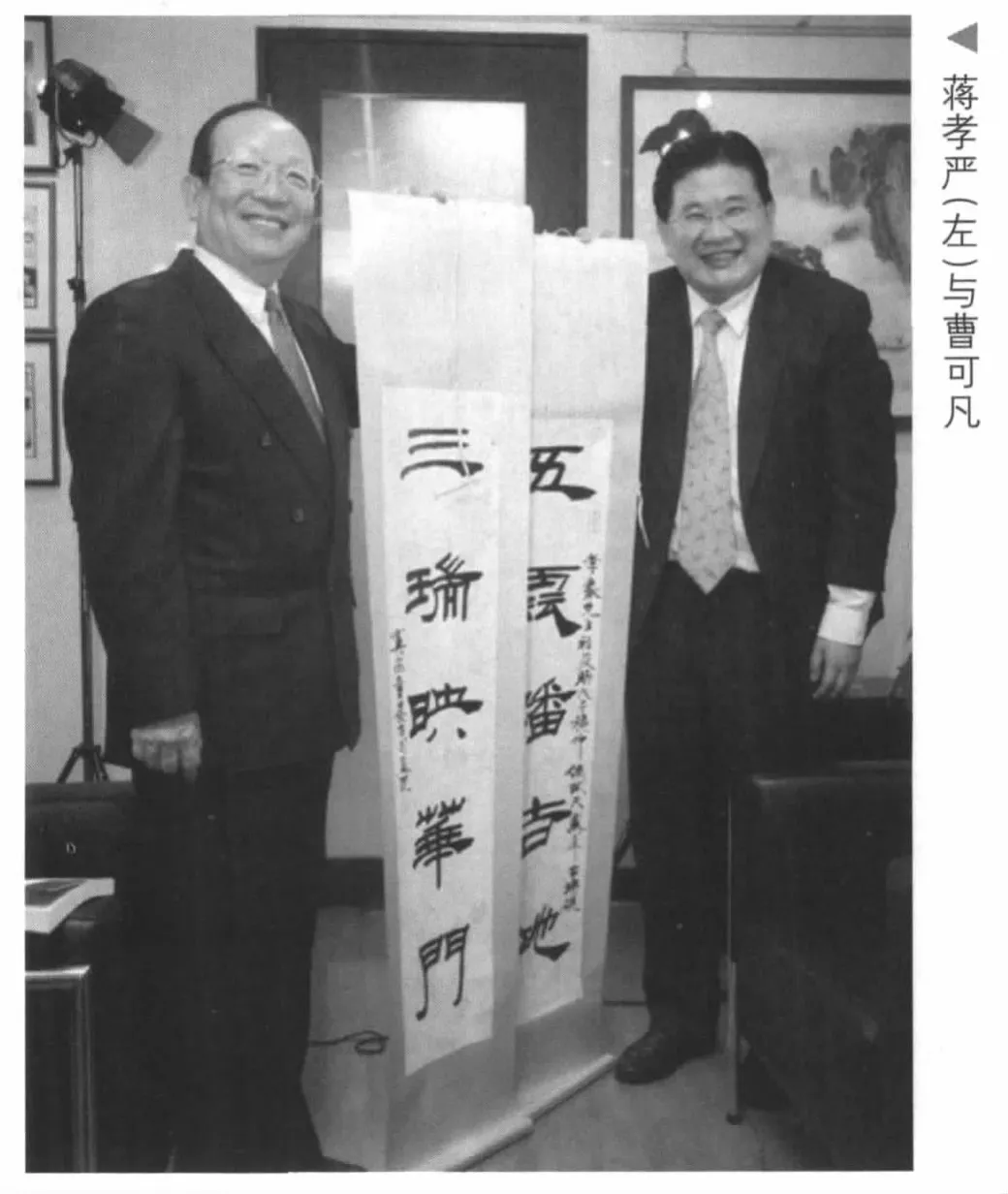
曹:最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孝严先生,您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花了很多的精力来推动两岸的互动,两岸关系的改善,现在两岸的关系已经呈现出春暖花开的景象,您对两岸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期许?
蒋:我很高兴看到现在双方面的访问越来越密切,现在层次也可以拉高,比过去八年要越来越宽松。这是一个好现象,我觉得台湾方面同样要更大的开放,让台湾方面负责的一些人士,也到大陆去,对大陆多了解,或者对大陆有误会的一些人,让他们去接触,去看看。我们中国人讲,水到渠成,我们看到水流不断,渠道自然会出来,不要满足于现状,不要以为理所当然。但是不要操之过急,能够有信心,勇敢迈进,我想成功是属于两岸的。
解说词:2005年,姓了63年母姓的孝严,终于圆了他的认祖归宗梦,不仅走进了奉化溪口的蒋家祠堂,也真正成为了蒋家门内的孩子。目前他作为蒋家第三代中唯一的男丁,将持之以恒地继续为两岸交流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