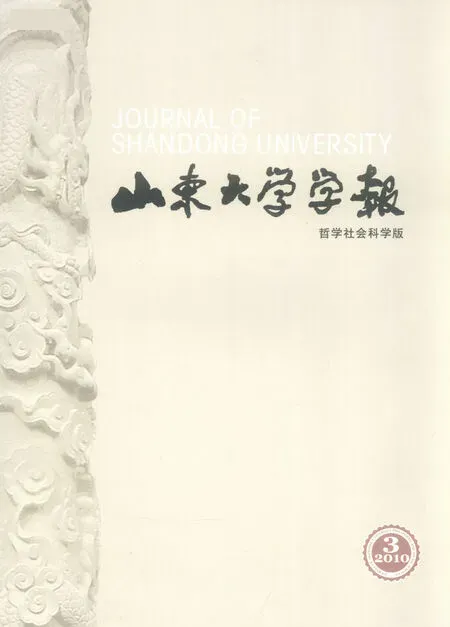异质文化背景下“景”的不同解读
2010-04-12于秋立
于秋立
“景”作为独立的绘画样式,为古今中外画家所青睐,且有着庞大的互动群体。它是人类“自然情结”的体现,是生命品质的文化传达,它以视觉回旋的形式抵达人类精神世界的彼岸。探寻其发展轨迹,由最初作为背景虚像到独立成像,无不体现着人类意识的自觉与审美情感的纯粹过程。中西文化体系是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自然生成,是屹立于人类世界文明之脉的两座高峰。就西方风景画的生成脉络与价值体系而言,画面映像更趋于符合视觉生理需求下的“风景”,中国山水画则是通过“摄情”领会其“景外意”以至呈现“情境”为至高的追求。需指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皆有侧重与嬗变,因而只能在相对的语境下作出论述。
一、风景画与风景化
人与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子母情结。由于地域环境等条件的差异,在探索自然本体奥秘之际,人类不断调整着与自然的罗盘。懵懂中有着繁杂的情感交织与纠缠,意识在提升中得到理性的总结归纳。直面自然,在极无奈的困惑中,西方将其搁置于无限神秘的神龛上,欲用智慧给以解读。中国人却将眼光从天国降至人间,悉心梳理着与自然的内在情愫,不企求认识的“绝对清晰”,以模糊性求得“适度”,因而,同体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最终形成“天人合一”的认知理念。这缕缕情丝聚合化作一股源泉,便以文化方式将其显现。
风景画在西方可追溯到中世纪,是西方自然观映照下的智慧结晶,是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是画家笔下思想情感的物化。风景画自肇始之日便致力于对客体美的发现,重在关注自然与人的直接具体的生存关系。就西方画坛格局而言,风景画终究未能成为主流样式,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人物画可传递更多的信息,但人与自然彼此对立相隔的理念制约了这一艺术样式的发展确是不争的事实。与西方风景画对应的中国山水画,却以别样的面容展现出东方奇妙的认知观与文化价值观。较之人物、花卉科,山水画因受造型的钳制较少,更易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因为审美情趣的飘移性极大,所以利于在更大空间上抒发其理想情怀。以自然为静养之源,蕴蓄林泉之意,为它的哲学理念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便是最佳的载体。风景画与山水画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它的生成过程中,一个滞于“观”一个进入“返观”,各自的智慧萦绕着不同的诉求路线升成,传达出中西认知客观世界相异价值取向下各自的文化符号。映物过滤的“单一”与“复杂”两种体式的结构性差异,使景的承载有着质的区别。在此意义上讲,将两种绘画样式称作“风景画”与“风景化”更贴切不过。
二、镜像与意象
毕德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奠定了西式哲学的基调,其宇宙观沿着辩证逻辑方向一路前行,其间虽有局部微妙转换与倾斜,但人、自然界、宇宙本原的三体并列的基本格局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誓将客观世界进行无穷尽的撕裂与逻辑解构,充分彰显人的智慧与力量,主导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始终环绕人与自然二位一体作俯察内省。因而,西方“风景画”以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为依托搭建起审美价值平台,艺术家把对外在世界美的精确完美的表达当作履行上帝的使命。他们在造物主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前被震撼了,画家成为大自然的歌手,为之讴歌礼赞,力争再现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视觉真实,以“镜像”方式呈物。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渊源是“道”、“玄”的锲入,秉承求“心”略“物”的认知方式,寻“道”体现着中国人对自然界整体观照的理念。这一认知方式不是注重思辨的抽象演绎,而是带有感情色彩的直观感受,是“意象”的陈述。宗白华先生有此论述:“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在感知角色上,西方是人自身的觉醒,东方是人与人化自然的联动觉悟,它涉及到东西方思维模式及认知价值体系。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的推进左右着绘画艺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引入透视、解剖与光谱分析,强化图像的真实感,向着致知客观世界的目标迈进成为时尚。中国人则秉持中庸之态,对美的感知有一个“度”的节制,他不会舍弃整体而滞于某一侧面作永久地停留。宋元以降,以文人画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绘画强化了它与人文学科的结合,逐步融合文学、诗词、歌赋、玄理等非造型因素,极大地削弱了画面的自然主义倾向,摆脱了单一视觉的局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结果是中国传统绘画已不再是单纯的绘画,而成为一种讲求才学修养的综合载体。这种民族审美趋向逐渐取得感官的认可,继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不可否认,相异的自然观所创造的经典艺术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的发展。
三、悦目与熨心
风景画与山水画都是画家借自然为介质,以实现主体精神逾越的文化活动,是情感世界的主观投射。达·芬奇曾言:“实践永远应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上,透视学就是正确的向导和门径,没有它,在绘画上就一事无成。”康斯泰勃又言:“风景画家必须怀着一颗恭顺自然的心灵在田野里散步,他必须以科学家那种严肃认真和专心致志的态度来研究自然。”以记录一个“瞬间”的视觉模拟图像,定格于与神性美的对接,求得刹那间的永恒是西方风景画家的至高追求,深层涌动着的是主导其思维定势的科学精神。而中国山水画却是另一番景象,明代唐志契有言:“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并非亦步亦趋追随特定范畴内的物象,心中涤荡大千世界的鲜活气象,以求得人与自然无隙的契合,广袤无垠个体更易消融其间。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旨在抒写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为此,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将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感受,与自己的体验认知相融合,酝酿为胸中意象,抒发为画面情景。黄宾虹一生追随着自然之美,笔端描绘出的却是无具体指向的“心中山水”。通过意象之象追求与营造美的意境,导引人们以舒缓的节拍进入佳境,细细品味道之无限,渐渐化入宇宙万物之中。潘天寿先生:“静之,深之,远之!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真为至美也!”宇宙的无限与永恒,将中国山水画导向天地自然的宏伟之美的追求。正是这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性思维突破了时空的桎梏,使山水画艺术达到“略物”——“至道”的高度。抽象的“线”与具象的“面”,“形”绝对静止与律动,生理视觉影像图式与突破有限达到无限之境界,风景画的“悦目”与山水画的“熨心”,谱写了一部诠释、解读与认识客观世界的永恒诗篇。
相异的理念设定了两条平行的路向,“风景”、“情境”作为人类精神智慧的使者,是人类情感世界文化印记,它们皆发出各自的光芒,照耀着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历史征程。在这一意义上讲,虽呈现的视觉面目各异,其文化价值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老人在不同时段会眷顾特定的区域,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则。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自不待言,其灿烂辉煌的历史亦有目共睹,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却毋庸讳言,这自然波及到绘画领域,一座高峰似乎被阴霾所遮蔽。此起彼伏的“拍卖会”屡屡炒出佳绩,遮掩不了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与虚空。当下,应客观公允地审视中国山水画的文化价值,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擎起中国文化精神这一面旗帜。路漫漫其修远兮!正是伴随着人性的觉醒,催化了人的精神世界向更高、更深层面递进。各有灵苗各自探,方使得文化艺术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相信,只要人类智慧存在,解读自然的文化帷幕就不会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