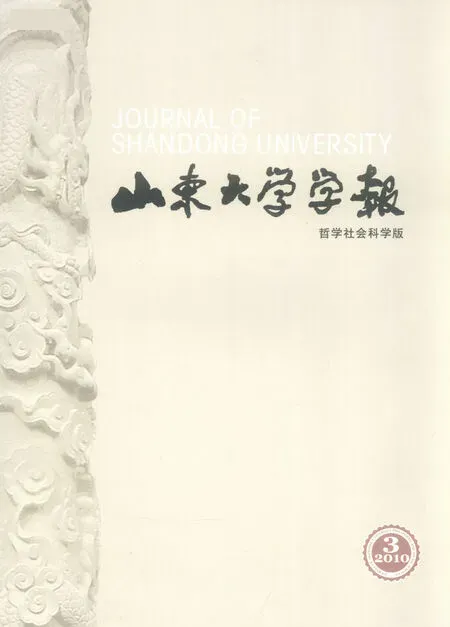论造物艺术中“动感”形式的存在基础
2010-04-12刘雁
刘 雁
从造物艺术的种种形式中,我们总可以感受到“动感”的存在,并且丰富多彩、历久而弥新。而为什么“动感”形式会生存、延续并绚丽多姿?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人们能够感知“动感”的形式乃至主动追求并创造这种奇幻的艺术现象?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讨论,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造物艺术生命活力的根本问题,也是寻求艺术对人类生活意义的必要内容。
一、生理之因:感官经验的认知与表达
在人自始至终的认知活动过程中,生理活动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是“动感”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首要条件,也是“动感”现象得以被人感知并存在的先决条件。在这里,“生理”并不是简单的器官反应,心理感受活动也是生理过程的一部分。
1.生理中的“刺激—反应”。人借助“感觉”来感知“动感”的属性,进而对其产生更高级、更复杂的心理认知。当具有“动感”的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就会刺激感觉细胞,在感觉器官内引起一定量的物理或化学变化。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刺激 -反射引起的,特别是视觉的反应功能,是造物艺术所必须的生理机制。那么,“动感”是怎么引起人的感觉的“注意”呢?这里我们主要从“光”、“力”这两种影响“动感”形式的物质进行探讨。
首先,“光”的刺激作用使视觉感受到运动。“光”是“动感”形成的条件之一。人类的视觉系统对光流是非常敏感的,“Schiff论述的光流的‘逼进’发射作用以及 Lee论述的光流平稳作用表明了这种敏感性。光流理解的基本输入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视觉场,这个视觉场可以是一个矢量场,每一个矢量表示一个实际点的图象光阵位置的瞬时变化。按照这种理解,光流就是一个瞬时速度场,视场上的每一点赋予一个二维‘网膜速度’,即该点穿过视场的运动速度。速度场的变化,使人的视觉系统感觉到平滑连续的运动,从而认知了运动物体。”①章明:《视觉认知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96页。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看到斑驳摇晃的树影,便会切身体会到“光”在我们感知“动感”时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光”也是产生颜色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色彩的色相、明度、艳度的多姿多彩以及冷暖、面积等方面的对比作用而形成的“动感”现象比比皆是。如在漆器艺术中,高饱和度的红色与黑色的强烈对比,给视觉以刺激,引起视觉的紧张兴奋,从而产生更富有动感的冲击力。“光”对于引起视觉反应发挥了根本性作用,这是我们“看”到事物“动感”所必须的硬性条件。
其次,“力”的生理刺激推动了“动感”的形成。不管是客观物理的“力”,还是“视觉张力”,还是由物理力转向的“心理力”,都是客观对象给人的一种强烈倾向性的“力”的刺激,从而使人们感知到了“动感”的方向、强度、速度等因素。
对于客观真实运动中“力”的生理感应,是视觉连同动觉、平衡觉等感觉的综合作用完成的。视觉能够感知到真实运动中物理力的存在,主要是当运动通过视网膜,对视觉细胞的刺激引起的。视网膜上靠近中心凹的圆锥细胞,主要是对光线、色彩、形状的刺激敏感;而在视网膜外周的圆柱细胞则主要对运动相当敏感。虽然身旁一闪而过的事物,我们没有看清楚它的具体形象,但我们能感觉到运动的存在及速度等。对于太快或太慢的运动感知,我们不能单靠感官机能,而更多地是依靠经验和记忆,“间接”或“推理”运动的存在。此外,还有其他感觉的作用。比如,当人们触摸到流淌的水或者光滑的平面时,会产生顺畅流动的感觉;如果摸到粗糙坚硬的表面,则很少会出现“动感”的感觉。这也说明,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长时期劳动,积累了触摸经验,人的手同人的视觉、大脑一起,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了一种机能复杂的、能进行复合分析的感觉器官系统。
然而,在造物艺术中,很多艺术形式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是相对静止不动的。那么,这其中的“力”又是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的呢?“力”的能量是如何聚集和释放的呢?在西方的艺术心理学中,是通过视知觉引起的心理反应作用来认识的。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认为是一种具有趋向性的视知觉“张力”,知觉对象是“力的式样”,这种视觉张力是生理活动的心理对应物,是一个观看后的“刺激 -反应”过程。“我们万万不能把‘刺激’想象成一种把一静止式样极其温和地印在一种被动的媒质上面的活动,所谓‘刺激’,实则是用某种冲力在一块顽强抗拒的媒质上面猛刺一针的活动。”①[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567页。阿恩海姆认为,物理世界、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本质上都是力的作用;并且推动我们自己情感活动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普遍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美学中的“风骨”、“气骨”等,也认为是体现了一定的“力”的存在和作用。尚气之美其本质也在于力的美,而这力的源泉又在于动。中国艺术“气”的世界,同样也是力的世界、动的世界。
各种感觉是认知的基础。“人们所做的‘感觉剥夺’的试验证明,当视觉、听觉、触觉和幻觉仅仅是一些不成型的刺激时——眼睛看到的只是一团混乱的光线照射,耳朵听到的只是连续不停的嗡嗡声——人的全部心理功能便呈紊乱状态,他的社会调节、平衡能力和思维能力均会受到极大的损害。”②[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4页。因此,人类生理感官的“刺激 -反应”对于“动感”的认知是最基本的条件。
2.生理与心理的“呼应”。在造物艺术中,对于“动感”事物的感知和创作,最终的目的都是器物与人的和谐、道与器的统一,使心理情感在器物中得以表达和释放。正因为“动感”所引起心理的波动,是客观事物属性的心理认同,生理方面的反应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情感才能借助于客观形式进行有效表达。这也是心物关系的对应理论。
其一,西方“格式塔”的“异质同构”理论。在西方,格式塔心理学派用“异质同构”理论来解释客观事物与人的知觉与情感的同构性。他们认为,“作为观照对象的客体总是具有一定的物理结构的,如下垂的杨柳,奔腾的海潮,屹立的山峰,这些结构分别呈现出一种物理结构的力场,或重力,或引力,或升腾的力,或下潜的力等。而在人的大脑中也存在一个相应的具有场的属性的系统,即大脑皮层细胞的兴奋、抑制过程,体现为一种生理性的力。后来的科学证实,这种力是存在的,是由大脑生物电流引起的;而这种生物性的力又直接与人的心理活动的力,即知觉力联系着,表现为一种心理的运动。这样以来,客体物理性的张力结构,大脑中的生物电力场,心理活动过程中的知觉场就发生相对应、相感应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叫异质同构。”③史风华:《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60-161页。这个理论同样说明:心和物都具有同样的格式塔的性质,都是一个相关的有组织的整体,它不是部分之和,而部分也不含有整体的特性。视知觉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审美经验的形成,认为“在外部事物、艺术式样、人的知觉组织活动以及内在情感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统一,它们都是力的作用模式,而一旦这几个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 (异质同构),就能激起审美经验。在他看来,事物的运动或形体结构本身与人的心理 -生理结构有相似之处,因此它们本身就是表现。”④史风华:《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研究》,第 161-162页。比如,风中飞动的战旗,迎风迅速飘动的旗的形象和被风吹动的呼呼声,传达了一种与人们战斗的激昂士气相吻合的结构特征。这样,外部的表现形态和人内心的深层情感达到异质同构,从而让人产生共鸣。
西方理论学者对形式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统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物我统一”境界,只不过他们运用了“力场”、“异质同构”等理论来解释了“物理 -生理 -心理”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审美心理结构及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感性显现”和揭示艺术创造和观赏的本质。
其二,中国的“物我合一”理论。中国古代美学在总结心物对应关系时,很多时候采用“体悟”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艺术体悟式审美思维的过程大体可分为感觉、心觉、神思、兴会这样几个既互相重叠、融合又有一定距离、区别的层次。”①彭吉象:《中国艺术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540页。这种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等特点,而且更是从“感”、从“心”出发,去“心物交会”、去“神与物游”、去“物我合一”。西方心理学中所说的“异质同构”,虽然与中国的“物我合一”有几分相似,但远不如中国美学所阐释的直接、精妙、贴切。
中国古人将“心”作为感觉和思维的器官,不是从生理、心理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所看所听,而是从情感出发,认为一切皆由心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梁]刘勰:《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138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心理是与外在的感觉呼应,生理与心理交会,从而将审美对象放在心象中去感觉、体验、联想,达到心领神会、物我交融。
对于具有“动感”的设计物的创作过程来说,人们首先“看到”客观世界所存在的运动物体,刺激了我们的视觉生理反应。这其中所展现出来的事物形体弯直曲折的线条或者整体所体现的刚柔强弱的气势,给人心灵上一种震动,从而触发创作的灵感,以表达当时的心理过程和心境。对于具有“动感”作品的观看,观赏者透过形式达到了心理、情感的共鸣,进入到设计者所创造的境界而受到感染。例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漆棺上的彩绘云气纹及瑞兽舞蹈画面,显示出飞速流动、飘逸和奔放不拘的形态与精神气质。设计者将平时对所见云气飘动的感受、神怪的幻想和楚风的神幻、浪漫与汉风的雄浑、豪放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将所设计的内容和形式形象贴切地展现在观者面前。我们现代人,即使是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也直接被其中的形象所感染和震憾。“在触物的瞬间,虚静澄明的心灵便被激发出巨大的感应力和透视力,有力地把内在空明投射到物象上去,使心中的氤氲之气交合自然的生命之气,于凝神之刻通过内外感觉占据对象的形式 (包括线条、形状、色彩、声音、时空、节奏等等),充分感受形式的亲和,心灵勃然而生感动之情,在激情的熔铸下心灵知觉力直透对象的内部,心与物交会,从而悟得对象的内在意蕴。”③彭吉象:《中国艺术学》,第540页。
“动感”形式的存在,首先以生理之因为起点。正因为动态事物给人感观上的强烈刺激,才使得人们被吸引并且极力去模仿它;正因为“动感”形式极富表现力的特点,才赢得人心理的感动。
二、生活之趣:审美心理的把握与追求
造物艺术也是生活的艺术,趣味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惊喜和愉悦。这是人类特有的情感之一。造物艺术在满足了功能性目的的前提下,趣味性会引导人们去注意、利用,从而装饰他们的设计物,形成丰富的装饰趣味;同时,形制上美学意义的加工,也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因此,“动感”具备并符合人们猎奇和美化的心理需求,从而让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情趣。
1.“多变”引起兴趣。首先,“变化”是“动感”的特征之一,这是引起人们兴趣的因素。寒暑交替、潮起潮落是生命节奏的变化;紧张与放松、兴奋与低沉是生命情绪的变化;形态曲折、色彩比对是生命形式的变化。不论变化给人们的感觉以强烈的刺激,还是循序渐进的刺激,当刺激停止后,便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奇妙的痕迹,让人们再次去注意它、认识它。
《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89页。正是因为大自然神秘奥妙的变化性,才让人们注意到宇宙的博大精深;而变化又是难以预料的,正因为周围世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才引起人们极大的探寻它的兴趣。
观察和现象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们对感兴趣的东西才加以注意,从而使所见到的事物形成了记忆。有了注意,然后才能谈到认识理解。我们平时被迫接受了千百万个信息,唯独对感兴趣的信息能产生重点和特征、“背景”和“前景”。由于对象从形式上造成强有力的刺激,感官便会全力集中于对眼前对象的知觉,通过生理 -心理的感知呼应,对形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组织,从而获得一种关于眼前对象在当时的整体形象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引起人们自身的快乐、紧张甚至恐惧的心理活动,从而加深对事物的印象;同时,这些经验为日后认识同样形式的变化,提供了规律总结的依据,从而创造出类似的形式。
其次,兴趣是人们的心理需求。为了满足自身的愉悦性,人们会更加注意变化中的事物。“趣”,本义是“趣向”。《周易·系辞下》:“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85-86页。“趣”,还有“意向”的意思,如嵇康《琴赋》:“览其旨趣”。可见,“趣”有指向性作用,指向那些有意思的、自己喜欢的、能带来快乐的种种事物。在人们注意到对象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活动有选择的朝向一定的对象,并且集中于此以便更好地观察它。对于“动感”形式的知觉判断相伴随的情绪上的效应,有一种感性的愉快。“这种愉快还不是那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所造成的精神的愉快;而是由于外在对象的结构适应了知觉机制,使其和谐运转时的一种感性水平的愉快。”②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页。这种愉快给人们带来身心的快乐感,从而引起更多的兴趣。生理上的愉快满足是最基本的,心理的满足则是更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之所在。
人们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某种设计的性质。但是,造物艺术更表现出人们对审美情趣的追求,体现着人类的精神性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类既按照物的特性,又按照人的情感需求进行造物。当这两者达到了完美统一的时候,它一方面适合人的使用目的,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另一方面具有某种观赏性,成为一个悦目的形式结构,从而显示出某种美的特性来。
2.审美趣味的追求。审美趣味的追求是人们在造物艺术中除却实用功利性的目的之外,更人性化、更富有情感的审美需求。这种需求促使人们创造更多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产品式样。
愉快的感觉是从生理上出发的,但却是以美感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动感”形式有时是不规则的、零乱的、变幻莫测的,但是,人们对秩序、对规律的追求,则是美的标准之一。在不断发现和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动感对人的刺激、人对动感的兴趣与人对美的秩序的追求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便会试图掌握、支配“动感”中引起快乐的规律,来服务于自己的创作,从而掌握其中引起兴趣的形式规律。
造物作为一种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具有强烈的功能目的性和形式目的性,它在指向某种功能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指向了形式价值和精神价值。既满足人们的实用需要,又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因此,人们在造物之时,形式上不仅仅是模拟自然之物,更多地是利用自己对其中规律的掌握,与器物结合,创造性地构造富有形式规律和意义的产品。例如,商代青铜犀尊、青铜象尊等器物,是对自然形态的表面模拟与更深层寓意的结合,更为有趣地是将动物的躯体形态与器物的功能合而为一,让人觉得生动奇趣,是创造思维的展现。像这类将仿生器形巧妙地与生活实际功能结合的器物还有汉代青铜朱雀灯、宋代孩儿枕等,举不胜举。趣味是造物艺术作品生机和情调的表现,是生活、自然生机的体现,同时也是造物者个人情趣、意味的展现,充满了人性的造化。
造物不仅是一种纯粹物质性的构造和组织行为、追求器物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制作活动,同时也是艺术性和审美性的精神方面的实践活动。造物艺术是生活中的艺术,人们生活中的趣味追求是造物艺术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需要。
三、生命之本:哲学观念的认识与思考
造物艺术中的“动感”形式及其思维方式,是人们哲学辨证思考过程的产物,是对生命情态及意义的探寻和把握。
1.对宇宙的辩证认识。对于引起“动感”的“动”来说,西方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中国学者则从“动”、“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作出了互补又全面的分析。这种辩证的思维模式,我们从成书较早的《周易》中就能发现。《周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89页。老子也认为,对立矛盾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列举出许多形成矛盾统一体的种种现象。《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类论述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思辨性特点。正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辨证逻辑。”④[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3卷数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 2337页。
那么,对于关涉“动感”的“动与静”这一矛盾统一体,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又是如何认为的呢?首先,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为静,阳为动。中国哲学思想论及宇宙以及生命时,必然谈及两种互为涵摄的力量,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有静就有动,有动就有静。其次,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动与静的对立并不是说二者矛盾不可调和,而是说各自有独特的情貌,有区别于对方的特点。宋朱熹说:“盖天地之间有自然之理:凡阳必刚,刚则明,明则易知;凡阴必柔,柔必暗,暗则难测”。再次,二者是相互转化的。所谓刚中寓柔,柔中寓刚,动中寓静,静中藏动。动与静统一于宇宙的和谐整体中,并且随着时空的变换而不断转化着。
对“动感”的研究分析,我们需要用辩证的思考方式来指导。比如,在古代造物艺术中,图形和背景、秩序与繁乱、形体与神采等,都是如何来体现生命的“动感”的?矛盾的两方面又是如何相生相克、互相转化达成和谐统一的?同时,通过这一对矛盾体的学习,找到与其他矛盾体的交融关系。这是艺术的辩证思维,是寻找生命结构与方式的有效方法,也是造物艺术无限丰饶的创作源泉。
2.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闻一多先生在《说舞》一文中总结各地域各时代任何性质的原始舞的目的:“(一)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二)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三)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和 (四)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①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59页。可以说,艺术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首先,对具有“动感”事物的觉察是人们生存本能。“辨物”是中国早期思维中观察能力的培养方式,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方法不是简单地“摹形”。识别方法是早期观察的一个发展形式,其特征或目的就在于确定事物的基本性质。这便是判断一定事物的标志,并且对于特征的把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对事物的确定。特别是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生存空间周围隐藏着许多危险的状况,动态的物体更能够引起人们的警惕,从而判断危险所在。人们对具有“动感”的事物的认识,首先就是对生存环境的分辨和认识,这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其次,“动感”是生命运动轨迹的延续。“动感”说明运动的存在,经历了一定时间,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一根线条、一个形体的存在并不是静止的,他们具有自身存在、发展的生命过程。每种动感也有自己独特的轨迹,极富表现力地展示着生命的精彩。树叶的脉络、螺旋的贝壳、树木的年轮都演示了生命运行的轨迹,它们所表现出来图案的形式感,是动态的形式感,也是生命的形式感。并且生命的运动是有节奏的、连续的、完整的。再次,“动感”是生命力的象征,阐释着生命的意义。中国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生命有机体,不是非生命的机械运动,人们在“动感”的形式中实现着自己的存在和本质意义。动感中所体现的“生动”,是宇宙生机活力的表达。我们从弯转的线条、艳丽的色彩、宏大的气势等等方面,都能感受到设计物的整个生命历程,感受到器物所带给我们的时代意义和精神。
中国古代造物艺术中所呈现的“动感”,将哲学思维融入于日常生活的设计中,注重宇宙生命的有机活力以及生命的运化规律,很自然地将功能与美联系起来,体现了生命的精神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