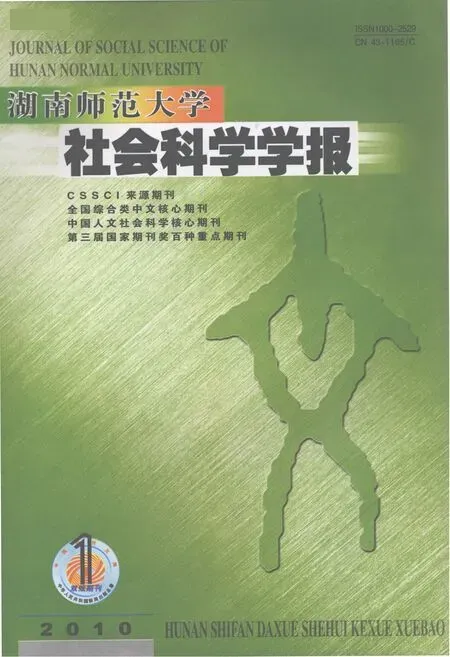“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努力
2010-04-11莫志斌梁志明
莫志斌,梁志明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努力
莫志斌,梁志明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很多且研究很深入。但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语言文化,却鲜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论及。事实上语言文化上的革新,对文化的传播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本身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白话文运动”以及“注音字母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大努力。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使汉语走上了“言文一致”的道路,使我国注音字母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扩大了影响,壮大了声势,并造就了我国教育与文化的新气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语言文化;白话文;注音字母
秦朝以来,中国长期处于相对的自我封闭之中,从来没有面对过强大到需要通过自我审视来对付外来文明的挑战,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也没有认真审视过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挑战,直至中国器物层面(洋务运动)和政治层面(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改革相继失败,以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独裁卖国、倒行逆施,“五四”时期的知识界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探求西方强大和中国衰弱的原因时,才最终追寻到语言文化的因子上,认为“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1]。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他们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或改良,这种通过发展语言文化建设一个全新国家的思想,被胡适等具有敏锐时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并付诸实践,其主要体现在发动“白话文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两大运动为推动中国内部语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做一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
今天一提及“白话文”这一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辈们的努力,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白话文。其实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创造出来的,早已有之,在“五四”以前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就有不少禅门语录、理学语录、信札传奇、诗词曲调、白话小说等白话文学作品。存在了数千年的白话文,为什么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大规模的提倡使用白话文的现象,一跃而发展成“白话文运动”呢?
研究“五四”时期中国语言文化的发展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语言文化发展的原因,充分认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要推动中国语言文体(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样式、体式)由“文言文”向“白话文”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白话文运动”在当时的兴盛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这场大规模地提倡和使用白话文运动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第一,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全国文人士子再不必用文言文埋头苦作八股、试帖了,从而笼罩全国读书士子心理的科举制度不能再替文言文做必要的保障了。此外,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满清帝室的腐朽统治,促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无疑它有利于一切新思想的出现,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后的一封信中说,“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P15),即是明证。第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 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观点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介绍并迅速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不同的时代对语言的应用有不同的要求,由于当时的“时代变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2](P3),想用文言来供给一个骤变时代的需要,“是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2](P3)的。因此,“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不能不改用白话”[3](P457)。并且从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文言文已经严重脱离口语,它的滞后性已经阻碍了汉语的发展。而白话直接记录口语,这种“言文一致”的特性有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可见提倡使用白话文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第三,晚清白话文体的突破性发展。当时黄遵宪就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而梁启超作文更是“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P77),说明他开始有意识地用白话文体写作。然而这一时期大多数人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5](P96),更“不曾(对白话)有一种有意识的鼓吹”[5](P97)。但他们的努力无疑促进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而在此期间在国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5](P242),深感我国语言文化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近代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发展的历史,促使他们更加大胆自信地进行中国语言文化的改革。白话文运动就是在这些因素的激荡中应运而生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展开文言与白话的大辩论,为白话文在理论上奠定了合理的地位。在晚清,白话文在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的努力下就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囿于当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始终都没有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直到1916年,胡适在绮色佳(位于美国纽约上州中部的城市)与杨杏佛、任鸿隽、唐钺三君探讨文学改良之法时,第一次用比较研究法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白话、文言之优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他着重论述了关于“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5](P6)的理论。如果说这只是胡适与学术界友人之间的一种探讨和交流,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的话,那么,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项主张,(八项主张即:“一是,须言之有物;二是,不模仿古人……四是,不作无病呻吟;五是,务去滥调套语;六是,不用典……八是,不避俗字俗语”[6])。则是首次向社会公开提倡白话文,文中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6],并进一步从国内外文学史嬗变的规律中,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6]。《文学改良刍议》遂成为公认的白话文运动的宣言书,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当时,这种观点无异于平地惊雷,引起了全国学界的广泛注意,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在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大辩论。
是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支持胡适的观点,声韵训诂大学家钱玄同更是坦言:“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蒙于胡君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赞同者也。”[7]同时他还认为白话——“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7],将白话文视为书面语(文言文)和口语相统一的重要工具,这种主张进一步推动对白话文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以林纾、章行严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闻风而起,质疑问难。古文学家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声讨白话文的提倡者,但是对于古文为何不当废,他却只能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8]。1919年3月18日他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提到古文不当废的理由之一是:“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2](P172)常乃德认为将文言文“善用之却可以助文章之省简……以常文(白话文)说之,累累数十倍未必能尽且肖,取相类之古典一二语代之足矣”[9]等,这实际上是反对者的一种成见,是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说话的,这种情感性的辩驳多于冷静研究的结果,不足以说明文言不当废。朱经农则主张一种“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的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0]的调和论,对于什么是“文言之精华”“白话之糟粕”,这种“雅俗”论却不能回答。对此,文化激进主义者纷纷撰文进行辩论,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散见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中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刘半农)、《我的白话文学研究》(吴康)、《白话文的价值》(朱希祖)、《文言合一草议》和《怎样做白话文》(傅斯年)等。而1922年,胡先、梅光迪等人在南京所办的《学衡》杂志,矛头直指白话文,其欲恢复文言法统地位的企图,鲁迅一篇《估学衡》就将其破灭了。他们在探讨和辩论的过程中解决了什么是白话和白话文,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如何做白话文等理论性问题,从而为白话文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地位。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5](P41)的理论目标,这种国语“即是中国今日比较的最普通的白话”[10]。
(2)创办一批有宣传力的白话报刊,大力提倡白话文。语言文体的生命在于应用,学术界展开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大辩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1918年1月,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沈君默、刘复、李大钊六人轮流编辑《新青年》时,开始用白话文发表文章。随后,《新青年》统一改用白话刊行,是年,陈独秀等人创办了白话刊物《每周评论》。紧接着,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白话杂志,它们成为白话报刊的成功范例。许多受此影响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白话报刊的创建。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生社的青年学生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地见了曙光一样。”[11]所以他们创办的《新声》白话杂志的本意非常明了,“就是想一方面想请人家引导我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跟着向这条路上来”[11]。1919年5月,白话文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五四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则是“以白话行文的定期刊物,遍于全国”[12](P23)。如《星期评论》、《曙光》、《少年中国》等白话刊物与日俱增。仅湖南长沙各校就出了十多种周刊,它们“都用白话做的,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13]。据统计,当年“这种刊物共有四百多种”[12](P23)。1920 年初《新青年》第七卷三号新刊一览中刊出的白话刊物同样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从中我们知道:在这一期,仅以《新青年》收到的为限,共收到《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妇女》(半月刊)、《建设》(月刊)等白话刊物33种。而这一期《新青年》公布的本志各埠代派处,涉及北京、天津、上海、长沙、武昌、成都等33个城市,多达61个点。仅从白话刊物辐射的地域范围看,如果我们考虑到全国400多种白话刊物,白话文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诚如郑振铎所言:“他们的势力是一天天的更大,更充实;他们的影响是一天天更深入于内地,他们的主张是一天天的更为无数的青年们所信从,所执持着了。”[14](P5)时势所趋,1920 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等重大报刊也渐趋白话化了,成为宣传白话文的重要助手。
(3)创造一种国民需要的白话新文学,努力培养一种白话文的国民心理。当白话文的理论建设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向社会推广白话文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生周祜就提出:“究竟是规定一种白话去统一国语,还是统一之后再用白话呢?”[15]这就涉及到白话文推广的程序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普遍的看法是“自然要从小学校里做起”[16],而盛兆熊等人的观点则是,推广的起点“当在大学,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工学校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里自然要注重白话文字了。小学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16]。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他们都必须建立在有足够的权力保障上,方能实现。以胡适为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推广白话文的关键,“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16]。任鸿也认为“改良文字并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须有几种文学的产品,与世人看看。果真有了真正价值,怕他们不望风景从么”[17]?说明他们已经不单注重到白话文的形式,开始注重到内容的问题了。其实,早在1916年,胡适就开始尝试用白话作诗,1920年完成白话诗集《尝试集》。这期间,沈君默、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做了不少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诗)是统统可以用白话做的”[3](P358)。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四号上发表《狂人日记》,引导人们开始创造白话小说,并且人们还纷纷向散文、戏剧等领域进军。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论在诗、小说、戏曲以及散文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4](P16)。不仅如此,大量的俄国、印度、美国、法国及北欧的文学作品纷纷以白话文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到1921年7月,以郭沫若、郁达夫为首的留日学生组织了“创造社”文艺团体,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青年社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最高的顶点”[14](P8)。创造白话新文学的好处是,一经实践,文言与白话文的优劣、利弊就清楚地显现出来,白话新文学使人的内心对白话文有了深切而又显著的感受,它既满足了国民的心理需要,又给反对白话文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调和论者以致命的一击。以致“从前有许多朋友们素来反对——其实是无目的反对——白话文的,现在居然也往往采用白话做起文章来了”[18]。有的甚至还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健将,这样“社会上做白话文的人,他的数目增加,真有一日千里之势”[18]。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又一重大努力,即是对我国汉字的注音字母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我国的语言文字原本是没有拼音字母的,使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给汉字注音,但这两种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就直音法而言,使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遇到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即便注了音也无法读出来,而反切是一种间接成音的方法。中国文字本来就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19]。人们“认识汉字的时候,既不能由形而得音,也不能因形而得义,只是纯粹的由机械的记忆法记住的”[20](P63)。中国文字的难读难识,既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又“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19]。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时,必须回答怎样解决汉字“难读难识”的问题。
随着语音的发展,“旧日的反切,仍用汉字拼切汉字,很不容易确切,因此各地的读音,歧变百出”[20](P63)。直音和反切注音的方法都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注音作用,为了补救反切的不足之处,晚清的有识之士展开了“切音运动”,提出了反切新法。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在吴敬恒、王照等语音学家的倡导下,次年2月,教育部设立了“读音统一会”,在“切音运动”的基础上“审定八千字之音”[21],采定字母,制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三十九个字母,原来都是中国固有的字,取那笔画极简单的,来做注音的符号”[22]。即用“汉字之旁以代反切之用”[23](P133)。此时,正值袁世凯蓄谋破坏共和之际,直到1918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一号上发表《论注音字母》一文,促使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注音字母问题的热烈讨论。在此之前,由于“文言中单音字太多”[24],极大地限制了注音字母的发展和使用,这一局限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迅速发展而得到改观,胡适就毫不讳言地说:“我四五年前也是很反对这种讨论的,近二三年来觉得中国古文虽不能拼音,但是中国的白话一定是可用字母拼出的。”[25]朱经农在《新青年》第五卷二号上发表《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一文,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吴敬恒进一步研究认为“审定之字虽八千,而同切者可类推,准而用之,无不可取得其音也”[21]。这样的讨论和研究推动了注音字母的发展,五四运动前夕,“北京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已能用注音字母出报”[25]。1918年年底,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搁置了六年之久的注音字母。1919年4月,教育部重新颁布了由吴敬恒审定的注音字母新次序,9月,《国音字典》出版。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类似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所的“讲习所”或“传习所”,大力推广注音字母,小学教材上的汉字生字都渐渐使用注音字母注音。1922年,钱玄同在《高元<国音学>序》中写道,“自从注音字母出世以来,坊间关于国音的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23](P1)。注音字母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注音字母相对于直音和反切注音来说要优越得多,它已明显突破了反切注音法的局限,着眼于从系统上根本解决汉字的拼音问题,是汉字注音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它并不是尽善尽美的。1918年,在《新青年》通信栏目中刊登了朱有《反对注音字母》一文,反对的理由是:“一注音字母不足减省学者的脑力;二注音字母不足改良中国的文字……”[26]说到底是因为这种注音字母仍然是汉字形式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拼音字母,音与字都是汉字形式,无形中增加学者的脑力。提倡注音字母的人开始向纯拼音字母形式方向研究,以图对注音字母进行修正和改进。钱玄同认为“其实大可不必另造新形,采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母”[23](P125)即可,这样我们还可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中获取经验教训。1923年,教育部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中,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方案”。1925年,刘复、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开始从事“罗马字式的注音字母”的研究工作。1928年,南京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定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罗马式的注音字母相对于汉字式的注音字母而言,又是一大进步,因为它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字母之数也减少,能更为准确方便地给汉字注音。由于罗马式的注音字母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它的影响远不及汉字式的注音字母大,但它却成为我国注音字母史上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拼音字母,它和汉字式的注音字母的使用共同构成了注音字母运动,推动了中国注音字母的发展。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努力,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一,就白话文运动讲,白话文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践活动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与推广。在白话与文言的论战中,白话文取得了全面的胜利,1920年10月,白话被称为国语,12月,教育部颁布法令,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实现了以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白话文运动中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5](P41)和“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5](P41)的主张。这就使汉语的发展走上了“言文一致”的道路,即书面语和口语相统一的道路。白话文运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虽文言的势力还是相当的大,并且,文言文的运用,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终究影响在缩小。1925年后,学衡派和甲寅派对白话文运动发起反攻,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第二,就注音字母运动而言,它造就了我国文字史上第一套法定意义的注音字母和真正意义上的拼音字母,在注音字母的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继承了反切注音法的合理部分,使我国的注音字母逐步向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并大胆地把它推向纯字母的方向,直接开启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先声,为新中国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基础。
第三,就社会影响来说。首先,它们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文言文的艰深难读,阻碍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怎样使这种阻滞消失减少?吴敬恒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一文中,对于怎样用最少日力,增长一点知识的问题,说道:“能够当此责任者,惟有拼音”[27]。“这便不能不依赖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最大的功用是:一改良反切,统一读音,二加汉字以读音,叫人容易认识,俾能收拼音文字之效。”[20](P63)白话文因其“浅近平易”、口语化,又利于传播和被大众接受,因而白话在推动教育的发展上的作用也不亚于注音字母,无疑,白话和注音字母为普及我国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有利于新事物新学理的输入,白话这一通俗易懂的文字成为宣传新事物新学理的利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国外带回或引进了新的思想,如实用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德先生”和“赛先生”等等。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传播。宣传白话文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在第六卷五号上就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期《新青年》刊登了18篇文章,共105个页面,其中有八篇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占65个页面,尤见其宣传的力度。再次,它们还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引领了中国文化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型。
[1]陈丹涯,陈独秀.通信[J].新青年,1917,(2):1.
[2]赵家壁,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A].饮冰室文粹[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5]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1):1.
[7]钱玄同,陈独秀.通信[J].新青年,1917,(3):1.
[8]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宜废[N].民国日报(上海),1917-02-08(12).
[9]常乃德,陈独秀.通信[J].新青年,1917,(2):1.
[10]胡适,朱经农.新文字问题之讨论[J].新青年,1918,(8):15.
[11]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生社.欢迎新声[J].新青年,1919,(3):15.
[12]赵家壁,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3]长沙社会面面观(社会调查)[J].新青年,1919,(12):1.
[14]赵家壁,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5]周 祜,钱玄同.文学革命与文法[J].新青年,1917,(2):15.
[16]盛兆熊,胡 适.论文学改革进行的程序[J].新青年,1919,(5):15.
[18]吴 康.我的白话文研究[J].新潮,1920,(3):2.
[19]钱玄同,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新青年,1918,(4):15.
[20]陈文华.注音字母究竟怎样教授[J].中华教育界,1920,(12):10.
[21]吴敬恒,钱玄同.注音字母[J].新青年1918,(3):15.
[22]钱玄同.论注音字母[J].新青年,1918,(1):15.
[23]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4]胡 适,陈独秀.通信[J].新青年,1918,(4):15.
[25]胡 适,朱我农.革新文学与改良文字[J].新青年,1918,(8):15.
[26]朱有画,胡 适.反对注音字母[J].新青年,1918,(10):15.
[27]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J].新青年,1918,(11):15.
(责任编校:文 心)
“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Effort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MO Zhi-bin,LIANG Zhi-m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is a movement of enlightenment,which has an extremely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It not onl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s,but also spreads the Western cultural ideas and achievements of progress.There are a lot of outcome of the“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Research,many of which are deep.However,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culture-the language and culture,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from a historic perspective.In fact,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the innovation has an immeasurable impact on the spread of culture,and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of their own.In this paper,the author wants to talk about“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developed by“Vernacular Movement”and“phonetic alphabet campaign”in these two aspects.Just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aspects,the Chinese language achieved a unity of the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making the China’s phonetic alphabet gradually standardized and systematic.And it expended influence of the“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reated a new atmosphere 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China.
“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language and culture;vernacular;phonetic alphabet
K261.2
A
1000-2529(2010)01-0123-05
2009-09-15
莫志斌(1950-),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志明(1984-),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