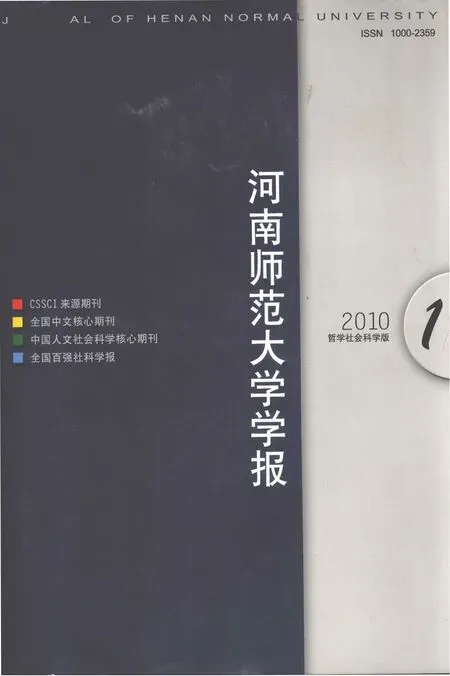近代东南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展成因探析
2010-04-11刘玲
刘 玲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006)
近代东南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展成因探析
刘 玲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006)
东南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在近代更显突出。海洋文明到来后,日趋整体化的世界经济对沿海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拉动,为中国东南沿海发展提供了先机;清政府仍用一贯的内陆文明思维,采取了“闭关”政策,既限制了东南沿海的发展,也使内地失去了发展机会;列强入侵致使东南沿海畸形繁荣,内地发展陷入滞缓,不平衡状况加剧;因得风气之先,更新迅速的思想观念对东南沿海起到了社会总动员的作用,为其长久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东南沿海;内地;不平衡发展;原因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普遍现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再加上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连接,这一问题更显突出。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伴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城市的开放,东南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日渐拉大,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帝国主义是造成不平衡发展的罪魁祸首、不平衡发展属非正常现象”的结论。但笔者考察后发现,形成原因实有多重: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18世纪的中国,已深处海洋文明浪潮旋涡,沿海发展超过内地是势所必然,属正常现象;但是,发展不平衡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则又属非正常现象,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则难辞其咎。此外,社会文化因素,对东南沿海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仅就五口开放后的东南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平衡的宏观原因略陈管见。
一、海洋文明的到来为东南沿海发展提供了先机
所谓“海洋文明”,是指伴随着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以及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航海事件的发生,洲际开始了海洋航线的连接后而崛起的取代亚洲内陆文明的欧洲海洋文明形式,海洋经济成为近代经济的突出标志。
区域发展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时代不同,这些因素作用力的权重有所不同。在内陆文明时期,经常起作用且为主导性作用的常常是政治和军事因素。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往往合而为一,多居于中原腹地和地形险要之地。如,雒邑(洛阳)因是“天下之中”[1]97而受周公重视;西安因地居关中,有“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1]269的优势,可以“阻三面而独守,以一面东制诸侯”[1]1632,而被统治者视为宝地。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刻意经营,使得这些地区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封闭、险要之地因自然环境险恶、交通不便终究没有经济发展的优势。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驾驭自然能力的增强,经济区的拓展不断走向纵深;再加上连年战争使人备受纷扰,战争权威性在不断下降,能安居乐业、水土丰饶之地渐渐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中国唐代以后,之前还被视作偏乡僻壤的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由于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人气聚集地,尽管并非军事重镇,但经济地位的上升带动了区域地位的上升,为后来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近代最初开埠的五城市皆有这样的优势。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经济重心南移后辛勤开发,到五口通商前,东南沿海地区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
交通情况对区域发展作用的权重也日趋增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交通网络,在内陆文明下,交通主要依靠的是内陆水网,长江、运河构成了主要的交通连接,所以沿江、沿运河的地方具备了交通便利优势。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政治中心,最为著名的有六大古都,它们都曾相当繁华,但后来差距却很大。如安阳、开封等曾经暄赫一时,但在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后迅速衰落;而南京、杭州这样的古都即使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却依旧繁荣。对比后发现其中原因就在于:后者有着便利的交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撑。在海洋文明到来后,洲际的联系任务由海洋航线执行,沿海处在海外经济影响、辐射和拉动的最前沿,由于有唐以来的发展基础作为铺垫,中国东南沿海具备了与外对接实力,所以,在进入近代后,与外互动,优先发展,势所必然。
一方面,海外市场对中国市场需求强烈:新航路发现后,原来在内陆文明背景下具有地理优势和经商传统从事国际间贸易的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退出交易中介平台,西方商人开始直接与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由于没有中间商的盘剥和中西方物价的差距,中西双方皆在获利丰厚后,还觉得占了大便宜。中国的商品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中国的绫缎杂缯、茶叶、瓷器、糖品果品诸物等,“皆所嗜好”[2],且需求量极大,这些需求和动机成为对东南沿海市场的强大拉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资本向外扩张也蓄势待发:东南沿海由于唐以后丝绸之路由陆上向海上的转移,不断南下移民对江南地区的长期开发,南方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市场得到较好的发育,远比内地发达,近代前的中国市场已呈现出较严重的不平衡性。内地市场的不发达严重制约着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东南数省占全国人口的50%,却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3]。这必然促使商人把争取利润的目光投向海外,对外贸易的愿望非常强烈。在政府禁止的情况下,这种愿望经常以走私的形式来实现,出现“海滨之民,唯利是视,走死地如骛”[4]的现象。“走死地如骛”正说明对外贸易已成为难以抵挡的时代潮流,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已被卷入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的旋涡之中。
中国不平衡发展自古有之,只不过在“内陆文明”时期,表现为北方内陆发展,东南沿海滞后,但是这种局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业已悄然改变。进入近代后,这种改变更加显著,人们的先入为主的审视习惯,再加上与外国列强的入侵时间契合,形成了人们对“沿海发展超过内地属非正常现象”,“帝国主义是罪魁祸首”的强烈反应。
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使东南沿海和内地发展受限
世界市场对中国沿海市场的辐射和拉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市场的互动欲望,已说明国际的交流和开放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如果能顺应形势,以海纳百川的自信对待“外夷”,大开东南沿海的通商门户,与世界接轨,沿海经济定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内陆文明思维依旧,视“闭关锁国”为治国“法宝”。
明代开始禁止民间贸易的海禁,至清代发展为既对民间又对官方的“闭关”: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所有贸易口岸;设立公行垄断对外贸易;限制经营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想尽办法将贸易额降至最低程度,实行非自由贸易政策。在商品经济蓬勃兴起、洲际通道大开、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做法实属不明事理,倒行逆施。其结果不仅使沿海地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更加重了内地的封闭程度,发展更加滞缓。
闭关锁国,是封建统治者在传统内陆文明中心观念支配下为其政治需要所采取的治国政策,根本不考虑商贸之利、民众生存等,对于依赖海洋经济为生的东南沿海商民和地方经济来说,禁海就是断了生计和失去了发展基础。“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又安,明效彰彰耳”[5]。一方面,“闭关”不仅使东南沿海的外贸优势尽失,也使因外贸而兴的其他各业没有了出路。康熙时江苏巡抚慕天颜曾明智地看到,开海禁不仅可“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还可使农工商业都随之勃兴,“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而货贿会通,立可以社贫寡之患”[6],更为重要的是,会进一步刺激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人蓝鼎元曾在其所上《论南洋事宜书》中论及此点:“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清政府的闭关,在使沿海地区的外贸优势丧失的同时,也使内地失去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政府为限制商民入海,发布禁止建造双桅大船的政令,不仅使造船业严重萎缩,对外贸易遭到扼杀,而且使国家的海防能力减弱,对沿海局势失去控制力,危害沿海安全的因素与日俱增,加上沿海之民的铤而走险,沿海地区成了动荡是非之地,经济发展失去了安定前提。
因此,闭关政策危害多多,不仅限制了贸易,贫困了沿海之民和防碍了内地发展,也使国家在消极防御中衰落下去而最终失去了防御能力。
三、列强入侵使中国东南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展加剧
如果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能认清世界大势,主动与外对等交往、贸易的话,中国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东南沿海因所具有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基础也会发展得更加迅猛,与内地的不平衡仍会继续且更加凸显。但是,我们同样也能预测到,随着与外国资本主义互动加强,不断生长的资本主义因素最终会摧毁封建堡垒,内地也会得到充分发展,逐渐赶上沿海,由不平衡走向平衡。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无视海路大通后的世界新格局,陶醉于“天朝上邦”的昨日辉煌之中,把死守国门作为国策,中国的国门被帝国主义用炮火强行打开,自主权和独立性皆丧失。这时的开放,已是非正常的开放;这时的发展,已是畸形、病态的发展。
不可否认,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先进管理模式的引进,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开放城市发展迅速。如上海在开埠前只是僻处海隅的一个小城,由于海禁,其优良海港优势一直无从展示,虽然身处内河航运体系,但由于居于长江末端,作用发挥不大。开埠后,临海位置使其江海交汇优势尽显,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宁波在鸦片战争前也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城市,但战后,在大规模的外洋商品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发展迅猛,至19、20世纪之交,各种商业行业多达80余种,从业人员至二三十万人;厦门由于是国内贸易的中转港,“商贾辐辏”,“市肆日闹”,商业繁荣之貌日显,在开埠以后,西方洋行接踵而至,促发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的蓬勃兴起,其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势头非常强劲。广州因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口岸,其外贸地位在鸦片战争后虽被上海赶超,但它所具有的出口香港的华南产品的“采购收集”站和进口产品的“分配传播”器的作用,无其他口岸可以替代[7]16-17。
但是,这种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繁荣只是一种表象,缺乏实际根基。因为当时东南沿海是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主权丧失,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下被强行牵曳进国际市场的,列强利用手中握有的种种特权,与中国进行不等价交换。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极强的买办性,所有商业活动皆唯帝国主义的马首是瞻,收购和出售皆依帝国主义的需要展开,面对帝国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打压,常常无招架之力。在加上封建根基依然坚固,内地厘金沉重,交通闭塞等,口岸较多地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传动和整合,东南沿海的经济一开始即走上了受制、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怪圈。
因商而兴是近代沿海经济繁荣的通则,但是,一个地方长久的发展和繁荣,必须有工业的支撑。在正常情况下,商业的发展会启动和诱发工业的发展,马克思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曾指出:“商品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影响,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8]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情形,则使西方资本主义的产品倾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阻碍和抑制的作用,因而,开埠通商后,中国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大量转移,相反导致了众多的民族手工业的纷纷破产倒闭。就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上海,工业也极为有限,有美国学者墨菲所言为证:“直到1895年,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9]
由于沿海地区工业没有得到很大发展,近代工业机制品的流通和原料需求对商品市场的开拓作用十分微弱。再加上国内贸易多在五口岸之间进行,沿海开埠城市的内贸是在外贸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内外贸重心的合而为一和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及交通条件的制约,无力支持更多的内外贸中心的形成,上海的崛起、广州的沉沦即是例证,正如马克思所言:“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10]1863年,《北华捷报》对当时上海的地位进行了描述:“从美国和欧洲开往(中国)通商口岸的商船……以及从事沿海和沿江运输的轮船……不论其最终的目的地是哪儿,它都要先开到上海。”[11]这说明,东南沿海的近代市场并没有形成扇形状的辐射的多个内贸市场,而形成了四口岸以上海为龙头的“条状”局面,这种市场格局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力极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些口岸城市与内地一些城市有贸易往来,只是所占比重极小。
总之,开放后的五口,由于与外经济联系密切,商贸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其带有很强的依附性,无法带动内地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虽然引入了现代工业,但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虽然城市繁荣,但是在外贸支撑下的繁荣,这一切都使得沿海五口无力带动内地发展,从而使东南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
四、观念改变对东海沿海的发展起到了社会总动员的作用
由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带动,由于东南沿海长期阻滞的资金流通通道的开通,由于海外压抑已久的商贸需求的释放,东南沿海在门户开放起初,发展能量喷薄涌出,非常迅猛,城市空前繁荣。后来,伴随着一系列沿江城市的开放,资本主义的触角开始由沿江深入内地,得到发展的城市更多。但由于门户开放的被动和有限,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所带来的种种约束,帝国主义的不等价交换和对农产品及工业原料的大肆掠夺,无论是沿江,还是沿海,发展极为脆弱,有些城市繁华一时,但转瞬间陷入萧条,但不管怎样沉浮,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始终趋前,直至当代依然如此,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思想观念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特有的精神和理念,有人总结为“拼搏精神,不向自然环境屈服;冒险精神,向海外发展;商业意识,受土地束缚较松;边缘意识,不在传统儒学中心;依赖科技,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7]27等。就近代而言,在接受外来新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突破传统、动摇封建根基的新思想最为重要,它对东南沿海人们观念、价值观甚至风尚的改变起到了社会总动员的作用,构成了长久发展的社会基础和软实力。
行为改变,思想观念要先行。传统思想的变化要由现代新思想来突破。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在五口建立教堂,设立医院,兴办学校,出版报刊,翻译书籍,通过多种形式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这些极大刺激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19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伟烈亚力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一家近代出版机构。1862年,福州的罗札里奥·马卡乐出版公司, 1869年,宁波的传教士会出版社和三圣教会出版社等相继建立,上海则更多。据统计,从1843年至1860年,西方人在五个通商城市和香港设立的出版机构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12]98,创办刊物也非常之多。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西人在华先后创办中外文报刊200种左右[13]。教会学校的设立更是如火如荼,著名的有上海徐汇中学、中西书院、圣约翰大学以及宁波女塾、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广州岭南大学、厦门毓德大学等等,据统计,1876年前后,教会学校多达800所[14]。这些学校皆采取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其中很多学校后来成为中国知名大学,学校是新思想传播必不可少的载体。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强调图书的公共教育功能,向社会开放,因而传播效果明显。1847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的“天主堂藏书楼”、1851年的上海图书馆和1857年建立的东方图书馆都是相当有名的图书馆。
正是这些宣传教育机构的广泛设置,加速了东南沿海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和接受,对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东南沿海的这种西方文化的先触优势造就了沿海人民的创新、时尚的近代意识和观念,与内地陈腐、守旧的封建观念形成极大反差。有人曾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做了这样的阶段划分:“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变化仅限于东南沿海五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三十年,变化扩大到南北沿海及长江一线;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变化才逐步向内地城镇推进。而广大的同地农村,则到本世纪(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根本的变化。”[15]可见,内地较沿海对新思想的接受晚了几十年,而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上落伍时间则更长。
西方文化在东南沿海的广泛传播,促使了新事物在这里出现,新思想在这里酝酿,新人物在这里产生,近代鼓吹变化、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多产生于东南五口及所在地区,如郑观应、王韬、胡礼垣、薛福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7]12。
如果说,对新思想的接受仅能在思想家的身上得到确切的考察,那么,人们的理念、价值观的改变则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得到检验。东南沿海之民思想观念有诸多改变,下面仅以其最具普遍意义方面做一例举说明,即重“商”弃“农”和崇“洋”尚“奢”。
东南沿海“重商”理念在明清之际即已萌发,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下,人们更加倾向商业,弃农、弃工而经商人员剧增。如上海,出现了“农工争骛于洋场,而乡闾之耕作稀”的状况[16]。相伴“重商抑农”而生的是对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的颠覆,以王韬对上海所见现象的记述为证:“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目中所见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盖贤愚杂糅,品类不一,天资稍厚者,日变浇薄,利之所在,则不知友谊矣。”[12]241这说明,在开埠城市,传统的“信义”价值观念已被商业性的功利至上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东南沿海由于得风气之先,人们崇“洋”学“洋”,蔚然成风。1869年,英国人呤俐对广州姑娘的欧化穿着做过这样记载:“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17]西方的很多奇技淫巧及前所未见、价廉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有载“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18],且“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19]。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因“洋”流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不再以“俭”为荣,以“奢”为耻,甚至有人公开为“奢”高唱赞歌,写文论说“奢华”的进步性、合理性:“假设一邦之富人食必糙米,服必布衣,用必粗恶之具,则营业工匠自食其力之人又何以自鬻其技能?安能各臻于富乎?民不能自富,国又何由富乎?”“唯奢侈之人爱求精巧之物,是以鼓励皆精巧,又为分财与人之道也。”[20]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改变本身,而在于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深层内涵:第一,重“商”弃“农”、商业性的功利至上的价值观念对传统的“信义”价值观的取代,是“海洋文明”到来后的必然结果,它对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对“洋”货的崇尚、对新事物的接受,有利于解放思想,冲击传统迂腐观念,对不甘“落伍”的心态的生成有促发作用。同时,大量西方工业品的涌入,一方面,势必造成中国相关手工业的衰落,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们对相关产业认识上了一个层次,眼界提升,对他们未来的创业定位和水平产生影响,无疑对产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追求“奢华”,说明消费已不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是要体现自我价值,证明自已的能力;反过来,要满足“奢华”欲求,就必须不断创业,不断努力,这种对“奢华”的追求有利于培育不知满足,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M].四部丛刊本.
[3]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61.
[4]王世懋.策枢: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六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4864.
[6]慕天颜.清朝经世文集:卷二六·请开海禁疏[M].
[7]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372.
[9]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4.
[10]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8.
[11]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41.
[1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郑大华,彭平一.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22.
[1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37.
[15]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73.
[16]熊月之.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34.
[17]呤俐.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
[18]王国平,周新国.江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43.
[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7:170.
[20]理财辩[N].申报,1874212201.
[责任编辑 孙景峰]
K251
A
1000-2359(2010)01-201662-05
刘玲(1964-),女,山东临沭人,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历史成因研究”(08SJD7700012)
200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