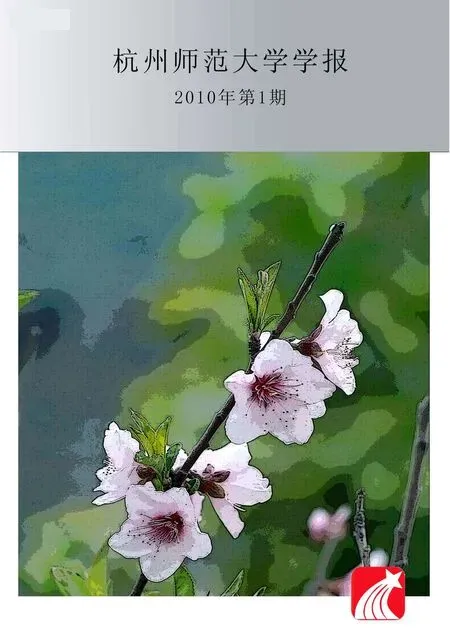新书刊
——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之一
2010-04-11周立民
周立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 巴金研究会,上海 200040)
新书刊
——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之一
周立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 巴金研究会,上海 200040)
所谓“五四意象”是指能够体现出“五四”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元素。在巴金的小说《家》中,“新书刊”就是这样的意象之一。作为能够体现新文化运动与旧的文化与传统决裂的新书刊,承载着作者和五四时代所赋予的很多启蒙的目标和任务。在此基础上,巴金作品中的“新书刊”还体现着极强的作者个人记忆和书写中的选择性,由此也透露出作者个人信仰的诸多信息。
巴金;五四;“五四意象”;新书刊
一 所谓“五四意象”
1957年——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一年应当是“文学革命”的40周年——张爱玲写了一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如张爱玲的惯有姿态,这是一篇解构“五四”意识、带着反讽意味的小说,它以1936年的眼光来叙述1924年的事情。*非常有意思,这个时间跟巴金创作体现“五四”意识最强烈的小说“激流”中的《春》(创作于1936—1938年)差不多,而1924年恰恰是《秋》之中故事结束(1923年)后的一年。在这篇以罗文涛的恋爱和婚姻为内容的小说中,张爱玲调动了很多带有标志性的事物以凸显出“五四”时代特点。比如小说中两对男女的身份,两位女郎是“女校高材生”,“那时候的前进妇女正是纷纷的大批涌进初小、高小。”可见作者并非信笔乱写,连称呼都有时代气息:“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女学生”是五四时期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她们的装束都有自己的特点:“她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因为眼睛并不近视。这是一九二四年,眼镜正入时。交际明星戴眼镜,新嫁娘戴蓝眼镜,连咸肉庄上的妓女都戴眼镜,冒充女学生。”一切都够得上“新潮”“摩登”,尽管最后一句已经露出作者对此的冷嘲。两位男青年是学校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集中了相当一部分文化人。还有不可或缺的,他们都是文艺青年,“又都对新诗感兴趣,曾经合印过一本诗集,因此常常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自称‘湖上诗人’……”所以,哪怕是出游也带着新出的书刊,常常“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这样的男女在一起,讲“恋爱”——张爱玲写道:“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1]——反对“包办婚姻”……不管以后的故事走向如何,小说中的这些元素几乎像符号标示着“五四”风习。我把这些带有鲜明特征性的事物称为“五四意象”,如上述的女学生、文艺青年、新书刊、自由恋爱等等。
所谓“五四意象”主要是指作品通过对象化的叙述所塑造出来的体现五四时代话语特征的事物、景象和人物形象。它们是作者个人记忆与时代共名的某种混合、过渡或转换。一方面这是作家五四记忆的转化,带有个人性;另一方面这些“意象”的创造又受制于整个作品的叙述需要,为了起到“还原”历史现场的作用,这些意象带有标志性和符号性,要能够体现出人们所熟知的“五四”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与作者个人性之间交织所构成的意象其中有很多可以阐说的微妙之处,这个微妙也体现了作家在强大的共名之下对“五四”的独特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五四意象”是指能够体现出“五四”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元素,并非是指“五四”时期最早出现的事物或者专属于“五四”的事物,即如女学生并非是1917—1923年的专有事物,但作为“五四意象”的女学生则集中体现了女性解放和个体独立,是女权意识得到社会关注的形象;这也并非说在以后它就不可能出现,或者没有体现出这些意识,而是说它体现了五四时代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事物,也体现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由此才把这个“意象”与“五四”共同进行命名。
“五四意象”实际上是作家对于“五四”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叙述,是对象化的叙述,即作家能够把他们认为有特征的事物和元素通过虚构等叙述手段的组合,以还原出“五四”的历史氛围和时代主题。它所叙述出来的这些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以选择记忆的方式折射出作者对“五四”的认识、基本态度。
二 新书刊:启蒙的灵药
以“五四”风暴对古老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的冲击为主题的“激流三部曲”,应当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最为集中的一部对“五四”叙述的小说,巴金的其他小说虽然不直接以“五四”时代的人和事为内容,但所呈现出的“五四”余绪和“五四”意象同样是对“五四”的另外一种书写。
通过“五四意象”,巴金较为集中地表达出五四时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和价值观念。但这些意象又不是镜子般被动地将这些命题和观念简单地折射出来,它体现了作者记忆的选择性,在他的选择中,还有对记忆的修改、变形,由此实际涉及到作者在潜意识中对于“五四”的设计、预想、阐释,它们都集中在这个“意象”上。
书刊经常作为小说中的“道具”来说明主人性格、心理或者暗示某种情节发展,如沈从文在《八骏图》中写到“教授甲”的房间布置时,提到这样的两部书很说明主人的思想趣味:“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2]茅盾在《子夜》中为吴老太爷安排的经典道具中就有《太上感应篇》。这里的书是静态的,起到的是“说明”作用,而作为意象的新书刊,特别是它们在巴金的叙述中所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仅是静态的说明,而还要参与到情节和人物内心的发展中。如《家》中引用屠格涅夫《前夜》的语句对大家庭中年轻人内心的唤醒。觉慧念出了《前夜》中非常能够表达五四青年思想觉醒和独立意识的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小说接下来描述了它对这个家庭中青年们振聋发聩般的冲击:“一股热气在他底身体内直往上冲,他不觉得激动得连手也战抖起来,他不能够再念下去。他便把书合上,端起茶碗大大喝了几口。”到后来在打算盘的觉新也停了下来。“一个莫名的恐怖开始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飞翔,渐渐地压下来。一个共同的感觉苦恼着这四个环境不同的人。”他们的内心中是这样的声音在呐喊:“这样的社会,才有这样的人生!”“这种生活简直是在浪费青春,是在浪费生命了。”*巴金《家》,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第109—110页,因为巴金的众多小说曾经有过数次修改,本文在讨论时多以初版本为依据,以《全集》定稿本为参照,必要时并对两个版本的差异略作说明。
这种手法当然不是巴金的创造,*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就曾有这样的情节,如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中《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个剧本就参与了情节的发展,启示着人物的内心情感。在西方小说中,这样的读物常常是由《圣经》来承担的。只不过巴金惯用它来叙述新文化新思潮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冲击和启蒙。从巴金个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家庭中,他们那一代人接受不容于传统的新思想新文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书刊,书刊可以超越学校教育具体条件的阻隔到达每个心灵中去,特别是在整个社会风气尚没有足够接受新思想的时候,书刊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秘密渠道有效地流通(正所谓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之乐)。从生活到小说,出现在巴金作品中的新书刊及其带给人物的精神震动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新书刊是启蒙思想的载体,它承担着启蒙的重任。而当作家描写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转变或者接受新的思想时所采用的手法,除了现实对人物的刺激之外,有一大半是因为阅读了“革命”书刊,所以书刊在巴金小说中的意义早已超出一个道具的分量;除此之外,书刊的内容还暗示了人物的具体信仰,传达着巴金对自己信仰的看法。
《家》中以新书刊的影响直接写出了“五四”带给高家兄弟的精神震动,小说中的描述与巴金自己的成长经历几乎一般无二:
于是“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底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底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他读了,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般点燃了他们弟兄底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等都接连到了他们底手里。旧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底前身《青年杂志》也被书铺里的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检了出来送到他们手中。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着这些书报,甚至于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3](P.49)
在这段描述中,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五四运动乃至后来的六三运动,这些学生和工人等的政治、社会运动对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新文化书刊中最有影响力者还是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青年》集团”的报刊。*湖南文化书社曾统计自1920年9月9日至10月20日一个半月间杂志销售情况,《新青年》独占鳌头售出165/155册(两期);《新潮》,25册;《改造》,30册;《劳动界》,130册(与书社的读者多为工、农有关);《少年世界》,15册;《民铎》,35册。见《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3页。它们所带给青年的影响恰如文字所描述“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这样的描述也并非小说家言,而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形的,尚在湖南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4]当时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的青年们致信《新青年》所表达的心情与巴金笔下人物的心情也是一致的:“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都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5]
可以说《新青年》的影子和声音充满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每一处,它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最重要标志物。如为《新青年》建立广泛社会影响的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和一些观点,吴虞《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观点都直接呈现在小说中并成为鼓舞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动力。不是将个人的享乐建立在他人和家族身上,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人生的幸福和个人的价值。在“五四”新风下成长的青年觉慧、觉民、琴都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这种意识,当琴的母亲有不同意她上学堂的想法时,琴在无助中读的是《新青年》,这上面所刊载的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中的话鼓舞了她:
她无聊赖地解下裙子往床上一抛,走到书桌前面,先拨了桌上锡灯里的灯芯,便坐在书桌前面的凳子上。灯光突然明亮了,书桌上的《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底眼里,她随手把这本书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底剧本《娜拉》。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眼前顿时明亮了。她恍然地明白她底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总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想到这里,一切的悲哀都没有了……[3](PP.40-41)
在这段描述中,《新青年》暗合了“灯”的意象,发出了引导琴走出黑暗的蒙昧之后的精神启蒙之光。“要努力做一个人”是对琴的最重要鼓励,也成为她反抗旧习俗的思想资源,在以后不断地给她带来力量。后来,因为剪发问题,琴要与习俗抗争,在许倩如的鼓励下,又是易卜生戏剧的启蒙之光坚定了她捍卫个人独立、拒绝别人操纵自己命运的决心:“我不走那条路,我不做人家底玩物。我要做一个人,一个和男子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3](P.254)而当她与觉民之间的婚事受到长辈干涉晦暗不明时,她仍是用《易卜生集》来鼓励自己(“……她大概是在那里面寻找鼓舞之泉源罢”),[3](P.341)这次读的是《国民之敌》。人所周知,这个剧本中有一句话是五四时期新青年反抗旧传统时最受鼓舞的话:“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新青年们往往处在一种强势的社会力量包围中,未免有着和之者寡的孤单感,而这出戏却告诉他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此时给他们以支持的是“五四”时期的“个人”观念,而《新青年》和易卜生又是这种观念的传播媒介。对此,胡适在《易卜生主义》*觉新就读过这篇文章:“而他只是一个胡适主义者,并且连胡适底《易卜生主义》一篇文章,他也觉得议论有点过火。”(见巴金《家》,《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9页)中认为,易卜生的两句话蕴涵着非常有启示性的道理:“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认为这是“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这主要是为发展“个人的个性”、“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6]所以,小说中有很多要走自己路的话,特别是在《家》的觉民身上,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个人主义。
吴虞和他那篇名文《吃人与礼教》也在书中成为激励青年人与虚伪的礼教和传统的习俗相抗争的一个思想武器。在《家》的第三章便提起吴虞,他不但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而存在,而且还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下学期我们底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面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吴又陵!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巴金《家》,《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第21页。在《全集》本这句后面,琴接话中又这样补充道:“吴又陵,我知道,就是那个‘只手打孔家店’的人。你们真幸福!”(见《全集》第1卷第13页)这是1950年代编辑《巴金文集》时候修改的(见《巴金文集》第4卷第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吴虞这篇文章的题目应为《吃人与礼教》,巴金均误为《吃人的礼教》,这种误记,比原题目更为明确了礼教的吃人本质。在《春》中,当淑英为自己的命运担心,看到《夜未央》中外国女子的行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真不懂: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作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这时琴向淑英转达的就是吴虞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二表哥他们要攻击旧礼教。他们的国文教员吴又陵把旧礼教称作‘吃人的礼教’,的确不错。旧礼教不晓得吃了多少女子。梅姐、大表嫂、鸣凤,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还有蕙姐,她走的又是这条路……不过现在也有不少的中国女子起来反抗命运、反抗旧礼教了。她们至少也要做到外国女子那样。”[7](P.435)这番话差不多可以用以概括整个《激流三部曲》的内容和主题了,在吴虞看来,道学家们实际上是“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如今讲礼学的人,家中淫盗都有,他反骂家庭不应该讲改革。表里相差,未免太远。”因此,他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最后他痛斥:“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8]巴金正是要揭穿礼教的虚伪和吃人的本质,他的三部曲反复深化这个主题。
新书刊还展示出主人公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也有代表性。小说通过勾画阅读新书刊的变化,呈现出觉慧这一代新青年的思想历程:
后来他进了中学……于是他底世界又改变了面目。从书本上,从教员底讲说中他渐渐传染到了爱国主义的热诚[和改良主义的信仰]。他又变成了梁任公底带着煽动性的文章底爱读者了。这时候他爱读的书是《中国魂》和《饮冰室丛著》,他甚至于赞成梁任公在《国民浅训》里所主张的征兵制,还有了投笔从戎的意思。可是五四运动突然地袭来,它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梁任公底主张被打得粉碎之后,他又连忙带着极大的热诚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他又成了他底大哥所称呼他的,或者可以说嘲笑他的:“人道主义者”,大哥底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不肯坐轿子。那时候他因为读了“人生之真义”和“人生问题发端”等等文章才第一次考究到人生底意义上面去。但是在最初他所能够懂得的不过是一些含糊的概念,渐渐地生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这些日子里的幽禁的生活,内心的激斗和书籍底研讨使他底眼界变宽了,他开始明白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做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他对于这种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生活开始痛恨起来。[3](P.111)
在《全集》本的《家》中,巴金在强调“爱国主义的热情”之后,还有“和改良主义的信仰”,说明他要强调觉慧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那一代人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那么在梁任公之后,“五四”带给他的“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是什么呢?在这里巴金没有点明,但在《春》和《秋》中却点出他是一个革命党。这都是借着觉新之口说出来的:“不过我担心的不是三弟会变坏,倒是怕他将来会变成革命党。”到后来觉新明确地说:“三弟在上海,思想比从前更激烈。我原先就担心他会加入革命党,现在他果然同一般社会主义的朋友混在一起。我劝他不要做社会活动,好好地读书,他也不肯听。最近他还到杭州去参加过那种团体的会议。”[7](P.71,385)在《秋》里,觉新说觉民“也走上了三弟的那条路。你们都走上了那一条路。”并指出他们的主张:“这是革命党的主张!这是社会主义!”[9](P.142)这个“革命党”从事的应当是无政府主义活动。“五四”这一代青年开始思考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小说中说:“那时候他因为读了‘人生之真义’和‘人生问题发端’等等文章才第一次考究到人生底意义上面去。”这样的文章和所讨论的问题也是五四时代比较通行的,陈独秀就曾写过一篇《人生真义》,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回答得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并认为:“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10]“人生观”问题是一个觉醒的人首先要追问的问题。
对于五四时代“觉新”这样一类青年的描述,则更见“五四”理念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巴金是这样描写他的:
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东西才把《新青年》底理论和他底大家庭底现实环境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而在他和他底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底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便常常引起他们底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地看新的书报,依旧继续地过旧的生活。[3](PP.49-50)
在现实生活中,觉新这样“两重性格”的人恐怕要比觉慧这样的人多得多,甚至可以说在觉慧的身上未必就没有觉新的性格。这是他们这样的“历史中间物”的必然承担的精神痛苦,他们的出身、教育和现实处境使其在新旧蜕变中间备受煎熬。作者曾这样交代觉新的思想来源:
他底两个兄弟底思想比他底激进[进步]一些,而他只是一个胡适主义者,并且连胡适底《易卜生主义》一篇文章,他也觉得议论有点过火。他很赞成刘半农底作揖哲学,他又喜欢托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虽然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不过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3](P.49)
也就是说觉新的思想也有“五四”的背景,不过,觉慧选取与环境抗争的一面,而觉新则从中选取了能够适应自身环境的思想资源。还需要做三个注释:(一)胡适主义者,应当是指一个非激进的改良者,所以才有他两个兄弟比他激进的话*关于胡适的这句话,在1958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4卷中被删除,见《文集》第4卷第46页,《全集》本亦然。;(二)刘半农的“作揖哲学”是从刘半农于1918年10月于《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作揖主义》的文章而来的。不过,巴金这里更多是从字面上来用的,指觉新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四处作揖、打拱以委屈自己换取“天下太平”的做法。而刘半农的文章则更多是在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不争论”的智慧,特别是针对当时遗老遗少们反对新文化的腔调,指出与之争论,还不如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三)无抵抗主义也是“五四”前后比较流行的思潮,蔡元培曾经这样介绍过“无抵抗主义”:
托氏是笃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仪式,完全不要,单提倡那精神不灭的主义。他编有《福音简说》十二章,把基督所说五戒反复说明。第一是绝对的不许杀人。第四是受人侮时不许效尤报复。第五是博爱人类,没有国界与种界。他的意思,以为有人侮我,不过辱及我的肉体,并没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点,我狠怜惜他罢了。若是我用著用眼报眼,用手报手的手段去对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蔑了。所以有一条说,“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劝他。劝了不听。你就请两三个人同劝他。劝了又不听,就再请公众劝他。劝了又不听,你只好恕他了。”这是何等宽容呵!《新约福音书》中曾说道,“有人掌你右颊,你就把左颊向著他。有人夺你外衣,你就把里衣给他。”这几句话,有“成人之恶”的嫌疑,所以托氏没有采入《简说》中。托氏抱定这个主义,所以绝对的反对战争。不但反对侵略的战,并且反对防御的战。所以他绝对的劝人不要当兵。他曾与中国一个保守派学者通讯,大意说,中国人忍耐的许久了,忽然要学欧洲人的暴行,实在可惜,云云。所以照托氏的眼光看来,此次大战争,不但德国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国人也都没有是处。托氏的主义,在欧洲流行颇广,俄境尤甚。[11]
巴金特意指出觉新对整个学说也不甚了了,不过对于曾经登在《新潮》上的托氏小说《呆子伊凡的故事》却看过,这个故事从托尔斯泰的本意来说,是反对好战分子、资本主义的托拉斯,而赞颂傻子伊凡这样的朴素的手工劳动者。巴金所取的是伊凡的性格,他什么都能答应,都说“好的”,恰恰如觉新将不该背负的事情都背负到自己肩上一样。以上可以看到,书刊在作者描写人物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巴金也展示了另外一种状况:哪怕获得了新书刊的启蒙,也会产生另外一种人生,那就是觉新式的人生。
三 新书刊与作者的个人记忆
上面所分析的都是呈现出“五四”最普遍特征的意象,但也有一些书刊暗示出巴金的个人信仰,巴金在小说中大肆渲染它们的影响力和带给青年的精神震动。在《春》等作品中,巴金明确点出新书刊让觉民确立了个人的信仰,让淑英和琴等人勇敢地反抗家庭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刊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物,作者在这里暗示了他的主人公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
恰恰在这时候方继舜从外州县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描写未来社会的小说《极乐地》和一本叫做《一夕谈》的小册。他当做至宝地把它们借给别的朋友读过了。《极乐地》中关于理想世界的美丽的描写和《一夕谈》中关于社会变革的反复的解说给了这群年轻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同时觉慧又从上海寄来一些同样性质的书报如《社会主义史》、《五一运动史》[进化杂志]、《劳动杂志》、《告少年》、《夜未央》等等,都是在书店里买不到的。在这些刊物和小册子的封面上常常印着“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一类的警句。的确这些热情的青年是闭了门用颤动的心来诵读它们的。他们聚精会神一字一字地读着,他们的灵魂也被那些带煽动性的文句吸引去了。对于他们再没有一种理论是这么明显、这么合理、这么雄辩。在《极乐地》和《一夕谈》留下的印象上又加盖了这无数的烙印,这些年轻的心很快地就完全被征服了。他们不再有一点疑惑。他们相信着将来的正义,而且准备着为这正义牺牲。《夜未央》更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这是一个波兰年轻人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活动的是另一个国度的青年,那些人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但已经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参加了为人民求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那些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么忠诚、那么慷慨、那么英勇。这便是他们的梦景中的英雄,他们应该模仿的榜样。[7](PP.365-367)
又过了一个星期觉民的信里说:“《极乐地》已经出版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今天给你寄上两包。你如需要,以后还可以多寄。……便是一本破旧的小册子我们也当作宝贝似的。前天我从学校回家无意间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小书,叫做《俄罗斯大风潮》,是民国以前的出版物,用文言翻译的,译者署名‘独立之个人’。书里面叙述的全是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读了真使人热血沸腾。我把书拿给存仁他们看。他们都不忍释手,说是要抄录一份。这本书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你要看我可以寄给你。[7](P.393)
这里提到的事情与巴金个人的经历几乎完全吻合。其中提到的《夜未央》《告少年》都是少年巴金的精神启蒙读物。其他书也都是中国较早的一批介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读物:《俄罗斯大风潮》,英人克喀伯著,署名“独立之一人”(马君武)译,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夜未央》,1908年巴黎新世纪书报局出版,李石曾译,描写虚无党人暗杀故事的剧本,后被多次翻印;《极乐地》,鲁哀鸣著,1912年出版,为一幻想小说,全书20回,描写白眼老叟反抗政府失败后,在海外找到了无政府、无剥削的极乐岛国的故事。此书后改名《新桃花源》,曾在《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连载;《进化》杂志,月刊,1919年1月创刊,编辑人为陈延年等,由郑佩刚在上海印刷,共出三期;《劳动》月刊,1918年3月创刊,上海大同书局发行,梁冰弦、刘石心等编辑,共出5期,同年8月停刊;《五一运动史》,芾甘著,民钟社出版的“民众丛书”之一种。*以上资料见《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9—1087页。
在《春》中,巴金详细描述了《夜未央》给青年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同样是调用了他个人的记忆。他写的是处在生命困境中正在寻求出路的少女淑英,在已经受到相当的新文化熏染的少女琴的启发下,观看一群年轻人演出的《夜未央》时所激起的心理波澜。桦西里和安娥所表现的热情的场面震撼了她的心,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对于自身处境不满和反抗的萌芽由此萌生出来:“我真不懂: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作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我们连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作一点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我们送进火坑里去……”[7](PP.425-437)她要争取做“人”的权利,而不是被当作“礼物或者雀鸟”。联系到她的处境,要么屈服于家庭,去做一个纨绔子弟的太太,要么勇敢地走出去,去争取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作者通过描述回答是:“她近来不再在叹息和悲哭中过日子了。她更用心地跟着剑云读英文,而且跟着琴努力学习各种新的知识。”[7](PP.438-439)《春》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是仔细地转述了《夜未央》的整个剧情,作者用意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演戏表现觉民等青年的革命宣传活动;二是通过看戏,表现出淑英等人所获得的启蒙,这两者互为因果。还有一点,能够看出作者本人所受到过这本书的影响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它的感情。
书是火种,引燃了人物的内心之火,巴金的笔下,书的启蒙作用被反复描述。《春》中的淑英在这样的启蒙下由大家庭的小姐变成了女学生;《雨》中的李佩珠从“小资产阶级女性”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她的启蒙读物是陈真留下的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在这里,作者强调的是这些书刊带给他们不同于原本生活世界的新气息和新感受。不但是佩珠,而且陈真当年也曾经叙述从这个书中所得到的感染。他说:“我已经读过了四遍,我每读一遍总要流不少的眼泪。我是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软弱了。”方亚丹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那是一本好书,我读了,还流过眼泪,”[12](P.128)接下来,小说详细描述了这本《回忆录》带给佩珠的影响:
那本十六开本的大书里面的每一个字,即使是她不认得的,也都像火似地把她的血点燃了。她的心开始发热起来,额上冒着汗珠,脸红着,心怦怦地跳。好像她的整个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要满溢出来一样。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不过她觉得有一种模糊的渴望在身体内呼唤她,这种渴望是她从前不曾意识到的。
在她的手里躺着那本神奇的书,她从来不曾读过这样神奇的书。从这本书里面一个异邦的女孩站起来,在她的面前发育生长,长成一个伟大的人格: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丈夫,到民间去,把从瑞士学来的医学知识用来救济贫寒乡村的农民。她经历过种种的革命阶段,变成了一个使沙皇颤栗震恐的“最可怕的女人”,革命运动的领袖,一代青年的指路明灯。她在黑暗的牢狱里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来叩门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到人间,重回到社会运动里来。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性格与信仰,伟大的人格的吸引力。
这本书在这里被作者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圣物般启示着它的信徒,李佩珠读书的激动情绪几乎就是巴金个人读此书心境的借用。巴金1927年就曾经这样叙述读此书的感受:
今年读到一本最好的书。几月前寄友人君毅信中曾说:“昨晚重读妃格念尔底自叙传,流了不少的眼泪。我在哭我自己!”可见这书感我之深了。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底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底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无穷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底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13]
看似夸张的情绪,实际上都有其生活的依据,关键是要进入人物的思想深处才有可能理解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心绪。巴金在写笔下的人物时是真正与他们融为一体了。接下来,他就写到佩珠经过妃格念尔回忆录启蒙后,“这一段话不仅指示出来一个美丽的玩偶居然会变为崇高伟大的人,因而给了她一线的希望……”[12](PP.131-132)
不做玩偶,而要做一个勇敢的、有用的人,这也是从《娜拉》而来的“五四”女性解放的声音。当这种声音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遭际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可以改变人行动和生活的奇妙力量。卡西尔在谈到启蒙哲学的时候,认为:“启蒙哲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努力,不是反映和描绘生活。毋宁说,这种哲学信仰的是思维自发的独创。它认为思维不仅有模仿的功能,而且具有塑造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使命。”[14]
书本改变了一个人的灵魂,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于语言的不满足,有行动的欲望和要求。“李佩珠热心地读着每一本书,把它们当作她的精神养料的泉源。阅读滋养了她的人格成长,使她感觉到单是这样读书已经不能够满足她的渴望了。她还想在读书以外做别的比较实在的事情,或者参加什么有益的活动来放散她的精力。”[12](P.208)这个时候,周如水甜腻的个人爱情早已吸引不了她了,做一个优雅的太太不但不是她的生活追求,而且是她再也看不起的事了。对于别人的讥讽,她毫不顾忌地反驳说:“难道女人就只该在家里伺候丈夫吗?”[12](P.248)等到《电》中,李佩珠已经成为一位大胆而镇定的革命家了,这种带有理想成分的女性,是作者的创造,而这种创造不能不说与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和妃格念尔的事迹大有关系,巴金借用了那些女革命家的精神气质使小说中的很多理想化的女性都有俄国女革命家的风采。
《夜未央》和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等书刊出现在巴金的小说中暗示着书中人物的特殊信仰和无政府主义的魅力。众所周知,不但是巴金本人,而是整个无政府主义信仰者那里,《夜未央》都是他们推崇的剧本并不断翻印和排演。妃格念尔的《回忆录》亦然。所以巴金的小说中,不经意的书刊可能蕴藏着作者的心灵秘密,而书刊的更换也别有深意。这体现在1949年巴金对自己作品的修改中。比较典型的是两例:抗战期间,巴金期望通过民众运动把战争引到无政府主义革命上来。《火》第二部中的一个细节也表露出这种想法,当决定青年团体今后去向时,李南星选择了留在民众中间组织斗争,并留给冯文淑一本书,称“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自传”、“它可以慢慢帮助你的人格的发展”。[15]这本书竟是《插图本克氏全集》中的《我的自传》一卷,尽管是一本很具有文学色彩的书,但它对这个小团体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暗示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意思的是后来巴金将这本书改为鲁迅翻译的《毁灭》,并“希望你多读它,它可以慢慢地帮助你认识自己,改造自己。”[16]
另外一个改动是在《第四病室》中,杨大夫带给“我”的第二本书,最初巴金是这样写的:
我拿起书来,读着那书名:“在甘地先生左右”,书名下面印着一幅甘地的画像,在甘地的身旁坐着一个缠着印度衣服的圆圆的中国青年。这封面引动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在这病室里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这些印在土纸上面的不太清晰的小字,我决定听从杨大夫的话,把这本薄薄的小书留到明天来翻读。
但是在后来的印本中,书换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拿起书来,读着书名:“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名下面有一个印着“罗曼罗兰著”,四周还有一个红色框子。书相当重,而且在这个病室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这些印在洋纸上面的小字,我决定听杨大夫的话,把这本书留到明天来翻读。*第一段引文参见巴金《第四病室》,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1年4月第6版,第234页;第二段引文见巴金《第四病室》,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5月第1版,1958年3月第6次印刷本,第192页;又见《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97页,后者文字略有改动。
赞美甘地的一段话相应也都删除了:
“我把书还给你,”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偏偏找不到,却说出来这样的一句,我从枕头下把两本书都拿出来预备交给她。
“不要还我,你留着做个纪念罢。我回来,你已经早走了,”她边说边做手势阻止我。但接着又伸过手来把书拿了去:“我给你签个字罢。”她摸出自来水笔,在两本书上都写了字,然后递还给我:[“我喜欢这本书,它把甘地写得可爱极了(她指着《在甘地先生的左右》)。他多么善良,多么近人情,他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真正的伟人应该是这样的。你常常读这本书,就仿佛你自己在甘地身边一样,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她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光辉的笑容,眉宇间阴郁的皱纹已经消散了。[好像她在甘地的伟大的人格之前,连她个人的烦愁也已忘去了似的。]她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地说:“我走罗。”[17]
以上[]中的两段文字都被修改或删除了,其中,第一处被修改为:
用姊姊对待弟弟的口气对我说:“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18]
这段话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巴金文学观的一部分,在最初的版本中,它由《在甘地先生左右》这本书引出是自然而然的,表达的仍是与巴金信仰相通的一些信念,有研究者曾这样论述甘地等人的“不抵抗”:“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暴力行动主义揭穿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暴力的成见。从梭禄到托尔斯泰到甘地,无政府主义者和权力分散论者显示了不抵抗的方法,即用非暴力的方法,能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引起人们良心上的反应。当然,这种非暴力活动不能造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由甘地的斗争而产生印度国家,但是埋藏在理想之中的反抗传统是存在的。”[19]这样看来,关于甘地的书出现在巴金的小说中与巴金的思想信仰还是有牵连的。后来修改本的话,中间似乎缺少相应的中介,未免有些突兀。难怪巴金对这种修改不甚满意。*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巴金捐赠的1953年9月晨光版第11版《第四病室》,其中有巴金1955年1月20日的一段题词:“一月十八日我得新文艺回信,主张删去甘地的一段,我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的原文讲到思想),但我也照他们的意思把关于甘地的一段删去,又扯去两页。巴金二十日。”“新文艺”指出版该书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另外,很重要一点,对于甘地的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巴金未必赞同,但他一定佩服甘地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和伟大而崇高的人格。《在甘地先生左右》是一本实有的书,它由古今出版社出版,笔者所见的是1943年8月再版本,1948年4月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作为“时代丛刊第一种”还曾印行过。可见这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书,他的作者曾圣提曾在甘地的身边生活过,并且颇得甘地的好感,“这本小书是圣提为了纪念甘地先生最近的一次绝食而写的。他用十日左右的时间,朴素无华地,记述他在甘地先生左右时生活的片段。”“圣提对我说过,接近甘地,你便没有私念,你只一心一意地想为别人服役,为人类祈福;接近他,你不觉得自己渺小(当你接近其他的伟大人物时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你只觉得自己磊落而光明,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20]这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甘地这种为信仰献身和为人类祈福的精神与巴金内心中对人类的责任感是相通的。而后来改换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虽然也是当年影响甚巨的一部书,也表达出作者的人道主义倾向,但未免有些牵强。看来,新书刊在作品中的玄妙真是不能忽略的。
[1]张爱玲.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M].//郁金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217-233.
[2]沈从文.八骏图[M].//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07.
[3]巴金.家[M].//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Z].//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418.
[5]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欢迎《新声》: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编辑[J].新青年,1919,(第6卷第3期).
[6]胡适.易卜生主义[M].//杨犁.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742-744.
[7]巴金.春[M].//巴金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吴虞.吃人与礼教[J].新青年,1919,(第6卷第6期).
[9]巴金.秋[M].//巴金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陈独秀.人生真义[J].新青年,1918,(第4卷第2期).
[11]蔡元培.欧战与哲学[J].新青年,1918,(第5卷第5期).
[12]巴金.雨[M].//巴金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3]巴金.俄罗斯十女杰[M].//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4][德]E.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4.
[15]巴金.火:第二部[M].上海:开明书店,1946.224.
[16]巴金.火[M].//巴金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28.
[17]巴金.第四病室[M].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1.243.
[18]巴金.第四病室[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199.
[19][美]特里·M·珀林.反抗精神的再现[Z].//当代无政府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
[20]罗吟圃.《在甘地先生左右》序[M].//曾圣提.在甘地先生左右.重庆:古今出版社,1943.2-3.
(责任编辑:朱晓江)
NewBooksandPeriodicals——OnOneoftheMayFourthImagesinBaJin’sWorks
ZHOU Li-min
(Ba Jin Research Society, Shanghai Writers’ Association,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so-called “May Fourth Image” refers to the elements which can reflect the May Fourth thoughts, ideas and values. In Ba Jin’s novel,Family, “new books and periodicals” is one of such images. New books and periodicals,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eak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the old culture and tradition, embodied many enlightening goals and tasks which were set by the author and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addition, the new books and periodicals in Ba Jin’s works also reflected his strong personal memory and writing choice, which revealed his personal beliefs.
Ba Jin; May Fourth; “May Fourth Image”, new books and periodicals
2009-12-15
周立民(1973-),男,辽宁庄河人,文学博士,现为巴金故居(筹)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著有《另一个巴金》《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巴金手册》《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巴金评传》等。
I206.6
A
1674-2338(2010)01-00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