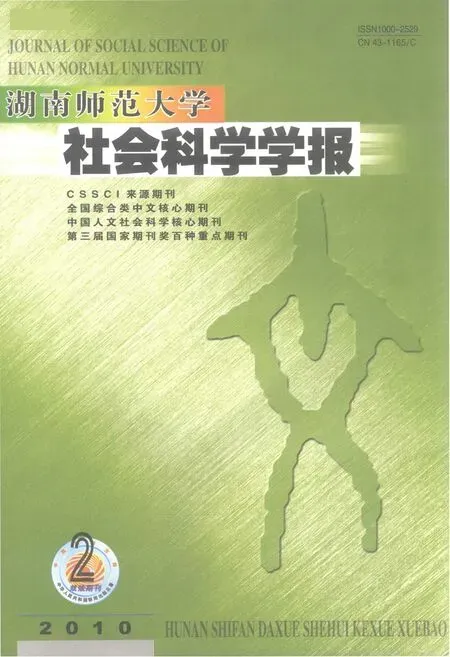宏日报以广言路——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
2010-04-11徐新平
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宏日报以广言路
——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
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何启、胡礼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办过报纸,但是,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所提出的新闻思想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进一步提高了当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对晚清政府压制报纸和言论自由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表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胆略勇气;他们认为日报的最大好处是“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有助于人们对报纸作用的了解;他们提倡新闻记者要具有“直笔”和“公平”的精神,对于记者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
何启;胡礼垣;新闻思想;新政议论;日报
何启、胡礼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长期生活在已成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香港,自幼接受过英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式教育,比起长期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一些改良派维新人物来,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他们最早宣传‘公平’思想,最早比较系统地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1](P173)作为推行资产阶级新政的措施之一,他们在著名的《新政议论》中所论述的“宏日报以广言路”的主张,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但是,在已有的新闻事业史研究中,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长期被忽略,至今未见到研究他们新闻思想的专文。这与他们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时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一、何启、胡礼垣及《新政议论》
何启、胡礼垣一生之中与报纸有直接关系的经历并不多,特别是何启从未在报馆工作过,而胡礼垣虽然有过在《循环日报》和《香港粤报》做翻译的经历,但工作时间也不长。他们不是以报人的身份谈论报纸,而是作为具有维新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中国政治改革的角度来论述报纸的。他们对于报纸的看法集中反映在著名的《新政议论》之中。
《新政议论》全名为《中国宜改革新政议论》,写于1894年冬,刊于1895年春。张礼恒在《何启 胡礼垣评传》中说:“此文是胡礼垣与何启的第二次合作。合作方式依旧是两人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由何启用英文写作,再由胡礼垣修饰润色,翻译成中文。”[2](P148)关于他们的合作,胡礼垣在《新政议论自序》中也有过说明:
予方有所欲言,而何君启乃条列新政要略,出以英文,邮寄与予。予喜其意之与予合也,重感于怀,不能自已,遂增以己意,复为此篇。议之而复论,论之而复议,反复推详,以见中国此时改革之为,实有不容再缓者。[3](P320)
这说明,《新政议论》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产物。这篇论文写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何启在序言中说:“方今之势,正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虽未及燃,不得谓之安也。”事实正如何启所料,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何启、胡礼垣怀着“时艰蒿目,日切杞忧”的心情写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兹当玉弩惊张之会,金瓯荡动之辰,将欲再奠元黄,永安社稷,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新”[3](P328)。可见,探讨中国改革维新、发奋自强的出路是何启、胡礼垣撰写《新政议论》的目的。
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提出的改革主张一共有16条,内容很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司法、新闻等方面。特别是将“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当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大公报》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报业家英敛之先生在阅读了《新政议论》这篇论文后,在1899年3月27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是晚始句读何沃生、胡翼南两先生《新政议论》讫,服其立言明白畅晓,说理深透切中,直欲向书九叩,不止望空三揖也。”[2](P153)其钦服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即1901年他为何启、胡礼垣的论文集《新政真诠》撰写序言的时候,又对《新政议论》《新政始基》等文章,作了包含深情的评价:
“全书之援古证今,旁讽曲喻,浩瀚数十万言,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掀翻跌宕,略无滞机。贾生之上书,逊兹精详;刘向之条陈,无此痛切;恻怛慈祥,若杜工部之每饭不忘愤激忧危,类屈大夫之行吟憔悴。立言如此,足与日月争光,堪为中华生色矣!嗟乎,使当轴者早用其言,岂有今日?然则先生之不遇也。是其不幸耶?亦国之不幸耶?”[4](P50)
当然,为人作序,夸赞溢美之词在所难免,但是,英敛之说何启、胡礼垣生不逢时,他们忧国之心如屈原、杜甫一样炽烈,他们的政治主张不被最高统治者采纳,不能在现实中奏效,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二、“宏日报以广言路”的新闻思想
在《新政议论》中,何启、胡礼垣把办报列为“因时制宜”的九条措施之一,认为只要做好了“复古”的七件事和“因时”的九件事,中国就会是“地则不负其为至灵,民则不负其为至善,学术则不负为其为至正,治术则不负其为至纯”[3](P484)。在“宏开日报”这段专论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宏日报以广言路。”他们希望谁来“宏日报以广言路”呢?当然只有政府。因此,他们的意见都是针对当时政府的错误做法有感而发的。围绕着这一主题,他们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
1.日报的最大好处是“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
何启、胡礼垣认为:“日报之设,为利无穷。”但其最大的益处是使人变得越来越聪明睿智。他说:
“人之才识得诸见闻,若闭其见闻,则与塞其灵明无以异。盖见闻不广,则思虑不长,则谋猷必碍。以无思虑之人而与有思虑之人较,则有思虑者胜矣;以思虑短之人而与思虑长之人较,则思虑长者胜矣。而思虑俱从见闻而生,见闻多由日报而出。夫古典虽多,不合当今之务,旧闻莫罄,难为世用之资。则欲长人之见闻,以生人之思虑,而使事则善益加善、物则精益求精者,莫如宏开日报也。”[3](P414-415)
他们从两方面的比较中,论述了“宏开日报”的理由。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方面比较,有见闻、有思虑的人与无见闻、无思虑的人竞争,前者必胜,后者必败。“而思虑俱从见闻而生,见闻多由日报而出”。二是从日报与古典方面的比较,能够让人懂得“当今之务”和获得“世用之资’的,当然是日报。这种以常识为论据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令人信服。
为了更好地说明日报“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的作用,在论文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日报多方面的好处:
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如议政局员条议各节,极之会议时,诸员之形容举动,皆列于报内,评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也。一案一讼,凡两造状师所辨事情,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中,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也。
若夫官家之颦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战守之时务,物价之行情,市道之旺弱,股份之价值,店铺之张歇,田宅之买卖,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才,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人员,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人才之选举,陪员之轮值,地方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划,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时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出,凡有益于民生、日用、性命、身心者,闻则无不录,录则无不详。[3](P415-416)
我将这一段话详细摘录出来,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到,何启、胡礼垣所认为的报纸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凡有益于民生、日用、性命、身心者,闻则无不录,录则无不详”。正因为报纸的内容丰富,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所以才对社会产生无穷的益处。他们在后来写的《新政安行》中又强调了这种看法:“泰西文治之法,最盛莫如日报。有一城百数十家,一家数十万里纸者,思虑辟,闻见周,上德宣,下情达,无以过此。是故士阅之而文艺愈进,农阅之而田功愈多,工阅之而技巧愈神,商阅之而贸迁愈盛。寰球时事如亲见之,世界光明,民心知向,靡不由来。”
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郑观应的新闻学论文《日报下》中,也有一段与此大体相同的文字。对照两篇文章,这一段内容与郑观应《日报下》中的文字,只是省略了几句话,变动了几个字,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属于原创,一个则有引用过多和改头换面之嫌。
从时间上看,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议论》写于1894年冬,刊于1895年春,郑观应的《日报下》,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夏东元编的《郑观应集》(上)的说明,是1895年《盛世危言》增订为十四卷本时所增写。而且,郑观应的《日报下》开头一句就是“《新政议论》云:‘宏日报以广言路’”。因此,可以认定,何启、胡礼垣的文章在前,郑观应的文章在后。郑观应写《日报下》的时候,是参看了《新政议论》的。
除了这一段文字之外,郑观应的《日报下》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与《新政议论》中的也很相近。摘录如下:《日报下》的原文:“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新政议论》中的原文是:“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加数倍,民之志量必高数筹。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必无止境矣。”[3](P418)“曾亦思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乎?”[3](P478)两相比较,除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外,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郑观应《日报下》中的部分文字与何启、胡礼垣《新政议论》中的部分文字确有相同和相似之处,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政议论》的被人重视与良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郑观应在写《日报下》时,引用过多的不足。
2.对政府压制新闻事业的抨击和对新闻自由的呼唤
何启、胡礼垣对中国新闻业的现状和萎靡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新政议论》中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日报之设,盖亦有年,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为什么报馆记者不敢直言呢?何启、胡礼垣认为,这并不是新闻从业者故意失职,不愿意直言,而是政府官员的逼迫所致。他们尖锐地指出:
“今有于官司之不讳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至查封,其主笔必至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笔言之者,其主稿者祸不旋踵,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之虚与实也。是故,不知忌讳者,不可以为日报,不识情面者,不可以为日报,知忌讳识情面而不肯阿谀奉承地方有司者,仍不可以为日报。于是,华人之为日报馆者,不敢自标其名,反借洋人之名,以求保护。其受制也若此,尚能望其有益于实事哉!”[3](P478-479)
像这样把中国新闻事业的落后与风气不振的原因直接归结到统治者的身上,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直言、敢言的胆气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在后来的维新派人士的言论中也很少见到。先于他们的王韬在他的论文中虽然也指出过中国新闻业落后的现状,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说:“顾今之所设者不过上海、香港耳,而内地各省均未之设,故其所闻之事犹有不尽不实,以贻局外之讥。”也希望朝廷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原则,给民众办报的自由。但是,对于中国报业为什么萎靡不振的原因,却避而不谈。王韬也生活在清政府管辖不到的香港,却没有何启、胡礼垣的锐气和胆略。
何启、胡礼垣对清政府查封报馆、逮捕报人,以至于报人都不敢直言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明确地指出,清政府禁止报馆是“以为毁谤时政,动摇人心,类讪上之下流,比横议之处士,而不知其大谬不然也”。他们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新政推行之后,这样以压制为内容的新闻政策,便不会再有了。“新政行,则事事整顿,焕然一新,无复虑此。”[3](P479)事实证明,他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在晚清时期昏聩腐朽的政府面前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有人在评价何启、胡礼垣的新闻思想时,说他们“最早要求自由办报和言论自由”[5](P189)。他们是不是最早要求自由办报和言论自由的人呢?当然不是,在他们之前的王韬就提出过新闻自由的思想。但是,何启、胡礼垣对新闻自由的呼唤更为有力,他们不仅直接批判了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愚蠢做法,而且明确提出了“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新闻自由思想阐发比王韬更为充分和明确。
3.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期望与提倡
既然“报馆之设,为利无穷”,那么,它的作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呢?在何启、胡礼垣看来,这一方面要靠政府政策的扶持,改变只准洋人办报而对国人办报则限制和打压的做法;另一方面,就要靠办报人的职业道德作保障。在《新政议论》中,他们对记者的职业道德,特别强调了“直笔”和“公平”的精神。
何启、胡礼垣一方面把中国的报人不敢直言的责任归之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另一方面,他主张记者最宝贵的品质就是敢于直言。他说:
“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若唯诺由人,浮沉从俗,遇官府旷职则隐而不言,曰:彼虽旷职,仍是官府也,以下讪上,不可为也。持此一念,势必至逢君恶,遇小民含冤,则忍而不发,曰:彼虽含冤,不过小民耳。贫不敌富,理岂不然。持此一念,势必至失人心。曾亦思《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乎?”
“盖言必能直于日报,方为称职,言而不直于日报,则为失职也。中国日报之设,盖亦有年,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3](P478-479)
记者最高的职责是什么?用什么标注来衡量记者的“称职”与“失职”?何启、胡礼垣认为,就是“言必能直于日报”,在报纸上敢于直言是称职,不敢直言就是失职。他们认为,中国的日报已创办多年,但是,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却不多,就是因为“秉笔之人不敢直言”,形成了一股“唯诺由人,浮沉从俗”的不良风气。而要做到敢于直言,就要继承中国历史上史家优秀的道德传统:“《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敢于揭露官府旷职,敢于为小民申冤。
所谓“春秋之笔”是指孔子修《春秋》的写作方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寄寓作者的政治理想,扬善贬恶,明辨是非,秉笔直书,爱憎分明。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P944)何启、胡礼垣希望新闻工作者学习“春秋笔法”,就是要学习《春秋》叙事简要谨严和持论是非分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直笔精神。
所谓“南董之风”是指春秋时齐国史官南史和晋国史官董狐的著史精神。他们都以直笔不讳、宁肯牺牲性命也不肯歪曲事实而著称于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无道,赵盾屡谏,灵公乃欲杀赵盾,盾出奔,盾族人赵穿因杀灵公,盾还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赞他为古之良史,谓其书法不隐。南史和董狐都是历史上维护历史真实而不怕牺牲的光辉典范。
同王韬一样,何启、胡礼垣非常推崇史家的直笔精神,认为记者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书法不隐”和“斧钺不惧”的精神。这不仅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史家与记者这两种职业的某些内在联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对记者的道德人格修养也有了明确的要求。从他们提出这一道德口号之后,关于记者要具有“史家精神”的思想便成了历代报人关于新闻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之一。
何启、胡礼垣认为,记者的“直言”精神一方面要靠政府的鼓励,另一方面,要靠记者自身的修养。他向最高统治者建议:
凡有志切民事、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底可绩者,天子宜特赐匾额以旌直言也。[3](P482)
对于那些敢于直言的记者,天子应该赐与匾额来表彰。只要在记者队伍中形成了不惮指陈、持论公平的风气,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盖据事直书者,必无齐东野人之语;实事求是者,岂有子虚乌有之谈。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门面之语,而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则其为利国利民之件实无以尚。”[3](P417)这段话中不仅说明了“据事直书”对于记者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新闻对于防止谣言的重要作用。
何启、胡礼垣在提倡记者应有“直笔”精神时,往往与“持论公平”相提并论。“据事直书”与“持论公平”其实是两方面的要求。据事直书着重于对事实的陈述,要求记者真实地纪录客观事实;持论公平着重于对事实的评论,要求记者客观公正地评价事实。
何启、胡礼垣关于持论公平的新闻思想与他们的社会公平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1887年春夏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曾论书后》(原名《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平”思想。他们认为,公平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国无公平则虽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勇夫如海,铁甲如山,亦不能服人心而昭众信。”
那么,什么是公平呢?他们解释说:“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贴,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也。”“公”是“私”的反面,“平”是“偏”的反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公平”的原则,就是“以庶民之心为心”,“以庶民之事为事”,而不是以君王之心为心,以君王之事为事。他们猛烈地批判当时清政府的专制和自私:“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只如贱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只如鹰犬也。”他们希望中国的统治者改变现状,以公平的原则来处理国事,做到“政则有公而无私,令则有平而无偏”。
他们认为,衡量是否公平的标准,不是制订政策的君主与官僚,而是民众的看法。“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公,自以为平,而公否平否,当以民之信否质之,乃得其至公至平……公平无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将这种思想运用于新闻领域,就是“持论公平”,报馆发表的意见不应有所偏袒,更不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而是要反映民众的心声,得到民众的信任。
他们还指出,日报的通病就是夸大其词,缺乏社会责任感。特别是面对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他们在《新政议论》中说:“惟外国交涉之件,其中宜和、宜战、宜攻、宜守等事,则宜尽听于议院日报者,只可为见闻之助,不可为决断所凭。盖日报每遇此等事,必好为过当之词,多作托大之语。不独中国惟然,推之天下各国,其不坐此病者,实鲜。”[3](P482)报馆“好为过当之词,多作托大之语”的原因就在于,报馆不用承担战争的责任,不用支付战争的费用;如果战争打胜了,报馆会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打败了,那是将帅的过错。假如要他们临阵作战或者出钱,那么,说话就会谨慎了。因此,他们希望新闻界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求实和公平的职业精神。
在新闻道德观上,何启、胡礼垣所强调的核心就是“直言”和“公平”。“直言”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平”就是说话要有公心而没有私心,不偏袒任何一方,站在客观的立场说话。这种精神对于新闻业来说,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总之,何启、胡礼垣在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中,虽然没有直接办过报纸,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新闻事业却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他们在《新政议论》中所提出的新闻思想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宏日报以广言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措施之一,进一步提高了当时社会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对晚清政府压制报纸和言论自由的愚昧行为所进行的猛烈抨击,表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胆略、勇气;他们认为日报的最大好处是“长人之见闻”、“生人之思虑”,有助于人们对报纸作用的了解;他们提倡新闻记者要具有“直笔”和“公平”的精神,对于记者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
[1]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张礼恒.何启 胡礼垣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新政议论自序[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4]英敛之.胡翼南先生全集·新政真诠叙[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5]郑大华.晚清思想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长沙:岳麓书社,1988.
(责任编校:彭大成)
Enlarge Saying Channels by Promoting Dailies——A Discussion on He Qi and Hu Li-yuan’s News Thoughts
XU Xin-p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i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 the early days,He Qi and Hu Li-yuan are well-known innovatory ideologists in China.Though they had not run a newspaper directly,their journalistic thoughts in the“New Deal Arguments”counted for much in modern history of journalism.They regarded“Enlarge saying channels by promoting dailies”as a way of China’s political reform,thus raising mor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journalism;They attacked fiercely on late Qing dynastic government because of its suppression on the news and free speech,which showed the intellects’stro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ategyic courage;In their opinion,the most advantage of daily paper is“open the mind”,“engender human thoughtfulness”,which helped people know the role of the newspaper;They called for journalists’free-spoken and justice spirit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ultivating reporters’moral qual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He Qi;Hu Li-yuan;news thoughts;New Deal Arguments;daily
G210.9
A
1000-2529(2010)02-0137-04
2009-10-0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闻思想史新编”(湘宣[2001]30号)
徐新平(1957-),男,湖南祁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