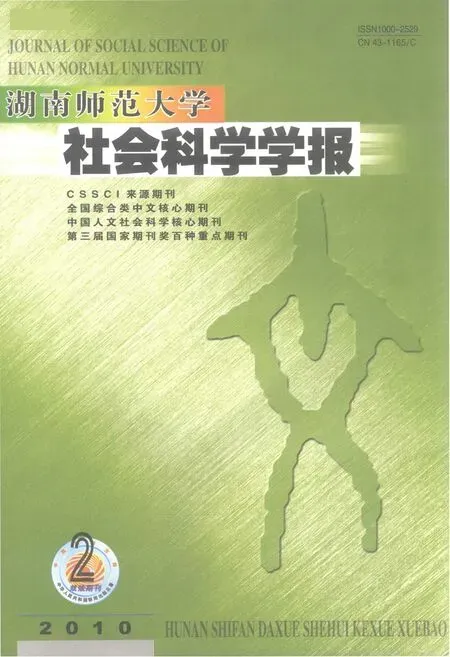从人间到冥世:宋代冥契文化述论
2010-04-11董春林
董春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从人间到冥世:宋代冥契文化述论
董春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冥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别具特色的现象,以其神秘的文化特质融通于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实物冥契,还是口头冥契,在宋代,不仅普遍盛行于民间社会,并且取得官方的认同,其中实物冥契的规范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清。他们在人间与冥世之间建构起一座沟通的虚拟桥梁,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其与儒家传统契合的过程中,平衡了宋人各阶层的心态,从而造就了宋代社会相对的稳定。
宋代;人间;冥世;冥契文化
“冥契”一词,始见于中古史料文献,《晋书·慕容垂载记》:“宠逾宗旧,任齐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岂甚此邪?”[1](卷一二三,P3083)这里的“冥契”,只是默契、暗含投合的意思①。此后的文献记载中也常见“冥契”一词,只不过喻意有细微不同,冥契既可指天机、天意,又可指生与死之间签定的婚约或契约,总而言之,冥契倒有一种神秘色彩。关于冥契的神秘色彩,久为学者贯以冥契主义(Mysticism)②,进行多方阐发,上与孔子学术相连,下与宋明理学相关。不过,所谓的冥契主义,只是神秘主义的代名词,学人借用“冥契”的神秘色彩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的神秘思想。从现有传世及考古文献记载来看,魏晋以来,冥契文书及实物冥契大量出现,尤以宋代的实物冥契数量达其极,言辞中的口头冥契也为宋人广泛沿传。关于宋代口头冥契,很少有学者论及,但中古实物冥契中的买地券文书,此前已多有学者对其文本格式及文化渊源进行考究③。笔者认为,宋代实物冥契及口头冥契显见于史料的这种文化现象,不仅说明由唐至宋世俗文化的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其昭示着政治教化与社会信仰的内在契合,以及儒家伦理与社会价值观在民间信仰之中的相互融通。基于以上论点,本文借助对冥契含义、特征及其形成背景的探讨,以期揭示宋代冥契文化现象的本源,以及冥契文化得以存在的社会意义,以此窥见神秘文化对宋代社会乃至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多元人鬼通行证:宋代冥契的种类及其特征
谈到宋代冥契一词,目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近年来出土宋墓中发掘出大量碑刻“买地券”文书,当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实物冥契。除了这些实物性质的冥契之外,宋代史料里也常见前代已有的口头冥契,这种冥契,要么指人与人之间暗中契合,要么指冥间或前世的约定,后者往往叫做“夙契”。显然,宋代冥契一词,除去表达一般的人与人暗中契合之意外,多直接用在勾通人间与冥世的关系之中。无论文字也好,口头也罢,都是一种神秘文化的产物。以下笔者将分别对宋代契约性质的实物冥契及口头冥契的特征深入探讨。
1.实物冥契
宋代实物冥契里的“买地券”,当指一种契约文书,这种文书多出现在发掘的墓葬之中,由于多是刻在砖、石之上,所以保存了完好的书写原貌。美国学者韩森转引Ina Asim的观点,并据收集到的买地券文本认为,公元1世纪到20世纪,买地券一直在中国地区使用着,其中大多是宋、金、元三朝所在的10-14世纪的,此前与此后都没有这一时期多[2](P141)。其实,元代人早已注意到这一时期民间买地券之流行,《癸辛杂识》载:“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县某都某山某圩地云云。此堪舆风俗如此,以为可笑。……此唐哀宗时事也,然则此事由来久矣。”[3](别集下《买地券》,P277)韩森据五代人陶有关葬俗记载认为,铁或石制地券一般为家境好的人才有,贫者则使用纸质或梓木等木板做为地券材料[2](P142-143)。而宋元买地券里流行的“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只是一个象征数字,阳世里所付的地券钱,不管多少都可折合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韩森认为,阳间买卖墓地中实际交易的币值与冥币兑换,并没有固定的折算率[2](P158)。不过,宋代有些买地券行文草率,买地券中换算的冥币值并不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江西出土的北宋元符二年(1099)买地券则载:“金银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文九分九毫九厘九忽……买得家北湓城山葬地一穴。”[4]江西出土的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一方地券里,“仅用钱帛万万贯,五彩信币酒脯牲牢等”[4],就买得良地。
实际上,宋代大多数买地券中所付冥币值都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可能因为这种早在唐末的买地券中就已有使用的币值,到了经过宋代官方详尽规范之后,才在民间广泛推广的缘故。宋代官修阴宅相地书——《地理新书》中记载道:“某年月日,具官封、姓名,以某年月日殁故。龟筮协从,相地袭吉,宜于某州某县某乡某原安厝宅兆。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掌四域;丘丞墓伯,封部界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若辄干犯诃禁者,将军亭长,收付河伯。合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安厝。已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月主。保人:今日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5](卷一四,P113下)显而易见,这是官方对买地券行文的明确规定,或者说是官方为民间阴宅相地文书制定的一个范本。在这个范本里,宋代买地券大致应涵盖买地者、去逝时间、买地所付费用、卖地者、地的位置及大小、交易时间、证人和保人、对侵犯者惩罚内容、鬼律咒语等九项内容。实际上,这些内容只是在大多数相对规范的买地券中才能齐全,少数宋代买地券内容单一,参差不齐。这可能与撰写者个人的文化水平及买地者家境情况相关,当然,各地的风俗也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买地券的规范。
与买地券相当的实物冥契,还有冥婚婚约和悲情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定情信物,这种冥契同样在人鬼之间搭起了勾通关系,因而在业已世俗化的宋代社会中影响颇大。冥婚婚约和现实生活的婚约相似,同样充当着婚姻双方协议或契约的关系,一旦婚姻破裂,婚姻一方还要写休书,以此解除婚姻关系。洪迈《夷坚丁志》曾记载,岳州平江令吉之,原配王氏去逝后,与同郡张氏再婚,张氏因生女儿后得病不能医治,最后,吉之不得不仿效人间夫妇写了离婚休书之后,张氏才得以病愈[6](P639)。和婚约相当的男女文字情书,有时候也同样能搭成人鬼情事。《夷坚志补》亦载,临川贡士张举赴省试,途中夜宿旅店,因在一美女画上书写“捏土为香,祷告四娘,四娘有灵,今夕同床”[6](P1637),以至于与鬼勾起春宵情事。此等冥契文书,虽常见于宋人笔记小说,但没有详尽的行文规范记载。
2.口头冥契
和实物冥契不同的是,这类冥契,有时称作夙契,只是一种暗中契合或冥冥之中口头约定,同样解决的是甲与乙之间的神秘关系。从暗中契合来讲,冥契一词过多地实用在人与人交往之中,表达一种非今世所动的前世缘分或天意使然。宋太祖征平淮甸,后世便言之“冥契神人”[7](P663);道士刘道渊称,已故的欧阳永叔与其有“夙契”[8](P882);曹子方为友张文潜、晁无咎、蔡天启赋诗“于兹邂逅如夙契”,以表达友情缘分[9](P912)。诸如此类的冥契投合之说,多见于宋代民间生活之中。与之稍有不同的人鬼冥契约定或契合关系,常常称之为前世或今生偶遇之中的夙契约定,多数旨在勾通人鬼之关系,从而给人提供人世之外的解决方案。这种口头冥契最常见于神怪小说,诸如,章丘暨彦颖与女鬼京娘有夙契,“得谐伉俪之欢”[6](P1319);殿前司游弈军卒李立前世与萧氏女有婚约,萧氏今以鬼神身份偿与李立的夙契[6](P1452)。
总之,宋代实物冥契或口头冥契,都在充当人间与冥界勾通的桥梁,实物冥契蕴含着契约特质,更多的是一种协议凭证,而口头冥契除了少数释义为口头约定之外,常常与缘分一词相通,表达来自于冥间一种不可更改的超自然关系。宋代冥契一如前朝,并没有太多新意,大多记载还来源于神怪小说,到底这种冥契是否真正行用在宋代社会,抑或宋人如何认知冥契,这一问题超出冥契本身的含义,从而关系到这一文化的社会意义。
二、合情合法:官方与民间对冥契的双向认同
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既离不开民间的广泛认同,也离不开官方的主导作用,宋代冥契文化也不例外,无论从民间实物冥契的普遍推广来看,亦或是从口头冥契的广泛流传来说,民间对冥契的认同都显而易见,而官方在这一文化形成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实际上,虽然冥契文化对宋代社会影响很大,但宋代官方对民间信仰并非完全持放任态度,对于有毁社会风化的巫风淫祀一贯从严打击,史载:“(大观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妖言惑众之人,令开封府迹捕科罪,诏毁在京淫祀不在祀典者。其假托鬼神送邻州编管。”[10](刑法二之五〇)而冥契却非简单的迷信产物,它的本源特征应该是构建人类或人鬼之间合法合理的契约关系,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越来越融入社会生活诸方面,诸如买地券一般的实物冥契的流行势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名公书判清明集》里便有关于侵犯墓地的案例记载④,从这些案件记载来看,宋代墓地买卖同样需要田契凭证。虽然韩森曾推论中古的买地券早于世俗社会的商品契约,人世间的契约关系或许源自人类对鬼神的信仰⑤,但宋代买地券的流行却一定受宋代契约制度的影响。天圣十年(1032)八月,并州的一块买地券载:“并州右厢开食店王信迁,奉上代父母,于阳曲县武台乡盈村税户白千处,立契买到地一亩二分,置围两座,各长十一步,各阔九步,准作价钱九贯文,折计阴司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卖地主白千,男白诚。”[11]这块地券里墓主白诚立世间田契买到一亩二分墓地,花掉的九贯文,然后折合成阴间钱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明道二年(1033)八月,并州民陶美买贰亩墓地,花壹拾贰贯伍百文折冥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文[12]。这里折算率可能并不固定权且不论,仅地券上透露出的人世契约关系,便可推论出民间对实物冥契的广泛认同,定然与宋代契约制度的推行息息相关。
如果说法律里有关墓地交易的案例还不足以说明官方对冥契文化倾斜的话,《地理新书》的颁布则给予这一问题更为详尽的解释。从《地理新书序》里我们看到主编王洙并非最初的官修阴阳书的编撰者,宋仁宗最初诏令官员的修撰,只是针对唐贞观中吕才主持的官修阴阳书“丛杂猥近、无所归诣”[5](P3)进行的修正,这便是最初的《地理新书》。皇佑三年(1051),又以原修的《地理新书》“浅漶疏略,无益于世”[5](P3),诏令丁度等置局删修,丁度死后,王洙典领其事。关于此书修撰特点,王洙曾言:“券之以经义辨空也,质之以史传信休咎也,广之以异闻求成败也,正史所传则存其可据者,不颛新见也,辞质而易晓便于俗也。”[5](P4)也就是说,官修的这本阴阳书的材料即来自于民间或传信,行文语句也通俗易懂,以期在民间流传使用。不管此书的目的是否仅“以圣人制作之德,广祖宗爱民之心”,王洙耗时二十一年的修撰里程,则已说明宋代官方对冥契文化的导向或规范。
正如《地理新书》的材料源自于史传或民间的特征一般,宋代较为规范的买地券文书并不始于宋代,这种地券文书格式早在唐代就有使用。唐开成二年(837),弋阳县姚仲然的买地券中已明确记载购地券者身份、买地方位、所付冥币、出售者、保人证人、惩罚方案、鬼律咒语等内容[4]。至少从实物冥契来说,宋之前的民间就已流行,官方认定的冥契规制也是来自于民间,只不过规定的格式更为严谨,而口头冥契则不同,宋代的口头冥契之所以依旧流行,与宋代社会的世俗化是分不开的。
宋代的冥契释义依旧沿袭前代,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口头冥契从世俗社会走向官本文化和学术领域,却昭示着一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形成。一如前文谈到宋太祖征平淮甸的“冥契神运”一般,宋代官方也在借用神秘文化来解释自己另一种合法性,究竟这种神秘文化如何与宋代官本文化达到契合,这或许与宋代士大夫面临着内忧外患境况下追寻儒学正统脱不了干系。宋初士大夫们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重新解读,不仅是简单的承袭韩愈的道统论而确立礼法的正统,诸如孔子的冥契主义思想也在宋儒学术构架中得到融通,当然理学里常谈的冥契可能与佛学冥契文化相关,但以儒学士大夫为主体的宋代官僚体系,对冥契主义的接受当无可否认。
与官方出发点不同的宋代民间社会,对冥契一词的认知则完全基于对理想之诉求,从冥冥之中的简单约定,得以对世间不平等或不可企及之意愿的心灵解脱。宋人笔记小说里常常描写诸如人鬼恩怨的悲情或美好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宋代的民间社会里人们正在普遍通过一个神秘手段解决人事问题。凤翔人王筌以夙契得遇神仙海蟾,得道为大臣所荐,赐封“冲熙处士”[6](P565);苏轼以“太真姑舅之婚,复见今日。仰缘夙契,听俞音”[13](P1372);李氏娘痛斥负心汉张生:“今夕相会,岂非夙契?愿见去岁相约之媒。”[14](P98)
三、大道之通途:冥契文化的社会意义
冥契文化是否盛行宋代社会,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就与冥契相关的冥婚习俗而言,可能并不为唐代儒者认同,白居易就认为冥婚“既违国禁,是乱人伦”[15](P1395)。黄景春认为,冥婚神秘性,属于巫觋道士合魂驱鬼、消灾辟邪的行为,一向为儒者所诟病;就其感情表达方式而言,则肆意宣泄哀痛之情,不符合以中庸、克制为特征的儒家礼制的要求。然而,黄先生又考证过唐代涉及皇室成员的四例冥婚中,有三例是唐中宗和韦后操办的,另外一例是唐代宗钦定的[16]。并且贞观年间,唐太宗同样诏令过吕才修撰阴阳书。基于种种相互抵牾的不同证据,我们无法洞察唐代官方对冥契文化的真正认同情况。然而,正如前文考述结论一样,宋代官方与民间却对冥契文化认同态度一致,即使是冥婚习俗也有长足的发展,不惟康誉之《昨梦录》里对冥婚过程的详细记载[17](P391),宋代除了活人与死人冥婚之外,人鬼结合的冥婚故事也散见于宋人笔记小说,不仅女鬼可以还生成婚,阴阳之间缔结婚约,诸如此类的记载都说明了宋代冥婚习俗发展并没有止步,而越来越充斥社会生活。
就社会意义而言,宋代冥契文化的盛行不仅仅取决于冥契形式规范与否,而是冥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入到官方或民间社会的各个角落,以非世俗化的手段处理人世疑难问题⑥,从而达到矛盾的缓和。当然,社会信仰驱使人们对未知冥界的诉求也不可回避,《夷坚志》里为人们刻画的地狱世界应该源自佛教⑦,而宋代买地券里的鬼律咒语当与道教相关。由此可见,佛、道等宗教信仰也为宋人拓宽了人鬼对话的空间。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冥契作为了一种契约性质的东西,为宋人由人间到冥世的观念里提供了某种保障,而冥契本身也是佛者与神勾通的桥梁,佛教为建构自己认知的合法性同样诉求于神给予的某种约定。
此外,宋代冥契文化的流行还不仅仅昭示着佛道信仰的广泛传播,对于人世间契约的合理性又从另一个世界得以印证,冥契为人鬼之间构筑起二次“合法性”交易,从而谋求人的心灵平衡。人间法律解决不了的冤狱,当事人也常常下意识的诉诸冥界法庭,更有甚者,宋人欲达终讼求直的做法,不只在人间“诉于州、于转运使”,还请求冥界“东岳行宫”的判决[18](P176)。作为人间与冥世勾通的桥梁,冥契也并非完全建构在宋代人的简单认知之上,儒学传统里倡导的礼教、中庸与神秘主义殊途同归,同样都在解决人的问题,都在搭建社会平衡的精神之柱。然而,冥契文化融入宋代世俗社会的过程中,似乎很难逾越儒学传统里的伦理道德。实际上,当神秘文化向世俗社会纵深发展之时,在宋代官方的大力推行下,冥契已不再仅仅做为惩恶扬善的理由凭证,而是欲发彰显一种伦理道德倾向。这种根源于儒学传统的伦理观,通过冥契导向了未知冥界,洪迈在其神怪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一个个阴阳情缘,也同样刻画出无数忠孝仁义等伦理故事。这也正好印证了有些学者的论点,在官方的主导下,北宋末年先后出现的《太上感应篇》、《阴骘文》,把封建伦理纲常和鬼神信仰加以糅合,炮制了一个新的枷锁,赐给世俗世界,并将儒、道合流推向了高潮[19](P246)。可见,世俗的礼法思想,在契约制度成熟的宋代社会之中盘根错节地存在,与冥间伦理观念的功用不无关系,儒学传统里鬼神与圣人合一的思想⑧,似乎又在说明宋人仍在继续对天地和祖先的崇拜,冥契成为构建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盛世之通途。从单纯的契约性质而言,冥契彰显的是一种宋人合法意愿之诉求;从深层的伦理角度来讲,冥契又是约束人心、追逐社会和谐的手段。冥契不仅行用于宋儒的日常言辞之中,就连理学里也留有冥契的迹象,“冥契天德”[20](P39),不单单是张载对天命概念的反击,亦在说明宋人是在追溯上古礼制传统之路上才产生对冥契的认识;而朱熹的“冥契”[21](P3669)情节,则仅仅是理学之外神秘文化的投影。
社会意义上的冥契文化,不是单一的角度融通于宋代社会,一方面,官本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动造就了冥契文化的盛行,而冥契文化又平衡了宋人的心态,使得宋代社会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能波澜不惊;另一方面,使得传统的忠义礼孝道德观念,在市俗文化的冲击及宗教文化影响之下,再次面对生命哲学里原初的存在空间。当然,五代以来,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境况下,宋人对伦理观念探索无不彰显一种危机意识,“存天理、灭人欲”与以义生利的思想角逐结果是,宋人个体实用主义态度裸露无余,融通冥契文化的宋代婚葬习俗恰如其分地素描了这一现象。[22]
结语
正如前文所论,关于宋代冥契的盛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然而,冥契无论文字也好,言词也罢,事实上都融入到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与人最近的婚葬礼俗上,冥契更是充当了至关重要的凭证角色,冥契作为一种契约性质的东西,在人间与冥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满足了人们国法之外的合法意愿之诉求。再者,冥契又是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又一载体,从孔子等先秦儒家的神秘思想到宋代理学的繁衍,冥契的神秘主义色彩并没有间断对儒家礼教的润饰。宋代冥契文化,以其浓厚的神秘色彩及合理凭证特征,取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双向认同,迎合了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宋代社会对大道盛世的诉求。
或许,冥契文化只是宋代社会生活中一道亮丽的彩虹,在其沿传过程中,常常被作为前代文化现象的简单承袭而被忽视。由于时隔千载,民间冥契的习俗久已离我们远去,科学与迷信的较量,使得我们无法再回到那个冥契文化风行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冥契研究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有益于我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社会意义的诠释。
注释:
① 徐复认为,冥契指的是古今中外人行事暗中契合。参见章炳麟著,徐复注《书详注》冥契第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页。
② 杨儒宾认为,前人多将冥契主义译为“神秘主义”、“密契主义”,冥契主义之名当优于神秘主义,语其实际,两者所涉的固是同一宗教现象,非有歧异。参见氏著《孟子与冥契主义》,《儒学与廿一世纪——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五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会议文集》,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9页。陈复则认为,“冥契主义”这个词汇,主要在指出其具有面对生命的神圣时刻的幽微性与印证性。参见《孔子的冥契主义》,《辅仁大学第五届哲学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系,2007年,第231页。
③ 陈柏泉在对江西出土的二十七道唐代至明代买地劵文书整理的基础上,初步对其文本格式、地券材质及其用途、特点进行了考述。参见氏著《江西出土地券综述》,第223-231页。黄景春则较为全面的对中古买地券、镇墓文的性质、起源、发展及现状做了深入考述。参见氏著《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美国学者韩森对以买地券为主的中古冥世契约做了深入考述,一方面,追溯买地券的渊源及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借此对阴间法司里佛、道信仰的世俗化作了论述。参见《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第141-203页。
④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坟墓》记载了有关正常契约交易的墓地内营造、垦种及墓地所有权归属等几起民事纠分,这些纠分中法庭判案的依据均是常规土地交易中的地契。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2-336页。
⑤ 韩森曾坦言:“最早从墓葬出土的契约,其纪年早至公元1世纪,它们看来是用于向冥王购买墓地的买地券,与人们在阳间购买墓地的地契或地券相对应……人们可能首先在与阴君协商的时候用上了契约,然后才在人世间互相协商时签订契约文书。”参见《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0页。
⑥ 夏广兴、王伶认为唐人入冥故事的流行,说明时人对死亡的恐惧及对冥界关心的观念已相当普遍,并取得了社会认同(氏著《汉译佛典与唐代入冥故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0页)。宋人对冥间的认知则不仅仅是沿传了唐人的这种观念,人鬼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沈宗宪在解释宋代史书方志中往往连称的“好鬼信巫”时,指出宋人惟其好鬼,相信一切人事均受制于另一个超自然世界,一旦日常生活中有不顺就邀巫对治,巫与鬼神密不可分(氏著《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1995年第91卷第6期,第27-28页)。王章伟也指出人鬼互动是宋人生活习俗的重要部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0页)。
⑦ 葛兆光认为道教与佛教互相渗透,学会佛教那些虚诞夸张的轮回、地狱鬼话,才导致掌握人的命运,监督人的行为的鬼神谱系膨胀(《道教与中国文化》,第243页)。卢秀满也曾谈到《夷坚志》的入冥故事中冥府的主宰者仍为佛教地狱观中的“阎王”(《洪迈〈夷坚志〉之入冥故事研究-以冥法判决之准则及其意义为探讨中心》,《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09年第6期,第118页)。
⑧ 《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韩 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 周 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J].考古,1987,(3):38.
[5] 王 洙.图解校正地理新书[M].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洪 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宋太宗.真定王赵普神道碑[A].全宋文(卷七四)[C].四川:巴蜀书社,1990.
[8] 苏 辙.蔡州壶公观刘道士并序[A].苏辙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邓忠臣.曹子方用釜俎字韵赋诗见遗予洎张文潜晁无咎[A].张耒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徐 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解希恭.太原小井峪宋、明墓第一次发掘记[J].考古,1963,(5):250.
[12]代尊德.太原小井峪宋墓第二次发掘记[J].考古,1963,(5):259.
[13]苏 轼.求婚启[A].苏轼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罗 烨.醉翁谈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5]白居易.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A].白居易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黄景春.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兼与姚平教授商榷唐代冥婚问题[J].民间文化论坛,2005,(5):99.
[17]康誉之.昨梦录[A].说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9]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张 载.正蒙·作者篇第十[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21]朱 熹.律吕新书序[A].朱子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董春林.宋型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力管窥[J].求索,2009,(12):203.
From Human Society to Underground World:Comment on Ming Qi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DONG Chun-lin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Mingqi,which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ha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ystery in Chinese people’s living space.In Song Dynasty,both physical Ming Qi and oral Ming Qi,which are not only widely prevalent in civil society,but obtain official recognition.The canonical form of physical Ming Qi kind remained until late Qing.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which is a kind of construction of a virtual,bridges human society and underground world,with its unique form of far-reaching effects on future generations.In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 tradition,Mingqi balanced Song people at all levels,thus made Song Dynasty relativly and socially stable.
Song dynasty;human society;underground world;Ming Qi culture
K206.6
A
1000-2529(2010)02-0132-05
(责任编校:文 心)
2010-01-05
上海市教委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宋代冥契文化研究”(J50405)
董春林(1978-),男,河南叶县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