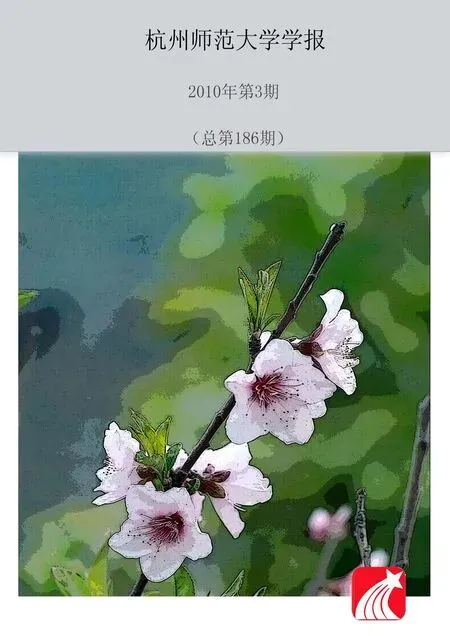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
2010-04-11凌继尧
凌继尧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汉代艺术学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的具有系统艺术学思想的人物,也没有像《乐记》那样比较系统的艺术学著作,然而它有自身的特点。汉代的艺术学思想主要通过哲学著作《淮南子》和《论衡》中的音乐理论和绘画理论体现出来。
一 《淮南子》的艺术学思想
《淮南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和他的门客所著。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汉武帝期间,刘安因谋反罪自杀。《淮南子》今存21篇,原名《淮南鸿烈》,东汉为《淮南子》作注的高诱说:“‘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在哲学倾向上,《淮南子》接近于老子的学说,但是也吸收了诸家的观点。在语言风格上,它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与淮南为楚地有关。
(一)“礼乐未始有常”
《淮南子》艺术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艺术的历史进化观。《淮南子·汜论训》指出,尧、舜、禹、汤、周制作的乐各不相同,但是都很有价值而流传下来。他们是根据“时变而制礼乐”的。社会历史情况改变了,先王制作的乐如果不合时宜,就应该废止而重新制乐。乱世的事情,也可择善而从之。圣人可以制乐,但不能够被乐所束缚。
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
先王制作的乐,如果不符合现实需要,就应该重新评价,直至废止,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观点。孔子深恶痛绝的郑声,在汉武帝时,不仅流行于社会上,而且盛行于朝廷和官府中,“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而且宗庙也不用雅乐。这是“礼乐未始有常”的生动例证。《淮南子》的这种思想得到晋代葛洪的继承。葛洪在《抱朴子·博喻》中写道:“能言者莫不褒尧,而尧政不必皆得也;举世莫不贬桀,而桀事不必尽失也。”
《淮南子》不仅指出了艺术的历史进化现象,而且把这种历史进化的原因与时代背景以及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联系起来,艺术变化的根源在于“时变”,艺术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淮南子·本经训》写道,钟、鼓、管、箫是用来表现喜悦的(“饰喜”),必须先有了内在的心情,才会有外在的表现(“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因此,艺术的发展必须以社会安定和物质生活充裕为前提。如果一个社会,横征暴敛,赋税沉重,民不聊生,“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民众“皆有流连(流离失所)之心,凄怆之志”,这时候才开始为他们“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那就“失乐之本矣”,就丧失了乐的根本了。《淮南子·主术训》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古代的君主关心民间疾苦,“国有饥者而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只有“岁登民丰”时,才撞钟击鼓,“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淮南子》看到了艺术发展与经济基础相平衡的特点。
《淮南子》之所以具有艺术的历史进化观,并把这种进化观与时代背景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是因为它的价值取向与先秦儒家传统有了很大的不同。孔子主张通过艺术来加强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而《淮南子》则把视野投向广阔的现实、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淮南子·泰族训》写道,人赖以衣食而生存,但是,如果把一个人“囚之冥室之中”,即使锦衣玉食,他“不能乐也”,因为“目之无见,耳之无闻”。如果在冥室中打开一个小洞,他从中窥见外面的景色,“则快然而叹之”。如果推窗开门,“从冥冥见昭昭”,必定“肆然而喜”。更进一步,“出室坐堂”,“见日月光,旷然而乐”。最理想的是,“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万物在其间”,“其为乐岂不大哉”!既然乐是表现快乐的(“宣乐”),它就应该表现这种把握外部广大世界所体验到的快乐,这才是大乐。
(二)“君形者”
在艺术创作理论上,《淮南子》提出“君形者”的概念,这是它的形神论哲学观点在艺术中的具体应用。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
把西施的面貌画得很漂亮,却不使人感到可爱;把孟贲(古代的猛士,据说能拔牛角)的眼睛画得很大,却不令人望而生畏。原因在于没有“君形者”。从字面意义上看,“君形者”就是主宰“形”的东西,就是“神”。在艺术创作中,形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神似。“古人经常把君、臣一类的词借用来形容事物的主次关系。山水画有把主山比为君,群峰比为臣的。”[1](P.15)画西施而不可悦,画孟贲而不可畏,关键在于不传神,没有做到神似,没有表现出人物特有的神态。《淮南子》多次阐述“君形者”的概念:
使但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淮南子·说林训》)
但和氐都是善于吹竽的乐师,但是,要使他们的演奏动听,必须自己吹竽自己按孔。现在让但吹竽,让氐按孔,虽然演奏符合节奏,但并不动听,因为不能表达他们内在的情感。这段论述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一人吹竽、另一人按孔的演奏方法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式进行,表现了一种技巧,是按部就班的操作,是可以重复的行为。而艺术演奏虽然凭借某种技巧,但它是充满激情、不可重复的,每次演奏都是独特的,是一种创作,虽然是第二性创作。王羲之的《兰亭序》写过多次,第一次写得最好,后来写的都达不到第一次的水平。苏轼写《赤壁赋》也是第一次最好,后来写的都比第一次逊色。他们的书写技巧并未减退,只是难现当时的激情和兴致。可见,创作是不可重复的。《淮南子·览冥训》还讲到,雍门周的歌唱使孟尝君感动得失声痛哭,因为他的歌唱表现了内在的情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如果让一个人只是肤浅地模仿雍门周的表情和声音歌唱,而缺乏“君形者”,那只会引人发笑。《淮南子·缪称训》也讲到这件事,“歌哭(哭犹歌),众人之所能为也,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虽然人人都能唱歌,但是,歌声要能够“入人耳,感人心”,只有“情之至者”才能做到。也就是说,艺术家要成为“情之至者”,才能够在创作中达到“君形者”的效果。
“君形者”的哲学基础是《淮南子》的形神论。《淮南子》中有三段对形神关系言简意赅的论述。
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淮南子·诠言训》)
以神为主也,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淮南子·原道训》)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淮南子·精神训》)
在形神的关系中,神为主,形为从,神贵于形。《淮南子》的“君形者”可以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的典型论相比照,虽然“君形者”远没有典型论影响大。“君形者”表明,形是事物的现象,神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典型论表明,艺术通过个别性揭示普遍规律。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艺术学中没有出现典型论而在西方古代艺术学中没有出现形神论呢?这与它们各自的文化土壤有关。古希腊的艺术本质观是模仿现实,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总结了古希腊悲剧的创作经验,他认为,悲剧人物和情节虽然模仿和描绘个别现象,但是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某种结果(可然律),或者在已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必然发生某种结果(必然律),从而形成典型论。中国古代的艺术本质论是表现情感,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怎样表现。结论是在表现中应该“神制形从”。《淮南子》的形神论不是直接针对艺术而言的,它是在阐发道家养生的理论,然后把“形”与“神”这一对概念与艺术创作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形神论。
《淮南子》强调艺术是真实的、自然的感情的流露。《齐俗训》写道,“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感情的外露,“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如同“水之下流,烟之上寻”,无需借助外力。而“强哭者”虽然呼天抢地却不令人感到悲哀,“强亲者”虽然笑容可掬却不令人感到融洽。真实感人的是,“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
在艺术创作中,对“君形者”的要求是统一的,但是,“君形者”的表现可以千姿百态,艺术中的美是丰富多彩的。《淮南子·修务训》写道,“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音调不同)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因为现实中的美是多种多样的,“西施、毛嫱,状貌不同,世称其好美钧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悦)于目。”(《淮南子·说林训》)
与“君形者”有关,《淮南子》阐述了艺术创作中的天才和技能的关系问题,它的总的倾向是高度重视天才,同时又不菲薄技能的重要性。《齐俗训》写道,艺术创作需要有技能,这就是规矩准绳,“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掌握了准绳,就可以达到平直,这是一般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学会的。然而,艺术创作不仅仅是要掌握准绳,它要的是“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即超越准绳又符合准绳的要求,这是一种高度自由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状态。这是“不传之道”,“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这是“不共之术”,是一种不可习得的、包含艺术家独特体验的天赋特征,“知不能论,辩不能解”。
不过,天赋要建立在刻苦训练的基础上。《修务训》谈到,盲人乐师“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不失一弦”。“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盲人善于弹琴,是长期练习的结果。只有认真训练,才能掌握高度的艺术技能。“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班不能以定曲直。”任何高明的艺术家都不能脱离一定的规矩和准绳。
(三)“师旷之耳”
如果“君形者”是《淮南子》对艺术创作提出的要求,那么,“师旷之耳”则是对艺术知觉提出的要求。《淮南子》看到艺术知觉主体的差异对知觉效果的影响,指出艺术知觉主体加强艺术修养的重要性。《泰伯训》写道:
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后听。
师旷名旷,晋国著名音乐家,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师”字。他生而无目,所以自称盲臣。《孟子·离娄上》把师旷之聪(听力)与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尧舜之道相提并论。《淮南子》用“师旷之耳”说明艺术知觉者的主体条件,没有“师旷之耳”,即没有艺术修养,再美妙的艺术也起不了作用。两千多年来,对艺术修养的各种比拟性说法,没有比“师旷之耳”更为形象的。并且,《淮南子》还把“师旷之耳”与其他听力作了耐人寻味的比较,显示出对艺术欣赏理解的深刻性。
“师旷之耳”是艺术之耳,审美之耳。与“师旷之耳”并存的,还有鸟兽之耳和“鄙人之耳”。有些动物的听力比人还灵敏,但是,动物不具有审美能力,动物之耳不能成为审美之耳。《齐俗训》写道:“《咸池》、《承云》、《九韶》、《六茎》,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人所喜爱的音乐,鸟兽听了惊恐万分。“鄙人”指缺乏音乐修养的人。《说林训》写道,“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鄙人”欣赏不了高雅的“徵羽之操”。《人间训》写道:“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廷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采菱》《阳阿》是至美的乐曲,“鄙人”听了,认为不如《延路》《阳局》可以相互唱和。这是一种曲高和寡的现象。不过,“鄙人之耳”完全不同于鸟兽之耳,人天生具有审美的潜能,经过后天的训练,“鄙人之耳”能够成为“师旷之耳”。在穷乡僻壤,鄙人敲打盆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如果尝试为他们击鼓撞钟,他们就会觉得钟鼓声更动听,从而不断提高音乐欣赏水平。这说明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淮南子》不仅论述了“师旷之耳”和“鄙人之耳”对艺术知觉的影响,而且注意到,知觉者的主观情绪能够干扰对艺术的正确的知觉,甚至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心有忧者……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淮南子·诠言训》)
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淮南子·齐俗训》)
内心本来悲哀的知觉者听到歌声反而哭泣,内心本来快乐的知觉者听到哭泣反而欢笑,这是内心已有的感情决定的(“载使然也”)。因此,知觉者在欣赏艺术时,要做到内心虚空,不受哀乐的感情干扰。这涉及复杂的艺术知觉心理学问题。
知觉者在欣赏艺术时,未必能够做到内心虚空。因为现代艺术知觉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艺术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知觉者的头脑中。知觉者应该对艺术作品进行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知觉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虽然艺术作品的结构标明一种途径,但是,知觉者不是同作者的路线不爽毫厘地、而是按照自己的路线、最重要的是带着某些其他结果重新经历这条途径。《淮南子》批评了“哀可乐者,笑可哀者”的现象,其意义在于,尽管知觉者可能非常不同地、独特地知觉艺术作品,然而艺术作品的客观结构为知觉者理解的主观性规定了极限,知觉者的情感和想象必须在艺术作品给定的框架内活动和调整。超越了这种框架,“闻歌声而泣,见哭者而笑”,就是一种错误的艺术知觉。
此外,《淮南子》还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思想解释音乐的起源。《天文训》写道,人的“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关节)”。《精神训》写道,人的“头之圆也像天,足之方也像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古希腊也有“人是小宇宙,模仿大宇宙”的说法,但是把人的各种器官与宇宙的各种现象作了如此详细和巧妙的比拟,还是第一次。
《淮南子》把天人相通的思想运用到音乐起源上,就得出“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天文训》)的结论。具体的对应关系表现为,五音配五行,八音(乐器)配四时,即琴瑟配春,竽笙配夏,白钟配秋,磬石配冬。[2](P.284)十二律配十二月,音律之数与一年的天数相同,“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天文训》)。
《淮南子》以“礼乐未始有常”的概念表明了艺术的历史进化观;以“君形者”的概念说明艺术创作中神似的重要性,艺术家要成为“情之至者”才能达到“君形者”的效果;以“师旷之耳”的概念提出了对艺术知觉者的要求。《淮南子》还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解释了艺术的起源。《淮南子》大大拓宽了中国古代艺术学的研究领域。
二 《论衡》的艺术学思想
《论衡》是东汉哲学家王充(27-约97)的著作。王充是会稽上虞人,家庭“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并非名门望族,而是所谓“孤门细族”。在东汉时代,博学多识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品格,[3](P.310)王充被称为东汉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论衡·自纪》中说自己少时“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成年以后更是“淫读古文,甘闻异言”。由于重视经验与知识,王充反对当时甚为流行的谶纬之学。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即“公布图谶于天下”。谶是一种隐语或宗教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纬是相对“经”而言的,以宗教迷信观点解释儒家经典。两者合称谶纬之学。
王充在艺术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开启了我国艺术批评的先河,他的艺术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疾虚妄”和“为世用”两个命题上,这两个命题同时表明了王充艺术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局限性。
(一)“疾虚妄”
《论衡·佚文篇》写道: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虚妄”指汉代儒生的“浮妄虚伪”“空言虚语”以及主观臆造的东西。“疾虚妄”是当时思想界强烈反对谶纬之学和神秘迷信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还有《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两都赋》的作者班固,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制作者张衡,“默而好深湛之思”的杨雄,融汇古今、博通六经的郑玄。他们“在注释经典的形式中强调的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任意想象,不是对圣贤哲理的敬虔心情也不是对微言大义的钩玄索隐,而是历史、事物以及语言文字的确定性知识,是对经典的学术性诠释”。[3](PP.309-310)
“疾虚妄”的思想运用到艺术领域中,强调艺术作品要真实,艺术标准是“求实诚”。“所谓‘实诚’,一方面是指作品所记之事要真实可靠,要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实事’。另一方面是指作品中包含的道理必须是真理,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从而有助于人们分清真伪,明辨是非。简单来说,‘实诚’,就是‘事’要实,‘理’要真。”[4](P.172)这样,王充所说的“真”有两种涵义:一是艺术所反映的客观生活的真实,这时的“真”王充有时用“事实”之“实”来表示;二是人们认识的真实性,这时的“真”王充有时用“是非”之“是”来表示。
与“虚妄”截然对立,王充提出“真美”的概念,他的“疾虚妄”锋芒所指正是“虚妄之言胜真美”的现实流弊。他所说的美既指艺术形式的美,又指艺术内容的美。在《论衡》里,美、善常常互用、连用,如“美善不空”(《佚文篇》),“采善不逾其美”(《感类篇》)。下面是《论衡》对绘画中的虚妄的两则批评: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世有虚语,亦有虚图。(《无形篇》)
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引连鼓相椎,并击之矣。……虚妄之象也。(《雷虚篇》)
在汉代,活着希冀长生不老、死后又期盼成仙的想法很普遍。王充认为人死了没有灵魂,反对厚葬。上面第一则引文中的“虚图”就是汉代成仙想法的图解,王充批评这种绘画,有反迷信的积极意义。现在从营城子汉墓的祭祀图中可以看到浑身长毛而有翼的仙人形象,与王充说的一样。上面第二则引文中的雷公形象和“图雷之状”从山东武氏汉画像石中可以见到。[1](PP.17-19)
之所以说王充开启了我国艺术批评的先河,因为他的相关论述符合后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专业化活动的艺术批评的主要特点。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1713-1784)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位现代涵义上的艺术批评家,他的《沙龙随笔》是艺术批评的范例,他把对具体绘画作品的艺术评价与艺术家的个性以及美学理论结合起来。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密切联系,但是又有明显区别:艺术批评所注意的直接对象是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艺术作品、是艺术遗产;艺术批评偏重于评价,艺术理论偏重于认识;艺术批评往往具有主观的、论战的色彩,艺术理论则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
王充的相关论述正符合艺术批评的四个主要特点:是对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的批评;侧重于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是对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批评;偏重于评价,旨在确定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论辩的、情感的色彩。
充分肯定王充对确立和发展我国艺术批评的重要贡献,并不意味着认同王充的艺术批评中的所有观点。在上述第二则批评中,王充明显地混淆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神话和虚妄的界限,把艺术虚构的虚和虚妄的虚混为一谈。画家所画的雷公的形象,属于神话创作。神话创作只要符合自身的逻辑,它在艺术上就是符合真实的,而根本不是什么“虚妄”。王充对神话艺术创作的批评表明他对艺术虚构缺乏了解,完全用生活真实来衡量艺术虚构。
《论衡·对作篇》说,“《淮南子》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羿上射九日”,这些都是“浮妄虚伪”。为什么呢?王充在《论衡·感虚篇》中对羿射九日的“虚妄”作出解释:“夫人之射也,不过百步,矢力尽矣”,而天和人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羿向上射日,怎能射得到呢?即使尧的时代天地相近,羿可以射到太阳,他也是不能够伤害太阳的,因为太阳是一团火,无法被射杀的。王充的这种解释说明他不懂得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
《论衡》不仅在艺术创作上“疾虚妄”,而且在对艺术功能的理解上“疾虚妄”。《论衡·感虚篇》对《韩非子·十过》所载的关于音乐功能的传说予以批驳:“师旷《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俎豆”是盛食品的器具),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晋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衰弱多病)。”这完全是“虚言”,因为“天之动行也,施气也”。风雨是气的运动,与师旷奏乐没有关系。
王充反对以神秘的传说夸大艺术的功能,这是正确的。但他混淆了人耳与鸟兽的耳朵的区别,认为动物也能够欣赏音乐。他说:“传书言瓠巴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此虽奇怪,然尚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禽兽见人之食亦欲食之,闻人之乐何为不乐?”《淮南子》则认为,瓠巴鼓瑟,沉鱼出听,伯牙弹琴,马不吃饲料,抬起头来听。但是,禽兽知声而不知音,没有审美能力,人耳和禽兽之耳有区别。王充比《淮南子》倒退了一步,错误地认为禽兽也有审美能力。
(二)“为世用”
如果“疾虚妄”是求真,那么,“为世用”是求用。王充的哲学是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从哲学上讲,王充的“为世用”表明,“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在于应用。所以,只是弄清了事实,明辨了是非,还不算真正的通博之人。真正的通博要归于‘能用’。止于知而不能用,这种人不过是‘鹦鹉能言之类’”。[5](P.317)《论衡·超奇篇》举例说明什么是“为世用”:“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一个人到了山上和郊外,能够知道各种树木和野草的名字,但是不会伐木盖屋,也不会采草和药,那么,他就仅限于知而不能用。
“为世用”运用到艺术上,就要求艺术具有社会功能,这继承了儒家“尚用”的艺术功能观。这种功能是什么呢?一是教育功能。按照《论衡·佚文篇》的说法,就是“劝善惩恶”,同时要“颂圣”,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这在《论衡》的《宣汉篇》《须颂篇》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典型的儒家艺术功能观。二是认识功能,艺术要使人懂得事理。对于艺术的这种功能,先秦理论家也谈到过,王充强调得更充分些。因为先秦理论家对艺术更多地强调的是“善”,而王充在“疾虚妄”的思想指导下,对艺术更多地强调的是“真”。王充的这种倾向反映在艺术功能上,自然会重视艺术的认识功能。
为了发挥艺术的功能,王充反对“尊古卑今”,反对“珍古而不贵今”,主张艺术反映现实生活。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论衡·齐世篇》)
由于儒家思想在汉代地位的提高,致使很多绘画描绘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和忠臣义士、孝子节女,这种风气在东汉时代很盛。王充反对这种风气,明确提出要颂扬当代以及相距很近的秦代的优秀人物,为他们作画。
然而王充又片面地认为人物绘画不如人物传记那样能够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艺术的“为世用”的特殊性。
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
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灿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论衡·别通篇》)
这段话说,画面上的古代人物,只见形象,不见言行,所以不能起到教育作用。竹帛所记载的他们的言行,在劝善惩恶方面,要远远胜过墙壁上悬挂的绘画。王充的这种观点不免片面,说明他对艺术的作用不够了解,他的观点与先秦一些理论家相比有所后退。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嘲笑王充的这种观点与“以食与耳,对牛鼓簧”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王充的这段论述涉及艺术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词语和图像的关系问题。王充在我国艺术学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希腊罗马艺术学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词语比图像重要。王充的观点与此相似。然而,中世纪圣像崇拜者在新的文化条件下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图像高于词语。原因在于图像的直观的、形象的特征。图像阐释不同于词语阐释。图像可以弥补词语的不足和局限。与词语和图像的关系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审美感官中听觉和视觉的关系。圣像崇拜者认为图像形象比词语形象深刻得多,因此,适合知觉图像的视觉也就比适合知觉词语的听觉重要得多,他们坚持视觉在各种审美感官中的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我国艺术学也重新思考了词语和图像的关系,把两者相提并论。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他把绘画同《诗经》的雅颂并列,认为绘画可以赞美伟大的事业,使它们流芳百世。在我国艺术学史上,陆机第一次把绘画的作用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艺术的特性和功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王充的“疾虚妄”强调了艺术的真,“为世用”强调了艺术的善,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真美”的概念。所以,王充主张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儒家所理解的应当同美统一的真是伦理学
上的真,“主要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的,指的是道德情感的真诚”,而王充所说的真是认识论上的真,指艺术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应该符合客观事实。“到了王充,美与真的统一,才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被提了出来。”[6](PP.538-539)
此外,王充主张艺术创作要有独创性,表现艺术家的个性,艺术风格和艺术趣味应当多元化,反对千人一面。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各为佳好。……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论衡·自纪篇》)
王充肯定了艺术美的多样性。他在《生死篇》中还讨论了形神论问题,“形”指人的肉体,“神”指人的精神。他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而有光也。”这为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形神”讨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1](P.15)
[1]葛路.中国画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