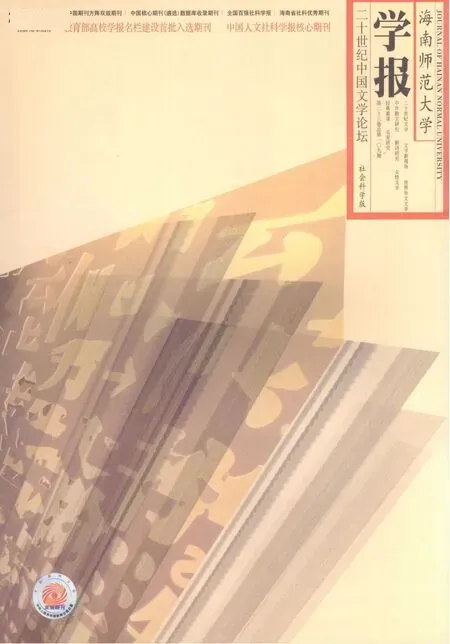书写何为?——论朱天文《巫言》书写本位意识与美学救赎实践的可能
2010-04-11张艳艳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 515063)
书写何为?
——论朱天文《巫言》书写本位意识与美学救赎实践的可能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 515063)
朱天文在近期力作《巫言》中体现了自觉的主体创作意图。在小说中写作者充分强调书写本身的本体论意义,藉书写构建存在物的纵深、多层次的灵性存在状态。而文章也进一步讨论其创作实践对现代都市景观化生存状态实现美学救赎的可能性。
朱天文;《巫言》;书写;物性;救赎;美学实践
从《世纪末的华丽》到《荒人手记》再到《巫言》,朱天文小说世界的转型已成既定事实,再不是“年少春衫薄”式的淡江系列,也不再是侯孝贤御用编剧式背景书写,渐次老到的这3部作品让其小说叙事渐成气候,自成一格,越来越显示出朱天文成熟、自觉的主体创作意识。从25岁“女巫”米亚的精油迷雾到嗜字八载炼金成瓷的巫者自道,朱天文越来越直接、充分地彰显对书写本身的强调。于此,小说创作不必仰赖叙述故事而获得合法性的存在,故事、情节、线性叙事等等传统小说赖以成为小说的特质被其悉数放弃。以“巫”自居的小说书写者,“巫言”是其存身的最本质所在,书写(巫言)本身便构成意义。那么书写(巫言)到底意欲何为?无疑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所在。对于书写本位意识的张扬,使得对在文学实践中重获感性物质生活与灵魂饱满整合的生存状态寄予厚望的现代人,无比期待《巫言》实现这一美学救赎的可能,同时这也构成本文探讨的重要向度,对书写本身的强调是否包含作者自觉的主体实践努力?是否寄予其对现代都市异化景观生存中的人类诗意救赎期冀?而其化身为巫的仪式又是否能切实地担当起沟通并复原生命生机的重任,找到改变现实的力量呢?
一 书写本位意识的自觉
(一)巫的姿态:叙述主体的叙述视角分析
《巫言》全篇存在着鲜明自觉的叙述主体,叙述者在大量的书写中毫不隐讳地表露自己的观念、智识,其不同于一般小说叙事叙述人隐藏自我的表述方式,《巫言》的叙述者不断强调自己的主体姿态,其以巫自居,在文本中可与之沟通的主体样态主要有:“菩萨”、“巫”、“不结伴的旅行者”、社会“左边的人”。故此我们首先厘清的问题是叙述主体的叙述视角与书写姿态。
篇首即一如谶语:“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者”。[1]1菩萨低眉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不涉入,不威权,不温情,他只对他们陈述事实。”[1]26为什么?因为“怕与众生的目光对上”,[1]25结合文本中不断敷衍而出的“不结伴的旅行者”,其特质在规避一切与他人进入凡俗关系交接状态的可能,最充分地保存自我的孤立性,或更深慎一点说:自我的独立性,由此获得自我的完整。而社会“左边的人”呢?叙述者由私己心仪的马修拈出:左边的人总有冲动将自我从合法化的正常社会一分子角色中出离,“总要走出去”,[1]204站在非社会化的最左边,化身为巫。如果我们仔细辨识,巫医江医生“菩萨低眉”式的不动心忍性,戴帽子小姐的不与人群交际,马修的走出去冲动,我们将见出叙述者自觉持守的姿态:不仰赖常态社会化人际关系确立自我,自觉摒弃猫母式的在与别人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我存在意义的方式,通过极大限度地与世俗保持距离由此获得省思状态的、独立的内在自我。一如近年来愈益退隐桂花低处的朱天文选择的处世姿态。
另一层面上,如此的主体姿态意欲何为呢?不仰赖现代社会常态关系的个体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又有着怎样更深层的寓意?于是我们很明显地注意到“菩萨”的隐喻所指,菩萨不涉入现世,但其“观度众生”,故而姿态是貌似冷眼,其实热肠,在文本中反复被叙述者提到的人类学的考察视角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彼此呼应的姿态:一如人类学家“如文明的拾荒者,从垃圾筒中筛选出他的财富”,[1]189以企图重构意义。叙述主体以置身事外的观看者视角获取救赎现世的可能。其以不介入自我的“恒温态”观察、描述现世,却满怀热忱地企图重新建立某种让生命更富有灵性与层次的内在勾连关系,故而其描述本身内孕着召唤,唤醒生命内在本应涌动的文明质素的部分。而以何为之?对叙述主体而言,唯有书写。
(二)巫之言:书写成为巫的本质所在
巫,在中古的文明谱系中,绝地通天者,握有神秘的感知世界本质的力量,藉由某种仪式,实现感通,以巫言传达交会。文本中,不止一次地,叙述者表露着对言语文字本体性至尊地位的膜拜。
即字即言,在远之又远的某个远古,远古里,字能通鬼神,占吉凶,是高贵的权柄。字后来当然是世俗化并一路贬值到今天,但它早时的烙记之深烙于用字者之意识底层,已成原罪。[1]19
我们看到自觉背负原罪的叙述主体——写字人朱天文的执着“找字之途”,她的“在命名,在找字。在路上,在途中”[1]199是有着极其迫切的使命感的,企图找回的来时路上有字原初具有而今已丧失殆尽的召唤万事万物灵魂的原初能量,其试图找寻、复原的无疑是书写与文字本位性的功能所在。故此我们对文本中看似矫情的对待名片的态度,对任何表意象形文字符号的膜拜与珍爱都将获得切实的理解。故而其中巫界部分对于书桌小物的来龙去脉不厌其烦的交待极具深意,用心良苦。我们重点分析一下那块模铸象形文字的黑铁纸镇。这一节写得激情四溢,巫气昭昭,令人心驰神往、唏嘘不已,实为华章。满含着追索、召唤的重大使命是写字人对其救赎自觉最感佩人心的集中表述。
这一方黑铁纸镇,那巫言昭昭的罗塞达石碑,当模铸其上的象形文字被唤醒的瞬间,“字从哑石般拓业里翻脱而出像蝴蝶飞出,摇摇晃晃,怔忡犹疑,看那,古埃及文明醒了。失语了一千年的古埃及醒来。”[1]317“托勒密”,“神显现”。文字被追索之途也即是文明被召唤之路,随着文字力量的复苏,一切沾染着灵性与生机的文明史中的事事物物皆款款而来,带着曾经的热度与魂灵。由此我们看到接下来深富寓意的另一层对应关系。与文字唤醒富有生机的文明质素一致的,写字人于黑铁纸镇下的500字格子纸上书写。“托勒密”,“那是纸莎草风拂过时的兮兮施施声从古代吹来吹开我写字的五百字格子纸吹落一室……”[1]319写字人一如女先知米利以乐音度众生,其以书写让神显现,让生命存在复其生机,获得救赎与重生,于此,其赋予书写的本位意识昭然于世,其希冀亦寓于其中。
二 书写:以恢复物性
(一)书写:以“离题”方式延宕
初读《巫言》,许多读者都会有近似的感受,文本基本没有什么完整的人物、故事叙述,迥异于线性叙事,不断的离题与延异。“我选择离题。拖延结局,不断的离题,繁衍出我们自己的时间,回避一切一切,一切的尽头。”[1]94当然我们可以循着有些学者给出的线索,将其看作朱天文向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致敬,另辟新的叙述路径。[2]于是实质上,曾经很是擅长讲故事的叙述主体放弃线性叙事不是不能为,而是有意不为,其逃离线性时间,无疑是让人重新省思于时间中的存在,生命存在。摆脱两点一线的直线距离,在交叉小径中以迂回来迹近,开发出多路向。不仅延宕了时空,更根本的是让人从生死始终的线性生物性过程中超脱而出,恢复彼时共在的生命存在的切实体验,一如其反刍式的重返社长(朱天文之父)生命终点的现场,借其父在此时空中呈现出的生命宽度与深度的禅悟,表达叙述人试图恢复其对普遍性的存在物之本有的丰富体验与深厚容量的价值观念,故而这是其以“离题”方式演绎出的内在旨趣了。
(二)叙述主体的“物性”情迷
由此我们来看朱天文笔下的“物”,不少论者谈到其文本中在在皆是的“物”书写,充满了冷知识与博物志。大量的访谈中朱天文对评论者对她的“恋物”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她讲到自己推崇的马尔克斯的观念,这个世界的事物都还太新鲜(我们理解这个“新鲜”指的是存在物其实葆有其鲜活的生机),我们还来不及命名(我们如此解读:但是其生机却未能被我们言明,内在生命的活性其实是被遮蔽着了)。①详可见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2008年10月7-9号。同样的,我们感受到朱天文在《巫言》书写中极其强烈的意图:将这被遮蔽的活性、每一物的生命来时路、其沾染着的生命印迹呈现于众。于是她看似小题大做式的写丝袜、写旧衣物、写妹妹的鞋子、写牛仔裤,它们的来龙去脉与生命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致于“每次我千里迢迢带回来自己的,室友的,同行者的垃圾,不是隐喻亦非象征,它们真的就是扎扎实实会占据行李空间的实物。除非没见到,见到了,我无法见死不救,这已成为道德的一部分”。[1]22因为在常人眼中的垃圾,在写字人眼中,皆因有着生命一路而来的痕迹而富有灵性与生机。
是故,朱天文的貌似“恋物癖”书写,其实是其巫化的艺术实践,作为特定的文化仪式,拯救已成死物的遗迹,回溯貌似死亡的过去,看似是做知识考古学的罗列,其实是层次性的试图恢复其本在的生命气息,它有着人类丰沛的生活内容,感性而充满灵气。妹妹的旧鞋子,恰因为她陪着妹妹走埃及、过土耳其、经克里特岛、过雅典……一路沾染文明的辉光,内含着妹妹如此深厚的生命印迹,一如海德格尔对凡高笔下农妇的鞋子的解读,叙述者无法把其当作死物,清理干净,珍重道别,送鞋子进入另一段全新的生命历程。我们在仪式中默默体察这其间的生命气息,并与之交会、感通,物之为物,散发其内在的、精神性的生机,藉此我们实现与物、与过往、与他者、与文明之古往今来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存在物之精魂,其内质在于,作为生命存在延续的过程中不断被构成与充盈,这些体验、经验、智识诸种的组合、融注,使存在物之间实现内在的勾连融通。一如小熊挂饰与浩室音乐的渊源,让原始人伯母与E时代的新人类有了可沟通共鸣的契机。生命存在本身不是线性、生物性、生老病死的被淘汰过程,而是纵深的、有层次的,彼此在大文明质素上,因皆沾染着某一构成质素的印迹,彼此交会沟通。在朱天文的视域里,生命不是当下的单向度孤立所在,其勾连着过去、现在、未来,是文明于此时在生命存在物上的聚集、显发,也是生命存在物获得灵性的根本所在,由此朱天文的“物在”情迷,试图传达给世人如此这般的生命存在的观念,实在应包含着其对重建现代生命存在内在交流的尝试与努力,其希冀召唤而出的生命的灵魂,是以对抗综艺化生存的现代都市个体,让每一个生命重获感性与灵性的饱满整合,重获生机,这是其艺术创作实践的要务,以美学化的实践方式努力实现的救赎。
三 美学救赎实践的可能
朱天文畏友黄锦树在评论《荒人手记》时探讨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题:他“以《荒》书本身为焦点,把它看成是主体实践过程的结果,试图处理的是朱天文的美学实践及它与她早期信仰的联系。”[3]从《世纪末的华丽》到《荒人手记》再到《巫言》,我们以为朱天文作为创作主体,其创作哲学与美学实践渐次成熟,是由初露端倪到惊艳展示到审慎省思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巫言》试图处理不仅是朱天文对其信仰自我的安顿问题,而有着更宏大的野心,是更一般性的现世都市生命个体生存安顿的问题。事实上,貌似退守桂花低处隐逸生活于现世的朱天文始终对台湾的当下注目,并葆有深挚的情怀。菩萨低眉,不是无心,而是不忍心,故其貌似冷眼,其实热肠。我们知道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念,以“胡调张腔”描述朱天文的写作谱系,①详见王德威等相关论述,最近的资料见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且不管朱天文以《巫言》为据不断否认辩解或试图独立而出是否决然成功,但有一点,朱天文在《巫言》中呈现出的救赎使命感比之胡张二人的清冷色调是热烈太多,也入世太多。当然其对现世的对抗与批判不是不可遏制的激愤,已炼达成契诃夫式的言笑。[2]
文本中,朱天文不断地表达她对台湾现世的否定批判姿态,无论是直陈政界事务,还是社会世相描述,从摩西大佬、约书亚先生选举到对Kitty猫风行台湾的揶揄,甚至从对美国灾难片的隐喻中生发,处处表达着其对这个综艺化时代的失望、悲愤与批判。这个文字贬值的综艺化时代,这个一切已综艺化的美丽岛世界,就像杵在世人生存空间中的活火山,人魔两界的界限已被这些政界魔鬼大佬完全冲毁,“魔不在暗晚不在黑里,魔在青天白日下。”[1]285人群已无处躲藏,无疑人人都能读得出从摩西大佬到约书亚先生,是对李登辉到阿扁政府的指代,其如此坦诚的表露,几乎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这样的书写策略,会导致贴近自身的存在被聚焦、裸露,经验性的细节,家族,甚至作者的政治立场,在有限的陌生化下必然无所遁形。这种坦然,在台湾目前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当然是太不够世故了。”[1]263然而若一路回望朱天文的来时路,作为40年次生的眷村一代,经历着一系列急遽更迭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变迁,朱天文在《巫言》中试图处理的不仅是文化原乡问题,其更致力在这部趋于成熟的文本中表述其多年省思而来的信仰与价值观念。所以对于综艺化的台湾世界,无效的日常生活浮世绘是含着深情的批判,“云雾吹开,坐在星空版图上的君父们啊我对你们说,你们打造的世界,我们却只能以负面列表式的活法,活在其中啊。”[4]在失落与哀叹中,更趋坚定地表达着自己否定性的但却是建设姿态的立场。“啊每一种伦理,亦每一种纽带。我朝向时间彼岸在那里的君父们说,每一种纽带不但是互不相连的力量那样相互平衡者,而且亦那样成为了繁复多样的说不的力量。不,我不同意。不,我不遵从。有这样那样的说不的声音,始足以对抗政治权力滥用始足以屏挡综艺化始足以守护珍爱——”[1]261
唯此,其艺术实践,其书写果然被其赋予了诗意救赎的重任,然而此一美学救赎的实践又有着多大的有效性?其寄托于书写本身,以书写复物为物、使存在物复现其自身纵深知识谱系与灵性光辉的努力是否显得过于迂回,而被淹没在貌似驳杂的博物志与文明史书写中,让现世读者迷惑而不得就里?作为书写者,朱天文的姿态多少给人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她的资质、情怀与智识似乎总与其哀婉表达已逝去的黄金古代的文化精英贵族息息相连,而在现世却难有大片蔓延的土壤。故而整个煞费苦心的救赎使命是否会变成自说自话、或者好一点,边缘群体中的乌托邦情怀?定语似乎是难下的,书写者本人却在貌似无奈与希冀并在中书写了一个巨大的隐喻。E时代的新人类竟然还有如食字兽这般珍爱我写字人字册的生命存在,这满满一纸箱要我写字人签字的字册自是让我满怀希冀,接下来却鬼使神差被错带入了垃圾场焚毁,纸片被高高扬起化为灰烬的瞬间,书写人的失落一如其耗尽心神乞求炼字成金,却一直找不到“釉下蓝”而只能“炼金得瓷”的无奈,然而叙述再一转,烈火中被毁灭纸片的命运又似犹太法典Mishnah:
只有会被火烧毁但仍存留的,是的自火中救出的,才能让人学习
到某种必要性,某种可能永远失去无法取代之物的必要性吗?神圣之书。[1]339
是在毁灭中涅槃,还是在涅槃中毁灭,读者的各自揣测体会本身也许是最富启示的收获,是书写人最期望看到的。
[1]朱天文.巫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唐诺.关于《巫言》[M]//朱天文.巫言·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M]//朱天文.荒人手记·附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238.
[4]黄锦树.直到自己也成为路径[N].联合报,2008-03-02.
On the Standard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esthetic Redemption inWuyanby Zhu Tianwen
ZHANG Yan-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515063,China)
Wuyan,a recent major novel by Zhu Tianwen,well reflects the conscious writing intent of the novelist,for the novelist has,in the novel,fully stressed the ontological meaning of writing itself and managed to establish the depth of substances and the multilayered intelligent existence.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further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Zhu’s writing practice to protect and restore modern urban landscape in an aesthetic manner.
Zhu Tianwen;Wuyan;writing;substance;redemption;aesthetic practice
I 206.7
A
1674-5310(2010)-05-0079-04
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诗学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CZW006。
2010-05-16
张艳艳(1978-),女,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