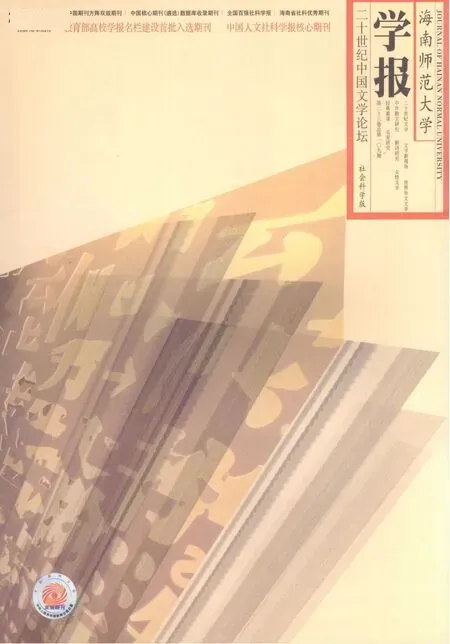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对中日文化互读的启示①
2010-04-11胡焕龙
胡焕龙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安徽淮南 232038)
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对中日文化互读的启示①
胡焕龙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安徽淮南 232038)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考察与研究的宗旨,就是力图超越现实民族矛盾,促进两个民族的互相了解,以期实现互相友好、互相提携的愿望;克服文化沙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偏见,互相尊重,则是两国人民乃至东亚各国之间真正实现互相理解与友好的基本原则。在研究路径上,他抓住日本神道教这一固有民族文化传统,从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民风民俗角度深刻认识、理解日本民族,充分肯定日本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这对于今天中日两国的文化互读与交流,仍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作人;日本文化;神道信仰;民风民俗;精神遗产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位重要名人先是因政治原因被学术界彻底抹去,后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出现于文学教科书里,近年来其生平、思想与贡献才被学术界全面探讨,几成为“学术热点”。人们终于认识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抹去了他也就成为残缺不全的历史。他就是周作人。
一 一位值得纪念的中日文化交流使者
周作人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五四”时期以最有思想深度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理论对文学革命的倡导作出了标志性贡献;20年代以后以其意蕴丰厚的小品文的倡导与创作使中国现代散文艺苑更加绚丽多彩;50年代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外国文学翻译成就使自己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一座桥梁。然而,周作人还有一项一直不被人们重视的重大贡献,就是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贯穿于其前半生的日本文化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具体的研究成果,更在于他的基本立场和独特视角。40年代的周作人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无奈中被拉下“地狱”,但纵观其一生的文化理想与实际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作为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使者,是当之无愧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地位在近两千年的交往史上经历了巨大的沧海桑田。从汉魏到宋明,中国以和平方式全方位地向日本输送先进文化,促使日本本土文明的突飞猛进。近代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同时成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并驾齐驱,中国的发展势头更是异常强劲。日本这个历来崇尚“与强者联合”的民族(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日本民族特性的定语)在19世纪的“脱亚入欧”、20世纪的“脱欧入美”之后,如今又高调“脱美入亚”,积极倡议所谓的“亚洲共同体”。不管这个邻邦怎样以实用主义精神忽“西”忽“东”,通过文化交流实现互相理解,建立稳定的睦邻关系,进而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则是中华民族的现实选择。回顾过去,我们不仅要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还应缅怀先贤,牢记他们在极端恶劣的历史环境中,为自己心目中的文化理想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周作人当年的日本文化研究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仍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周作人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应该重视、深入研究的一位文化使者。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日两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从外在表现看,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堪比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包括后世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然而从本质上看,古罗马之于古希腊、后世欧洲各国之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可以说是属于同一文化母体、同一文化圈内的起源与传播、扩散关系。中日之间则是不同文明母体间不对等的交流关系,即传播与借鉴、吸收关系,他们在实质上是互相独立的两个文明实体。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一衣带水的邻邦没有能很好地审视、研究对方,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水平甚至还不如西方世界。所以,周作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诚恳地向日本人公开表示:“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正的知己。”[1]32而实际上在日本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称得上中国文化的“知己”呢?
在20世纪日本侵华、中日民族积怨很深的时代背景中,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观察、研究,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他虽然没有成系统的日本文化研究专著,但诸多介绍日本文化的篇章中随处可见其真知灼见;文章中所闪烁的超然现实的科学精神、以友好互助共同发展为宗旨的美好情怀以及独特的观察视角等等,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回顾与悉心领会。
二 美好愿望与现实批判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以其对日本文化特征的精确剖析享誉世界,然而其研究的目的是应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征召,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而探讨日本文化特性与国民性,实质上是战争行为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体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其宗旨是热切企盼东亚这两个文化渊源极深的民族消除隔阂,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他始终怀着这一美好愿望,祈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友好往来。他非常推崇黄遵宪,在他看来,黄“在中国是最早也是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1]30“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2]138黄遵宪在考察日本文化、风土民情过程中深刻意识到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强调应当真正认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其意义,不能因自身的文化自负和对日本侵略的仇恨而轻率贬低、排斥日本文化。周作人因而深赞其明智的态度与博大的胸怀。[3]361-362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次年,黄遵宪就作诗:“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4]作为战败国的国民,面临空前的割地赔款的屈辱,仍然以友好情怀与博大胸襟表达中日友好、互相提携的善良愿望,毫无一点弱者心态,周作人不禁由衷赞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1]30他明确表示:“因相知遂生情谊,个人与民族虽大小悬殊,情形却无二致。”[1]32周作人早年长期留学日本,沉浸于日本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方式。周氏家族实际上成为中日民族融合为一的缩影。这使他在思想和感情上能够最大程度地超越中日之间的民族与文化隔阂,实现两者的沟通与理解。真诚热爱两个民族、两国文化而深知其异同,致力于沟通,是周作人能成为两国之间真正的文化使者的原因所在。他在文章中坦率地表示:“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他的所有的东西。……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5]178消除误解增进友情,正是周作人与黄遵宪日本文化研究一脉相承的宗旨和出发点。这正是今天东亚各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互相理解而应共同遵奉的基本精神。
遗憾的是,周作人并不是生在两国和平交往的隋唐或两宋,而是处在日本大举侵华,两国互相仇视的20世纪前期。时也,运也,决定了周作人的“命”,这使他的人生和事业充满悲剧性。“英雄”未能造时势,反被时势所毁。否则凭他的才华与声望,他定能谱写出中日友好交往的辉煌篇章。他怀着文化理想主义的憧憬回顾古代中日之间的和平交往,无奈于目前的政治纷争与民族压迫。他写道:“日本与中国在唐朝的往来真是人类史上最有光荣的事,纯是文化的友谊的使节,一点都没有含着不纯的动机……。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害,……”[1]34为实现中日之间真正的文化交流,互相理解,他以文化使者的独特立场,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对日本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同时,痛斥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民族沙文主义态度,真诚呼吁两国人民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以实现“相知生情谊”的美好境界。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隋唐与两宋之际,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总体上是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因而中国人对日本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心态,认为日本文化皆由中国输入、模仿中国文化而来,没有自己的创造,不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故中国人历来不注重对日本文化的认真考察与研究。周作人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人这种文化“自大心”,他指出: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6]171
他在许多文章中用大量事例为日本文化特性辩护,说明日本民族不仅善于学习模仿,更善于在借鉴过程中择善而从,为己所用。他曾精确地概括日本民族的善于吸收而非盲目照搬:“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2]145更何况,日本原有自己的精神源泉——源自远古神话与原始民族宗教的神道教。而日本文化表面的“中国色彩”使中国人始终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他敏锐地指出:“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切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6]173日本文中的汉字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豪于自己的文化沐浴扶桑,光被四海,一厢情愿地产生了“同文同种”的亲近感,却丝毫意识不到正是这两国共用的汉字,成为蒙蔽自己双眼使之无法认识对方的“海市蜃楼”。没有超越两国畛域的胸襟与文化眼光,没有对两个民族真诚的热爱与深切的生活体验,周作人是不可能有如此的独到发现和深刻认识的。日本有着自己的文化渊源、文化传统、文化特性而并非中国的文化殖民地,要让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仍然不是容易的事。
而近代以来的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民族压迫,更成为两个民族无法实现真正了解、平等交流的现实政治障碍。周作人在谈日本文化的文章中反复表达着自己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与蔑视:“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出现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7]75更重要的是,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恨之情比普通中国人含有更深层的内涵:“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动摇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5]178周作人不仅痛恨于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本身,更痛心于由于这种野蛮侵略造成的两国文化交流的中断和人民之间感情的恶化。中国人虽然有着难以消除的文化自大心,但这种自大心下是对东亚各国始终怀有的“同文同种”的认同感与亲近感,是源源不断的慷慨赠与,然而近代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国策下,对中华民族表示极大的蔑视,不屑与中华民族为伍,视之为劣等民族;“支那猪”、“半边和尚”(形容清朝人的剃发留辫)等成为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习惯称呼。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深深的伤害!1926年,周作人读到安冈秀夫的《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一书,针对书中对中国人的轻蔑嘲骂,他立即著文,表达自己的愤怒与鄙视: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劣点只应由本国人自己来举发,……我只觉得“支那通”的这种态度不大好,也决不是日本的名誉。我们知道现代希腊的确有点坠落了,但欧美各国因为顾念古昔文化的恩典,总不去刻薄的嘲骂他,即使有所记录,也只是平心的说,保存他们自己的品格。……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确是有点像希腊罗马,不是毫无关系的路人。中国现在坠落到如此,日本看了应当很是伤心,未必是什么很快意或好玩的一件事。……“支那通”的那种轻薄卑劣的态度能免去总以免去为宜。我为爱日本的文化故,不愿这个轻薄成为日本民族性之一。[8]368-369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苛毒压迫,周作人始终坚持通过真诚的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提携。即使在遭受日本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时,也真诚希望这种“轻薄”不要成为日本民族性之一,因为他是那么真诚地爱着这个民族!周作人坚信:“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2]145“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运命也是整个的。”[9]1501926年8月,以周作人为会长的中日教育会在北京报纸上刊出启示,阐明该会宗旨:
我们因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在文化上更有割不断的因缘,觉得为彼此的将来计,为东亚大局的前途计,确非互相理解互相提携不可。然而要互相理解互相提携,先得有充分的互相研究。……[10]228
虽然没有确证这是出自周作人手笔,但完全表达了周作人的思想和愿望。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九·一八事变,进逼华北,全中国仇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周作人却高调宣称要做一名“亲日派”,即超越现实纷争,真正“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介绍日本文化到中国,从根本上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亲日派”,而决不是那种中国所痛恶、日本所欢迎的卖国求荣的“亲日派”。[1]31他坚持以超越的眼光和开放的文化胸襟把现实政治与文化交流分别对待。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1]76也就是说,应把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日本固有文化精神区别对待。因而对日本文化的研究“非耐寂寞者不能入手,或如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因为“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11]73所以他宣称自己对日本的态度是:“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5]178
周作人的这种态度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当时注定要四处碰壁。而且把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与其文化精神截然分开,分别对待,也属于书斋中的书生论剑。故多年后,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感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题目的难做”。由于“思想顽固,不大会得融通,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由于始终坚持这种纯文化主义立场,结果“抗日时或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于是只能“烦恼自取。”[12]53难能可贵的是,周作人并未因此而丝毫改变他的文化立场与友善情怀。他以其坚忍不拔的“骆驼精神”,始终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好交往而努力着。周作人是不幸的,时势毁了他,但历史又从另一方面成就着他——正是这种看似迂阔不切实际的纯文化态度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善良情怀,为今天新的国际环境中东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理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假如东亚各国真的在走向互相理解、共同发展的道路,周作人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共同缅怀、永远纪念的“文化使者”。
三 研究途径:宗教精神与情感模式
作为身受中日两国文化熏陶而又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中国文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观察、研究始终保持了一种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它表现在既对日本民族与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真诚热爱,又对中日文化根本差异有着清醒认识。这使他的文章充满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在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之情日益高涨之际,周作人毫不掩饰他对日本的独特情怀,他说:“日本是我所怀念的一个地方。……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13]15-16“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但同时表示“我终是中国人”,从文化上说,“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5]178他说:“我向来不信同文同种之说,但是觉得在地理与历史上比较西洋人则我们的确有此便利,这是权利,同时说是义务亦无不可。……”[14]83这使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考察,不管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显示了一种独特性与超越性。
出于西方学院式的求“真”目的,或现实的商业、战争等具体现实目的去理性地研究一国文化,虽能很好地把握其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组织、行为模式等外在特征,但是很难真正理解对方鲜活的灵魂。周作人对日本民族与文化的切身感受使他获得了以生命体验为特质的“心领神会”,这是仅通过对书面材料的“科学分析”或“身处事外”的“实地考察”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无法得到的。同时,他又能以理性眼光,跨越两个民族的认知误区与情感误区,看到两者“东亚共性”表象下的本质差异。在具体生活情境中,他感悟到了在浓重的“中国油漆”外表下,日本文化本身自古以来的一贯精神,因此特别强调要承认、尊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从日本民族本源性的精神遗产中去考察其真正的文化渊源,从而把握其文化特质。对于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来说,这一见解可谓是革命性的。以文化哲学或文化比较学的“学科眼光”看,这一观点也是中的之论。
周作人认为,要把握日本文化的一贯精神或根本特性,一是从宗教入手,一是从国民的情感方式与民风民俗入手。这是非常正确的。两个研究路径一为形而上之道贯通于日本的文化史,一为日本文化特性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展现,都具有根本性意义。它们互相印证,从不同侧面体现着日本文化精神与国民性。
日本文化精神与国民的根本特性是什么?周作人也曾被日本社会那层“中国油漆”所误导。30年代后,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法西斯化和对东亚各国的野蛮侵略,周作人发现在日本军人身上,根本就体现不出中国儒家那具有普世意义的“仁”及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对日本社会切近考察后的悉心研究,他终于发现,万世一系的神国传统及其凝结的神道教,始终是日本民族的根本信仰。这是以“仁”、“义”等世俗性社会伦理为圭臬的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根本性的精神差异。因此,他确信神道信仰研究是理解日本文明及国民性的根本途径。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周作人写到:“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日本常以书画美术等中国系统的文化给西洋人去看,又以机器兵械等西洋系统的文化给中国人来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却并不提出来,……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日本思想界少数贤哲的思想并不能反映整个国民性状态,于是,“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12]61因而他反复强调:“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14]86他坦言,由于自己缺乏宗教情绪,对神道教知之甚少,难以体会神道教徒陶醉于祭神活动时的心理状态,早年仅仅从文艺入手研究日本,因而是肤浅甚至失败的。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又重申这一发现:
鄙人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即曾声明,自己从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中日两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15]179-180
通过研究一国的文艺作品去研究其文化特质与国民精神,作为文化研究或跨国文化比较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崇尚。①2009年10月下旬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的“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仍有不少中外学者强调通过文艺作品的解读进行国际间文化研究的意义。从符合会议主题的要求看,此观点无可厚非。从学科角度看,若把文学途径当作文化研究、文化比较的主要途径甚至根本途径,则有失于偏颇。回顾周作人的独到发现,应该能给予我们以某种启示。文艺途径固然是民族文化研究和比较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文学艺术集中体现了某一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国民性格等,全方位展现其精神特质。然而,文艺作品毕竟是特定民族社会精英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属于高浮于空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原始而本真的日常生活相比,它只能是极其有限的“流”而非“源”。源自本民族固有宗教情结以及由此而凝结、延伸而来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乃至诸多生活细节,才是酝酿与蕴藏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渊源。周作人宣称自己从文学艺术方面理解日本国民精神“全是错的”、“完全是徒劳”,固然有其失望之时的偏激之处,但他正确地指出了民族宗教情绪及其民风民俗等生活海洋本身才是民族文化精神之“源”,而文艺只是“流”而已。许多人的文化研究常常陷于书斋论道,就在于这种舍本逐末之误。
即便考察特定民族的现实生活,也应追寻其背后的根源性因素,方能透过表象,识其根本。这是周作人通过大量事例告诉我们的。比如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爱国,他觉得这很不得当。他认为这“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他深刻地指出:“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永久不变的国民性”。[16]13“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13]17这就从精神源头上看出了中日两国在封建时代“忠君爱国”的本质差异,从而显示两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差异。
正是本着从宗教情绪的独特视角考察一国文化精髓原则,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深入考察、比较中日两国人民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心态。他看到日本人在祭神活动中总是在精神上达到“神人和融”[12]59的颠狂状态,那种超理性的宗教沉醉可以说正浓缩了这个民族最本质的精神气质,这正是外国人能否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关键所在。而中国人的各种祭祀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可以说礼有余而情不足”。总之,“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注意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17]116,120,121周作人发现,中国世俗性的礼仪文化与日本万世一系的神国传统,是中日两国人民基本精神差异的出发点: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绵延不绝,中间别无改朝换代或异族入侵,这种独特的历史对国民心理影响至深且大。其一是对于国的感情,它“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各族逐鹿中原、朝代更迭、民族意识淡薄的“归顺”文化形成对照。其二是对于君的感情。日本社会虽有阶级差别,但自古以来家国一体,幕府具体负责国家大事。天皇享有族长之尊,人神一体,接受人民宗教般的爱戴与崇拜,这种感情更是真情而非公式化的。明治维新后,神道教被尊为国教成为国家神道。明治政府通过宣扬天皇的神性,激起百姓狂热的宗教感情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和牺牲品。周作人正是通过对神国传统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在宗教氛围下,感情丰富细腻的日本民族何以“一夜间”激发起令人恐怖的“兽性的爱国”狂潮,肆意侵略和屠杀东亚各国人民的。[13]19日本民间祭神风俗的精神颠狂状态,就隐藏着日本民族的本性。
与此相关的,是周作人通过在日本长期生活的实际经验,认识到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须着眼于其内在的日常情感生活,从其民俗入手去理解其人生观与宗教情绪,从而把握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认为:“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的文化大略,结局是徒劳而无功,后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无及,如要卷土重来,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古今文学美术之菁华,总是一时的少数的表现,持与现实对照,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或者反有抵牾亦未可知,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18]126他生动地写道地:“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裲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花草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16]13再如对于武士道文化,周作人看到日本武士道文化极其残酷、非人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日本战国时代,武士的女眷们在战后仔细疏理、清洗割取的敌人首级,使其看上去象生前的模样,从而在令人恐怖的血腥与野蛮习俗中发现存在于日本民族中的“武士之情”。[1]34-36西方人眼中的武士道与日本人自身如新渡户稻造先生眼中的武士道自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理解与感情色彩,①新渡户稻造著有《武士道》一书(见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全面介绍日本武士道文化,享誉世界。但周作人在血腥杀戮中,透过民间风俗发现武士精神的另一面,在表面蛮野的民风民俗中发现日本民族文化特性中的人性与人情美,并深刻领悟到隐藏在这人情美之中的东方古典神韵。这是置身于日本民间生活之外的任何外国人都难以做到的。正是对日本社会风土人情的深切体察,使周作人比善于进行实证分析的西洋人更能透过平常世相,发现日本人的“真面目”。所以,周作人以其在日本的切近观察和亲身体验,写下大量介绍日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的精彩文章,通过那娓娓的叙述与生动描写,我们不仅从理智上认识了这个民族,更随着作者的笔触亲切地感受了一下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情感世界;在看似平常的描绘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意义,具有单纯理性的“科学分析”所难以达到的人性深度。这是周作人作为两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往往比某些专业学者更具深度的原因。
四 结束语
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是不可重复的。首先,作为一个饱尝侵略战争之苦和民族歧视屈辱的弱国子民,他以执着的理想主义情怀,力图超越严峻的现实政治纷争,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国的文化交流,呼吁和推动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与尊重。在险恶环境中,他在表达着对侵略者的愤怒与蔑视的同时,诚恳地向日本人民表示,中日同为亚细亚民族,应友好往来、真诚携手共进,应在这一宗旨下互相理解。这决非弱者的祈求,而是显示着中华文化精神所铸造的博大胸襟与高尚情怀,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显示着一个古老民族固有的仁者风范、强者风范。它理应成为当今世界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今天,崛起中的中华民族应继承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以博大的心胸,友善的情怀面向世界,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化互读与交流中,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的这种博大与友善,这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输出”、“价值输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互读,应以此为终级价值。在这方面,黄遵宪、周作人等应该成为我们永远纪念的先贤。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
周作人的文化视角还启示我们,分别克服文化沙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互相尊重,是两个民族友好往来的现实平台。对于中国人来说,克服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自大心,承认并尊重日本固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承认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是两国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话的科学基础。今天的日本虽已全面西方化,但其固有的民族精神依然存在于其血管之中,并不时在关键时刻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透过日本社会的现代“西方油漆”和传统的“中国油漆”,从其本土本源性的精神遗产中看日本民族与文化的真实面目,是今天的中国人解读日本文化精神与民族特性的关键,而再不能在“同文同种”的情感误区中越走越偏。而平等地对待亚洲各国人民,克服百年以来的种族优越感,也是日本人民理解亚洲近邻的重要前提。不管是中国人对于日本民族的“同文同种”幻觉还是日本人视中华民族为“劣等种族”的鄙视(尽管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已经开始淡化或转入其潜意识中)都不可能使彼此互相尊重和真正理解。对于日本民族来说,缺乏真正的友善、忽而“脱亚入欧”忽而又要“脱美入亚”的实用主义态度,也不可能使其在口称儒道,手写汉字之际,真正理解自己身边的中华民族和这份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其三,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增进友谊,决不是仅靠少数学者在书斋里对“材料”的研究而实现,而是由广大人民相互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接触、密切往来而实现。周作人之所以能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民族有深刻的了解,就在于他几乎毫无心理与现实隔阂地往来于两个民族之间,深切体察各自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与内在情感,因而悟出通过日常民风民俗与感情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正确方法。今天,在加强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的同时,推动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密切往来,尤其是广大人民之间日常生活中的互相接触与深刻了解,是达到各国人民之间深度理解、友好相处的现实途径与根本途径。因此,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周作人式的真诚而高尚的文化使者是强有力的纽带和宽广的桥梁。
[1]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哈迎飞.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马关纪事)五首其一[M]∥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140.
[5]周作人.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周作人.日本与中国[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其二[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哈迎飞.谈虎集·支那民族性[M]∥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周作人.草囤与茅屋[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1]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周作人.日本管窥之四[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周作人.日本管窥[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周作人.怠工之辩[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周作人.关于祭神迎会[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8]周作人.缘日[M]∥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On the Revelation of Zhou Zuoren’s Study of Japanese Culture in Understanding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HU Huan-l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Communication,Huainan Teachers College,Huainan232038,China)
When observing and studying Japanese culture,Zhou Zuoren aims at attempting to transcend the actual ethnic contradiction,and to enhanc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peoples so as to realize the hope that they can guid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a friendly way.Overcoming cultural and ethnic Chauvinism respectively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even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Eastern Asia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and live in harmony.In terms of studying methods,Zhou focuses on Japanese Shinto,the inherent ethnic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people by studying their daily life,emotional life,social customs and highly appraises the uniqueness of Japanese culture,which is greatly significant in today’s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Zhou Zuoren;Japanese culture;Shinto belief;social customs and folkways;spiritual heritage
I 206
A
1674-5310(2010)-05-0055-06
2010-04-12
胡焕龙(1960-),男,安徽凤台人,淮南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①本文系2009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日本大手前大学共同举办的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责任编辑胡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