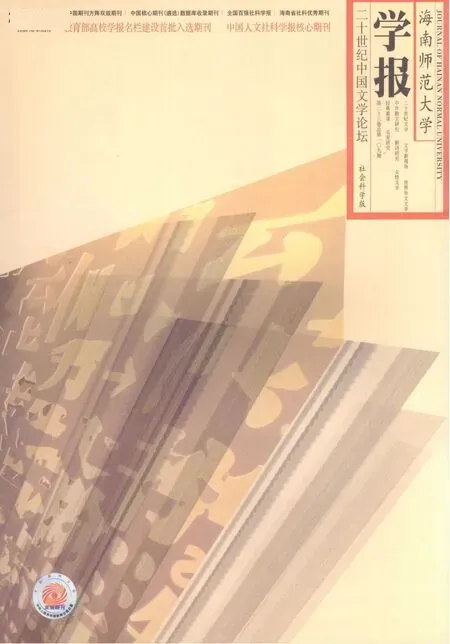论知青小说的叙事模式
2010-04-11侯桂新
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论知青小说的叙事模式
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80年代主流知青小说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通过选择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以实现创作群体在社会上寻求自我定位的意识形态企图。小说对往昔苦难的“真实”描写与有意回避,目的是将苦难转化为价值重建的精神资源。作家们的叙述,不是指向以往,而是指向当下。
知青小说;叙述角度;叙述姿态;社会空间;价值重建
一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转移城市人口、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文革”始终,在事过境迁之后,也随着对“文革”的全面否定而被总体否定了,然而这只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被称为“空前的民族大浩劫”的动乱年代,却造就了一代知青文学蓬勃发展,尽管这点文学上的成就与整个历史的代价相比未免显得过于渺小,然而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看,却也是一种值得深省的收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知青小说几乎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表明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主要来自于给读者造成一种强大的情感冲击。知青小说的作家们,源自个人和社会的双重需要,在经历过初期短暂的伤痛与悲吟后,迅速获取了一代知青代言人的身份地位,①由于相似的人生经历与心理体验,知青作家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作为一代人代言人的身份最为明确。如郭小东在《论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中所说:“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他们背后有一堵密密麻麻的巨大的人墙,一堵由他们的同时代人,千百万知青组成的已经沉默且沉思着的严峻的人墙。他们是作为这‘人墙’的代言人出现在当今文坛上的。他们是这一代人浓缩了的身影。”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以他们区区数百篇的小说作品(绝大部分为短篇),概括了整整一代人上下十余年、纵横数万里的没齿难忘的“独特”生活。对于有过知青经历的读者而言,阅读这些小说无异于一次对往昔生活的重访和温习,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寄托;而对于别的读者,他们阅读知青小说,则可透过纸面,了解一代人的生活甚至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知青生活,可以说是知青小说引起人们兴趣的焦点所在,而情感的抒发和诉求,则是知青小说引人回味的灵丹妙药。从总体上看,知青小说是一种“抒情”文学。
为了达到最佳抒情效果,必须选取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和叙述姿态。陈村曾写过一篇《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写一个昔日的知青从城市重返乡村旧地,追忆往昔生活(主要是一段爱情生活)。仔细分析小说的题目,可以发现知青小说吸引人的最大秘密所在。“我”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第一人称叙述的选择,最大目的与效果即在于直抒胸臆,加强作品的真实感。“曾经”一词点明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时间距离,彰示叙述是通过一个抚今追昔的回忆的姿态来进行。“这里”本来应该是“那里”,指知青往日上山下乡的生活所在地,表明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空间距离。之所以说“这里”,同样是为了使叙述更加迫近对象,增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生活”是几乎所有知青小说描写的重点内容。因而,“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这一完整的表述,包含了知青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姿态、叙述时空和叙述内容,“一个知青叙事者通过回忆书写上山下乡时期在异乡的知青生活”,这一叙事模式可以用来概括大部分80年代的主流知青小说。
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四季郁郁葱葱,遍地是涓涓的清流。(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明明是在回忆“彼时彼地”的“生活”,却通过特定的叙述视点和手法,尽量拉近时空距离,使回忆不露痕迹,让读者对作品的描写感觉既新奇又可信。叙述者暂时远离了当下所居城市的一切,全身心地浸浴在对往昔的追怀和咀嚼中,并引导读者一起参与他们那过去了的“可歌可泣”的生活。知青小说正是这样,在极力追求“真实”的基础上,去实现其或隐或显的诸般意图。
二
大部分知青小说选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增强作品真实性和感染力。不过,从总体上看,知青小说对叙述人称和视点的选择经历了几番变化,①不能说这些变化发生在所有知青作家身上(部分作家往往钟情于某一人称的写作,前后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中有反复),在同一时期,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所有或绝大部分作家采用同一种叙述人称的情形。不过,将知青小说按年代排序,确实可以发现叙述人称的变化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带有某种规律性。而这些变化暗寓着作者主体意识的发展,以及他们对过往生活的认识过程与评判变化。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知青小说的发展历程。
“文革”后最早产生的知青小说大多属于“伤痕文学”的范畴,或者说“伤痕”阶段是知青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它在时间上大约只跨越了1978-1979年。这一时期的作品,“以一代热血青年被蒙骗和愚弄的愤慨和悲哀,抒写出由狂热转入怀疑、苦闷、迷惘和愤怒的知识青年的心”,“它的主要内容是揭露,主要情感是愤怒”。[1]《伤痕》(卢新华)、《在小河那边》(孔捷生)、《聚会》(甘铁生)、《生活的路》(竹林)、《蹉跎岁月》(叶辛)等是其代表。这些作品在整个知青文学中可说是“时代气息”最浓的,它们以强烈的揭露和控诉,将“文革”“血雨腥风”、“颠倒黑白”的残酷历史另作一番只经粗浅加工的文学叙述,将新政权对历史所作的现成结论再行印证一番。它们揭露和批判的,不外是“文革”实行的错误的“左”的政治路线、“反动血统论”对人的侵害,以及“文革”留下来的思想遗毒。批判的目光,大都集中于社会-政治层面。这一阶段,以批判为主题的作品,几乎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形态,固然如许多论者所言,伤感和愤怒是其基本样式,然而,我以为,在其情感底色中,“屈辱”也许占了更大成分。
一代知青是在下乡后开始长成的。在下乡前,他们还是一群“未成年人”,心智远未成熟,理想与盲信交织,对事物难以作出自己清醒独立的判断。遵从“伟大领袖”的教导,②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满怀豪情壮志,憧憬着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下乡后,壮阔的理想在贫瘠的现实中碰壁失落,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岁月的蹉跎和生命的虚耗,这才发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彻头彻尾的欺骗。人一旦受骗,尊严遭到严重亵渎,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先产生的必然是莫大的不可遏制的愤怒之情。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而言,受骗后强烈的屈辱感则更加深沉,持续时间更长,也更令人难以忍受又难以启齿,是一种莫名的痛。文学作品描写愤怒易,表现屈辱则难,因为愤怒针对的是外部对象,而屈辱则作用于自身。对屈辱的表现,需要严厉解剖自我灵魂、深刻自省的勇气与冷静多思的头脑。而且,对屈辱的正视最后势必发展到对自我进行忏悔,这对一个“受骗”的主体无疑是残酷的。处于“伤痕”阶段的知青小说,在潜意识中对这种屈辱和自忏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回避处理,而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正是回避的一种方式。已经成年的知青作家,对未成年时感受过的深刻屈辱记忆犹新,但却通过讲述“他”或“他们”的故事,无形中与作品中的人物拉开了距离,使得对苦难的叙述显得更加“客观”,从而对揭露的主题加以强调,而避免正视自己赤裸裸的灵魂。对苦难的回忆本身也是令人痛苦的,但第三人称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相比,却无疑可以降低情感的热度与浓度,多少让人好受一些。这些小说通过讲述“无辜者受骗”的故事,让人物获得历史的宽宥而无须承担历史的责任,正如卢新华一篇小说的标题所示:《上帝原谅他》。其内在的逻辑便是:因为他还是孩子,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是无辜的,应当得到生活和历史的原谅,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这期间的知青小说,便是通过这样的逻辑叙述,为知青一代寻求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在倾诉苦难的过程中卸掉历史重负,相对轻松地进入现实生活,这可以说是它们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
由图2可知,酸奶的稠度可以很好地表示酸奶内部流动性,稠度越大,其流动性越差,可表现酸奶凝固程度的大小。黄精酸奶的稠度随着蔗糖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蔗糖添加量6%时酸奶稠度最大,凝固型最好;酸奶坚实度是反映酸奶强度的重要参数,表示酸奶表面成型受外力破坏所需的压力,黄精酸奶坚实度随着蔗糖添加量的增加变化不明显,在蔗糖添加量为6%时坚实度最大,黄精酸奶的强度最高。
尽管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的策略,一些小说文本还是留下了明显的裂隙。卢新华的《伤痕》(1978)向来被推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但这篇作品中“控诉历史”与“忏悔自我”两个主题处于矛盾交织的状态,这一矛盾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小说描写了一出因为主人公盲信出身论、与母亲“划清界线”、与家庭决裂而造成的生离死别的悲剧。从具体描写看,作品重点写的是主人公李晓华因一时错误的举动而遭致的悲惨后果,以及她为此产生的强烈忏悔与苦痛。然而在作品的最后,母亲的死固然带给她巨大的伤痛,同时却也让她通过醒悟摆脱了自我内心谴责,她在心中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样,她就通过将责任推还给历史本身(具体责任者是那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小拨“坏人”),获得了自我解脱,重新拥有了正常的生活权利,向着未来而“大步走去”了。就整部作品来看,叙事者对人物的态度难以统一,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时期的知青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微妙的置换,争取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并初步建立起一个面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参与的主体自我。
这样就迎来了知青文学的第二个阶段:反思阶段。在时间上,它横跨80年代前中期。反思即是反思“伤痕”的由来,这是在面对伤痕进行一番哭诉与抚摩从而获得相对的心理平衡后顺理成章的后续。自然,“伤痕”型知青小说中也存在反思,如上述《伤痕》中自我忏悔的主题。不过只有到了第二个阶段,大规模的反思才开始出现,反思的意识才更为明确与强烈。在第一阶段知青文学对伤痕进行展示后,此期便面临着为伤痕的产生寻找社会与个人、历史与文化缘由的现实任务。同样,在伤痕阶段知青小说为知青确立了在现实中的合法性,此时便要为他们在现实中寻找到确定的位置。总结历史教训,寻求人生出路是此期知青小说的根本任务。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知青小说有《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南方的岸》(孔捷生)、《绿夜》、《老桥》(张承志)、《世界》(晓剑、严亭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等。其中的一些作品,由于描写了对城市庸常生活的拒斥与对乡村田园生活所蕴涵理想的回溯,又被称为知青文学的“回归”。此期作品对知青自身精神建构与成长历程作出了持续探索。在这一阶段,知青小说选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大大增加,开始大规模地讲述“我”和“我们”的故事,标志着特定知青群体主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发挥功能。第一人称叙事特具的自叙传特点与效果,强化了知青作家的代际与群体意识,使得知青文学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所指的文学类型。然而,第一人称叙事具有双刃剑的效果,在加强主观抒情以增加作品真实性的同时,势必对理性反思的深度与彻底性有所损害,阻碍它达到本来应当达到的高度。反思的不够彻底常常成为知青一代心中难以明言的隐痛,因为这样一来,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历史合法性的证明始终因不充分而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一个历史不够“清白”的主体,在现实中必然是内在虚弱的。
80年代中期以后,根据题材与主题的拓展深化,一些评论者认为知青小说出现了“非知青化”的转型。[2]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与阿城《棋王》以此被认为是不典型的知青小说。事实上,像《桑树坪纪事》一类小说,虽然描写重点由知青转向农民,但视点却异常明确,即通过知青的双眼去看与之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农民。相对于人称,更为内在的视点也许对于知青小说更具统摄意义,对于表述“知青意识”更具决定性价值。[3]而《棋王》的叙事者是知青,描写的是知青生活,原本应视为典型的知青小说。一些论者由主题入手对文学进行分类是很没有道理的,规定某一类文学只能表达某一种或几种主题无疑是荒谬的。将《棋王》等排除在典型的知青小说之外,恰恰说明了知青文学主题的分化加剧,预示着知青这一群体的分裂与离异。
90年代的知青小说已经不再具有某种思潮或类型的效应。零散的作品宣告着知青群体意识的进一步裂变,具有众多共同性的知青群体主体已经难以寻觅。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作品对人称和视点的选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综观知青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叙述者“我”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同步成长的,他们在精神意识上具有某种同构性。这可以归因于时代的发展。在打破“文革”僵化的思维模式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知青作家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并把这种认识成果同步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从这一角度说,知青小说的作家们是在完成对作品人物成长故事的叙述后,最终完成了自身的成长历程。而作者与作品的人物处于同一认识水平,必然使作品的思想性大打折扣;以今日之认识赋予昨日之人物,也易给人虚假的感觉,使作品的文学性受损。作者这样做,源于对文学功利性的过度强调(用文学总结社会与历史,充当时代的“传声筒”)。以此,知青小说虽一时轰轰烈烈,能够流传久远的却很罕见。
三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里”,面临的是知青小说的空间叙事。对空间的叙述既包括自然空间,也包括社会空间,后者更是知青小说表述的重要内容。
知青小说笔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格化了,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们或作为被征服的对象,寄托着青春生命的价值(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或作为大地母亲的化身,在安抚知青那颗躁动不安灵魂的同时提供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青草》);或象征某种个人无法把握的人生境遇,让人物面对自身处境对存在进行反思(孔捷生《大林莽》)。正是在与自然的对话和碰撞中,人物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并进而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知青小说对社会空间的叙述,即对知青异乡生活中所面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叙述,集中在两个方面或说两对矛盾上:知青与农民(农场或兵团人员)的关系、知青与知青的关系。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原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和农民的关系应当是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关系,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知青与农村这一环境通常格格不入,和农民常常处于相互教育以至对立的地位。他们眼中的农民形象,时常具有滑稽可笑的意味。如《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这样描写队长和书记给知青留下的第一印象:“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走在最前头。书记披着干部服,左胸别着两支钢笔。队长穿着干部服,左胸别着一支钢笔。”知青们在村子里有自己这一伙人的“聚居点”,往往远离农民的住所。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尽可能坚持自身从城市带来的生活方式。除了在队长口哨声的命令下被强迫和农民在同一块天地里一起进行“修地球”的无穷无尽的体力劳动外,在精神气质和思想上他们和这一方土地并无深刻的有机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在此处,心却始终游离在农民的视野之外。尤其是后来下乡政策出现松动,各种招工、招生的机会来临之际,他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农村的“过客”,不可能真正融入这一片土地。对于自己接受再教育者的身份,他们的认识也往往充满矛盾,很少有人真心认为农民可以担任他们的教育者的。相反,他们目睹农村的落后与农民的蒙昧,常常依靠自身所掌握的一点科学知识,进行垦荒、科学种植、修路、建水坝等,通过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用事实来教育农民。在此过程中,城乡文化交流得以发生,但对于那些“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的农民来说,这种交流只能发生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在贫瘠土地上困苦生活的农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一个让知青啼笑皆非的水平上,他们把知青看作来抢自己口粮的一拨人,因而自然而然产生了敌意(《桑树坪纪事》)。
与异乡家园的格格不入,加强了知青的群体意识。同甘共苦的经历促进了友谊的萌发。处于青春期的个体天性渴望理解、害怕孤独,在一个陌生的天地里,这种意识更为强烈,于是,不管原来相识或不相识,他们互相走近,自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知青小说写的大多是“我们”的故事,对知青友谊的书写成为许多作品的动人之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广阔天地的一角》(王安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都对这一主题有鲜明表现。然而,另一些知青小说文本又解构了这种友谊的“纯洁”性。为了回归城市而明争暗斗、背叛朋友(《杨柏的“污染”》(徐乃建)中“君子国”的消失、《69届初中生》(王安忆)中热情的恩人成为陌生的路人),或者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世界》中“七条半好汉”踏上各自的征途、《但愿人长久》中八姐妹从一起居住的草房子里一个接一个远去),这种友谊得而复失的经历成为知青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苦涩。
为了更好地理解知青文学的空间叙事,不妨具体分析几部最重要的对农民和乡土进行重点描写的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3)被誉为一首温馨浪漫的田园牧歌,它“寓庄于谐,寓悲于喜”,以“拙朴愚钝其外,博大精深其内的表现方式”,“把‘我’与陕北人民的那种崇高的情感顶礼膜拜,抒写我们坚韧的民族气质和纯洁的人性道德”。[4]小说受到广泛好评,源于它散文化的亲切笔调与对情感温和的处理方式。它一反早期知青小说激烈的抒情方式,代之以娓娓而谈的诉说,以记忆之线串起众多生活细节之珠,情感深沉而悠长,与被描写的对象——浑厚博大的黄土地显得相当和谐。小说中的“我”较深地融入了那片土地,我与“破老汉”的情谊也显得亲切自然、真挚动人。不过,在表面的平静下有锐利的隐痛,因插队生活而双腿残废的“我”虽然能够达观地面对生活,却不能不时时想起生活本身的残缺性。再者,小说在充满深情的回忆中对作品中的人物多少有一些美化,为了文本的和谐而牺牲掉部分“生活的真实”。
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1985,加上《桑塬》、《福临和他的婆姨》与《私刑》,共同构成“桑树坪”系列)博得一片喝彩,源自对农民悲苦生存境遇与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对历史的深挚反省。作品选取第一人称视角,但把表述重点由知青转向了农民。虽然是透过“我”的眼光去观察桑树坪众生相,对乡民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不过,叙事者与对象大体处于一种平等对话的位置,没有许多知青小说中常见的明显的优越感。当然,叙述者不时所发出的悲天悯人的感慨,多少破坏了这种平等关系,同时提醒读者知青叙述者“自我”主体意识的顽强存在。[5]作品中的“我”显然拒不接受被派定的接受再教育者的身份地位,他对农民有同情,积极介入他们的生活,但又相互提防,必要时他会为了扶持弱者而利用乡下人怕官的深刻意识,拿自己的父亲来威慑生产队长李金斗,迫使他放弃对弱小村民的惩罚。
李锐的《厚土》(1986,共包括《锄禾》、《古老峪》、《合坟》、《假婚》、《选贼》、《眼石》、《看山》等七个系列短篇)
叙述重心更进一步,几乎完全转移到农民身上,可以说是知青小说中描写农民最本色的作品。在《桑树坪纪事》中,“我”和李金斗等人还存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交流与对峙,而《厚土》中的“他”几乎成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对农民生活与观念的变动毫不起作用。《厚土》中的人物都没有名字,没有个性,像一群丢失了“自我”之魂的生灵,浑浑噩噩地生存着。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忍受生活中难以忍受的屈辱(《眼石》中两个男人通过性的交换重新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假婚》中的男女进行食与性的交易、各取所需;《锄禾》中的女人为了一点生存利益委身于队长并充当男人之间的润滑剂),将生活本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使道德臣服于生存的需要。人物对于主体自我没有意识,而处于“厚土”底层的女人更只是作为男人世界的工具而存在。[6]作品给人的感觉,似乎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是一汪死水,亘古不变,偶然激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又立即复归于平静。这样的生活,给人深深的震撼。仿佛是受到这种生活的感染,作品中的知青,其主体意识也处于一种模糊与消退的状态。他无法进入农民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以及与农民的交流方式。在《古老峪》中,工作队队员小李自告奋勇加入乡亲们的劳动当中,结果使得双方都难堪异常,只好狼狈而退。他对那个有着一双黑亮眼睛的农家姑娘抱有希望,见她听文件时非常认真,于是提议让她当先进代表,结果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啥也听不懂,我是看你念的好看。”这种描写,“揭示出了那种游离于农村现实之外、又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书生文化意识,在面对真正的农民及其生存处境时所显露出来的虚妄和无能。”[7]而作者选取第三人称叙事,并将作品中的知青设置成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式人物,大概正是出于对这种虚妄和无能的无奈吧。
四
上文的论述已经从知青主体意识以及知青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对知青在农村的生存状态有所揭示。推广而言,劳动、“阶级斗争”、恋爱与思考,是知青生活的主体内容。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知青生活都处于一种严重“匮乏”的状态。对贫苦生活的描写是相当一部分知青小说的重要内容,而且往往通过劳动的艰苦与饥饿的强烈相对照,突出对苦难的刻画。不过,知青小说在进行饥饿描写时只注重知青自身感受,似乎没有一篇作品对终年劳苦的农民的饥饿感受进行过描绘。知青精神上的饥饿主要表现在无书可读,由于绝大部分理论著作与文艺作品都被打成“毒草”,知青要找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因而,书在他们眼中简直成了神物,为了得到一本书,他们甚至不惧杀身之祸。在《黑夜·森林·傻青》(吴欢)中,主人公为了一本书在黑夜步行数十里,在归途中与两匹狼展开殊死搏斗,虽然保住了性命,却遗失了珍贵的书。而《红樱桃》写的更是因书而起的生命毁灭的悲剧。知青精神上另一方面的饥渴则源于被剥夺了爱的权利,造成情感上的匮乏。《赫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乔雪竹)写了兵团领导对爱的桎梏与仇视,以及由此引发的青春夭折的悲剧,平缓的叙述潜流下,潜藏着作者对那一段历史错误路线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可以说,知青小说所着力描写的,正是这种物质精神的双重贫乏与情感需要无法满足的悲惨境遇。
对于这一段充满苦难、禁锢与屈辱的生活,知青作家前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伤痕”阶段的知青小说对它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将它叙述成一个“噩梦”,有意忽略生活的丰富性,对于生活中必然同时具有的亮点还来不及发掘。然而,对历史的彻底否定意味着同时也否定了他们自身的青春。到了“反思”阶段,知青小说对这一思路进行了反拨,不管经历的是怎样的生活,青春作为一种先验的正面的价值形态得到了肯定。作品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立足于现实回味旧梦,从失落的青春中追寻流逝的岁月珍贵的馈赠,并从中找到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坐标”,于是,“旧梦由不堪回首变作不能忘记,对苦难岁月中美好东西的深情眷恋代替了对生活全盘否定的片面的诅咒”。[1]也许张承志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众多知青作家此期对昔日生活的评价:
我不以为下述内容是一种粉饰的歌颂: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痛苦、思索、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8]
类似的表述相当常见,如“无论后世以什么标准,从何种角度去评价,事实都无可变更——它铸造了一代富有特质的中华儿女”(孔捷生)、[9]1“正是那段经历,造就了我们,使我们在新的生活中,充满拼搏、向上的激情。我们既然经历了那样的岁月,我们也同样能够迎接并开创新的生活”(甘铁生)、[9]225“不必夸大他们的功绩和美饰他们的品质,但那穷乡僻壤、天涯海角里成熟的心智和肌骨,将烙印于中国直跨入下一个世纪的历史”(韩少功)、[9]241“能当一个知青,应该讲是幸运的,虽然我当年并不这么想”(陈村)、[9]317“有人说这是蹉跎时光,而我却以为正是那生活的艰难困苦,那使人寒颤的歧视、压制,那山里人的纯朴、勇敢,以及大山、森林、溪流的庄严雄浑,给我们启迪,把我们锤炼、陶冶。在那里,我们所得到的比所付出的,要多得多……”(李海音)、[9]529“我感谢冀中平原那密密实实的青纱帐,它把我领进生活,教会我永远喜悦人生”(铁凝)。[9]851
这些认识自然都是源自现实的需要。它们从“独特”与提供给日后生活的认识价值两个角度入手,对昔日的知青生活进行回味、发掘与肯定。在这里,撇开当时生活的具体内容与给人心灵带来的诸般复杂感受,单单是生活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本身,便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样,知青小说便将往昔的苦难转化为一种今日价值重建的精神资源。尽管在此过程中必然具有某种回避、虚幻和自欺的成分,但这种转化却是必要的。现在,再来看看“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的完整表述,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一陈述直接针对着“现在”,对往昔的追怀其实也构成对现实思考的一部分。知青小说也许在阅读效果上使人真切地沉浸于过去,然而知青作家们对自己的位置与处境异常清楚。他们所有的叙述,不是指向以往,而是指向当下。
[1]刘思谦,孔凡青.旧梦和新岸的辩证法——关于知青小说的回顾与思考[N].文艺报,1983(7).
[2]李运抟.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发展趋势探讨之二[J].文艺评论,1988(2).
[3]李运抟.知青视角:知青文学性灵之弦——新时期知青文学评价之三[J].文艺评论,1988(5).
[4]北帆.论史铁生小说的艺术变奏[J].小说评论,1987(4).
[5]贺绍俊,潘凯雄.桑树坪里话“自我”——朱晓平部分小说创作漫评[J].当代作家评论,1987(3).
[6]段崇轩.“厚土”底层的女人们[J].文学自由谈,1989(5).
[7]陈坪.深切的体察与理解——评《厚土》的艺术追求[J].当代作家评论,1987(4).
[8]张承志.我的桥[J].十月,1983(3).
[9]贺绍俊,杨瑞平.知青小说选[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The Narrative Mode of Educated Youth Novels
HOU Gui-x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In the 1980s’,the mainstream of educated youth novels laid much emphasis on social utility.By choosing a special narrative mode,the educated youth writers intended to seek a right social position for themselves.The writers avoided describing their past sufferings faithfully so as to be able to turn the suffering into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value reconstruction.The purpose of such a narration is not geared to the past,but to the present.
educated youth novels;point of narration;narrative attitude;social space;value reconstruction
I 206.7
A
1674-5310(2010)-05-0049-06
2010-09-06
侯桂新(1976-),男,湖南安仁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