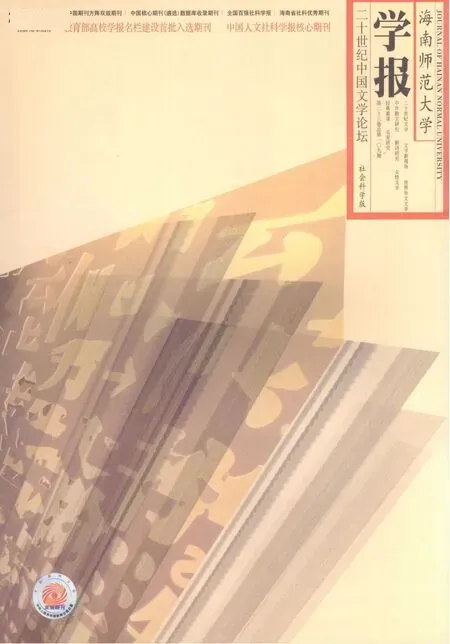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交织下的女性形象——析铁凝小说《笨花》中的三组女性形象
2010-04-11王宁宁
王宁宁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北京 100081)
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交织下的女性形象
——析铁凝小说《笨花》中的三组女性形象
王宁宁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北京 100081)
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似乎是以“第三性”(即超性别)的视角撰写的以男性为主角的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采用了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的视角、立体地审视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历史意义的女性文学。论文以小说中塑造的三组女性形象为例,说明此小说表面被遮蔽的、实际上在深层仍存在的女性视角以及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女性思绪。小说的成功正在于塑造了这些更深刻更丰满更耐人寻味的女性形象。
铁凝;《笨花》;日常叙事;宏大叙事;女性形象
铁凝擅长对女性灵魂世界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笔端充盈着浓厚的人文关怀。随着创作的深入掘进,她逐渐把日常叙事和启蒙叙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长篇小说《笨花》是铁凝新世纪的近作,是她潜心6年写出的“一部与以往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1]
表面来看,《笨花》似乎是以“第三性”[2](即超性别)的视角撰写的以男性为主角、且男性多于女性、与作者以往作品不同的宏大叙事文本,而细细研读之后会发现,小说中塑造得更深刻更丰满更耐人寻味的还是女性形象,作者仍是在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了女性的历史境遇和灵魂世界。小说虽然描写了诸如军阀混战、民国成立、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采用的是还原历史生活原生态的日常叙事,通过对笨花村的日常凡俗生活的细致描写,将个体的命运特别是将女性群体置放在战争历史的特殊背景下,表现出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境遇。铁凝曾说: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第三性”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实际上在这部小说里,铁凝是跳出了女性伦理的小叙事,采用了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的视角,立体地审视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意义。
《笨花》以向氏家族三代人为叙述主线,第一代向喜,从一个卖豆腐脑的普通农民,离乡从军,在军旅生涯中磨砺成名震四方的军阀将领,晚年隐退为一个挑粪工人,是被动地卷入历史的笨花人;第二代向文成,乡村智者,自觉地应对时代的挑战,融合新与旧的特质的一代人;第三代武备,在抗战中走向革命的一代人。实际上使主人公向喜形象更立体的是他的三位太太,她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更加耐人寻味,她们也是帮助读者解读现代女性历史文化际遇的深入点和三重维度。向文成和武备都是理想化的男性形象,似乎没有什么人格缺点,更令人深思的反而是他们身边的取灯、梅阁、小妮儿等女性形象。
下面就以《笨花》中的三组女性形象为例,从女性群像的角度来解读这部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交织起来的隐藏了女性话语的大书。
一 同艾、顺容、施玉婵——三种不同人生表现的女性
同艾、顺容、施玉婵是小说主人公向喜的三位太太,也是向喜(或说男人)的三维需要。小说似乎是写了“在笨花这个世界里,女性们自觉的遵守着男女两性的道德秩序,妻妾之间和平地共处着”的表象下的“女性许多辛酸和无奈”。[3]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家族的变迁,描写了数千年的封建体制在瓦解,乡村的生活传统面临着转型和嬗变,现代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侵袭到乡村,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下女性不同的人生选择。
(一)同艾——既恪守传统又具有现代自立思想的女性
同艾是向喜的原配夫人,是一个品貌双馨的女性。同艾的美貌和温柔体贴并没有留住新婚的向喜,向喜还是弃农从军,奋勇拼搏、出人头地去了。同艾的勤劳贤惠、心灵手巧,也没有能够留住向喜的心,向喜并不专情,他背着结发妻子取了城里的顺容。当同艾与儿子在汉口享受着自认为是嫁给向喜的“福中之福”时,人高马大的二太太顺容和两个会喊爹的儿子突袭而来,使毫无准备的同艾惊骇地昏死过去。尽管向喜给同艾打了铸有“向梁氏同艾”的金戒指,郑重确认了发妻的身份,但是爱情的乌托邦还是幻灭了,以至于多年后向喜突然回村,惊喜之下的同艾莫名患上神经性腹泻的毛病,不能与向喜亲近,似乎是洁身自好的同艾对于向喜的曲折抵触。向喜又娶了三太太,同艾不再对爱情有奢望,只留一份亲情,守望了43年,默默地抚平伤痛,越来越心静如止水。
同艾是一个背负着传统包袱的弱者形象。她承受着男尊女卑之苦,固守着家庭秩序,恪守着传统妇德的教化,无力拯救随心所欲的丈夫,也无法离开背叛自己的向大人。她是合乎男权秩序和合乎礼法规范的牺牲品。
同艾是一个悲剧的妻子形象。她不自觉地成为了封建男权秩序、尊严、门面的维持者和协作者;也是一个经济地位不能独立的无奈的顺从者。她感激向喜给与她和儿子的一切,包括有形的村里最阔气的房子和地位以及无形的人们出于对向大人太太的拥戴。
同艾是一个坚忍不屈、自爱自强的女性。她长于学习,积极接受城市人的生活理念。为了儿子文成和不被人看不起而自强自立,最终用博爱平复了受伤的婚姻创痛,以自己的宽容大度赢得了家族和村里人的尊重。
同艾是集一切传统美德于一身的母亲形象。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深明大义,做事从容不迫,为了革命同志不惜放下尊严全力营救;以博大的母爱接纳了城里女儿取灯,并支持她参加抗日。同艾几乎营造了一个圣母的形象,身上展现的尽是大善大爱。
(二)顺容——固守城市、拒绝乡村的市民女性
顺容是向喜的二太太,保定汤记茶馆老板的女儿,是一位健壮结实、泼悍固执、精于打算的城市市民形象。
向喜寂寞之时,遇到了20已过没有婆家的二丫头。“二丫头高于同艾,壮于同艾,黑于同艾。现在她穿着卡腰小夹袄,人显得倒不蠢,刚洗过的头发又黑又直,不时有一股洋胰子味儿飘过来。”[4]56城里的二丫头没有乡下的同艾漂亮,但对向喜却有某种现代气息的诱惑。
顺容和向喜之间没有爱情,顺容只是向喜自我怜惜的补偿,是战乱年间一个男人守不住清苦而寻找的慰藉。向喜不是一个寻花问柳的男人,他需要的是可以调教的良家女子。顺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向喜军旅生活的犒劳品或慰藉品。
对于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向喜而言,传宗接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艾只为他生了一个文成,还有眼疾。“二丫头的腰壮,能生孩子。”[4]56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顺容成了向喜偷偷娶下的二太太。实际上顺容也是向喜的生育工具,她争气地生了两个体面的城里儿子。
顺容与向喜不仅在餐桌上、生活中不协调,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品行、民族大义方面不协调,二人是貌合神离。
当然顺容有她善良包容的一面。她给予了非亲生女儿取灯无私的母爱。同样忍受了丈夫的背叛和离弃,最后独自孤苦地守着空屋生活。
顺容也是男权秩序和婚姻的牺牲品。她在不知向大人有家室的情况下嫁给了他。突袭同艾之后,自己也未能留住丈夫的心。向喜娶了三太太,她也不再去闹。因为她根本无力与男权社会抗争,也无法管束丈夫。她同时需要依靠向大人,所有物质的来源,养育孩子和赡养父母的费用都要依靠丈夫,她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何况还是一个苟且偷生之人。
顺容是无论如何不会跟向喜回乡下过日子的,她是一个拒绝乡村、贪图安逸的城里人。在抗日斗争中,她是非混淆,绝没有同艾的民族气节和勇敢行动,是个苟安的没有灵魂的市民形象。
(三)施玉婵——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现代女性
施玉蝉是向喜的三太太,一名技压群芳的走钢丝名伶。她年轻挺拔、神情大方、浑身洋溢着快乐。向喜对施玉蝉一见钟情。施玉蝉执意要行走江湖,不巧遭遇海盗,为了生存不得不投靠向喜,作了向喜的第三房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取灯。但女儿3岁时,崇尚自由的施玉蝉又重拾技艺。
施玉蝉不像同艾、顺容一样逆来顺受,甘受命运摆布,她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具有积极入世的品格和能力。她没有兴趣做贤妻良母式的典范,也不需要一味地依附男人;她身怀绝技,可以自食其力;她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同,她宁可放弃母亲的责任和丈夫的宠爱,她的身上显现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和追求独立的现代意识。
铁凝对施玉蝉着墨不多,却充满赞赏和肯定。向喜面对如此执着于事业、秀外慧中、执意不依附男人而特立独行的三太太,无计可施,只能尊重其选择,既憎恨又敬重其所为。作为艺人的施玉蝉拿得起放得下,与向中和大人和女儿一刀两断,一心一意扑在玉鼎班上。施玉蝉在追逐自我价值体现和社会价值认同的过程中,也永远舍弃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母亲的天职。
实际上施玉蝉之于向喜,不过是向喜发迹之后,买地置房、娶妻纳妾,炫耀男人身份与价值的一种标志。施玉蝉是向喜奢侈生活中的快乐情调,是成功男人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装饰物而已。只是施玉蝉并不甘心附庸向大人的情调,也不想常年做一个附属品。这里彰显的是打破女人依附男人的封建秩序,实现男女性别平等的现代意识,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可以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独立精神。
二 梅阁、小袄子、取灯——三种不同人生追求的女子
与其说“梅阁、小袄子、取灯她们三位象征天堂、地狱、人间三种境界”,[5]不如说是铁凝对于中国女性在中外文化撞击和融合下的三种不同人生追求以及现实选择的深入思考。
(一)梅阁——笃信上帝的病圣女
西贝梅阁,向喜邻居西贝牛的长孙女,在县里上女师时迷上基督教,虔诚地信仰上帝,笃信“人世间的事,不论善恶,惟有上帝才会做铺排”。
梅阁,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一心信上帝,做些让村里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在雨中不慌不忙地散步),说些让家里人不知所云的话(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她是村里唯一不顾世俗非议、接受受洗仪式的基督教徒。
梅阁,一个富有爱心的传教者,常在寒冷的冬季召集一些女伴,共享《圣经》故事;村里女伴“觉得受过洗的人就不再是人,身上好像笼罩着一层仙气,遇事阴阳怪气”。[4]240
梅阁,一个体弱多病的不会做农活儿的另类农村女孩,实际上也是外来文化、基督教文化对河北农村产生影响而水土不服的一个真实写照。除了信仰上帝,现实中她只信任瑞典传教士山牧人和智者向文成。在她心里,主是人类最后的幸福,是最终的归宿。
宗教是患病的梅阁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她躲避尘世混乱和喧嚣的唯一港湾。她相信死亡是靠近天堂最好的捷径,也是最好的解脱。“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救主,我信他听他话我的主耶稣。”[4]460病入膏肓的梅阁甚至感到,“自己离主更近了一步,主就在天国向她招手。此时日本人的来与不来对她来说已是微不足道,假如由于日本人的到来能促使她进入天国,这岂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4]463梅阁唱着天国之歌“假神去了,真神来了,天堂之光永照耀”,死在了日本兵的“排子枪”之下。同艾说得不错:“也许这孩子真得救了,也好。”[4]469
对现实充耳不闻,对基督的笃信,让梅阁走向了不归路。对信仰的皈依,并没有使梅阁摆脱悲剧的命运,她的生命是不沾恶的,但罪恶并没有放过她。她用信仰摆脱了村里人和家里人的桎梏,摆脱了男权文化的压制,她用死亡靠近天堂,得到了自我解脱,却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我解放。因为她的奇怪的言行,笨花村没人理解。她代表着一种虽崇高但病态的人生追求,也是一种思想基督化了、不服中国水土、不切实际的女性现实存在。
(二)小袄子——追逐虚荣的淫荡女
小袄子,寡妇大花瓣的女儿,聪明伶俐,天真俏皮,从小崇尚物质享受,对村风野俗谙熟。在小袄子身上较多体现了女性原欲的躁动和生命原始真实的激情。她为了挣花勾引规矩的佟继臣,为了追时尚买新衣搭上有妇之夫金贵。她一面认同抗日,一面与汉奸勾搭,摇摆不定。
小袄子机灵过人,日语一学就会,关键时刻能用日语缓解日本人和村民的紧张气氛。她不甘寂寞,报名上了夜校。她虽认同妇女解放、向往自由,却有坐享其成、追逐时尚的天性;她为抗日做过贡献,可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清醒自觉的行为,是为炫耀自我。她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和人格尊严,以身体为手段换取男性在情感和物质上给予的满足,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素日放纵的小袄子在基督教善恶观的影响下,曾承认自己“淫乱”:“我就整天觉着有魔鬼牵着我往地狱里走,我背过的片儿上画的地狱,可叫人害怕哩。”小袄子在利用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被人利用。她一方面真心敬重取灯,一方面又经不起利益的驱使而出卖了取灯;她得到的是死到临头仍不知醒悟的被处决的可悲结局。
在小袄子身上,流露出铁凝对女性所遭受的性和政治的双重压迫的悲悯以及对于女性生存境遇和女性命运的批判性思考。小袄子的悲哀在于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女人,在于她太过追求物质的虚荣。她曾经追求过革命,但是最后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小袄子是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对于社会规定的淑女形象的悖反,她不矫揉,但风骚;她聪明,但肤浅;她机敏,但功利;她不乏人情味,但没有是非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在日常叙事里小袄子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放荡女人,但是放在宏大叙事下她就是一个自绝于人民、丧失气节的淫荡女子,和日本汉奸合伙出卖了革命者,最终死在荒郊野外,仿佛堕入地狱般的咎由自取。从文学意义而言,小袄子是一个具有复杂丰富魅力的文学形象。
(三)取灯——积极入世的巾帼女
取灯是向喜和三太太所生的女儿。取灯是笨花人对火柴的叫法,取灯是个光亮儿。取灯在向喜眼前玩耍,向喜自觉眼前就闪烁起光亮。取灯的性格是开朗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母亲的性格。取灯3岁时,亲生母亲离家追求自己的事业去了,但是她并不缺失母爱,先是得到了保定顺容妈的关爱,接着获得了笨花村同艾娘的疼爱。
取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新式教育,是有教养的美丽“洋花”。在日常叙事下,取灯是一个走在人间正途的常态化的才貌双全的完美女子。
取灯从城市到农村,被同艾娘的处事风格和向文成大哥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最终扎根乡村,这是作者亲近乡土、某种程度上流露出都市文化折服于乡土文化的倾向。取灯在笨花村找到了根基的感觉,她脚踏实地,积极进取,为人大度,对中国革命有着崇高的信仰。她满怀热情投入到抗日斗争中,组织夜校,团结村民,感召并鼓励当时心忧天下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
取灯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投身战争,选择了伟大的解放事业,巾帼不让须眉,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永恒。她对革命的信仰,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哪怕是出卖她的小袄子,内心里也是真心敬重她的品行。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死亡是必然的,战争中女性的死亡更是让人怵目惊心。取灯越是出色,越是受人爱戴,她被日本人强暴和残杀的惨状就越是让人无比痛心。女人在战争中的牺牲不仅仅是生命的消失,而且还有人格与尊严的污损,这里表达了铁凝对于战争中的女人受到战争摧残和男性虐待的双重伤害的思考,女人并不会因为投身男人化的战争而丧失了女人的性别特征。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战争中的走正道的女人比男人要付出得更多。
取灯是脚踏实地的抗日女英雄,她死后,有敬爱她的革命同志西贝时令拔枪杀仇,有大哥的痛惜,弟弟们和侄子的深深敬仰。她是在宏大叙事下而成就的女中豪杰。
三 大花瓣、小妮儿、元庆媳妇——三种不同人生际遇的笨花女
大花瓣、小妮儿、元庆媳妇是笨花村里的底层女性、弱势群体,不能仅仅把她们说成是“乡风民习使女性在常态下沉沦”的“第二性”,[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也是活出了各自精彩的笨花女。虽然她们出身卑微,但毕竟还是作为与男性同等的“人”的形象而不是什么狐仙形象获得了铁凝的认可。
(一)大花瓣——爱憎分明的寡妇
大花瓣是笨花村一个风骚美丽的寡妇,她常年吃着西贝小治打猎来的兔子,和小治靠着,也常年消受着西贝小治媳妇的房顶叫骂;她和村里花主向桂混着,常年以钻窝棚挣花为生计。
大花瓣,是小说里最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之一,是乡村野俗的代表人物。窝棚是笨花村花主占有棉花资源的风流窝,也是一个传统文化边缘无序化的暗地堡。在窝棚里贫穷女人或好逸恶劳的女人用身体换取棉花,是一种乡村形式的变相卖淫。大花瓣不以钻窝棚为耻,她一边靠着向桂,用身体换取棉花,一边为向桂不如意的婚姻筹划,为他找来处女小妮儿,最终成全了二人的真情。大花瓣活跃着笨花村人的自由浪漫气质,缓解了传统文化对笨花造成的拘谨和古板,但她也践踏着笨花村人的家庭伦理规范和道德秩序。大花瓣以性感的身体、豪放的言行,让男性得到了短暂的生理和心理满足,而换来自己生活所需的棉花,但是在村民的心里却长久地失去了人格的尊严,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她的恶名影响到了女儿,即使小袄子不做什么也会被歧视,如果不是取灯宽容而觉悟高,小袄子几次差点被剥夺学习的权利。
大花瓣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染着污泥的笨花,她不顾及名声和操守,名声等东西就肆无忌惮地损毁着她和她的下一代。大花瓣是孤芳自赏的,在钻窝棚挣花方面不服初出茅庐的小袄子。但在关乎民族尊严大是大非面前大花瓣却比小袄子清醒而有觉悟。“大花瓣想,金贵什么人,笨花村一个没良心的男儿。”“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有良心的男儿为什么当伪军?”[4]483大花瓣儿因为小袄子靠着汉奸金贵而与她分了家。当女儿生病求到门上,她仍展现了母爱的宽容照顾起小袄子。
在日常叙事下大花瓣充其量是个敢于追求自我和自由的风尘女性,铁凝对她的生活际遇表示了理解和同情;而在宏大叙事里,大花瓣儿身上的闪光点似乎比她的劣根性更要引人注目。
(二)小妮儿——知恩图报的弱善女子
小妮儿是被大花瓣儿领来给向桂做妾的贫穷女孩。小妮儿小脸黄白色,眼球灰黄,偏瘦的身材,“脚是一双天足,倒显出她的天性天然”。[4]83这是一个不谙世事,正在发育,为了生计,被父亲逼着钻窝棚挣花的身子单薄的弱少女。她假扮内行躺在被窝里的娇小可怜,深深地打动了向桂。向桂的婚姻是不幸的,他的大房聋扔子是一个粗蛮如男人的耳聋丑妇。小妮儿与聋扔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向桂用10块现大洋收获了小妮儿父女的心,并娶了小妮儿做二房。
小妮儿是感恩的,她甘心情愿地作着向桂的妾。小妮儿在向家受到聋扔子的百般折磨,动辄就遭粗暴打骂。一次聋扔子咬掉小妮儿的一个手指头,小妮儿事后还说:“老大打我,我并不记恨老大。是我抢了她的人哪,向桂本是她的人。”[4]174小妮儿的忍辱负屈得到了向家人的同情。向桂带着小妮儿把花坊迁到了县城里。
进了城的小妮儿不用下人,自己买菜做饭,把院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向桂每每看见小妮儿伤残了的左手就心疼得要命。小妮儿是男权秩序体系的顺应者,她以柔克刚,以弱者身份示人,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几把花,贫穷的她可以在父亲的胁迫下去钻窝棚,而进了城的小妮儿视野越来越开阔,为人越来越大气。
卑微的小妮儿赢得了人们的认可,特别是同艾大嫂的赞赏,是因为她的人情多,是非少。小妮儿表面是弱者,实际上还是活出了比强者还要让人慨叹的精彩,在这里弱者不完全是不幸的代名词。小妮儿,一个命不好,但运尚可,于苦难人生中幸遇真情,虽是弱者,受人怜悯,合乎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秩序,是女性历史生存不幸境遇中的幸运者。
(三)元庆媳妇——寻到真爱的“活犄角”
笨花村的元庆媳妇,是元庆在外打长工领回的女人。所谓“活犄角”是笨花村的迷信说法,是说天上打雷,人间有个活犄角给雷公打工,打雷下雹子活犄角就会昏死过去,醒来胡言乱语,是一个不吉利的人。元庆媳妇就是土廊活犄角的后代,受到笨花人的非议而很少出门。村里的有妇之夫走动儿恋上了这个女人。
每日黄昏走动儿自东向西的“走动儿”是笨花村一道风景。元庆和儿子奔儿楼会主动出门躲避,成全走动儿与元庆媳妇互为靠家的相好。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得到村里人认同,实际上是乡村愚昧麻木、贫穷落后,以及男女关系不平等的折射。女人为了生存,不惜装疯卖傻,以身体去交换物质,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解放,是女性无处不在的所受压迫和生存境遇的体现。
抗日了,走动儿与元庆媳妇不再有闲情逸致的“走动儿”故事,走动儿做了抗日上下游走的交通。走动儿跳出了自我,表现了伟大的品格,而且在元庆夫妇死后引领其儿子奔儿楼走上抗日正途。
元庆媳妇是笨花村最底层的女性,是受到压迫的小心谨慎活着的弱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五短身材,不漂亮,不出门,不优越的女子,竟然把堂堂的走动儿迷住,让走动儿放弃干净利落、顺眼体面的原配三灵,天天黄昏在众目睽睽下去和她约会。这真是一个扭曲荒诞的故事。然而这就是铁凝所要表达的弱者不一定弱的思想的流露。
元庆媳妇的活犄角身世让家人和村里人嫌恶,她的外在条件不好,孤苦无依,然而她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以及内在力量经营起一段婚外保障。她让走动儿动了真情。在她生病,在她迷离之际,都是走动儿的真诚相助才使她得以解脱疾病和获得全身入土。走动儿也诧异是否中了她身上的仙气,怎么会单恋上这个又短又小的女人?可是“她实在是个人,她给予他的一切都符合人间的事”。[4]416走动儿珍惜着他们之间神秘的真爱。
铁凝确实让读者在女性不幸的历史生存境遇里看到了温润,看到了结实,看到了大巧若拙,看到了沉重中的轻盈,保守中的不愚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相互扶持。
四 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交织下的女性群像
铁凝的《笨花》试图以第三性写作来超越性别,但实际上还是留下了性别的痕迹,说到底《笨花》还是一部描写女性更丰满更到位更深刻的女性文学。性别是任何作家也无法超越的,只是隐蔽的程度如何。“笨花”名字本身就寄托了铁凝对于特定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女性文化的想象。
上述分析的三组女性形象是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放在一起就是铁凝把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刻画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群像画卷。
“《笨花》中出现了高大、伟岸,正义、智慧、勇敢的男子汉形象,这在她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他们如父如兄。”[6]这话有道理,但是表达得不够准确和完全,铁凝对于在战争历史语境下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忠孝品格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但是铁凝仍以隐蔽的女性视角对历史沿袭下的男权弊端和男性弱点表达了清醒而理性的批判。特别是通过同艾、顺容、施玉婵三位太太的书写,实际上是揭示了大男子主义的三维需要,一个是男权的秩序门面,一个是男性话语的补偿工具,一个是男性世界的情调饰物。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向大人传统价值观被冲撞,他对于施玉蝉的自立选择既痛恨又手足无措,既敬重又无奈,最后还是间接地死于施玉蝉的牵连。向大人最后几年孤独地挑粪的结局正是一位女性作家让他赎罪的刻意安排。
笨花女性更是在新旧文化交替下无处遁身。同艾既无法摆脱旧秩序的束缚,也能够积极地接纳自立自强的现代理念;同艾既恪守着传统的妇德,又在新的历史考验下深明大义,是一个经历了思想痛苦嬗变的有深度的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
梅阁、小袄子、取灯三位女性是铁凝笔下具有三种不同人生追求和现实选择的女性形象。有评论说:“三个女性的追求与毁灭,说明了女性解放的艰难,也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作家对女性的出路的绝望”,[5]并不准确,不符合铁凝要表现笨拙之中的“轻盈的、飞升的”[7]乐观思绪。相反,铁凝确实是“抱着对人类的体贴、善意和温暖,对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热情而执著地寻求女性自由、平等、幸福之路”的。[6]铁凝是想通过“笨花”一轻一重的人生和日子,引领读者思考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女性要追求崇高,要有信仰,应像梅阁一样坚守信念至死不渝;女性无可避免会遇到功利的现实,遇到各种物质虚荣的诱惑,不能像小袄子一样没有主心骨;女性应该独善其身,应像取灯一样优秀,积极入世。正如铁凝自己所说:“我在宏大叙事和家常日子之间找到了一个叙述的缝隙,并展现了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7]
当然,在这里铁凝也思考了在中外文化撞击和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对于中原大地的渗透。梅阁是一味地接收基督文化,脱离中国实际,造成严重的文化水土不服。六神无主的小袄子对于外来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她曾经也受到基督善恶观的震撼,但没有引起实质的内在变化;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她的摇摆不定使她左右不是人。小袄子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从她身上也流露出作者关于乡土中国女性需要精神的重建、以及现代文明进程和妇女真正解放的艰难性的思考。取灯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尊重是一种积极务实的态度,但是取灯们生不逢时,她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或说需要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人文环境。
《笨花》中的女性不是历史进程宏大背景下的强者,但是她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小说把这样一群女性置放在一个民族危机日盛一日的时代背景下,放在抗日战争生死对决之中,她们和男性一样要面对严峻的道义选择。当然乡村的包容,又让她们有了较为宽松的选择空间。因此,作品中的乡村女性,她们共同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面对传统、如何面对乡土、如何面对男权、如何面对民族大义、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等等现实问题。她们虽然身世卑微,承受了政治的、战争的、男权的、性的多重压迫,但是她们还是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活出了各自的精彩。看看同艾、大花瓣、小妮儿、元庆媳妇,她们都是笨花村的底层女性,是弱势群体,她们身上不都闪耀着爱憎分明、坚韧感恩、自省自立、互相扶助等人性的光辉吗?也许在铁凝心目中,这些女性才是真正的凡俗而神奇的笨花吧。
[1]铁凝.封二[M]//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红孩.铁凝的北京“结”和永远的文学世界[N].北京日报,2007-03-11.
[3]周利萍,肖云.也谈“道德秩序”——从《笨花》中几房太太共处现象谈女性解放[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5).
[4]铁凝.笨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张贵田.女性的性别在战争中凸显——论铁凝《笨花》的女意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6]闫红.《笨花》女性叙事的隐痛及其艺术解决[J].当代文坛,2006(5).
[7]王干.花非花人是人小说是小说——关于《笨花》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6(2).
An Analysis of Three Group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ie Ni’s Ben Hua
WANG Ning-ning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and Law,Beiji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Beijing100081,China)
Tie Ni’s novelBen Hua,seemingly a neohistorical novel themed on males in the“third gender”(super-gender)point of view,is virtually a novel of feminism scrutinizing holistically the living circumstance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femal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routine narrative and grand narrative.By sampling the three groups of females in the novel,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on the female visual angle which is concealed on the surface but omnipresent in the deep surface as well as the female thinking as shown between lines in the novel.The success of the novel lies in the delineation of those deeper,better-developed and more thought-provoking female characters.
Tie Ni;Ben Hua;routine narrative;grand narrative;female characters
I 206.7
A
1674-5310(2010)-05-0037-06
2010-07-27
王宁宁(1965-),女,山东文登人,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文法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