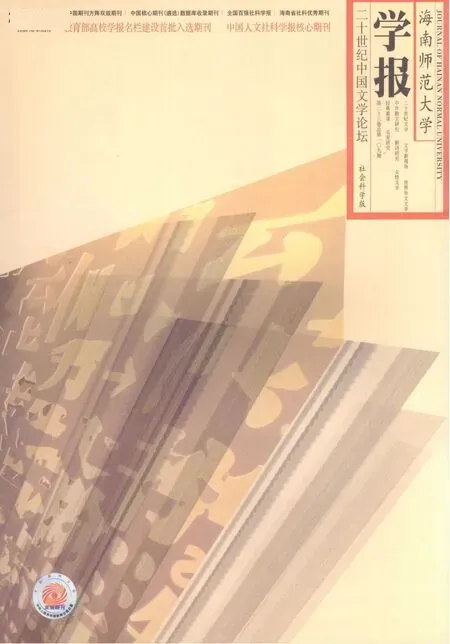爱情,以革命的名义——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革命与爱情”叙事范式比较论
2010-04-11吴国如
吴国如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爱情,以革命的名义
——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革命与爱情”叙事范式比较论
吴国如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革命与爱情”虽是十七年小说和革命文学共同的叙事范式,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创作主体、创作理念、创作特点及其发展脉络等层面,前者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开创时期左翼文学的雏形,后者显示了革命胜利后左翼文学的成熟形态。
革命文学;爱情;知识分子;悖反;缝合
历史告诉我们,文学史就是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前代文学的写作模式与审美风格并非都能在后来的现实中得以原封不动的保留,它的持存与流变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时代历史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审美风尚、大众伦理道德、受众的接受水平和文学好尚以及创作者的各种诉求等都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革命与爱情”虽是十七年文学和革命文学共同的叙事范式,但毕竟是一个复杂的语义结构。和社会环境与人类情感的密切关联,使得这种创作模式成了形势变化的晴雨表和微妙情思的症候表达。从充满狂热革命激情的二三十年代,到历史的天空已斗转星移的十七年,即使是同一种叙事范式,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一
就革命与爱情分配在两类小说里的叙事篇幅而言,两者并不相同。十七年小说由于受到建立在集体解放基础之上的、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追求目标的左翼政治启蒙思潮的巨大影响,比较强调革命目标的追求而相对警惕与之关系不很密切的其他叙事。如因担心对爱情的过多描写会冲淡革命叙事的目的和效果而对爱情叙事时刻保持抑制。爱情话语受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语法规则的制约,只能以一种象征的修辞方式作为革命话语的陪衬而存在,缺乏自己存在的独立品格。而革命文学虽然也强调以革命的手段达成革命的目的,也认识到爱情叙事在表征创作意图上的作用,但由于距离“五四”启蒙运动还很切近,受到“五四”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之上的、以现代性自我为追求目标的启蒙思潮的巨大影响,加之传统文人心态的主导,对爱情叙事普遍表现出迷恋的姿态,甚而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独立存在,爱情叙事的篇幅普遍超过革命叙事。蒋光慈曾经如此谈过:“‘革命+恋爱’小说作家们照例地把四分之三的地位专写恋爱,最后的四分之一把革命硬插进去,与初期的前八本无声,后两本有声的有声电影一样的东西。”[1]
同样是站在现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两者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带出不同的叙事效果。尽管革命文学注意到了爱情叙事在革命表达中的重要意义,但由于缺乏十七年那样的强有力的严格纪律约束和太多的政治禁忌,革命文学关于爱情的叙事明显缺乏一种理性和节制。创作者因过于注重个性的解放、主体情感的宣泄和自我意识的张扬,使小说关于爱情书写陷入一种欲望的迷恋,性的作用不仅被夸大,甚而堕入一种卑俗的自然主义式的书写,并在事实上使“革命+恋爱”的浪漫谛克叙事陷入一种主观与客观构成的悖论。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显示出这方面的迹象。单就小说的结尾来讲。革命惨遭失败,何月素“的右腿略受了一点微伤”,在革命者看来本没什么大事,但具有小资情调的她却很渴望得到爱人张进德的抚慰并颤颤地对他说:“张同志!我右腿受了点伤。”张进德投其所好,毅然“走上前去,用着两只有力的臂腕将她的微小的身躯抱起来”。于是,“何月素也不反抗,两手圈起张进德的颈项。两眼闭着,她在张进德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梦……”矫情的叙事、比较露骨的挑逗,这种情况之下,革命者“新的生活的梦”到底是怎样的?确实耐人寻味。这样的的小说结尾,也许只能存在于革命形势还不明朗、胜利的希望依稀渺茫的大革命失败后人心惶惶的革命低潮期。茅盾的《蚀》三部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型。搂抱随处可见,同居家常便饭,性爱毫无顾忌,爱情的情欲化叙事使对与性有关的描写十分传神、逼真,富有挑逗意味,不愧是得了商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擅长性爱描写的海派文学的真传。特别是三部曲里面的后两部(《动摇》和《追求》),里面充斥大量与女性乳房有关的性描写。作者本想在悲观失望的革命低潮时以性作为革命的手段激起革命者的斗志,借此体现一种人欲的解放思想和性爱之于革命的积极意义,但放在革命的语境下,却多少显得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放纵的笔墨彰显出爱情的趣味是世俗的、肉体的、物质的,甚至有点病态卑下的低级庸俗气,显然和严肃、健康而神圣的革命不相一致。当革命者因把性当作革命的唯一无奈之举的时候,这种革命被人讥为是乳房的革命、色情的革命,而非暴力的革命。在革命者看来,革命应该是暴力的才对,这种乳房、色情的革命无疑因与之相悖而失去正当性。特别是当革命者因此而患上梅毒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也就幻化成了泡影,宣告革命的滑稽与破产。于是,一种阴郁悲观虚无的绝望情调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全文,笼罩在大革命失败后阴翳的天空,像一个幽灵一样,萦绕在革命者的心里。这不啻是对革命的一个嘲讽。事实上革命文学的作者也意识到以这种方式进行革命书写确实不妥。为了表示革命高于一切的主导地位,最后总要往其中添上几笔,通过主人公对爱情的扬弃,让爱情叙事对革命叙事做出或正或反的证明,同时也用以弥补男女情爱大书特书造成的因情爱叙事对革命叙事的严重不平衡带来的喧宾夺主现象。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革命者的突变现象。这样,爱情叙事的篇幅必然超过革命叙事的篇幅。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学的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来的明清以来古代士大夫风流狎狭的情调,特别是在性上流连忘返、诗酒爱情的举止所体现的高蹈于革命之上的不合时宜的名士风流气度,无疑与他们创作的主观政治意图和自身的革命者身份构成深刻的矛盾,造成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尤其是颓废幻灭没落情调的出现,加剧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叙事效果之间的分裂。
十七年文学则竭力扼制了这一点,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叙事效果之间,在个体与历史、浪漫激情与政治理性之间进行了有效缝合。如果说革命文学放纵的笔墨彰显出的爱情趣味是世俗的、肉体的、物质的,甚至有点病态卑下的低级庸俗气,和严肃、健康而神圣的革命不仅不相一致,而且,所激起的色欲、性放纵感反而部分抵消了革命所激起的崇高感,爱情也跟着相应贬值,那么,十七年文学则用节制的笔墨避免了革命文学过于放纵的情欲描写,彰显出的爱情趣味是观念的、精神的、理念的和含蓄的,脱离了革命文学那种病态卑下的低级庸俗气而和严肃、健康而神圣的革命相得益彰。而且,十七年文学那种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的写作姿态所激起的情感也恰到好处地从一个重要方面衬托了革命的崇高和伟大,爱情也最终显得美好圣洁高尚。《创业史》里作为知识分子的徐改霞在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头人梁生宝的恋情中总是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态势。在一次两人的约会中,徐改霞“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公然挑逗的样子。然后,她把身子靠得离生宝更贴近些……”而梁生宝在这一霎时只是心动了动,对这种引诱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这个对自己倾心相爱的闺女搂在怀中,亲她的嘴,但他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有一个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小说对爱情进行了谑而不虐的叙事,在一种轻松的喜剧气氛中表达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借此对受众(特别是对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革命者并非好色之徒,一切当以革命为重,沉溺儿女私情会妨碍党的伟大事业。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避免了过于严肃的说教带来的枯燥与呆板,所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宣示效果更又是革命文学爱情描写所不及的。正因为强调爱情是革命理念载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权力话语的的规约下,自我意识强烈的小资徐改霞最后还是在梁生宝的冷落中无奈地选择了离开,以致越到后来越淡出读者的视线。角色承载的功能完成之后,必然要遭到放逐。而梁生宝对此很坦然洒脱,对革命事业的专注冲淡了与此无关的一切。悲剧的爱情很快为自己事业上的阶段成功和另一段志同道合的爱情喜剧所替代,中和的审美元素带来的乐观坚定否定了革命文学的颓废幻灭情调,也避免了《咆哮的土地》中的矫情暧昧的气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爱情的美满应该出现在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之前,怎么有心思谈情说爱呢?在个人的私欲成为公共禁忌的时候,这样沉溺儿女私情无疑是对革命崇高事业和革命者光辉形象的亵渎。十七年文学无论如何不会这样。
二
之所以如此,这牵涉到十七年小说与革命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主体的身份问题。
应该说,革命文学是一个过去正在进行时,只给了人关于“革命是美好”的承诺和愿景。它可以壮怀激烈地书写革命,可以让勇敢的革命者享受性爱的短暂幸福(韦护与丽嘉、章秋柳与史循),体会爱情的慰藉与激励(张进德与何月素的亲密拥抱),但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前景还很不明朗的时代,这个期待还谈不上是充满希望的期待,更不要说是美好的期待。它始终缺乏书写革命与爱情完满的勇气,甚至连预言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都有所保留,更谈不上刻画完美的革命知识分子了。因此关于革命,关于爱情,关于革命与爱情,关于知识分子,它永远是一个未完成时,一个值得期待的期待,最终的结局只能定格在十七年,只能在这个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无产阶级话语一统天下的语境里,寻找到正确而完满的答案。在此演进过程中,任何关于爱情的革命化想象,或革命的爱情化想象,革命文学的作者都是以革命的启蒙者自居。为便于达到对大众进行政治启蒙的目的,他们喜欢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设置为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的代言人,而客体的身份不拘,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可以是工农兵(革命者),如《韦护》中韦护之于丽嘉,《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李尚志之于王曼英,《到莫斯科去》中施洵白之于张素裳、《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刘希坚之于白华,《追求》中章秋柳之于史循,等等。作者的出发点可谓用心良苦,但是,现实实存与小说虚构中具有同构色彩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未汰除的小资气质,部分地支持了以他们为对象的爱情想象的小资情调。主观与客观的背离造就出四不像的“革命”自然要遭到质疑。而十七年小说的作者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被启蒙者、被改造者的身份出现的,赎罪的心态让他们的作品往往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置为革命的客体,以为自己的代言人,而主体的身份则一定是工农大众或已经革命化的知识分子。这样,现实实存与小说虚构中具有同构色彩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就必须让自己在与工农革命者的爱情过程中处于从属的、被引导的、被支配的地位。任何谮越都被认为是对革命权威的冒犯,是自己不认真接受革命改造的表现。爱情的取向就是革命的取向,知识分子常以能够得到革命者的青睐而骄傲,对革命有一种为了信仰,青春无怨无悔的献祭精神。爱情的距离就是革命的距离,爱情的道德就是革命的道德。任何小资情调的不恰当表现都会受到鄙视(江玫、李佩钟)。革命者驱使情欲,不革命或者反革命者被情欲驱使(《战斗的青春》中革命者许凤与叛徒胡文玉)。尽管由于共同的人性,十七年小说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爱情与革命的情感与理性的人生十路口的艰难抉择之时,体现出了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内涵。爱情的一方(有时兼为革命者)可能表现出喜新厌旧,但最终还是重归于好,能够像其他革命者那样以理节情,及时地重新回到了革命象征秩序的轨道,如《红豆》中江玫与齐虹的分手、《三家巷》周炳与区桃的诀别,凄美的爱情构成了对同时代爱情描写(克制僵硬)的超越,但已不是革命文学革命与爱情一一对应的简单回响,而是及时地被控制在了革命的道德伦理范围之内。
三
叙事者明白,“在权力、德行、合法性三者之间,革命者能选择的常常是德行,有德有行者才能具有顺应人心的可能,才能进行革命运动的考虑,才有可能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最后说明这场革命的合法意义。”[2]也就是说,身体、爱情、道德与革命、信仰、精神互相喻示。病态的身体、爱情、道德喻示病态的革命、信仰、精神。反之亦然。所以,这里的革命者不会再像王曼英那样因为革命的暂时遇挫导致误入歧途而误以为自己得了梅毒,也不会像章秋柳那样实实在在地被革命的虚无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传染梅毒,更不会像曾经的革命者王诗陶那样,在她的革命者丈夫牺牲之后不但没有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情绪和报复行动,反而为了生存而卖淫苟活。在俗世看来(整个社会的文化阐释系统里面),梅毒无疑是一种不光彩不道德的疾病,隐喻着深刻的消极文化内涵。有论者注意到了性病的隐喻作用:“性病,是小说最为有效的隐喻,表明了幻灭的传染作用。一旦秋柳被感染,它的破坏性便全部展现,至少在比喻的层面,她是所有人心中最后的希望。”[3]随着革命者梅毒的感染,革命者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从而表明了革命的最终幻灭。目的与手段的背离,构成对革命的深刻嘲讽,也是革命者病态精神与信仰病态的喻示。所以,身体的疾病源于病态的革命导致的深刻精神危机,病态的精神与病态的信仰也让身体的放纵造成对革命的伤害。诚如黄子平所说:“身体在革命中的得到解放,也可能被革命所伤害,她们的放浪形骸既是对旧道德的一种革命,亦可能危害革命本身。”[4]而在十七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具有了对人的非理性私欲的巨大征服力量和询唤功能。革命伦理所提倡的勤劳、节俭、勇敢、道德、乐观、理性、专一有效地克制住了情感的泛滥和人欲的放纵,革命文学由于婚恋上的不严肃导致革命神圣性的消解,到建国后这种模式发生了转变,在此意义上,十七年小说也意味着以前那种任性的写作姿态要被新的叙事方式取代。诚然,十七年文学也有关于革命者的疾病书写,但革命者的患病再也不是因为情爱上的放浪形骸,而是因为强烈的革命敬业精神。革命的天然正当性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取得胜利的美好期待让革命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利的革命工作环境和忘我的革命干劲让信心十足充满期待的革命者即使因此罹患疾病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革命者所患之病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性病之类,而是高尚之病,比如肺病,它不像梅毒。梅毒引人恐惧、憎恨、厌恶、逃避,意味着溃散、失败、幻灭、绝望,代表着一种对革命的质疑和革命神圣性的消解;肺病意味着一种情绪的感染、革命的感召、正义的诉求、一种积极进取力量的凝聚、一种九死不悔的精神追求,代表同情、感染、鼓舞、希望、光明。这类“疾病给人带来尊严,那是因为它展现了人的精神品质;它使人庄重、使人威严、使人崇高”,[5]充分显示了革命者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比如《小城春秋》里的四敏、《战斗的青春》里的周明,坚贞的革命信念和忘我的革命工作献身精神所焕发出来的同仇敌忾的气势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成为其他革命者的力量之源和行动的灯塔。他们所患的肺病隐喻了对革命的热诚与激情,坚贞与不屈,即使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在爱情上不再游移,对革命的态度成为他们抉择爱情的唯一尺度。他们在性爱上也不再放纵,对情爱的克制就意味着服从一种崇高的革命理性。游移与放纵只配给那些不革命或者反革命者。受这种革命精神力量感召,林道静、周炳、运涛、江涛、张嘉庆、许凤、银环、焦淑红、江玫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高尚的疾病喻示高尚的爱情和高尚的道德,也喻示了革命者高尚的人格,是对革命正义的重申,从而使神圣的革命获得合法性的坚实道德伦理基础。
由于处身不同的时代语境以及文学自身具有的阶段性发展规律特点,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开创时期左翼文学的雏形,后者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左翼文学的成熟形态,但就左翼革命文学这一点而言,两者还是有很大的相通处和很强的可比性。这种相通处和可比性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本文就是从这两者“革命与爱情”的共同创作模式入手,就它们的相通处在创作主体、创作理念、创作特点及其发展脉络等层面作一探讨,以期明了这两者内在的一致与不同、联系与区别,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加深对十七年知识分子形象叙事及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认识。
[1]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J].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
[2]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68.
[3]〔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M].江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6.
[4]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5.
[5]〔美〕梅耶斯.疾病与艺术[J].顾闻,译.文艺理论研究,1995(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Intellectuals’“Revolution and Love”betwee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17-year Novels
WU Guo-r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While“revolution and love”is a common narrative paradigm for both the 17-year novels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ey are manifested differently.In terms of the novelist,ideas of creation,features of cre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al course,the former shows the embryonic form of left-wing literaturethe at the beginning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whereas the latter exhibits the mature form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love;intellectuals;reversal;suture
I 206.7
A
1674-5310(2010)-05-0019-04
2010-09-02
吴国如(1974-),男,汉族,江西新干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