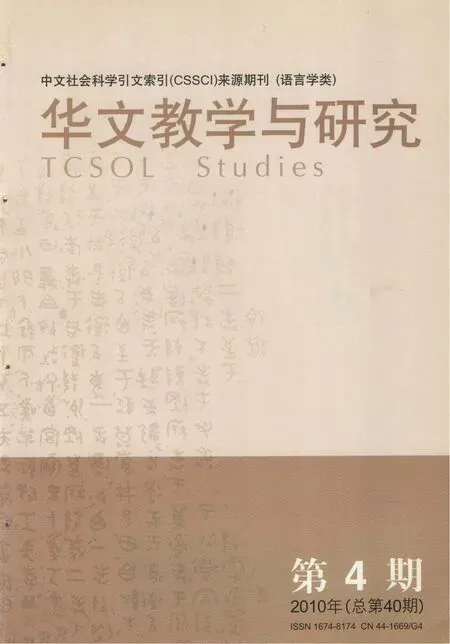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史述略*
2010-04-10吴原元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史述略*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发展史
发韧于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汉语教育,至中美建交时已有百年历史。在这百年间,美国的汉语教育受国内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形势等外部因素以及汉语教学方法、语言教育思潮等因素的牵制,经历了初创、转折、跃进到停滞等一系列波折变化。美国汉语教育在这百年间所历经的波折变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内涵,折射出百年间中美关系的变迁和学习汉语动机的更移;同时,它亦启示我们,当下海外“汉语热”能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久性,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增强中华文化对海外人士的内在吸引力。
每一国的汉语教育史,都具有独异的风格,其走向和态势会随时代变迁、境围更移而变化。发韧于 19世纪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汉语教育即是例证之一。学术界对 20世纪 80、90年代以来美国汉语教育的现状、汉语教学模式、汉语教育方法等问题已展开了相关调查和研究。笔者陋见,近几年即有肖炜蘅 (1999)、王晓钧(2004)、印京华 (2006)、王群与褚智歆(2009a;2009b)等大量成果;关于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的发展演变史,成果也很少:何寅与许光华 (2002)从美国汉学发展的视角对其作了简略介绍,郭熙 (2007:第三章第三节)从海外华文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华文教育缘起及发展历程的梳理,李天锡 (2000)对北美洲华文教育历程及特点作了探讨。基于此,笔者拟结合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美关系、美国人的中国观,从历史角度对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史进行梳理①郭熙 (2009)认为,海外汉语教育包含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学两种类型。对外汉语教学着眼于非华人的外国人,非华人的外国人在学习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的过程中,当然也需要了解语言承载的文化,但这种文化了解是为了促进互相理解,避免人际交往中的误解和冲突,减少民族之间的文化误读;华文教学以海外华人为对象,它包含国家认同教育、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以及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学习教育这三部分内容。本文所考察的美国汉语教育,仅指美国的汉语教学,并不包含以海外华人华侨为对象的华文教学。。
孙越生在《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1993)一文中,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分为草创时期 (19世纪 70年代至 20世纪初年)、独立时期 (20世纪 20、30年代)、发展时期 (二战至 50年代)、跃进时期 (20世纪 60、70年代);李天锡在《北美洲华文教育的历程及其特点》(2000)一文中,认为北美洲华文教育经历了萌芽时期 (1875~1911年)、发展时期(1912~1945年)、停滞时期 (1946~1970年代)及振兴时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四个历史时期;郭熙 (2007)认为 1941年至 1960年是美国华文教育的停滞阶段,20世纪 60年代后则是复兴和再发展阶段。笔者在参考上述学者对美国中国学或华文教育发展阶段所作划分的基础上,以美国汉语教学的发展史实为依据,将中美建交前美国汉语教育划分为 4个阶段:初创期 (19世纪 30、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转折期 (太平洋战争~1949年)、跃进期(20世纪 50年代后期~20世纪 60年代末)及停滞期 (20世纪 70年代~中美建交)。
一、美国汉语教育的初创期
自 19世纪中叶,美国商业资本开始向中国扩张,“对纽约和波士顿的整整一代人来说,到广州和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为容易,更加赚钱。19世纪头 50年,中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就和英国人在 18世纪遇到的情形一样。”(王建华,1990:139)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接踵而至,1886年至1918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就达 2524人。 (Fairbank,1974:105)伴随美国商业资本以及海外传教活动向中国的扩张,汉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卫三畏 (SamuelWells W illiams)曾言道:“无论是商人、旅行者、语言学者还是传教士,都应该学习汉语……如果所有的人都掌握了汉语,就可以避免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恶感,也同样可以避免在广州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轻视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双方交流倍受限制,主要原因在于外国人对于汉语的无知。”(W illiams,1848:500)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美国开始出现汉语教育。首开先河的是耶鲁大学,它于 1876年创设了美国第一个中国语文讲座;随后,哈佛大学在 1879年开设汉文讲座,加利福尼亚大学于1890年设立阿加西东方语文讲座,哥伦比亚大学于 1901年设立丁龙中文讲座。到 1914年,已有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讲座。 (Latourette,1955:7)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928)的报告,当时美国设立中国语言专系的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 9所学校;设有汉语专修科的有起伦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两所学校;筹备设立者有伊伦诺斯大学、密西根大学等 17所大学。 (吴原元,2008)另据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27~1928学年,全美高校开设的中国语言课程有 39门; (Carter,1929:46-47)1929~1930学年,又新增 12门。 (Griffin,1931:9)
在创设阶段,美国汉语教育多由具有来华经历的传教士和外国学者主持。耶鲁大学创设的中国语言讲座便是聘请回美不久的卫三畏主持;哈佛大学则邀请中国学者戈鲲化任汉文讲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加西东方语言讲座一直空缺,直到 1896年才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受命此职;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首任教授是德国学者夏德 (Fridrich Hirth)。(宋晞,1962:143-147)进入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本土汉学家开始登上汉语教育讲台。1940年,魏鲁男 (James Roland Ware)在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部主持汉文教学;顾立雅 (H.C.Creel)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初级汉文”和 “中级汉文”;卜德 (Derke Bodde)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汉文教学。 (王重民,1940a:46-4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校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质量不容乐观。富路特 (Luther C.Goodrich)在天津妇女同乡会的一次演讲时指出,“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合格教师数量,我们用两只手就可以计算过来”。(Goodrich,1931:75)1936年,费正清 (John K.Fairbank)走访美国高校时发现,各高校中能够使用汉语的人寥寥无几。 (费正清,1991:147)
自 19世纪中期以来, “白种人优越论”、“西方文明中心论”弥漫美国社会。20世纪初出版的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前言中,编者这样写道:“唯一有历史意义的人种是白种人,其他人种都不值得记载”;同时代另外一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也如是言道:“古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这些古代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们是我们研究的中心。他们都属于白种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是白种人。” (Timothy,1923:19)对于大多数美国学生而言,值得他们学习的“哲学自然是欧美人的哲学;历史是西方人的历史;艺术是欧洲人的艺术”;在他们眼里,中国文明是一种古老的、已经死去的文明,“东亚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区域”。(Cameron,1948:117)
受“西方中心论”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学生“对于中国只有微弱的兴趣”。 (Griffin,1931:15)富路特断言,“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从事中国教学之时,无论是卫三畏还是傅兰雅我怀疑他们是否有大量的学生。”(Goodrich,1931:73)富路特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戈鲲化到哈佛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班上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是哈佛的一位拉丁文教授,戈鲲化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恩 (GeorgeMartin Lane)。刘恩任哈佛大学的拉丁文教授达 43年之久,逝世之后,《美国语言学杂志》称他为 “美国最伟大的拉丁语学家”。出于对语言的敏感,也出于对新事物的追求,这位当时已经颇负盛名的拉丁语教授找到戈鲲化,愿意随他学中文。后来戈鲲化所开设的课程渐受注意,但最多时学生也只有 5个。(张宏生,2001)成立于 1929年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当年只有 9名学生学习汉语;192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人数为 270名,其中学习汉语和日语的学生为 43名;1930年,该系学生总数增加到392名,学习汉语和日语的学生为 56名,据说这样的数目在当时已经很令人鼓舞了。(Griffin,1931:15)
美国学习汉语人数不甚理想的原因,除西方中心观等因素外,汉语教授的方法亦是不容忽视的原因。1940年,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学系提出明确的教学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须先阅读高本汉的汉文形音,10月至次年 2月底读肯尼迪博士所编之短篇故事专集约 200个单字,3月 1日起读徐映川复兴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大学毕业生之中文课程,初级读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自序及第一章第一、二两节,以获识单字至少 1000个并能了解文法原理为度;中级选读本纪、列传等历史体裁与孟子等哲学体裁各若干节,外加梁启超论说文一篇;高级读左传、庄、荀、书经、论语及王国维文至少一篇或满清内阁文书二、三件。(王重民,1940b)这个要求表明,美国汉语教育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汉语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林德贝克 (Lindbeck,John.M.H)对此批评道:“二战前,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院校所开设的汉语课程,主要是为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 (Lindbeck,1971:47)卡梅伦 (Meribeth E.Cameron)也指出,“在美国,外语一直以来是作为理解外国文化和研究工具而教授,强调的是阅读而不是听说……这种方法在 1941年前的远东语言教学中非常流行。” (Cameron,1948:131)
由上可见,美国高校自 19世纪开始尝试进行汉语教学,但由于中国对美国而言更多的是商业利益和传教事业,加之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以及在汉语教学方面强调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等因素影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致力于学习汉语的人仍寥寥无几。基于此,这一时期可称为美国汉语教育的初创期。
二、美国汉语教育的转折期
费正清曾就太平洋战争对美国亚洲研究的影响这样评论道:“对于亚洲研究的发展而言,最大贡献者莫过于日本的陆海军,它在一夜之间给予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的资助与鼓励远远超过了之前二十年和平时期所提供的。” (Fairbank,1959:3)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美国汉语教育。太平洋战争不仅给美国汉语教育增添新的助推剂,也使其教学方法发生变化。
对美国公众而言,远东地区并不是一个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区域。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于军事和外交的需要,美国需要了解远东。为此,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军事和文职人员进行培训,以使这些将被派驻到远东的人员对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和民族风俗有所了解。例如,美国国防部推行 “特种军事训练计划”,要求新入伍的军事人员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防部指定的 25所高校接受为期 6个星期至 9个月不等的远东语言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培训;为培训即将到日本、中国等地区任职的指挥官,美国政府在西北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院校开设为期 6个月的 “外国区域与语言课程”短期培训班;此外,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海军语言学校,在弗吉尼亚的夏洛特维尔设立陆军语言学校等。 (Cameron,1948:117)
基于战时所需而推行的这些措施,使一大批美国人得以了解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战时汉语培训冲破了美国人对汉语所抱有的固有观念。长期以来,美国人视汉语为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语言。然而,战时汉语培训使一大批美国人能够说汉语,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信心。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年青人来说,汉语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涌向中国课堂的学生较之以前有明显增加。用卡梅伦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时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学习正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正如任何美国妇女俱乐部的活动所显示的那样。”(Cameron,1948:118)
二战前,美国汉语教育主要是为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强调的是阅读,而不是听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各种短期培训计划,旨在使接受培训的人员在短时期内掌握汉语、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为此,承担培训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探索新的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开始尝试对学员进行现代汉语的听力和口语表达方面的强化训练。1941年秋,哈佛大学的 “陆军特别训练班”便设有中文和日文班。其中的中文班由赵元任主持,他找了一批说北京话的中国学生协助,课文、语法等由赵元任上大课,再分小班进行口语训练。(周一良,2010:185)这种教学方法使一大批接受过培训的学员具备了现代汉语的听说能力。
当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语言教育界就战时培训中所发展起来的语言教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和平时期的大学教育展开了激烈论争。毕竟,战时语言培训是为取得明确结果而设置的,在性质上与正常大学教育有很大区别。结果不同,意味着方法也应不同。在 1944年召开的远东研究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指出,“尽管在战争环境之下汉语、日语、俄语、蒙古语的语言强化课程取得了成功……半强化课程仍将继续开设,无论何时人们对这些东方语言的需求似乎都证明这些强化或半强化语言课程的开设是正确的。问题是,这种占用学生绝大多数时间的语言强化课是否能够安排在正常的大学课程中。大学课程由其性质决定,不以让学生熟练掌握某种单一技能为目的。”(Cameron,1948:138)
战时培训中所采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使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至少能够掌握最低限度的汉语阅读与会话,这对战后美国的汉语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大学纷纷打破已有的汉语教学模式,力图汲取战时语言教学方法的优点,并将其融入到正规大学课堂的教学。耶鲁大学在战时曾同美国空军合作,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汉语培训基地。战后,耶鲁大学借鉴战时汉语教学的方法,教授中文时强调从口语入手;(王方宇,1978:62)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在狄百瑞 (W illiam Theodore De-Bary)主持下,使用强化学习方法,将 4年汉语学习时间压缩为 15个月; (DeBary,1964:65)在哈佛大学,费正清、赖肖尔等人对战时培训方式进行合理改造,通过采用区域研究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费正清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必需的工具,而且它也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的其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正确的利用语言学习,不仅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而且对这种文化的许多方面也会有一个基本理解,这对于学生而言意味着更为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最为有效的初级语言学习方法是一半时间学习语言,一半时间修区域课程。在初级水平,强化语言课程被证明是比旧式一周三个小时的方法更为有效。然而,如果全天候学习语言,“其收益是逐渐减少。”费正清强调,“语言教学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在口语和阅读方面的提高应有一个大致的平衡”。(Reischauerl&Fairbank,1948:123)
概而言之,在太平洋战争的推动下,美国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将汉语学习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战后学习汉语的人数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与此同时,战争期间所采用的强调语言运用和教授现代汉语的教学方法,打破了过去注重阅读和教授古代汉语的教学模式,直接推动战后美国高校探索不同以往的汉语教学方法。故此,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9年这一时期,可称为美国汉语教育的转折时期。
三、美国汉语教育的跃进期
进入 20世纪 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国内掀起麦卡锡主义狂潮。当以极端 “恐共”、“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弥漫美国社会时,所有与共产党中国有牵连的机构、组织、个人都难逃被打击的命运。费正清曾形象描述道,“20世纪 50年代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得像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无人问津,连狗见了恐怕也要掉头作呕。”(费正清,1991:429)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美国的汉语教育不可避免要受影响。麦卡锡主义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报名学中文的学生从 29个减少到 10个。福特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亦显示,这一时期大学对中国的兴趣和注册学习中国课程的学生人数都已大大减少。(韩铁,2004:81)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的兴起、共产主义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壮大和苏联军事科技实力的迅速上升,美国感到全球霸主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挑战,美国开始关注外语教育。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在今天,外语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美国肩负着领导自由世界的重任。然而,大多数美国人缺乏外语知识,尤其是亚洲、非洲和中东那些新成立国家的语言。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而言,我们必须克服这一缺陷。”(吴原元,2007:210)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于 1958年通过了旨在加强外语教学和非西方地区研究的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现代外语教学研究中心,每年为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财政资助不超过 8 000 000美元,并规定应为那些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中小学现代外语教学或管理人士提供高级培训,在培训期间每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员可获得每星期 75美元的补助金,其家属也可获得每人每星期 15美元的补助。(吴原元,2007:211)
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美国汉语教育开始迎来转机。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行的报告书,联邦政府在 1959年至 1964年期间共拨款 8 555 660美元,用于各大学设立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及开展教学。 (Low&Legters,1964:87)另据林德贝克统计,截止到 1968年,联邦政府共向 28所高校的汉语教学提供了 15 040 000美元的资助。 (Lindbeck,1971:48)为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等外语的兴趣,联邦政府在 1959年至 1970年期间总计发放了 8 950 000美元的国防外语奖学金。 (Lindbeck,1971:79)受联邦政府对汉语教学重视的影响,基金会、高校等机构亦加大对汉语教学的资助力度。1959年至 1970年期间,基金会和高校各投入了 25 933 462美元和15 000 000美元用于汉语教育及中国区域研究。(Lindbeck,1971:79)
随着大量资金涌入外语教育,美国汉语教育进入所谓的“跃进”时期。截止到 20世纪 50年代末,美国只有 20~30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Ku,1975:107);到 1965年,已有 78所高校开设汉语课程,1968年则增加到 108所。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也与日俱增,从 1960年的1844名增加到 1965年的 2561名,1968年则剧增到 5061名。 (Lindbeck,1971:49)斯蒂尔(A.T.Steele)在走访各高校后这样评论道:“我们发现散落在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洛矶杉、匹兹堡、旧金山和费尔班克斯的中心都在从事汉语教学。”(Steele,1966:192)
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中小学汉语教育也受到重视。费正清在 1959年的亚洲学会年会上建议:“更多的人应该从 10岁起就开始把汉语选作第二语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把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纳入美国教学体系。” (Fairbank,1959:7)他的这一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美国政府不仅投入资金加强中小学的汉语教育,还为开展中学汉语教师培训的机构提供特别资助。洛杉矶师范学院等机构所开展的中学汉语师资培训即是由联邦政府提供全额资助。1962年至 1964年,卡内基基金会先后拨款 100多万美元,用于中学汉语教学及汉语师资的短期培训;福特基金会则是一项中学汉语计划的积极推动者和资助者,此项计划由波士顿的萨尔学院发起,旨在通过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合作,对波士顿地区的中学生进行汉语学习指导。 (Steele,1966:192-193)到1970年,全美已有 150~200所中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接受汉语教育的学生为 2000到 3000名。(Lindbeck,1971:48)
美国学者贺凯 (Charles O.Hucker)认为,“20世纪 60年代亚洲语言及区域研究的发展……最主要是得益于国防教育法的推动。”(Hucker,1973:43-44)这一时期汉语教育能够快速发展,当然与 1958年国防教育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一时期推动美国汉语教育发展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中美之间尖锐对峙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正是为了应对苏联和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加强了对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和教育的投入。总而言之,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无论是开设汉语教育的学校数量还是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发展,故此这一时期被称为美国汉语教育的 “跃进期”。
四、美国汉语教育的停滞期
由于中美之间相互对立和敌视,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被压抑了 20多年。当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人对所有中国的事情都有了兴趣。1972年,《纽约时报》以《中国:20年后美国最新鲜的事》为题报道称,从时装到食品、从旅行到贸易、从医学到教育,美国人似乎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Whitney,1972)在这种环境下,选修汉语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初级汉语强化班课程的学生从 5人增加到 19人。一所大学的外语系负责人唐纳·斯温 (Donna Swain)介绍说,“在此之前很少有人选修汉语课程,以致我们经常不得不取消这门课。现在有大量的学生前来登记选修这门课,我们不得不培训新教师。我们的教师中有一半人想去学汉语。” (Whitney,1972)然而,随着共产主义中国的神秘面纱逐渐褪去,美国人因封闭隔绝而对共产主义中国产生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也逐渐淡去。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此起彼伏,20世纪 70年代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1972年颁布的 “综合高等教育授权法案”,专门规定联邦政府在1973年度应为民族传统研究计划提供 1500万美元的资助。 (Owens&Merchant,1973:61)由此,涌向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潮开始消退。林德贝克描述道:中国研究和其他领域一样正面临着危机。……国会不再批准用于国际教育的资金,联邦政府压缩了用于外国语言及地区研究的奖学金。(Lindbeck,1971:104-105)确如其所言,联邦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国防教育法为1971~1972年度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较 1970~1971年度减少了约一半。 (W ilson,1971:315)尼克松政府提出,从 1973年 7月 1日开始的新财政年度预算将把用于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及训练的拨款削减 1300万美元。 (韩铁,2004:326)哈佛大学的傅高义 (Ezra F.Vogel)对财政资助的消退深有感触:“我必须承认,1973年当我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后……中国领域获取基金会资助的 15年光荣岁月已无可奈何花落去。” (柯文 &戈德曼,2000:152)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20世纪 70年代后的美国汉语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联邦政府支持的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从 150个削减到50个,其中只有 8个有关东亚。(Crerar,1974:116)美国亚洲学会 1976~1977年的年度报告这样描述道,“美国高校用于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的资金较之以前更为捉襟见肘,……中文和中国文化课程对于大学生依然没有吸引力,选修的学生人数较之 20世纪 60年代减少了许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1978:327)1975年 7月,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和战争与和平研究中心在威斯康辛联合举办了关于如何促进中文教育及中国文化在美国中学发展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指出,当前中学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育面临两大困境,即资金及学生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此次会议的主旨是探讨在财政资助及整个社会对汉语教育热情下降之际,如何看待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在中学里的位置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措施。 (DeKeijzer,1976)。概而言之,受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中美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无论是对汉语教育的资助还是选修汉语的学生人数都大不如从前。由此,20世纪 70年代至中美建交被称为美国汉语教育的停滞时期。
五、结语
专事美国语言教育及语言政策研究的蔡永良曾言,“研究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尤其是语言教育,不能就事论事,它们后面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乃至政治内涵。” (蔡永良,2007:298)我们在考察美国汉语教育史时,除了关注美国汉语教育的现状、汉语教育的模式、方法及其特色等有关语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外,汉语教育在美国所历经的波折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内涵。举例言之,美国汉语教学方法从强调古代汉语和阅读转变为注重现代汉语及口语能力,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国对美国而言价值利益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于美国更多的是商业利益和传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于美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亦体现了美国人对中华文化从非实用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20世纪 40年代之前,美国人注重学习古代汉语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通过掌握古代汉语了解对他们而言具有神秘色彩的中华文化。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是许多美国人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20世纪 40年代后,美国已深深卷入远东,要使美国在远东的行动更为明智就必须掌握远东语言,并对其文化有所了解,基于此美国人对于汉语的学习转向注重现代汉语和语言的实际运用。美国汉语教育在这百年间的发展演变,不仅透射出百年来美国社会政治环境、中美关系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变迁,这也正是研究美国汉语教育发展变迁的价值所在。
如前所述,美国汉语教育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主要仰赖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推动的汉语热是不稳定也不具持久性的,美国汉语教育在这百年间的波折起伏即是例证。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当下美国汉语热的持久性表示担忧,因为当前美国的 “中文热”在本质上仍是 “现实利益驱动”,一方面是美国意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是否具有全球语言和文化能力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安全,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美国政经界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东方巨人对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基于此,美国前总统布什于 2006年宣布启动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将汉语与阿拉伯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一道列为美国最急需语言人才的“关键”外语。白宫要求国会在 2007年财政预算中批准特拨1.14亿美元用于启动该项目,扶持学校对关键外语的教学,派遣美国学生到海外学习语言。“中文热”能否在美国持续,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维持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因为正是中国的繁荣崛起和由此带来的巨大机遇使中文的实用性价值日益凸显;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文化吸引力。英国学者克里斯朵在《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里指出,英语已在 70多个国家成为官方语言,100多个国家成为主要第二外语,英语的这一地位乃是源自于它对近代文明内容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只有当以中文为载体的中华文明能够为当下社会提供富有启迪性智慧,为未来文明生产出更好内容时,当前的中文热才能持久稳定。
保罗·柯文 默尔·戈德曼 2000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朱政惠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蔡永良 2007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费正清 1991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
郭 熙 2009 《文化视野中的海外 “汉语热”》,《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 4日。
郭 熙 (主编) 2007 《华文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韩 铁 2004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 寅 许光华 (编著) 2002 《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天锡 2000 《北美洲华文教育的历程及特点》,《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4期。
宋 晞 1962 《美国的汉学研究》,载陶振誉 (主编)《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大典编印会。
孙越生 1993 《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载孙越生、陈书梅 (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 群 褚智歆 2009a 《汉语热在美国持续升温》,《语文教学与研究》第 16期。
— — 2009b 《美国印第安娜大学中文特色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 3期。
王方宇 1978 《记董作宾先生》,载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 (编)《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台北:艺文印书馆。
王建华 1990 《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61~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晓钧 2004 《美国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世界汉语教学》第 1期。
王重民 1940a 《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近况》,载《图书季刊》新 2卷第 4期。
— — 1940b 《1940哈佛大学远东语文部工作概况》,载《图书季刊》新 2卷第 4期。
吴原元 2007 《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载朱政惠 (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 (第 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2008 《试析 1949年前美国高校的中国知识教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第5期。
肖炜蘅 1999 《当代美国华文教育浅析》,《八桂侨刊》第 3期。
印京华 2006 《探寻美国汉语教学的新路》,《世界汉语教学》第 1期。
张宏生 2001 《中国赴美任教第一人戈鲲化——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答记者问》,载《中华读书报》2月 21日。
周一良 2010 《天地一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Cameron,Meribeth E. 1948 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7 (2).
Carter,Edward C. (ed.) 1929China and Japan in Our University Curricula.New York: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Relations.
Crerar,John. 1974 Conference on priorities for f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3 (1).
DeBary,William Theodore 1964 East Asian studies:Acomprehensive program.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356 (1).
DeKeijzer,Arnel.J. 1976 China in the schools:Directions and prioties.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16(3).
Fairbank,John K. (ed.) 1974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 erica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John K. 1959 A note of ambiguity;Asian studies in Americ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1).
Goodrich,Luther.C. 1931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7 (1).
Griffin,Eldon 1931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n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1929~1930). In Kenneth S.Latourette(ed.),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Huker,CharlesO. 1973TheAssociation forAsian Studi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Seattle: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Ku,Theresa Shen 1975 Present statu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Paul K. T. Sih(ed.),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58~1975.New York: St.John'sUniversity.
Latourette,Kenneth S. 1955 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5(1).
Lew,T.T. 1923China in Am erican School Textbooks.Peking: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Lindbeck,John.M.H. 1971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 ent of Am 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Low,Donald N.&Legters,Lyman H. 1964NDEA Language and A rea Centers:A Report on the First Five Years.Washington,D.C:Office of Education.
Owens,Becky Howard&Merchant,David M. 1973 Federal legislation and Asian studies.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11 (3).
Reischauerl,Edwin O.&Fairbank,John K. 1948 Understanding the far east through area study.Far Eastern Survey17 (10).
Steele,A.T. 1966The Am 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McGraw HillBook Compan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 1978 At the age of thirty:Annual report for 1977~1978.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8 (1).
Whitney,Virginia 1972 China:After 20 years it's the latest American thing.NewYorkTimes,February 16.
Williams,Samuel Wells 1848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W iley&Putnam.
Wilson,Richard W. 1971 Chinese studies in crisis.
World Politics8 (1).
A Review of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WU Yuan-yuan
(Social Sciences Dep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befor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of developmen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es back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which experienced a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Influenced by domest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ino-US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aswell as themethodsof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language education trend and other factors,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during this century,such as start-up,turning,leaping and stagna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entury indicat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motivation of learning Chinese.At the same time,it also tells us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overseas“Chinese fever”lies in how to enhance the inherent attract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to overseas.
H195
A
1674-8174(2010)04-0011-08
2010-06-01
吴原元 (1977-),男,江西东乡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益于初审和二审审稿人以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笔者在此深表感谢。
【责任编辑 宗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