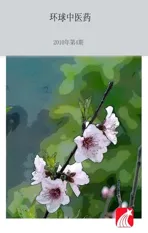关于中医“西化”的文化思考
2010-04-09温长路
温长路
近年来,关于中医“西化”的问题一直是医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中医界热议的话题。什么是“西化”?如何认识“西化”?至今没有定论也无法定论。这是因为,“化”的确是存在着的现象,“化”又的确有不可排除的因素,围绕二者间的仁智之见自然也就各有其说、各得其说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方法很多,或许文化思考的方法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找到二者间比较接近的链接语。
1 “化”与中医
何谓化?《说文》的解释是:“化,教行也。”后世由此引申出的意义大体有十几种,变化、感化、教化、随化、造化、进化、风化、消化、募化等皆为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彖辞·贲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表现为生命连续性中的日新日化。“化”的主题是变化,是所有学科进展历史中的必须与必然,中医学也不例外。在变中创新、化中进步,始终左右着中医学发展的方向。不过,“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任何学科的“化”,都必须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化”的前提、“化”的方式和“化”的结果,是人们谈变说化的先决前提。
从本质上看,中医学是“化”的产物,它是从生活中进化而来、升华而来的。先民们求生存的实践和本能是酝酿医学的温床,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洗礼,逐渐提高和完善,聚沙成塔、积浅为深,于是才有了从零散的疾病认识到系统医学的进步,有了从多家的论述到汇为一集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黄帝内经》。在历史长河里,这一过程始终是在不停地进行着的,从无休止、反复在“化”着的。这种“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由无序到有序,不断再造、不断发展,最终脱胎换骨形成了实用的、系统的、完整的医学科学,并且始终处于动态中,或明或暗地“化”着。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中医学与时俱进,“化”出了博大与深邃,“化”出了灿烂和光明。打开中国医学史,到处都是中医“化”过来的实例、“化”出来的路子:扁鹊随俗为变,“过邯郸,闻贵夫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1]这里,“随”是“化”的形式,地域差异、文化习俗差异都是“化”的前提,为民众健康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务是“化”的宗旨和目的。医者不是“郑人买履”,单凭主观思维和技艺强迫受众适应,而是积极寻求适宜于民众需求的新思路、新方法,“化”是积极的理念、主动的行为。晋时,中外医药的交流不断加强,西域各国的沉香、檀香、薰陆、郁金、香附子、诃梨勒等药物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医学不是闭门只修家中事,而是敞户汲取世外香。这里,“进”是“化”的形式,异药中用,无疑对中医学具有补充的作用。隋唐时期,国外医药不断向我国渗透,天竺和西域医方书十余种被引入我国,并开始传播。大唐盛世,文兴医茂,留下了历史的辉煌。这里,“传”是“化”的形式,溶异入我,化异为我,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就药物而言,晋时我国从国外引进的新药就有114种,医家郑虔还把西域传入的药物汇成一集,名曰《胡本草》[2]。元代朝廷设立的“广惠司”,使用的大都是采用阿拉伯医生配置的回回药,政府还组织力量编译了阿拉伯的医书《回回药方》。中医学包含着智慧的多民族元素,以惠及更大的人群。这里,“增”是“化”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内容[3]288。明代,一批欧洲教徒以中国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作引线,把大量的西方文化书籍输入我国,著名者不下百数十种,其中也包括与医学有关的《人体概说》之类[4]7-29。外来文化的冲击,必激发东方文化的昂进;外来思想的深入,定带来学术的新鲜气息。这里,“输”是“化”的形式,聪明的中医人看看“西洋景”也未必不受启迪、没有收获。清代医家王清任,“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其人之求学,亦饶有科学的精神。”[4]310无论他个人是否接触过西医,他的行为在客观上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有割不断联系的。这里,“学”是“化”的形式,实体思辨对阴阳思辨的验证和补充,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历史,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渐加深,16世纪以后认识论出现的由综合向分析阶段的转变成为必然。人类逐渐用分析的方法逐一对事物进行分解,学科自然就出现了。认识论上的这种变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5]。西医就是这一潮流促生下的产物,其对医学科学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否的。中医学正面平视西来的浪潮,冷静应对着风吹浪打中的莫测时变。近代的新文化运动,给西医在中国的快速繁殖注入了生长剂,中西医学在吵吵嚷嚷中开始了“汇通”、“体用”、“参西”的艰难磨合。这种异文化之间的摩擦、撞击、对话、渗透,不断荡起涟漪,搅得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去研究自己、研究对方。“他动”与“动他”,“我动”与“动我”,这种融合与不同,蕴含着无限的创新与生机。正是这种各地域、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比拼、交流,人文与科学的互动,才使世界变得如此精彩[6]。
2 关于中医“西化”
科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中西医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西医逐渐反客为主,成为我国的主体医学,中医的正常“化”开始向“西化”扭曲。这种“化”,从语法关系上似乎找不出什么歧义,仍如美化、绿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等词语一样,作为词缀使用,表示事物转变的性质或状态;从意义上讲,可就大不相同了,“化”成为中医失去自身规律的潜台词:中医的名被屈化了、理被误化了、人被趋化了、阵地被异化了。一句话,中医不仅逐渐失去了在“正统”医学圈内的话语权,而且在痛苦挣扎中慢慢缩小着“自我”。究其因,一缘于外强,科学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医如影随形而来,势如破竹;二因于内弱,分析方法的崛起带来的人文教育、人文意识的弱化越来越凸显起来,成为导致现代以来文化发展中人文资源积累和建设性不足的重要原因[7]。这种“化”法,严重影响了中医学发展的进程,也让中医人感到不解、忧虑和气愤:为什么曾经在这块土地乃至土地之外都长期被器重的国医,稍不留意会“化”到深不见底的沟壑里去了呢?为什么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外来医学,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在中国称王称霸呢?为什么看似正常的文化融入、学科知识交叉,会“化”出传统文化的防线、“化”出中医的底线了呢?历史给一向自恋的中医人的这一掌也打得太过猛烈了些,阵痛中给中医人带来的反思、教训和觉醒是刻骨铭心的。在中西方文化并不对等,并且医学界依然为西方中心主义所支配的今天,对西医的批判更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医文化自觉的前提[8]。中医反“西化”的呼喊,乃至多种抵抗行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被逼出来的。
中医学要发展,既需要中国文化复兴、自强的大背景支持,更需要中医学优势的自我张扬和支撑,其中也包括变“西化”为“化西”这种符合文化特征的主人姿态、凛然大气。立正必须矫枉,而矫枉的关键是抓准问题的症结。在对待“西化”的问题上,中医人需要进行一番冷静、耐心的“辨证”,极端是走不得的,不能把西医的正常融入也一概武断视为“西化”。盲目“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其言多牵强附会,徒长笼统嚣张之习,识者病焉。然近世矫其弊者,又曾不许人稍合汇通,必挤祖国于未来之蛮民,谓其一无学问,然后为快,嘻!抑亦甚矣”[4]302。也就是说,盲目崇拜西医、用西医系统取代中医不可取,对西医避之莫远、讳之莫深亦不可取。不顾中医的学科特点,完全用西医的思维、模式看待中医、评判中医、改造中医,是违背东方文化特质和中国国情、民情的霸道,属于非正常的“化”,不能以此作为挤兑和排斥中医的托辞;中医在坚持本学科之长的基础上,学习西医之长、溶化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属于“化”的正常范围,不能以此作为中医固步自封的理由和借口。对于正常的“化”,不惟不惧怕,而且是应当持欢迎态度的。“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淮南子·泰族训》)中医要大大方方地、虚心地向西医学习。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人之德矣,业之幸也!对于非正常的“化”,要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辨明是非,拨乱反正,用真诚、平等、以理服人的态度争取和维护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扬我国学,卫我国医,人之责矣,业之兴也!面对正常的“化”,躲躲闪闪,其实于事无补;面对非正常的“化”,牢骚满腹,实乃郁闷自残;对于一时说不清的“化”,一概排斥,亦非明智之举。“智不甚相远,苟积学也,理无不可相及,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与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其误缪正相等。质而言之,弊在不学而已。”[4]302发展中医,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9]。 面对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我们既不能做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也不需成为外来文化的附庸之徒。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应该正确处理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谐的文化氛围[10]。
3 西医也在“中化”
人们在担心中医“西化”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西医“中化”的问题?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从一开始就生活于东方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国文化的包围之中,呼吸的是这方土地上的空气,进食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五谷,接触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亿万年的民众,耳濡目染无法避免。完全承诺西方文化的信念和价值,全然不顾本土文化的信念和价值,这会使国际准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更紧张[11]。要想很好地生存,就得学会适应。固执、偏见会迷失方向,孤傲、清高会失去朋友,这是谁都明白的普通道理。加之学习和掌握西医的大部分人,原本是世代接受了中国文化训化了的华夏子孙,骨子里流淌的是属于东方文化血统的血液,彻底摆脱具有民族特征的本土文化影响是既不可能又不现实的。文化的本土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其体现出的维护与整合的基本含义同样适用于舶来的西医。因此,西医自从进入中国这片沃土,就在情愿不情愿、自觉不自觉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吸收着中国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在与中医争夺相同服务资源、争取和平共处的接触中,更无法避开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组成的中医学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生活于中国的西医,已不是西方文化支配下的原模原样,而是已经和正在走着被“中化”的路子,其中也包含着被中医的感化、同化。以环境论,中国政府明确要求西医学习中医,不仅在西医的学校教育里要设专门的中医课程,而且从事西医工作的人员也要学习必要的中医知识。以养生论,习惯于用竹筷子夹着猪肉、白菜吃的中国老百姓还一下子难以完全接受西方人用金属刀叉驾驭着的夹生烧烤,西医不研究国人的生活习惯不行,不讲中国的养生方法老百姓不买账,要讲就得涉及中医学的内容。以用药论,不少老百姓,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世代生活于草药丛中的农民还习惯于使用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的偏方、草药,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现实。入乡随俗,西医也不得不玩起“土造”的中药来。有调查说,在全国使用的中成药数量中,开出处方第一位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当然也有对中医理解不深或断章取义而开错的。
对于西医的“中化”,西医人既不以为然,也从来没有过被“化”掉的担心,因为他们是坐在主宰医疗市场的“老板”位置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是建立在中国老百姓习惯于服从老板主旨这一传统文化错觉之下的。西医传入中国后,其直观解剖部位的新颖感,曾经像一块巨大的强有力的磁铁,把许多中国人的“心”吸了过去,并被迅速“磁化”[12],这是他们得以自信的砝码。殊不知,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的。现代性无疑是由科学技术直接支撑起来的,而当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其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因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将成为当代文化的主题[13]。中医从五千年的浪尖上走过来,有过丰富的经验和太多的教训;现代科技文明的历史还显得短暂,现代科技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千万不要把眼前中医、西医的地位、规模、成就当作神圣不变的东西,要用战略眼光去看待中医、西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医学的普世价值是复合性的,如在生命伦理学中表现出的不伤害、有益、尊重和公正等这些基本价值,为不同文化所共有。虽然我们在执行这些准则及作为基础的原则时必须考虑文化情境,但没有理由否认其普遍的适应性[11]。单是西医或中医就能单个成为普世价值,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8]。回眸历史,早期的中西医学是具有共同特征的:如被动性、非理论性、经验性、无地域性等,其救护本能与医疗行为、求食活动与医药知识、巫术活动与医学渊源、朴素原始的解剖知识等等,都是从人类求生的本能荒漠中走过来的,两者有众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14]。因此,西医学习中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化”,应当视为是文化轮回和融合的结果,是21世纪文化变革大趋势中识时务的表现。
4 对“中西医结合”的思考
中医与西医在疾病的认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西医诊断疾病有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彼此分明,指向专一,依据的是构成论;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阴阳属性的平衡和谐及五行属性的生克制化中实现的,依据的是多元并存、和谐适中的生成论。道殊法异,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中医与西医,从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走来,这是历史的自然[3]50-57,此其一;殊途同归,从本质上看,中西医之间不仅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体,而恰恰是可以互补的协作者,此其二。 在同一片蓝天下,谁都无法用“不共戴天”的诅咒驱除对方,谁也没有“离我其谁”的符箓独霸天下。因此,中西医之间要解决的不是谁主谁次、谁能淘汰谁的问题,而是如何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问题。这种“互相”关系,就是建立和诠释“中西医结合”基本涵义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至于对“中西医结合”名称的争议,大不必把它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上去费力费时,因为“结合”词义的本身包括着复杂的含义,正如人们从不担心男女结合成夫妻之后会从本质上改变对方的实质一样,中西医结合也不会造成任何一方的实质性突变或被吞噬。
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无限性与医学认识活动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多元性[15]。如果说全球化的文化样态必然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沟通与对话,那么,全球时代的医疗保健体系,必然也是不同医疗文化体系的对话与互补;当代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必然是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优势互补、通力合作的成果[8]。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是国情决定、国策确立、国计需求、民生选择的基本方针,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目标出发,中西医都需要有更多的大度、包容、团结精神。西医用近视镜看中医和中医用远视镜看西医,同样不能达到对对方的正确认识和互学互补的目的,如何校正自己视力,是两个学科都必须要首先理智对待的话题。在西医反客为主、本土医学中医处于相对弱势的今天,西医尤其需要的是更多的虔诚、虚心和平易,中医尤其需要的是更多的宽容、开放和借鉴[16]。
[1] 司马迁.史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846.
[2]温长路.略论中医学的产生发展与河南的关系 [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24(S):15-21.
[3]曹东义.永远的大道国医[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罗炳良,靳诺.论语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8-29.
[6]王宏,郭勇.中西医结合的另类思考——论通约于“不可通约”[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4):839-841.
[7]温长路.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2010,3(1):58-61.
[8]邹诗鹏.中医学的文化自觉[J]. 中医药文化,2010,5(1):19-23.
[9]韩启德. 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N].健康报,2009-07-31.
[10]高薇,张京平.生命伦理学本土化之文化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6):47-48.
[11]邱仁宗.促进负责任的研究,使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2):3-7.
[12]余文海. 论中西医结合的价值取向[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4):842-844.
[13]周华,章诚杰,黄国毅.试论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与途径[J]. 中医药文化,2010,5(1):24-26.
[14]唐乾利.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及方法论比较探析[J]. 大众科技,2008,(2):135-136.
[15]梁中天.破除对科学的迷信,认清中医的价值[J].中医药文化,2010,5(2):15-18.
[16]温长路.书之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