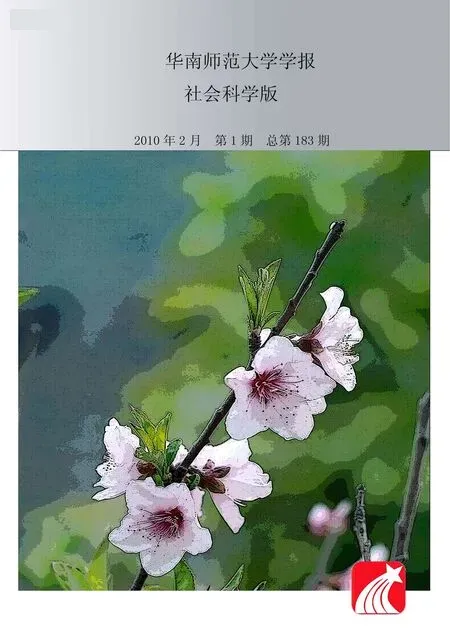珠三角农民工同乡聚居及其生成机制分析
2010-04-08胡武贤游艳玲罗天莹
胡武贤,游艳玲,罗天莹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珠三角农民工同乡聚居及其生成机制分析
胡武贤,游艳玲,罗天莹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农民工同乡聚居给外来人口管理留下了隐患,已引起珠三角各地政府的高度关注。调查分析表明,缺乏专门训练的普通劳动者依靠地缘、血缘关系获取劳务信息进入珠三角从而形成扎堆就业,进而形成同乡初始聚居,并且在社会资本依赖和社区失灵两种因素作用下使得同乡聚居进一步稳定下来。农民工同乡聚居现象有利有弊,只要因势利导,措施得当,就能趋利避害。
农民工;同乡聚居;珠三角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聚集在城乡结合部,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汇集地。值得注意的是,以零散形式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农民工,通常以来源地进行聚集,在较长时期内居住在同一社区,规模在数千人或万余人不等,成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经济发达的乡镇非常普遍的现象。民间多以其来源地指称,如“河南村”、“安徽村”、“攸县村”、“贵州村”、“四川村”、“广西村”等等。据深圳警方统计,仅深圳市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就有643个,近200万人,其中聚居人数在1 000至3 000人的“同乡村”达437个,73万多人;6 000至1万人的50个,36万多人;万人以上的同乡村有15个,23万人。[1]这类聚集往往有独特的内部规则,有的甚至还私设了“村长”和“保安队”以对抗合法管理,极易形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给维护社会稳定留下极大的隐患,已引起珠三角各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2008年4月至10月,课题组先后深入珠三角各地进行调研。调查地点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和集中程度配额选取,调查对象分为外来农民工、本地居民和社区管理人员三类,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据统计,共调查外来农民工聚居地32个,其中,广州市5个、深圳市5个、佛山市5个、东莞市5个、中山市3个、珠海市3个、惠州市2个、江门市2个、肇庆市2个。共向外来农民工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32份;向本地居民发出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3份;访谈外来农民工64人、本地居民64人、社区管理者32人。调查过程围绕外来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展开,从外出务工动机、生活状况、工作状况、社会交往与支持网络、社区参与及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重点调查,试图揭示外来农民工同乡聚居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一、农民工“同乡聚居”的界定
本文所称农民工“同乡聚居”是指来自珠三角以外的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较长时期集中居住在同一社区。下面对这一定义的关键词作出说明。
第一,“珠三角以外”的含义。在珠三角工作的农民工,主要是来自广东省周边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海南等省(区),也有来自本省的粤东、粤北、粤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空间距离、文化差异和体制障碍等方面,珠三角以外的本省农民工都优于外省农民工,身处异乡的感觉不很明显,同乡聚居的愿望不甚强烈。所以,本文将主要讨论来自外省的农民工。
第二,“同一来源地”的含义。身处异地的农民工对“老乡”的认同是多层次的,通常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呈强烈相关关系。如果两个农民工的家同属一个村或一个乡,两家距离不会太远,他们来到珠三角后关系会非常密切;要是两者本身还沾亲带故,更会亲密得像一家人。如果两个农民工来自同一个县,由于口音和生活习惯相同,他们会很快变得亲热起来,并保持长久的密切关系。如果两个农民工来自同一个地市或同一个省,他们会很快找到共同点并变得熟悉起来,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以“老乡”相称。可见,农民工对“老乡”的认同随着行政隶属关系的扩大而逐步降低。为简便起见,本文所称“同一来源地”主要以省为观察单位。
第三,“较长时期”的含义。上个世纪末,人们普遍把外来农民工称为“盲流”,带有明显的轻蔑之意。近些年来,人们将其改称为“流动就业者”或“灵活就业者”,不再有轻蔑的含义,但仍然与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联系在一起。鉴于此,本文所称“较长时期”是指农民工在一个社区内连续居住1年以上。
第四,“集中居住”的含义。农民工选择居住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既有市场的因素,又有社会文化的因素。就某一个社区而言,居住在此的外来农民工可能不是同一来源地,但很有可能某一来源地的农民工占较大比例,形成“集中居住”的景观。
第五,“社区”的含义。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区域通常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可能是在一个“城中村”,也可能在城市近郊的某一个村庄,还可能在中心镇的某一条街道。这里用“社区”来概括农民工聚居的区域,仅具有地理空间邻近的含义,而不具有行政管辖的意义。
二、农民工同乡聚居的生成机制
农民外出谋生基本源于经济动因,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进入经济发达地区,试图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在劳动者缺乏专门训练、劳务信息不对称和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农民工外出务工采取同乡聚居的方式就成为最理性的选择。
(一)具有一定文化但缺乏专门训练
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市场给劳动定价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供给,而劳动者数量的供给取决于劳动者受训练的程度和所从事行业的技术含量。从来源地来看,进入珠三角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广东周边的省份。其中,湖南人最多,占20.3%;江西人次之,占17.5%,广西人占12.2%,湖北人占11.4%,四川人占10.9%,贵州人占10.4%,云南人占8.5%,海南人占3.2%,其他省区的人占5.6%。从文化程度看,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一般都不高,初中毕业的最多(占50.2%),高中毕业的次之(占23.8%),受到良好训练的较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9.3%,但文盲也很少(占2.8%)。从行业分布来看,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27.5%),以男性居多;从事餐饮和宾馆服务业的次之(占19.9%),以女性居多;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占15.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打零工为主(占19.1%)。
问卷调查表明,农民工来源地与进入珠三角的便捷状况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交通越便捷的省区,进入珠三角的农民工越多。在珠三角工作的农民工通常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具备了远走他乡、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受到过专门训练的很少,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男性多分布在第二产业,女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可见,进入珠三角的农民工多数都缺乏良好的技能训练,收入水平通常较低,从而抗风险的能力往往较差。
(二)离土离乡不离故土亲情
外来农民工进入珠三角后,基本割断了同原籍地政府的联系(占76.3%),即便有联系也主要是向政府缴费(占22.6%),但是,当他们离开原籍地后,仍然同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们承包的集体土地大多数都没有放弃,或者由父兄代管(占31.8%),或者转包他人(占35.0%),或者干脆荒弃(占29.4%),仅有3.8%的农民把土地交回村组、解除承包关系,彻底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多数仍在原籍地,成为他们永远无法割舍的念想。仅有3.0%的农民工把父母带来了珠三角,就近照顾。而子女则多在原籍上学,或由爷爷奶奶管教(占67.6%),或在学校寄宿(占17.1%)。正因为这样,他们离开原籍地后仍然用电话同家乡的父母、妻儿、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占97.3%),平均每月打电话三次(占34.7%)或四次以上(占37.0%)。
(三)差序信息引导农民工进入珠三角
费孝通先生在1940年代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被波纹推及的就产生关系,从而整个社会构成以个人为中心,以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络,“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2]尽管“差序格局”理论提出已有60多年了,但中国农村依然保留着“差序格局”所描绘的社会结构形态。在“差序格局”社会中,通常表现为以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地缘关系来传递信息的现象,有的学者称之为“差序信息”。[3]农民工进入珠三角的务工信息多数源于差序信息。
调查表明,农民工外出工作属个人行为,户籍地政府基本上放任不管,既不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占86.4%),也不向他们收取任何费用(占89.4%)。在此情况下,农民工进入珠三角的务工信息主要依靠在珠三角工作或居住的亲戚朋友提供,比重高达85.0%,而且夫妻(或携子女)同来、与亲友老乡结伴而来的比例达到72.3%。
(四)扎堆就业引致同乡初始聚居
外来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居住状况与就业状况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差序信息传递过程中,一个先行者可能引来一批同乡扎堆就业,从而引起同乡初始聚居。实地调查表明,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通常从事相同的或相关的工作,或者在同一家企业工作,或者在同一个地方从事搬运、收废品、小商品贩卖等。当农民工聚居到一定规模,还会吸引一些同乡从事理发、餐饮、小百货、旧货买卖、缝纫等服务业。例如,居住在深圳石厦村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湖南攸县人,约有3 000人以开出租车为生,加上他们的亲属超过10 000人;居住在深圳黄贝岭村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四川达县人,多以房屋装修为生;居住在深圳合水口社区的主要是广西人,多在附近工厂打工;在深圳固戍社区共有商铺2 000多家,大小工厂约600家,外来人口达14.5万人,主要是贵州、四川、湖南人,尤其是贵州毕节人最多。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有时会自发地拥护一个“头人”,很多同乡都会对其言听计从,农村社会中的“村庄精英”仍然在发挥作用。[4]我们在增城市某镇调查中,镇政府负责人告诉我们一件事。该镇某企业主因为没有满足湖南籍农民工“头人”的要求,导致“头人”带领数十名湖南籍农民工集体罢工、跳槽,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由此看来,农民工同乡聚居通常都有产业作支撑,较为稳定的工作才带来较为稳定的居住。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62.8%的农民工工作较为稳定,并不经常变动工作,甚至27.4%的农民工自从来珠三角后就没有变动过工作单位,仅有9.8%的农民工经常变动工作,很少在一个单位工作超过一年。从农民工在调查社区居住的时间看,居住1-2年的比重最大(占30.9%);居住3-5年的次之(占29.9%);居住不足1年的占24.1%;居住5年以上的比重较小(占15.1%)。可见,农民工的流动性并没有我们直观感觉的那样强烈,一旦他们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有了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如果剔除新加入者所占的份额,真正常年“漂泊不定”的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外来农民工愿意在珠三角“扎根”,源于近年来珠三角民营企业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权益的增进,“血汗工厂”已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农民工对其工作环境和条件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占88.9%),对其工作场所感觉安全或基本安全(占82.8%),对其工作强度感觉可以承受(占70.3%)。而且,近半数企业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占48.4%),虽然有的企业偶尔会拖欠工资(占29.6%),但拖欠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多在一个月内(占68.8%)、或两个月内(占19.8%)。如果需要加班,1/3以上的企业会按《劳动法》规定足额发放加班费(占35.3%),近半数企业尽管不能按《劳动法》规定足额发放,但也会发一些(占44.8%),完全不发加班费的企业已越来越少(占19.9%)。通常情况下,多数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占72.9%),但大多数被排除在行业工会之外(占80.7%)。
(五)依赖社会资本防范风险
最近几年来,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浓厚兴趣。尽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和索洛强烈反对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5][6]但还是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将其概括出三个命题:一是社会资本影响着工具性行动的结果;二是社会资本反过来也受个体自我先前位置的影响;三是社会资本也受较弱联系使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甚至还超过较强联系的使用。[7]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交互作用,个人的好行为和坏行为的选择受到他所处网络中周围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个体发生空间迁移后,仍然依赖于他原有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而更多的是为了防范风险。于是,农民工对于社会资本的依赖使得初始的同乡聚居变得更加稳定。
问卷调查表明,外来农民工进入珠三角后,同本地居民的联系很少,多数仅偶尔交往(占69.8%),但会尽可能地利用原来的社会资本,与在广东工作的亲友、老乡密切交往(占68.4%),以降低迁移带来的各种风险。当他们失业了,多数会找亲友、老乡帮助介绍工作(占63.1%);当他们受到他人威胁,会把情况告诉亲友、老乡(占52.5%);当他们急等钱用,会找在广东的亲友、老乡借(占36.7%);当他们同老乡之间、同当地人之间或同其他外来农民工之间产生了矛盾,通常情况下会找同乡好友调解(占67.1%);当他们在单位受到不公正对待,心里感到郁闷,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向同乡好友诉苦(占71.1%)。
(六)社区失灵使农民工缺乏归属感
经济学家使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来描述这些治理结构在资源配置上的失效,而用“社区失灵”来描述在文化整合上的失效。“大多数人都在具有相似关系的群体中寻求团队成员,如果没有就会感到很孤独。归属感障碍通常包括恶劣对待不属于该团体的人。当社区内外因为基于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的不合与道德冲突而产生分歧时,社区治理可能会更多地鼓励辖区内的种族敌视和狭隘意识,而不是弥补市场和国家的失灵。”[8]以邻里关系为平台的社区失灵而产生的团体同质性阻碍着外来农民工融入社区新环境。本地原住民一般不轻易接纳外来者,而外来农民工则顽强地保持着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造成珠三角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相互隔离,大大延缓了农民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进程,进一步加强了农民工同乡聚居的稳定性。
外来农民工进入珠三角后,基本上处在社会管理的半游离状态。问卷调查显示,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仅直接给他们提供治安服务(占47.6%),并通过市场化途径提供出租屋信息(占52.7%)和就业信息(占41.1%),至于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法律咨询、文化娱乐、子女托管等方面的服务很少;同时,农民工基本不参与社区管理或选举(占86.4%),也没有成立或参加同乡联谊会、同业协会等自我管理的群众组织(占78.3%)。
另一方面,珠三角本地居民对待外来农民工的态度是矛盾的。本地居民深知,正是外来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他们才可能由“耕田”变为“耕屋”,坐地收租才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表面上看本地居民并不排斥外来农民工,甚至70.8%的人还声称愿意同外来农民工交朋友。然而,实地访谈表明,本地居民对外来农民工是戒备、冷漠和不屑的。他们很少有人同农民工交往密切(仅占9.4%),多数人只在有事的时候(主要是收房租和水电费)才偶尔交往(占71.7%),有的人甚至从不与农民工打交道(占18.9%);真正同农民工交朋友的本地居民很少(仅占6.9%);如果农民工因为生病、失业、急需钱用等需要帮助时,只有少部分本地居民愿意提供帮助(占41.1%);如果社区进行民主选举,同意外来农民工参与选举的本地居民还不到1/3(占30.5%)。
于是,农民工便选择了“同乡聚居”这样一种非正式组织以替代社区服务,满足其公共服务需求,获得归属感。即便需要搬家,重新选择居住社区,他们也把“老乡多的地方”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占38.4%)。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珠三角的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广东周边、交通成本较低的省份,通常只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缺乏专门训练,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收入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弱。在我国劳动市场不发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传统文化依然厚重的前提下,农民工通常依靠地缘、血缘关系获取劳务信息而进入珠三角,形成扎堆就业进而形成同乡聚居。自然形成的同乡聚居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一方面来自农民工自身的需要,他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资本以抵抗失业、疾病或其他未知的风险,从而产生一股凝聚力把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来自农民工身处异乡的外部环境,社区整合失灵和对生疏环境的恐惧产生一股压力迫使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聚居在可以相互照应的范围内。
目前,珠三角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框架基本上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由公安部门主导,采取“控制式”和“防范式”进行管理,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民工聚居人口数倍于当地户藉人口的“移民社会”的管理要求。我们认为,农民工同乡聚居现象的出现和存在有其深刻的体制、文化和经济背景,只要因势利导,措施得当,就能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首先,对农民工管理不仅是一个人口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着眼于制度创新,对现行的城乡分割、地域分割的不合理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进行全方位改革,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其次,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治理是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过程。要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平台,广泛开展省际区域劳务合作,实行来源地与居住地互动治理,把劳动力在市场力量引导下的盲动变为在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有序流动,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再次,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建设。要推行农民工聚居地自我管理,按比例配备农民工身份的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党组织成员,鼓励增建各具特色的群众性自律组织,如同乡联谊会、同业协会等,通过组织形式,将外来农民工的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整合起来。
最后,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治理需要社会工作全面介入。社会工作者能运用专业知识、技术与方法,通过发掘和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农民工解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个案工作的专业技巧直接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心理辅导与咨询,或者通过开展团体社会工作,把有心理需要的农民工组成多个小组,定期在他们之间开展生活、工作交流会,让他们可以相互倾诉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共同分享各自的感悟和收获,从而帮助他们纾缓心理压力,增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信心和勇气。再如,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吸引、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提高自身素质的社区活动,或者通过团体社会工作,多方位促进社区内的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通过宣传、学习、表扬、批评、关怀等方法,促使外来农民工走出狭小的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接触当地文化,培养现代市民意识,转变行为方式,从而帮助农民工顺利实现从“村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
[1] 陈文定,等.深圳市治安攻坚战:“同乡村”治乱已经刻不容缓.南方都市报,2005-11-16.
[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26.
[3] 马元驹.企业经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差序信息”现象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6).
[4] 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4).
[5] 肯尼思·阿罗.放弃“社会资本”∥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25-228.
[6] 罗伯特·索洛.论经济运行与行为模式∥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29-234.
[7] LIN,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58.
[8] 萨缪尔·伯勒斯,赫尔伯特·基提斯.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29-151.
【责任编辑:王建平】
C91
A
1000-5455(2010)01-0010-05
2009-10-1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珠三角农民工‘同乡村’调查及治理对策研究”(06H06)
胡武贤(1963—),男,湖南临澧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游艳玲(1976—),女,江西吉水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罗天莹(1978—),女,湖北宜昌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