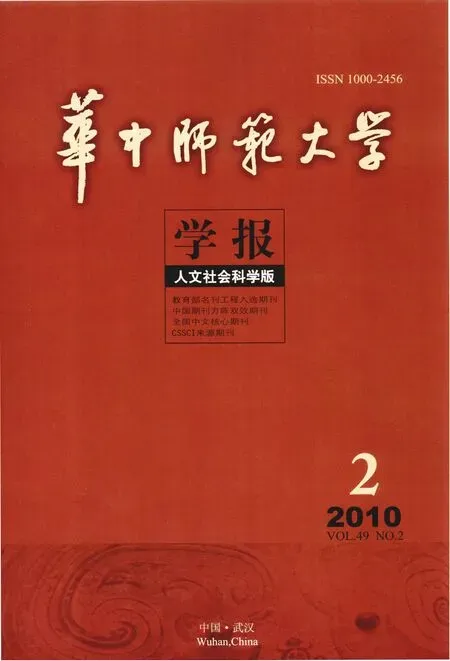《庄子》“神人”解
2010-04-08孙雪霞
孙雪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庄子》“神人”解
孙雪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解析“神人”是理解《庄子》的关键。“神人”美、超越尘世、功力非凡、以不才为祥、特立独行、和光同尘。神人与真人、至人、圣人都是庄子理想精神境界的外化,但也有细微的差别:飘然尘外之神人,修炼得道之真人,归隐山林之至人,无为而治之圣人。
《庄子》;神人;至人;真人;圣人
《庄子》共有9处提到“神人”,《逍遥游》中的神人形象尤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神人”是《逍遥游》乃至整部《庄子》的灵枢,笔者认为,不透辟解析“神人”,则难得《庄子》之阃奥也。故作此文略申管见。
一
首先,神人是“美”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是我们对《庄子》神人最初的印象。崇尚美,是人类童年时代本能的反应。闻一多先生说“他(庄子)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①,实在是把庄子的天真烂漫看得很透彻。这种率真,使得在《庄子》开篇处,他要让神人如此隆重地登场。庄子固然有他的牵挂他的深思远虑他的老于世故,但在几乎皆为神话的《逍遥游》中,目之所及却是一派天真、率性与对未来美丽而光明的期许。这样的安排有如开天辟地般的豁朗,时空皆在笔墨间焕然一新。
古希腊艺术(包括神话)难以企及的原因,部分就在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希腊的艺术作品,几乎都弥漫着古希腊人天真的童性。尽管古希腊人大部分居住在贫瘠的丘陵山地,只能种植耐寒的葡萄和橄榄树,但从未泯灭的童性却让古希腊人将丑恶压抑、淡化和遗忘,从而使得他们的神话充满着美的馨香,也使得古希腊神话成为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同理可推,《庄子》文本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感动着、影响着华夏民族,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在那样一个朝不保夕的乱世,在那样一个理性横行的世界,庄子居然可以如孩童一般煞有其事地、自顾自地讲着如此荒诞、无邪而美妙的关于“神人”的神话。这份旁若无人、这份我行我素、这份超然物外,让《庄子》神话魅力永存。
其次,“神人”超越尘世。“神人”的超越性特征,使她毫无疑义地成为《庄子》神话的标志性意象。“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这份超越性几乎成为后来道教信徒们修炼的途径和准则。五谷,乃人生存之本,神人“不食”五谷,让她在根本上与“人”有别而近于“神”,但同时,她又并非“不食”东西,只不过她所食之物是“风”是“露”,这与宗教中受后人供奉祭祀,只闻牺牲馨香的“神”又显然有所不同,故庄子不称之为“神”而称之为“神人”,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虽然《逍遥游》中的列子也能“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然而“风”之起落,乃自然之变数,凡人难以掌控,所以也就陷于有待。而神人不同,其所乘乃“云气”,宇宙之初,便是一团云气,它亘古而然,无须“等待”。至于飞龙,那更是神界之物,惟有游走于六界之间,才能信手拈来,让它俯首称臣。拘束于人间世的凡人,当然无法企及,甚至难以理解。而《庄子》此处所讲的就不是“人间”,惊怖其言也好,说他大而无当也罢,庄子并不在意,他要的是游乎四海之外之神人的会心一笑。
其三,“神人”功力非凡。变形与神力,是神话的两大要素,如果以此来比照《庄子》“神人”的描写,那它已经是相当神话了:“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庄子的愿望很简单:不疵疬,年谷熟。神人超凡的功力在于只要她的精神专一凝聚,就能使万物不遭受病害,年年五谷丰登。无须励精图治,无须大动干戈。神人之神力不可不谓大矣!战国时期,兵荒马乱,草芥般的民众只能自求多福,现实充分说明神人之神不“凝”,这本来只需神人举手之劳,她为何选择放弃?原因在于神人恼怒人间的混乱,不让神“凝”,故而愈加重了人间悲剧。此处表面看似赞美神人,实则暗含对人间世深刻的谴责。造成人间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悲剧不是老百姓本身的堕落,也不是天上之神的渎职,而是人间君主的肆意妄为。这样的思路我们在西方神话中也经常看到,众所周知,挪亚方舟的建造便是为了拯救人类免于水患,而水患的产生实际上又恰恰是神对道德堕落的人类的惩罚。
神人的非凡功力还表现在“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虽然《庄子》仍称之为“人”,但显然她已脱离了“人”之物性,那是人类与生俱来,在时间河流中沉淀、传承而来的无法抹杀的物性牵连和畜群意识,即使自诩最文明最理性的现代人,也难以将其自然的“性底性”根基一笔勾销,而神人,与物作揖相辞,外物伤害不到她,甚至影响不了她,正因为此,她才能真正挣脱外物的层层束缚,抵达“无待有待”之境。
其四,“神人”以不才为祥。《庄子》内、外、杂篇对“神人”的本质揭示是有所发展的。外、杂篇中的神人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神”,而内篇,看重的是“神”与“人”融通,换而言之,是侧重于神性在人世间的显现。神人以不才为祥这一特征,应该说便是典型的代表。以“无用为大用”是很具《庄子》特色的思想,也许这与老子之“无为而无不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后者很容易沦为政治阴谋论,而前者,展现得更多的却是齐同万物、天地一气的宽容与平和。如其坚不能自举的大瓠,不中规矩绳墨的木材,牛之白颡者,豚之亢鼻者,人之有痔病者……这些都是俗人眼中无用之物,但在庄子看来,大瓠可以系于腰间助人渡河,不材之木可以避斤斧尽天年,有缺陷之人、物亦能免于灾祸。“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庄子·人间世》)能全身保命者,近于神矣。此处之神人不似后面外、杂篇那样遥不可及,它少了神之高渺,多了人之气息,只要留心,隐匿于人世间的神人处处显现其神性。
其五,“神人”特立独行。《逍遥游》也好、《天地》也好,神人都是独来独往,飘然尘外,无所羁绊。《徐无鬼》对神人的这一本性讲得更为透彻:“是以神人恶众至,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神人讨厌召引众人,召引众人容易导致不和睦,而不利之事往往紧随不和睦而来。此话自然有其现实意义,当时儒墨各家几乎瓜分天下之徒,熙熙攘攘以招收门徒、传播思想为己任。庄子虽然也不乏追随者,但他们彼此之间更像自然村落,或者说是地上的块茎,不争先恐后,也不气急败坏,流而不派,一切顺应自然,无阻无碍。只有卑微者才是聚众而居,虽然世间万物在庄子看来都是等量齐观,展翅南飞的大鹏与翱翔蓬蒿的学鸠都有可取之处,没有谁比谁更高尚。只是,在六合之外,在四海之外,庄子却愿意相信有那么一个神人,泠泠然昭示着无待有待的所在。因而尽管表面看来,《徐无鬼》的神人是对庄子平等精神的背叛,但是,究其深层,却能发现在终极性上,它是对庄子思想合理的阐发。奥林匹斯山上有一群神,他们组成一个团体,操控着人世间的命运。神们大部分时间各司其职,对人间进行分门别类地控制。而《庄子》神话,却只由一个神构成了神界,是理性让神的存在成为奢望?还是无法与乱世同流合污的孤独情怀,让庄子之神只能在藐姑射山上寂寞地独孤求败?
其六,“神人”和光同尘。《庄子·天地》对神人做了进一步阐发:“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神人不仅腾云驾雾,而且乘驾光辉,和光同尘,难觅其踪,与天地同乐,与万物齐情,与宇宙混冥。单看此段,也许缺少了“叙事”的元素,不过,它对神人性征倒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如果说《逍遥游》处的神人尚有如雪之肌肤、处子般之绰约让凡人一睹风采,其真实性还引发肩吾与连叔的争论,那么,《天地》篇显然是将神人往“神”的维度继续推进,使其和光同尘,常人再难睹其风神。而且,《天地》篇是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神人的神奇,就像《圣经·旧约》中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大气磅礴,势无可挡。也许古往今来,神就是无迹可寻的。《庄子》外、杂篇对内篇常有出人意表的发挥,有时是踵事增华有时是南辕北辙,不过,此处对神人的描写,倒是准确捕捉了神性:和光故不辉,故能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这反映的也许正是后庄子时代,人们对“神人”形象普遍的心理期许吧!
二
上述六点,大致是《庄子》神人的主要特征,那么,它与《庄子》中屡屡提到的至人、真人、圣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四者间是否存在等级序列的不同?按照《逍遥游》、《外物》、《天下》篇的相关描述,大概可以排出如下几个等级:(一)至人——神人——圣人;(二)神人 ——圣人 ——贤人 ——君子 ——小人;(三)天人 ——神人 ——至人 ——圣人 ——君子。但是,这几个等级之间显然已互相抵牾,不能谐和,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贤人、君子、小人都不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至于神人、至人、圣人之间如何排列,则实在是难分伯仲。至此,我们不能不质疑:做这样的排序是接近庄子的原意,还是对庄子精神的背离?让我们学着庄子说一声:“请循其本。”
最早出现至人、神人、圣人的是《逍遥游》,成玄英疏曰:“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②林希逸说得更直截了当:“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以游于无物之始而无所穷止,若此,则无所待矣。此乃有迹无迹之分也。至于无迹,则谓之至人矣,谓之神人矣,谓之圣人矣。‘无己’、‘无功’、‘无名’,皆言无迹也。特下三句,赞美之又赞美之也。”③此言甚是。齐同万物的庄子,又何以会将至人、神人、圣人以及真人进行所谓的排序呢?而且我们发现,看似有意将这几者进行排序的都出现在《庄子》外、杂篇中,我们知道,儒家理想人格是有等级序列的,这难道不正是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的庄子后学们,对庄子精神有意或无意地发挥吗?由此看来,将至人、神人、圣人、真人进行排序实在是庸人自扰,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具体化。
既然如此,第二个疑问拾级而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四者可以互用,不分彼此呢?对于庄子这么一位思想大师、语言大家,对于《庄子》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倘若如此笼而统之,似乎又显得有些草率了。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此四者还是存在些微的差别。
先说真人,这是《庄子》文本中一个创造性的开显,也几乎成为道家学说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形象,难怪乎唐代《庄子》地位受到尊崇时,《庄子》被奉为《南华真经》,庄子被尊为“南华真人”。真人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与神人有着相似之处,似乎也带有某种超越性,但是,真人的这种超越性不像神人那样与生俱来,真人的超越性是修炼得“道”的结果。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派飘然尘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奇之象。真人却是“其容寂,其颡頯”,呈现出来的是得道真人静寂安闲,气宇轩昂,介然不群,心志开阔,舒畅自适,充实宽厚之格局和气象。
真人显然与凡人有异,但是,他又不是高高在上,拥有法力能够变形之神,他是通过不间断的修炼——“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而得道之人。他看透生死,他看淡荣辱,他调和喜怒。所以尽管“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表达看似神性洋溢,但是庄子同时也说得很清楚:“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真人显然是“登假于道者”。如果说神人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境界,那么,真人的出场便为一切有心人提供切实可行的修炼途径,无待有待的逍遥之境也似乎一时间从天上走向人间,与此同时,庄子后学们还煞费苦心地为“真人”找到了现实版的对应物——“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子·天下》)神人、真人在《庄子》内篇处的细微区别,到了外、杂篇便产生蝴蝶效应:神人不断被神化,成为和光同尘之“神”;真人则不断被宗派教义利用,成为修行得道之“人”。
再看“至人”。《齐物论》借王倪之口明确说出至人与神人的相通:“至人神矣!”,然后又历数至人的种种性征,“几乎与《逍遥游》的神人几乎没有太多的差别:同样是“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登高不惊”,同样是“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而且,至人又像真人一样有生死,无强大的神力。
而在《德充符》中,“至人”是对孔子的尊称,熟悉《庄子》行文的读者自然不会因此而以为此孔子乃真孔子。“至人孔子”在此处要阐明的是“才全而德不形”的道理:“比起不以国政为事的至人,像鲁哀公那样‘执民之纪而忧其死者’,可以说还未进入道德之门。”将至人与以国政为事之君主相对立,依然有神人的影子,《逍遥游》中不是说“是其(神人)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神人也是不愿意把世务当作一回事的。
不过,笔者认为此处至人之精神气质,与《逍遥游》中的许由更为接近。尧让天下于隐士许由,许由断然拒绝,表明了自己绝不越俎代庖的心迹;而《德充符》中的鲁哀公听闻哀骀它的贤能,召而观之,传国与他,哀骀它却与许由一样,去国而行。这两则故事皆以“至人”指代隐士许由和哀骀它,由此看来,至人与“隐士”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应帝王》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至人的用心有如镜子,任物的来去而不加迎送,如实反映而无所隐藏,所以能够胜物而不被物所损伤。此处不讲神圣,也不讲修炼,让我们深切感觉到至人的平和平静与平淡。
至人近于隐士这一精神,在庄子后学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天运》讲:“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隐士自食其力,逍遥无待的做派跃然纸上。《庚桑楚》云:“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也是一派隐士的淡定无争。
最后看看圣人。圣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不似神人、至人、真人,是《庄子》的自铸伟辞,在先秦诸子中,圣人出现的频率颇高。据顾颉刚先生考证,“聖”与“聽”实为同字,是声人心通,入于耳而出于口的意思,简单一点说,“圣”就是“闻声知情”,聪明能干之人皆可称之为“圣”。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人们渴望产生一个伟大人物拯救人们于水生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共同愿望的敦促下,“圣人”慢慢向崇高、神秘和玄妙莫测转化。圣人是一个具有治理天下、统一天下的能力的人,这几乎成为先秦各家的共识。顾颉刚先生以老子的小国寡民为例,指出老、庄的“圣人”观念,不过是从相反的方面来到达罢了,同时以《庄子·缮性》为例,认为其中所讲到的圣人“完全是凭主观想象编造出来的东西,是宣扬历史退化论,极端的唯心主义”④。顾颉刚先生从古史辨派的角度出发,对历史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表示理解,不过,《庄子》对圣人的解析,我们认为还有商榷的余地。
圣人一词在《庄子》出现的频率比神人、至人、真人要高得多,这说明正如顾颉刚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圣人的确是战国时期拯救苍生之英雄的代名词,人们渴望圣人、呼唤圣人,《庄子》也不例外。所以,相对其他诸“人”,我们不难发现诸如神人、至人、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超越性在持续消退,而如何经世治国的现实性却得到不断凸显。在《庄子》内篇,圣人多次与“众人”相对而言,如“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如“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等等。众者多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与之相对立的“圣”理解为“一”,也就是“君主”呢?答案是肯定的。《庄子》与老子所讲的无为无不为的圣人之治实在是有牵连,彼此的共同之处显而易见,不过,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他的“弗居”很大程度也是为了“不去”,这一点庄子却是摈除了。圣人在《庄子》内篇中多指治理国家的君主。庄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般地避世,他也关注现实,圣人正是庄子对于最理想政治家的设计。
《庄子》内篇中圣人的这一主要特征在外、杂篇有的得到深化,有的却被彻底歪曲。可以说,庄子及其后学对圣人理解和阐释的分歧是最为显著的,这恰恰说明圣人一词的确是战国时期运用颇为频繁的词语,各家各派皆根据自家学说的不同,为圣人不断累加意义和内涵,这层叠式的累积,遮蔽了圣人的本义,也混淆了庄子本人赋予圣人的意蕴。
三
如果说神人是升入神界之人,那么,真人、至人、圣人则是落入凡间之神,他们是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是庄子对无何有之乡的憧憬,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庄子并非寡情也不清高,能入其眼实际上还是大有“人”在:飘然尘外之神人,修炼得道之真人,归隐山林之至人,无为而治之圣人。三人为众,庄子的世界已然熙熙攘攘,生气盎然。
将《庄子》中独特的神人意象与真人、至人、圣人作细致地比较,绝非为了使诸“人”各是其是,壁垒分明。从神人内部看,神人、真人、至人、圣人由同怀而泯合彼此,从神人外缘看,神人之领地因开放而消弭间隔。《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在神人与真人、至人、圣人的相互涵养、濡染、补充、融汇及互通声息中,无待有待,逍遥自在,自有一番中国式的风神。《庄子》神人亦因为有此众“人”的存在而神采飞扬,熠熠生辉。
注释
①闻一多:《庄子》,见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14页。
②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页。
③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 9 页。
④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见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 712-728页。
责任编辑东园
2010-10-05
广东省社会科学“十一五”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中的《庄子》神话研究”(09J-1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9年校级青年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