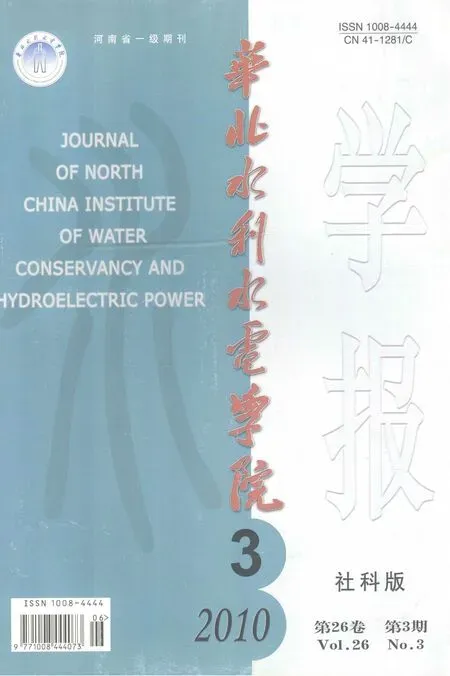《十九信条》保障权利条款缺失的宪法解读
2010-04-07李永健
李永健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十九信条》保障权利条款缺失的宪法解读
李永健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十九信条》曾被一些宪法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但学界一直对这部宪法缺少研究的热情。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认为在《十九信条》中没有规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这是晚清政府欺骗民众的临时举措。透过对这一独特宪法现象的文化意义分析,我们可以从源头上理解国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对于中国宪法发展的深远影响。
《十九信条》;权利保障;解读
《重大信条十九条》(以下简称《十九信条》)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清政府所颁布的惟一一部宪法[1](P351)。但一直以来宪法学者对于这样一部重要宪法文件缺少必要的研究热情。本文将从宪政主义的立场出发,尝试对《十九信条》中保障权利条款缺失这一宪法现象进行分析。
一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居于该国法律体系的最高层级,制约和影响整个国家法律体系。那么,处于最高法律位阶的宪法究竟应该规定些什么内容?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问题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从理论上讲,现代宪法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关于宪法的修改问题。但以上所说这三方面的内容,也都只是从纯粹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宪法应有内容。实际上,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各个国家对宪法基本内容的规定存在巨大差异。不过,随着近代政治文明和人权观念的不断发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逐渐成为各国宪法的根本目的,并已形成共识。“就一般国家的宪法而言,此种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究为构成宪法的重要部分”[1](P6),这一重要特征也成为我们鉴别近现代以来各国宪法的主要标志。
以此种认识和理解作为参照,可以发现《十九信条》在宪法条文内容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保障基本权利条款的缺失。在其简短的19条规定中,它所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对皇帝、国会(资政院)和内阁三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作为国家的元首,在《十九信条》的设计中,皇帝不仅头顶拥有无上的光环,而且也是握有一定的实质性的权力。“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2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第10条),不过其权力不仅受到了宪法及法律的约束,“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3条),同时还要受到国会(资政院)和内阁的制衡,“宪法由资政院议决”(第5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6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第8条)。此种规定,就其进步意义而论,不仅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观念的藩篱,也是中国近代走向政治文明的曙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了英国近代的虚君立宪制。
虽然在《十九信条》的规定中存在着极大的不足,即所有条文中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竟然只字未提。究其根由不外是当时的制定者(也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宪法认识的最高水平)认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有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才是“重大”的权力,应该加以重视和规定,其它诸如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都属可有可无。“凡属立宪国宪法共同之规定,则暂从阙略,俟全部起草时,再行拟具”[2](P101)。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认识,注定了制定者不会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写进《十九信条》的内容之中。
二
事实上,放眼近代各国宪法发展演变的历程,即便在西方国家中,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反对把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纳入宪法的思想和言论。在此,我们仅以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为例进行说明。在世界宪法发展史上,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因此美国宪法对于此后各国制定宪法具有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美国自认为一向珍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不过,在美国宪法制定的初期,一些制宪者也强烈反对把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写进宪法。
那些反对将公民基本权利列入宪法的制宪者,一方面固然因为美国宪法通过分权的原则所建立的政府不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太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类规则对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太大用处;或者认为这类规则隐含着某种危险性,反而可能会危及人们的基本权利。例如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反对派当时就认为:“将权利法案列入拟定的宪法之中,不仅毫无必要,甚至还会造成危险。权利法案会对那些未授予政府的权力做出各种限制性的规定。”确如他们所言,“美国宪法旨在保护的个人权利,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文献所能穷尽列举者”[3](P233-234)。任何宪法或文献都无法穷尽基本权利的所有内容,对某些公民权利的明确列举,就有可能被政府或者某些人解释成对某些未列举权利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进而伤害到权利本身。
但人们(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也很快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在宪法中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明确的规定,那么在宪法所必须授予政府的某些权力中,“一定有一些权力是可能被用来侵损个人权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个人权利加以特殊保护”[3](P234)。
经过反复的争斗,美国国会一次性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对于公民的各种权利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保障,并且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宪法保障的原则,并对其他各国宪法的制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自此以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逐渐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各国的宪政共识。以至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对此作出了高度赞扬:“一开始决定不将一项《权利法案》纳入《美国联邦宪法》之中的各种理由,与后来说服那些甚至一开始就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宪法的人士的种种理由,在美国宪法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方面,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宪政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赞同将基本权利内容纳入宪法,还是反对将基本权利内容纳入宪法,其根本出发点却是相当一致的。一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障,或者说是为了发挥宪法保障人权的最大功能;二是希望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大程度的保障,进一步发挥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作用。此外,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虽然宪法限制政府权力是手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目的,但宪法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制度工具,宪法也有其深刻的价值性,并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深深地栖居于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
反观《十九信条》的制定者未将公民基本权利纳入宪法的原因,恰与西方宪政国家中反对把公民基本权利纳入宪法所提出的理由大相径庭,或许从中我们更能体会出中西方在宪法和宪政文化上的差异性。这也可能正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宪政发展如此曲折艰辛的原因所在。进一步论之,即使《十九信条》将保障公民权利等内容写入条文中又能如何?正如此前清廷在《钦定宪法大纲》中将公民权利义务等条款置于“附则”之中,其背后所折射的宪法观念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如果不在宪法观念、宪政文化以及公民观念的教育与普及上下功夫,不扭转在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权力本位”观念,恐怕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
林来梵等在《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一文中曾指出,就西方的情形而言,哈耶克所说的“剥离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这一论断,“其实可以改为而且最好改为:‘剥离一切表层之后,立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4]。在西方宪政国家,自近代以来,“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是宪政制度赖以建立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脱离了这一基础,宪政制度只能是徒具形式的躯壳。这种徒具形式的躯壳不仅无益于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相反可能被独裁专制者所利用”[5]。宪法的实质不仅在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权力的分立原则,更在于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有效的保障。或者说,宪法对于政府权力限制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保障。
同时,在近代西方(欧洲)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民主宪政历程的演进路线是非常清晰的:15世纪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的宣传;16世纪对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17世纪社会契约思想、分权学说产生,英国立宪政体的产生;18世纪民主思想的激荡,法国民主政权的建立。总之,“欧洲的民主思想进程是先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等思想,然后再集中表现为开设议院的主张,遵循的是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5]。也就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由于有着深厚和优良的法治环境,随着自由平等思想广泛深入的传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革,最后才有议会制度的产生,即采用一种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模式来对公民个人业已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行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平等等思想既是议会政治产生的思想基础,又是它的精神实质所在。
而《十九信条》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缺失,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立场和文化意义,正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中的缺失和缺位的结果。或者说是在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的支配下,在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观念的深远影响之下,“从而形成了‘国家优位’或‘国家本位主义’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4],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和公民个人都不可能产生出个人与国家相互对抗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缺少了宪政主义产生的思想空间和精神资源。因此,自近代中国的立宪主义拉开帷幕,“就显示出与国家主义的天然亲和性,而与自由主义则是前世冤家”[6](P215)。
与此对应,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历程的演进路线则是:19世纪60年代极少数中国人开始批评专制制度不能通达民情;70年代个别改良派开始提出设立议院的议论;80年代部分洋务派提出立宪问题;90年代开设议院的主张普遍提出,并且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开始传播;20世纪初革命派民主思想激荡,专制制度最终被推翻。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完成了西方几个世纪才完成通向自由民主国家的任务,而且在近代中国宪政的发生、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遵循的是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样的一条恰与欧洲相反的逻辑”,是“从政治制度入手,先提出立宪的主张,而后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5],而宪政发展路线上的差异即反映了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特性,又决定了我国宪法与西方宪法不同的特质与禀赋。
四
事实上,在清末立宪的过程中,无论《钦定宪法大纲》将人民权利的规定放在附录之中,还是《十九信条》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缺失,只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政治运作都是围绕国家政治权力做文章。这一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义,就是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宪政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的自由主义,由于既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又与中国近代的社会主题——“富国强兵”难以相容,于是就有意无意地被近代中国各阶层的精英们所忽视。
无论是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自身所主导和推动的预备立宪运动,还是由立宪派所鼓吹提倡的君主立宪运动,甚至孙中山等革命派所极力主张的民主宪政运动,“其目的充其量是在通过推行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来吸收民众的能量,以壮大国家的实力……而力图将中国塑造成中央集权的近代立宪国家”[4]。这种观念产生于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此种环境又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而在很长的时间内,大多数中国人对民主、权利、自由和宪政缺乏真正的、全面的认识,这恰恰又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所必须的”[5]。
正是由于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缺失和缺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宪政产生环境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就导致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选择宪政道路时,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国家主义的宪政道路。而国家主义与自由宪政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恰恰是直接对立的。“因为奉行国家主义的政治家们常常会以国家的利益为借口,取消宪法的最高性和有限政府等宪政主义的基本要素”。“国家主义在本能上是反宪政主义的,实质上它是一种经过化妆的专制主义”[6](P214)。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一开始就没有把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作为它的最终价值目标,而是强调以国家和社会为最高目的和原则。
[1]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英)F.Von.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4]林来梵,凌维慈.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5]殷啸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生及其反思[J].法学,1997,(8).
[6]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Abstract:The Key Doctrines was called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China by some constitutional scholars.But the others scholars were so indifferent that they had no interest in studying it.The most severe criticism thought that The Key Doctrines made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temporary means to cheat its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no clauses on the right-protecting.While the paper shows that analyzing the unique constitutional phenomenon can help us understand originally that the ideas of nationalism and law realism hav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Key words:The Key Doctrines;Right-protecting;Study
(责任编辑:宋孝忠)
A Constitutional Study on the Absence of Civil rights of the Key Doctrines
LI Yong-jian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 450001,China)
K25
A
1008—4444(2010)03—0105—03
2010-04-07
李永健(1976—),男,河南宝丰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硕士。